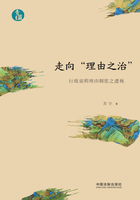
第一节 理由在公法中的变迁
一、近代以前的理由变迁史
在当代公法和公共治理中,“理由”正日益获得重要的地位。理由的形成、说明和审查,在各种公法程序中日益深入,基于各种理由的互动也在根本上改变着公共治理的内在结构,同时对理由的研究也不断丰富,大大拓展和深化了公法的合法性基础。然而,这一切并不是崭新的事物,当我们将眼光放到整个制度史中,就会发现,理由的沉浮在西方经历了上千年的变革,从中世纪中晚期开始,它就几乎一直是公法的一个核心概念,只是近一两百年曾经有过短暂的退潮,但晚至20世纪上半叶的法学思想中,它都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2]20世纪70年代以后,它又在当代公法中改头换面地重新崛起。要充分理解理由在公共行政和行政法中的作用,我们就有必要深入认识“理由”概念变迁和发展的历史——不仅在历史中看清楚理由概念内涵、外延和用法的演变,也更深刻地看清楚它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理由”(reasons)[3]是我们得以认识事物、评价事物和作出选择的事实与价值基础,是法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法律中的理由来源于拉丁语的ratio一词。Ratio原先等同于希腊文的λόγος(逻各斯),[4]其含义在罗马以后的岁月里非常广泛,它既指人或宇宙普遍的“理性”,也指皇帝下的行政机构分支,[5]还指计算、比例、份额、体系、学问、原则等,又指某种具体的理性因素或价值依托,最后一种含义即发展为今天的“理由”。和“理性”一义不同的地方在于,“理由”可以是复数的,它是多样化、主观化的,不存在唯一绝对正确的答案,只要能获得一定程度的可接受性即可,今天的“立法理由”“裁量理由”“说明理由”等用法均取此义。理由在罗马法中即已屡次登场,不过,在罗马法中,ratio的作用远没有今天广泛,在公法方面只作为笼统的法律原则使用,更加强调“理性”含义的整体作用,如《学说汇纂》中著名的段子:“已接受的法律规定如违反法律理性,不生效力”[6];但也一定程度上从非普遍性、多样性的意义上适用ratio一词,如“同样的理由将导致同样的法权,相似的情形导致相似的判决”。[7]这些情形下可以认为此处的ratio兼有理性和理由之义,因此可统称为“理”。后来,“理由”的含义日渐从“理性”中独立出来。Ratio的复数形式日益得到释放,以及ratio后面的修饰成分逐渐丰富,是理由在公法中逐渐登场的外部标志和社会语言准备,后一种变化更是强烈地催生了一系列的“理由”类型概念。经过漫长的演变,“理性”与“理由”日益分离,而“理由”最终拥有了独立于理性之外的丰富内涵。
“理由”在公共领域中的最初出场,就是起源于古罗马著名的“国家理由”观念。这一观念的最初形式并不是“国家理由”([意]ragione di stato,又译“国家理性”),而是被表述为许多其他的形式,最终被后世思想家抽取出“国家理由”概念。例如,西塞罗就是频繁地使用这类“理由”的一位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在他的《论义务》中有“(公共)利益理由”(rationem utilitatis,[8]后世的“公共利益理由”的来源)、在他的《论共和国》中有“公共理由”(rationes civitatis)[9]、“公共事务之道理”(rationibus rerum civilium)[10]等。虽然这些概念很少在制度和合法性的领域内被运用,但它们已经暗含了相当大的扩展潜力。例如,它们可以被拓展为一个关于增进公共福利、判定公共行为在道义上是对是错的“总问题”;[11]它也可以用来为避免战争的选择提供正当化论证;[12]这种概念还被用作质疑所谓“博学者”作为政治掌舵人的依据。[13]这些概念通过罗马时期的著作为后世学者所认识和扩展,不断出现在日后法学家和政治学者的论述中,直至经过熟悉西塞罗与塔西陀 [14]著作的马基雅维里的重新诠释,逐渐演变成后世极具争议的国家理由概念。[15]
不过,在这一时期,理由始终没有真正叩开公法的大门,无论在政治家的学说中多么引人注目,它始终被隔离在罗马公法之外。虽然法学家们不止一次地使用“理由”这个词,如著名法学家盖尤斯在其篇幅浩繁的著作中使用了自然理性(naturali ratione)[16]、保罗和尤里安使用了法律理性(rationem iuris)[17]、乌尔比安使用了最公正之道理(ratio aequissima)[18],但这些都和公法罕有联系。罗马公法中充斥着有关职权、职责、人员构成、税务法则、土地管理准则甚至官员选举程序的内容,就是没有明显地要求包含、运用、说明或审查“理性”或“理由”的规则。不过,也不能说罗马公法中完全没有ratio的运作余地,它有时以“理性”或“道理”的面目出现,如在《查士丁尼法典》中罗马皇帝直接以“不违反理性”为由维持了行政总督对喂养赛马案件的定性,[19]以“正当道理”(proiustitiae ratione)来支持士兵获得分配利益优惠的特权;[20]有时甚至直接用“理由”的面孔出场,如皇帝宣称承诺包税的行政官员“完全有正当理由让欠税人先补足税款,然后再行使他们对赊买者的追索权”[21],在军费开支部分更是用了“最大且不可避免之理由”(maximas et inexcusabiles rationes)[22],即士兵负有保家卫国之职责来为这笔开支增添合法性的依托。但总体上看,理由在罗马公法中施加作用的余地并不大,不仅没有进入正式规则或在司法中被进一步发挥,而且这套话语,甚至包括自然理性和法律理性,在西罗马帝国衰亡之后很快被后继的蛮族政权及制度所淡忘。
“理由”在公法中的真正兴起和辉煌,直到中世纪中晚期才开始。在中世纪前期,随着罗马帝国的衰亡和蛮族政权的兴起,“理由”一度完全销声匿迹。在这期间,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生活大大缩减,凭借私人权力、迷信和宗教权威即可以实现强有力的统治,公共生活中多元化的“理由”自然也缺乏容身之所。这一时期称得上是政治学著作的作品都在讨论权力和权利问题,甚至日后触发理由在公法中重新登场的契机,也是由皇帝是否对私人财产拥有所有权的著名问题引起的。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贸易和商业的繁荣,社会群体、利益结构和价值观的分化,特别是沿海城镇中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的复活,理由终于得以再次有机会走上前台。
在罗马法复兴和教会法相结合的背景下,ratio开始在公法中崭露头角。早在11世纪,就有学者从罗马私法中挖掘出管辖理由和实体理由来为国王的统治权辩护。[23]在12世纪,著名神学家和法学家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正式揭开了“理由”之舞的序幕,他宣称:“每一个‘国家’(respublica[24])都是一个由上帝恩典注入生命的法人(corpus),受到一种理性(理由)的统治。”这一说法被认为是日后“国家理由”和各种类似理由登场的序幕。[25]在这一时期,原先曾由神学—哲学进程统一过的“理性”概念开始重新分解,ratio的“理性”一义向“理由”一义的部分回归已经重新开始,不同种类的ratio开始喷薄而出,如ratio utilitatis statu(s 国家利益理由)、ratio reipublica(e 公事[26]理由)、ratio statu(s 国家理由的早期版本)及ratio civitati(s 公义理由)等,每一种ratio的表述在此处均代表着适用于政治体的理性形式,但它们在用法中更多是作为政治行为的评价依据或辩护根据,或者作为公权利的基础,因此作“理由”看也完全合适。值得关注的是,ratio作为公权利的基础,被用于解答一个非常重要的公法问题,启发了长达数个世纪的争论,这就是神圣罗马帝国腓特烈一世在1156年提出、由罗马法学家展开的“皇帝是否对私人财产拥有所有权”的系列问题。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认为,皇帝无权从他人处获取想要的财产,除非基于法律授权、公平正义或公共利益理由(ratio communis utilitatis)。[27]这些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学者,包括远在英格兰的布拉克顿,也曾学习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学说,而将其融入自己的王权观念中。[28]
在欧洲学界,围绕前述问题的讨论广泛地扩展了ratio的类型和功能,到13—14世纪以后,在中世纪神学理性化及理性类型化、场合化 [29]的大背景下, ratio在法律中的作用进一步扩展开来。特别是意大利半岛众多城邦的兴起引起公共政治的复兴,导致政治技艺和政治法则的重新发现,[30]也使得ratio在政治领域的运用进一步扩展。基于亚里士多德的重新发现及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等学者的思想,政治开始重新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在这个时期,除原有的理由类型得到强化外,政治和法律学说中又出现了善好理由(ratio boni)、[31]统治和管辖理由(ratio gubernationis et jurisdictionis)、[32]王政理由(ratio status regis,在ratio Reipublicae或ratio civitatis之下)[33]、最高理由(ratione supremitatis)[34]、保护和管辖理由(ratione protectionis et jurisdictionis)[35]等,出现了一个内涵丰富、功能多维的理由之网,既有叠合也有交错,初步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理由结构。
到了近代,理由的网络被基本固定下来,但向新的视角和内涵发起冲击。马基雅维里之后的焦万尼·波特罗是提出“国家理由”概念的第一人,也正式开启了各种“理由”类型作为一个术语群给公共活动提供多元化合法性基础的丰富历程。但国家理由在智识传统上并非一个新的产物,[36]而是前述古典序列的继续发展。此后较为突出的概念还有公共利益理由、“自然理性(理由)”[37]、康帕内拉使用的“政治理由”(ratio politica)[38]及维柯等使用的“文明理由”(ratio civilis)[39]等。
这些“理由”全部可以看作某种类型的“理性”,而且还可以一定程度上相互置换,如文明理性在一定范围内就是自然理性,[40]政治理由也和国家理由有着很深的相互影响。[41]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和世俗王权的巩固,世俗权力、世俗秩序和合法性急需得到一个法理支撑体系,因此就出现了一个专门用于加强合法性或支持法理秩序的“理由层”。“在18世纪,如果一个国王依然诉诸君权神授以获得人民的顺从的话,无异天方夜谭,因为当下每个人都在怀疑这个权力来源的合法性。相反,没有人会质疑一个基于理性、洞见并诉诸人的权利的斟酌。”[42]这时候的理由,很大一部分已经出现在现代民族语言而非拉丁语的作品中,并且开始在论述中担当中坚力量。例如,博丹在《国家六书》中基于“必要理由”(raison nécessaire)来为国王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作辩护,[43]这种通过“理由”的支持由合法性(Legitimität)方向突破合法律性(Legalität)秩序的路径,经过修正后一直延续到卡尔·施米特身后的政治理论中。又如,曾经在法国红极一时的最高理由(raison suprématie),[44]也被大量运用于政治和公法论证,如神圣理由(理性)和最高理由分别导致建立教会和世俗秩序两种权力。[45]自马基雅维里以后一两代学者的时候起,到“二战”结束前止,“理由”已经繁衍成为欧洲大陆政治理论和公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层次,尽管随着代议制国家的兴起它们在后一两百年有所消退,但仍然占据着舞台一角不可或缺的位置。
在这数百年间,“理性”的类型化、场合化和特定化,非常有力地推动了“理由”在公法中的兴起。经由ratio的特定化,每一种政制、法律、秩序乃至价值诉求都有其自身的ratio,这种ratio不仅是历史的,还是变幻无常的,甚至可以根据外部条件而变化,这将它的含义不断从单一的、铁一般的“理性”中推离,而大大加深了它的“理由”含义。[46]
“理由”的角色一旦被解放出来,就引起了深刻的学理格局变化。虽然它们在当时有时被用来为统治者的行为辩护,如备受争议的“国家理由”概念就常常被用于给统治者的政治行为提供辩护;但总体上它们还是起了很积极的作用。对于其辩护机能,这是由当时的历史背景、学术传统和政治形势决定的,并不取决于某个特定的个人或流派所提出的思想。例如,自马基雅维里后逐渐成长起来的“国家理由”长期受到褒贬不一、两极分化的评价,但和马基雅维里持不同进路的学者也在使用类似的概念和论证。和马基雅维里基本同时、备受后世盛赞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稍早于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写出《一个基督教王子的教育》,后书获得的正面评价曾长期远超前书。但就在这本书里,伊拉斯谟也写道:“……对王子的正确教育并非着眼于他的个人收益,而是致力于使他的整个国家获得福利。一个国家须给一位王子所有的好处,这是有许多正当理由支持的。”[47]这种现象的出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权威并不是韦伯所言的法理型权威,而单纯的传统型权威又渐显贫瘠,不足以提供充分的正当化能力;这些“理由”正好充当了两种权威类型之间的过渡角色。
不过,中世纪的许多学者是有思想立场和独立品格的,并非一味唯当权者马首是瞻。这个时期的系列类似概念,如公共利益理由、公家理由等,有时也被用来限定统治者行为的发动条件,乃至否定某种政治举动。[48]除前述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外,英国法学家布拉克顿和著名思想家阿奎那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在民族国家兴起以后,这方面的出色例子首数普芬道夫(Pufendorf)。普芬道夫在论述政治社会和政治权力的生成时,限制了义务理由的作用,而选择基于“安全理由”[49]来建立契约、建立共同的政治指引。[50]在经由“双重契约、一个法令”建立政治社会和政府权力后,权力并非为所欲为,最高统治者不能一人统治全部,他不仅需要臣僚和理事去从事处理民众纷争、侦察邻国动向、指挥士兵、收集和分配资源、管理公共利益等公共活动,还需要对这些活动提供理由。[51]没有理由,君主也不能强征钱财;[52]只有作为贡品或税收时,政府才能向民众收取一小部分财物,此外则需要受到“紧急的、公共的、必要的善”之理由的严格限制。[53]对公共权力的行使附加理由的要求或基于理由进行限制,已经成为政治思想家和法学家对大众主权国家正式建立前公权力行使加以约束的一种流行方法。遗憾的是,这种方法一般停留在纸面上,而没有办法转化为一种稳定的、明确的制度,但至少在思想上,“理由”所形成的缓冲地带,依然形成了一片无形的合法性边界,对统治权力依然施加了某种程度的软约束。
更重要的是,与此同时,这些理由被用来深入解释法的精神,发展法的义理,大大丰富了公法的内涵,扩展了公法的知识疆域;它们为肯定或否定的合法性评价[54]提供了价值性和规范性的中介层,这一中介层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可调节的,由此这种灵活的评价结构为后来“理由”在现代公法中的复兴奠定了基础。这一中介层始建于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年代,而奠基于大法学家巴托鲁斯之手。巴托鲁斯为公权力合法性奠定了一条“意志加理性”(voluntas et ratio)乃至“理由加权威”(rationes et auctoritates)的道路,并且将多种尚未定型的理由运用于公法论证中,为日后理由类型在世俗政治体中的展开确立了基础。通过理由类型日积月累的发展,各种理由构成的中介层逐渐在政治学和公法著作中占据了一定的实质分量。
不过,虽然当时“理由”已经成为公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的众多作用途径显得太过纷纭复杂,而缺乏统一的分类和辨识标准,也没有获得论题学意义上的单独归类和独立发展。这使得公法中如此重要的主题和领域,竟至于几乎逐渐消亡在现代性的喧嚣中,为意志因素居首要位置的现代政治法律框架所日益淹没。
大众主权的兴起使得意志因素在近代国家中一度占据绝对权威的地位:民众选举政府进行统治,将自己的意志转变为法律,多数决就是权威,无须让“理由”来插手。更何况,许多理由本身就充当过粉饰政治、高抬政权的角色,像“国家理由”一类的概念在政治思想史中的位置并不光彩,在当代民主体制下尤其在议会立法政制的形式法治国时期,那些粉饰高权者的理由不可能再有立足之地。康德的批判更是在哲学上给了众多林林总总假借理性之名进行论证和辩护的托词致命一击,厘清了理性本身可能的证明限度。在无须太多理由的中世纪和无须任何理由的大众主权国家之间,“理由”之花在政治和公法理论中曾惊鸿一瞥地绽放,但又不可避免地凋零。不过,由林林总总的“理由”所组成的公法学思维结构,毕竟还是给现代的公法学留下了一笔引人深思的遗产;而现代行政说明理由制度的一些萌芽,也在这套知识几乎完全销声匿迹之前出现了。[55]
二、理由在当代法律实践中的复兴
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合法性日益被民主代议制的合法律性所填充,基于理由的公法学思维一度销声匿迹。但是,近代排斥各种理由、高扬纯粹意志因素的公法理念并没有持续太久,就出现了各种问题。首先,以主体意志为合法性基础的治理机制太依赖于多数决。如果承认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就只能坚持一人一票原则,而当意志的方向发生冲突时,就只能根据相互平等的肉体数量实行力学意义上的意志冲抵,这是从霍布斯开始就根深蒂固的一种论证思路,[56]尽管看起来似乎比较粗鄙,但基于纯粹意志取向的合法性理论一直无法从根本上摆脱这种逻辑,如果不对意志的内容加以区分而赋予其不同意义,单纯考虑意志的形式,最终的结果就只存在一个空洞的形式性整合过程,对于意志冲突而又必须解决问题时,只能无奈地落入多数决的最终解决方案。在这种系统下,少数(在多元化选项投票和分阶段投票中还不一定是总量上的少数)[57]不仅无力抗击多数的压制,更没有任何机制去促使多数把事情做得更好。在这种系统下,大量群体被迫采取激烈方式站到制度的对立面,导致了19世纪风起云涌的一场又一场暴力革命和社会抗议。最终,单纯的多数主义政治系统还放纵了纳粹的诞生,导致巨大的人道灾难。在20世纪,关于“多数人暴政”的批评与争议更是风起云涌。各国的政治和行政体制不得不在原先单调苍白的多数主义方案中插入了许多制衡多数权威、充分保护个体权利的机制,辅以强化的社会福利体系,力图缓和社会矛盾。
但是,少数在民主的政治话语系统里,毕竟占有天然的劣势,从理论上看,单纯基于意志聚合的正当化体系无法给予少数人制约多数的能力,这种制约必须和意志以外的因素结合起来,才能和多数在部分事务上相抗衡,进而促使多数将事情处理得更公平、更妥善。表述这种因素的概念,最初就是中世纪公法中的“实质理由”(ratione materiae),这种理由为了保护内容确定的对象和利益,可以抗衡简单多数的权威,[58]这也是德国《魏玛宪法》第76条(修宪权发动的三分之二多数要求)的理论基础,而在后来的联邦德国《基本法》中,一些基本权利、价值和制度被直接确认为不可修改的,在价值方面,最典型的就是第1条“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及保护此项尊严为所有国家机关之义务”。当然,这些权利、价值和制度及其理论基础并没有使用“实质理由”有关的名义,但它们本身采取了这种思路,并作为超越意志因素的一种理由类型而存在。
“二战”以后,对纳粹的全面反思催生了“社会国”思潮,[59]政治权力的运作明显柔和化,公共领域在迅速转型。公共性观念在社会福利国家中被制度化,而它只有通过作为社会和政治运作的合理化进程才能实现。只有随着这种合理化的进展,才会再次出现“一种社会,超越了定期或偶然的国家机构的选举和投票,并且处于一贯和长久的整合过程中”[60]。出于这个需求,立法、行政、司法对理由的重视都大为增强,所有权力分支的活动中都已经离不开理由的身影。自然正义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和正当期待理念更是进一步促使说明理由制度逐渐得到重视,如1932年英国多诺莫尔(Donoughmore)委员会报告认为,说明理由是法治的要求,“为我们国家对正义的认知所需”,获得决定理由是“自然正义的第三个原则。”在1971年的一份报告中也认为:“说明理由义务应被公然认为是自然公正概念的一个内在要素。”在英国1971年Breen v. Amalgamated Engineering Union案中,丹宁勋爵论及自然正义是否要求说明理由的问题,认为如果当事人所主张的是他不存在请求权的特权,那么行政机关可以拒绝请求,且无须说明理由;如果行政决定构成对已有财产权的影响,或影响到当事人基本生存,或涉及对任何权利、利益或正当期待的剥夺,则当事人应享有被告知理由和获得听证机会的权利。[61]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不仅是行政决定,在广泛立法、行政和司法活动中,说明理由已经进入了较为全面的制度实践之中。
三、立法和司法说理的展开
在立法方面,立法理由的说明在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内容丰富、意义深远的长篇论述。在西方法治国家中,即使对立法理由并未作出法律上的硬性规定,立法机关一般也自觉说明理由,而司法审查更是对此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例如,在美国,虽然对立法说明理由尽管没有明确的制度要求,但司法通过发展出立法记录(legislative record)概念,促使立法留下一定的支持证据与材料来说明立法选择。如果立法的相关书面材料不足,可能会导致法院认为立法违宪,自从里程碑式的“阿拉巴马大学诉伽雷特”(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v. Garrett)[62]一案后,这方面的司法审查之路已经彻底打通,“立法记录审查”(legislative record review)成为一类颇有特色的审查。[63]法院当然不会用自己的观点取代国会的判断,但法院在信任国会、尊重立法判断的同时,会从国会留下来的大量书面记录中检视国会的判断是否合理。[64]这类审查早已趋于严格,如在更早一些的“金美尔诉佛罗里达大学案”(Kimel v. Florida Board of Regent)中,联邦最高法院深入检视了国会立法所依托的信息,认为这些信息过于散逸(anecdotal)或在地理意义上过于狭窄,并且几乎完全是从议会辩论和立法报告中断章取义得来,进而否定了立法理由的充分性并认为立法违宪。[65]而在阿拉巴马大学诉伽雷特案中,法院更是直接要求国会立法必须有理性基础(rational basis),法院可以通过审查立法依据是否合理而确定立法的合宪性。[66]在其他国家,立法理由的展示也通过其他形式得以展开。例如,早在2000年,据学者对亚洲和欧洲61个制定有成文宪法的国家的统计,有34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规定了立法机关实行公开制度;另据世界议会联盟对81个国家议会的统计,有70个国家使用电台对议会审议法案进行实况转播,有58个国家使用电视转播议会辩论的情况。[67]立法意见的碰撞与立法理由的成型过程,在这种公开制度之下直接展现在公众面前。
司法中的判决理由更是历史悠久,但最近半个世纪,判决说理正得到如火如荼的发展。普通法系国家从中古以来一直保持着司法判决说理的传统,至今仍十分发达;而大陆法系国家也渐渐开始要求说明理由。判决要说明理由的做法,在意大利从16世纪起、在德国于18世纪逐步确立起来;在这点上,法国只是在 1790年、德国只是在1879年才作为一项普遍义务强使法官接受。但到今天,判决必须说明理由这一原则今天已经极为牢固地被树立起来了:在意大利,宪法本身就此作了规定。[68]在德国,宪法法院第一审判庭于1973年发布的一项决议(法律续造的决议)中规定:所有法官的司法裁判必须“建立在理性论证的基础上”。[69]目前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司法判决的说理已经和普通法系国家各有千秋,相得益彰。我国也开始逐渐加强司法裁判文书的说理工作:“近年来,在最高法院的大力推动、全国法院的高度重视、专家学者的建言献策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法院裁判文书的规范化建设和说理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全国法院各类文书样式得到统一规范,裁判文书说理问题受到普遍重视,裁判文书制作的整体水平显著提高,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裁判文书和典型案例。随着裁判文书上网公布的力度不断加大,数量不断增多,裁判文书说理的社会效应也在不断扩大。”[70]
与此同时,民众与政府之间围绕理由而展开的对话和互动日益活跃起来,甚至成为爆发公共舆论风潮、点燃重大事件的重要引子。在国内,2004年万州事件[71]、2005年池州事件[72]、2008年瓮安“6·28”事件[73](以下简称瓮安事件)等对整个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突发事件,都与政府在说明理由方面的某种作为和不作为关系密切。例如,在2008年的瓮安事件中,有报道和评论指出,贵州省瓮安县的相关行政人员至少存在三处说明理由上的不作为或作为不当,首先是“由于当地警方没有耐心细致地做好解释说服工作,死者叔叔与一个警察因沟通态度不好引发新的冲突,使死者亲属对公安局失去信任,成为矛盾激化的‘分水岭’”;其次是“在没有辟谣和做通死者亲属工作的情况下,公安局不顾现场仍有大量群众围观,且群众对死者的同情和对警方的愤怒已达极点的现实,仍然给死者家属下发了《尸体处理催办通知书》,促成了包括学生在内的群众游行”;[74]最后是始终“等不来一个领导说话”的人群向县政府转移,终于点燃了县委大楼。[75]当然,沟通、“说话”和“做工作”并不完全是说明理由,但却和说明理由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万州事件和池州事件更是直接和说明理由本身有关:万州事件是对行政事实行为说明理由的完全不作为,而池州事件则是由于主客观原因导致说理效果不佳。在万州事件中,警察匆匆将打人者送上警车、采取强制措施驱散围观人群时,没有重视周围群众怨气、耐心进行说理工作,致使围观群众十分不满,后又听信传言,造成突发性事件;而池州事件则是在“领导会袒护招商引资引来的老板”的传言下,也可能包括领导自身工作技巧的原因,导致说理的效果“十分不理想”,最终引发群体事件。在社会隔阂越来越大、社会信任普遍缺失的情况下,说理的工作以及围绕理由的社会互动过程在今天已经显得特别重要。
四、行政过程中理由的崛起
在当代行政过程中,理由更是占据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行政说明理由制度在许多国家相继兴起,揭开了理由在行政过程与行政法治实践中崛起的序幕。在20世纪的行政法实践中,说明理由的要求随处可见。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7条规定:“一切决定,包括初步的、建议性的和临时性的决定在内……应当包括下列事项的记载:对案卷中所记载的事实的、法律的或自由裁量权的实质性争议所作的界定、结论及其理由或依据。”《西班牙公共行政机关法律制度及共同行政程序法》第54条第1款规定:“应通过简单阐明事实及权利依据来说明理由的情形如下:1.限制主体权利或合法利益的行为;2.裁决依据职权对规定或行政行为进行复议的程序、行政申诉、司法途径前的申诉及仲裁程序的行为;3.与上述活动所遵循的标准或咨询部门意见相脱离的行为;4.不论因何种原因而达成的取消行为的协议,以及采取本法第72条和第136条所规定的临时措施;5.进行紧急审理或延长期限的协议;6.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所作出的行为,或依据明确法律或条例规定应该如此的行为。”[76]《日本行政程序法》第8条(在驳回申请请求的行政许可、认可时说明理由)、第14条(作出不利益处分说明理由)也规定了说明理由的前提和形式。法国更有特殊性,其通过专门立法(1979年《说明行政行为理由及改善行政机关与公众关系法》)规定“自然人与法人有权及时知悉与其有关且对其不利的个别行政决定的理由”,又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六类行政决定时应当说明理由,说明理由应当以书面形式进行,且应指出构成决定根据的法律理由和事实理由。[77]英国也通过法律原则和相关判例建立了行政说明理由的制度性要求。[78]而在德国,不仅联邦《行政程序法》第39条详细规定了行政机关的说明理由义务,这一义务在法律实践中更是获得了十分详尽的解释。[79]此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行政特别法中,关于说明理由的要求更是数不胜数。中国不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以下简称《行政强制法》)等重要单项立法中强调了行政机关的说明理由义务,在我国行政程序法典化的重要突破——2008年《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中更有着大量对说明理由的要求,有关说明理由的条款达20条之多,涉及重大决策、一般行政执法、行政指导、行政应急等众多事项及行政执法相对人权益保障、专家咨询、公众参与、机关(部门)间互动等多个面向。总之,一个非常突出的事实就是,“理由”在当代行政法律规范及行政活动中已经成为一个随处可见、遍布行政过程的重要概念,使得对公共行政的要求日益丰富起来。
说明理由制度只是“理由”在行政法中兴起的一个方面,真正让人不得不重视的,是围绕理由进行的互动和审查方式在日益悄然取代过去单纯围绕形式合法性的互动与审查。这是一场真正的公法革命。几个著名的事件与案例可以明显地体现出这一点。在美国,从国会立法到行政机关的决定,在司法审查中都难免要遭遇合理性评价,而有关公共机构所提供的理由的可接受与否,就是这种评价的关键一环。例如,在1997年判决的一个经典案例中,联邦最高法院用了整整一个分节讨论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关于《有线电视消费者保护和竞争法》中“必须负载条款”(The“must-carry” provisions)的合理性,决定接受国会的理由,进而最终对该条款是否违背第一修正案作出判断;又如,在1974年判决的另一个经典案例中,联邦能源委员会(FPC)发布的行政命令因未能充分说明如何确保小生产者的天然气定价是合理的,而被联邦最高法院推翻;尽管该机构声称考虑了所有与公共便利和需求有关的因素,并且认为定价的合理性可以由市场过程证明,但其说服力未得到法院的接受。在美国公法实践中,甚至出现过不少通盘讨论合理性(整个合法性判断镶嵌其中)的案例,这种现象是因为细致立法越来越困难,议会经常只能在立法中规定行政机关要采取“公平的”或“合理的”措施,但又语焉不详,使得合法性审查在很大程度上变成围绕行政机关所述理由进行的合理性审查。在我国,围绕理由进行审查的行政案件也已经开始出现,不仅对行政机关是否尽到形式上说明理由义务的司法审查案例为数众多,对理由进行检视的实质性步伐也开始迈出。[80]而在德国,对裁量理由的审查也早已广泛展开,德国《行政法院法》第114条规定:“对行政机关有权依其裁量作出的行为,行政法院也有权对行政行为、拒绝作出行政行为或对行政行为的不作为是否违法进行审查,审查行政机关是否逾越法定裁量界限、是否以不符合裁量授权目的方式使用裁量。”[81]在德国,行政法院关注的行政裁量瑕疵主要有:裁量逾越,即行政机关没有选择裁量范围内的法律后果;裁量怠慢,即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裁量权;裁量滥用,即行政机关没有遵守裁量规范的目的;违反基本权利和一般行政法原则,主要是比例原则。在某些案件中还可能出现裁量收缩,尽管法律规定行政机关有权在不同法律后果中选择,但在某些具体案件中,只有一种决定没有瑕疵,则行政机关有义务选择这个唯一决定,否则法院可以宣告其有裁量瑕疵。[82]这在我国也已经广为人知。可以说,行政过程中所说明和运用的理由在司法审查中的地位已经日益占据要害位置,特别是在行政法治成熟的国家,行政行为的形式合法性很少存在明显瑕疵,围政理由进行的审查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不仅如此,民众对说明理由和围绕理由进行互动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强。尤其是在当代中国,越来越多的行政活动正在面对民众强烈的说明理由的要求。民众要求的,很多时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结果,还需要“给个说法”,给出作出决定的依据和道理。这几年日益清晰的一个趋势是,如果行政机关在关键事务上出现说理不足、神神秘秘或闪烁其词的情况,在网络上和现实生活中都会招致公众铺天盖地的质疑。说明理由已经成为行政机关不得不掌握的一项重要工作技巧。在一个公共交流和公共产品竞争日益发达的年代,公共关系研究者早已指出,政府“光说不做不行,光做不说也不行”。[83]在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力量有渐趋均衡化的趋势,民智亦日益不复如封建社会一般壅塞,建立在相互理解和商谈基础上的公共理性更是对公共行政活动中无须解释的一言堂式行为有着根本的抵触,因此,现在行政机关面临说明理由的任务日益增多、日渐重要,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总体上看,理由已经在当代公共行政和行政法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美国学者贝勒斯将说明理由称为“第三条自然法原则”,[84]中国学者也早已认识为行政活动提供理由的重要意义。[85]它在维护程序公正,促使相关各方接受与信服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要更深刻地认识理由在行政法中的根本功能与深远意义,我们还需要做一番深入的理论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