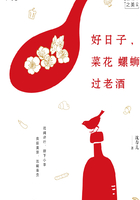
21 鼻尖上的年味
傍晚,走在小区,鼻子里充盈的是各种各样的美好滋味:南边这家在炖鸡,香!北边那家是萝卜炖肉,再走……哦……在干煸鲳鱼。一路走,一路美滋滋地享受着这年的味道:红烧鱼、醋熘带鱼、炸肉丸、包蛋饺、炒花生……各种气息里,是美美的年,是火热热的生活。
有人说,中国所有的节日都和吃有关:清明团、端午粽、立夏蛋、中秋月饼重阳酒,节日食品的品种与花式多得匪夷所思,不是本国人估计对这种文化很难理解。过年,是中国人最大的节日,仪式隆重繁复、食品多样有趣,过年也因此成为众多异乡人返乡的最大理由。你看,我们周围有多少店铺的老板或老板娘,会因为过年早早关了铺门?连买个早点都快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过年了,咱们都回家吧,好好准备,过个好年——人们都这么想。
年前半个月,是做冻米糖的时间。村里妇人们在腊月初就早早地准备了“冻米”(晒干的粳米饭粒),请师傅炒黄了再做成条。炒冻米做冻米糖的师傅,一年也就来村子这么一回。主妇们老早就相互叮嘱,小心关注着炒米师傅的动向,生怕一不小心把自个儿落下了,那样的话不但做冻米糖成了泡影,还会被家里那位责备,被孩子们埋怨。师傅到村里的这几日,整个村子似乎都会被炒冻米和冻米糖的香味笼罩。那是一种怎样的香味啊?甜糯扑鼻,那种无以比拟的香气里,混合着土地的芬芳与汗水的馨香,告诉人们:嗨!快过年了!
炒黄、炒香了的冻米,咬起来脆香脆香的,有的人家还会将一部分用饼干箱藏起来,正月里客人来了加了糖泡茶喝。那是又一种香,更甜腻,更温暖。
做冻米糖对师傅的功力要求很高,不但要有炒的功夫,更需要能够很好地掌握火候,把握好麦芽糖和糖的比例,熬得嫩了或者老了,那些炒好的冻米仍旧会各顾各,成为一盘散米,做不成好吃的“冻米糖”。
等过了小年,那香香的味道就更是一日重似一日:二十三送灶,做六个菜,特别要有香甜的糖菜糊住灶王爷的嘴,不能让他上玉皇大帝那里乱说;二十七杀鸡宰鸭,煮得整个村子都是热腾腾的香气,小孩子都馋涎欲滴到处乱窜,期盼着在什么地方能够先捞个鸡爪啃啃;二十八九,兄弟姐妹多的就开始分岁,那菜肉的味道,飘得整个村庄都是香的。
我家父母没啥兄弟,因此就在自己家过年。年三十要从早上忙起来:炒花生和瓜子,炒好后凉透,装进彩瓶里,客人来了随到随吃;包蛋饺,在一个小小的煤炉,起个小小的油锅,耐心地舀一汤匙蛋液,煎一煎,然后把肉馅包进去。刚包好的蛋饺最香,边包边盼着能够吃一个。那滋味,现在想想都美!家里还会做一些其余的菜肴,肉圆啊、红烧鲢鱼啊、油豆腐炖肉、鲞冻肉啊,整整一天,都在准备正月里待客的东西,不多,但那隽永的香味,至今久久回荡在我的鼻端。
晚上,就是团圆饭了。记忆中的团圆饭每年都是那几个菜,但每年都觉得新鲜,从来吃不腻。要有香煎鲢鱼,有头有尾的一条;要有油豆腐炖肉,红红亮亮的一碗;要有斩得大块大块的鸡肉和鸭肉,有活蹦乱跳的虾和十脚齐全的蟹;有六个素菜(豆腐、香干、素鸡、油豆腐和千层包,另加一碗炒青菜)。十二个菜荤素皆备,祭拜祖先,然后就做一个肉圆汤和一碗甜羹,一家人一起喝点儿香香暖暖的甜米酒,在喷香的晚宴中除旧迎新。
正月初一,那是到外婆家、舅舅家拜年的日子。自然,长辈手里不但有压岁钱,还有香香的瓜子、甜甜的糖果。最喜欢的还是那每家每户都做的“冻米糖”,各家各味道:有的添了许多芝麻,香脆馥郁;有的加了花生米,甜糯可口;有的还点缀了各种彩色的什么,更是香甜可口,赏心悦目。
过年的那些回忆,色彩绚烂,但更多的是香味的记忆。那些记忆始终徘徊在我的鼻端和心尖,多年未曾淡去。现在的年,过得更加多姿多彩,自然更加芬芳四溢。盼望着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我们的年过得更加芬芳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