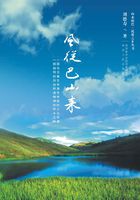
序二
河两岸是生命之树
——刘德寿《风从巴山来》读札
风来花开,冰心玉壶。在我看来,作家刘德寿先生的散文创作中,关于人和地域之间各种现象的发生和关联的描述,有如《遥远的班城》远比地理学家李特尔用德语“连结”(zusammenhang)一词指示的含义丰富得多。先前,另外一位地理学家布洛克曾向自己的同行们呼吁:“把地球作为人的世界去了解它。”这一极富诗意的构想已经成为人类生态学的光荣使命。如今,德寿在探索生命与物质的一般联系的同时,也越来越注意着人与生存环境的精神默契。这种产生于主客体关系上的当代意识,具体反映为社会意识的生态化。国内某些学者根据对社会心理的广泛考察,认为生态化是当今时代意识的一个日益显著的趋势。显然,德寿作为一个散文作家不可能拒绝这种当代意识。
近年,刘德寿先生表现出对生态学的浓厚兴趣。有这样一些作品,如《故乡的炊烟》《故乡,一些远去的鸟儿》等等,相率提出“人如何对待大自然”这一现实的生态问题。毫无疑问,一个作家是否具有人类生态学意识,不在于他在多大程度上触及了生态问题,也不仅反映为对于大自然的科学认识或道德态度。他更有代表性地无疑是侧重从文化背景方面入手的一部分作品。它们从生存环境与生存方式的同一关系中揭示了人与大自然的精神联系。大巴山的风光与江南不同。大巴山风光是山为主体、水为魂灵的世界,山水相依,神韵相伴,和平相处,平分秋色。离开山,水就迷失了方向;离开水,山就失去了原能。这不像江南风景,水就是一切,除了水,一切都是附庸,是配饰,是花絮,是点缀。德寿的《洋水三叠》大概可以算得一篇有代表性的作品。这里边比较容易看出作家审美思维的某些特点。文章主要描述的对象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条河:泾洋河。它被人为地用三座混凝土翻板闸截断了,人为地决定了河水的流动或不流动,什么时候流动。貌似在写一条河及河两岸的风景,其实是借河喻人。在这篇简洁短小的作品中,由于个人与社会的局部不和谐状态被置于广漠的文化背景之下,人生的选择还映衬着人类与自身生存环境的复杂关系。在这里,时空的延展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值得注意的是,命运的颠簸早已使泾洋河这条曾经波涛汹涌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的大河向生活敞开了胸怀。我理解,河流的这种选择,与其说发自个人爱好,或是条件提供了机遇,毋宁说反映了一代人海阔天空的精神视野。不是吗?你堵住了我流动的渠道,使我成为河东河西人们眼中静止的风景,但我毕竟是一条河,一条有生命的河,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我分解为无数条涓涓细流,越过翻板闸的桎梏,汩汩北去,不舍昼夜,奔赴长江。“河流作为一种原始意象,以蜿蜒的曲线一波三折地勾勒出人类命运的掌纹,以流动的声音诉说着古老的记忆,它拥有最温柔的涟漪,也有最恐怖的深邃,它曲折的轨迹恰如人类心灵的流动……”因循着河流的走向,我漂流《口泉河》……来到了德寿儿时放牧牛羊的乐园——古坟湾,听见了张姓的瞎子叔下井挖煤时和走出煤井时随口唱出的茅山歌,看见了和瞎子叔对歌的老处女。“这唱山歌的老处女是瞎子叔童年的相好,但瞎子叔为何眼瞎,为何终身未娶,有情人又终未成眷属,至今仍是一个谜。”(《古坟湾》)这个谜的谜底,德寿解不开,我也解不开。但他和她的对唱山歌的情景,已成为一个优美的意象,镌刻在大巴山的群山众岭间,永不褪色。而另一篇《远去的黑公羊》中,把德寿与瞎子叔之间的融洽关系书写得叶落花黄回肠荡气丝丝入扣。一个瞎子叔偷偷放掉德寿的因偷吃邻居庄稼被邻居关起来的黑公羊的细节,令瞎子叔的形象更显厚重。他具有遇事冷静、沉思、内向、坚韧、忍耐的性格特征,就是处于逆境,也从来没有剧烈的言谈举止。我以为《古坟湾》《远去的黑公羊》两篇是可以当作散文化小说来看的。正因为有了无数瞎子叔、老处女,我这样的大巴山人,生活、劳动、收获在大河两岸,所以,“水就有了涟漪,有了瀑流,有了浪花,有了永远也无法离弃的古老的歌”。这歌不仅为大河此岸瞎子叔、老处女这样的平凡人而吟,也为大河彼岸像符先辉、彭辉、钟明锋这样少小离家戎马倥偬的人民军队高级将领而唱,更为20世纪30年代初川陕边界闹红而抛头洒血,骨埋巴山的有名或无名的烈士们而吟唱(《青鹤·青鹤》)。那时,镇巴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边缘地带,亦称游击区,红白对垒分明,拉锯激烈。如1934年1月,在赤南坪落庞家院子成立的中共陕南县委,至11月即告失败。他的这一批散文,由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篇章共同构成,散散漫漫,又浑然一体。形成的艺术力量,自然是渐渐的,逐步汇集增强的。它的力量,绝不是忽而紧张,忽而消散。它有一定的控制,然而这种控制,就像射手控制弓弦一样。这种力量的形成,最好的比喻就是起于溪流,终于海洋。当云雾蒸腾,风雨交织,山林承接,形为泉渠。曲折奔溢,排击阻碍,汇为江河。它奔泻千里,所经过的有深山大泽,有禾田花岸,有各种风物,有各种情绪。互相激发,互相推重。但是总的目标,就是艺术的道德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这,也就是河两岸的生命之树所构成的风景。
也许,大多数散文作家在其创作思维过程中,并非参与人地关系的自觉意识。他们不曾考察过人与环境的系统转变,也无以构想生态的流动模式。而刘德寿先生的兴趣,多半在于自己那一区域的风俗、民情、方言、物产、自然形胜和历史沿革……所有这些,在他眼里无不充满生活的诗意。正如诗人德谟克利特所说:“具有一个好灵魂的故乡,就是整个世界。”他的大巴山,他的由镇巴的九条大河串联或并联起来的平坝山坳间的村落和山民,就是一个具有好灵魂的故乡,具有好灵魂的血脉和文本。也许,有的人会对此表示大惑不解。之所以如此,根本的一点是他们没有看到德寿抓在手里的正是一种可靠的文化形态。这些东西似乎游离于时代潮流,其实更为深刻地反映着人与环境的实践关系。它们意味着人自己所创造出来的环境,它们以散漫的存在方式暗示着生态学上所谓的“聚落”的概念。它们附着某种集体意识,经过一个世代又一个世代的积淀而变得相当坚实、稳固。所以,德寿抓住这些,对于完整地描述人的生存环境及其基本状态十分有利。他已经学会了这一手,他或以感悟的方式,或借助读者的美感经验,使自己的世界达到了某种完满、自足的程度。这种完满、自足,即是时间与空间的同一、主体与客体的同一,以及二元或多元的同一。于是,我们在他的许多散文作品里看到,自然、历史与人三者归一,浑然一体。
我本巴山人,风从巴山来,按理说,我是理应知道风的形象和味道的,但我不知道。化用一句古诗:不识山风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我想,大巴山中的艺术天地,应该犹如生活之树一样,是流动的,是发展的,是常青的。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刘德寿先生在其已完成的散文之中删削补充点儿什么,但是,希望作家能在今后的创作中,为描写大巴山的作品中增添些新生活的异彩。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巴山新生活的“长卷”真正的“画家”应该是生活本身。时代的足音总是回响于各个生活领域,即使是偏僻、闭塞的山乡也势必受到时代浪潮的冲击,因此散文作品的地方性因素的内涵,必当包含“当代性”。屠格涅夫的散文集《猎人笔记》被文学史家誉为“艺术编年史”,正是由于他的散文特写作品以其浓烈的俄罗斯色彩反映了俄国社会生活的新变化,作品的地方性因素完全被浸透在当代性中。最后,我想引用拜伦《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三章中的一段作为这篇灯下漫笔的收束,
哪里有崇山峻岭,哪里就有他的朋友出现,
哪里有波涛翻滚的大海,哪里就有他的家园……
沙漠、森林、洞穴、浪花上飞溅的泡沫,
都是他的伴侣;他们所说的是一种共同知晓的语言,
比用他的本国语写就的典章文籍更加清晰,
他也经常地把这些东西抛到一边,
而去细读那被阳光照在湖面上的大自然的书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