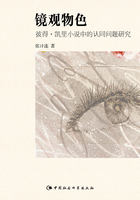
第一章 彼得·凯里小说中的认同问题及其迷踪
英文中的identity一词源自古法语identité和晚期拉丁语identit's,受晚期拉丁语essentit's(essence,存在、本质)的影响。它由表示“同一”(same)的词根idem构成,这一词根类似于梵语idém(同一)。[1]因而,这一术语被用于表述“同一”(sameness)、“相似”(likeness)和“整一”(oneness)的概念。Identity的基本含义指:“在物质、成分、特质和属性上存有的同一的性质或者状态;绝对或本质的同一”,例如,谢林(Schelling)的形而上学原则“绝对同一”(absolute identity),即“想法和事物都是同一物质的现象上的修改”,以及“在任何场所任何时刻一个人或事物的同一性(sameness);一个人或事物是其自身而不是其他的状态或事实”,例如,心理学中的个体特性(personal identity)。[2]从这两层基本含义来看,identity包含着关联人或物的同一和区分人或物的差异,而且,同一和差异都属于概念范畴,也就是阿多诺(Theodor Adorno)所谓的概念的自我同一,即“每一思想对象与自身的等同”。[3]此外,identity还可以表示身份、同一人(或物)、同一(性)、特性等意思。可见,术语identity大致处于纵横两个维度的张力之中:纵向,它偏重的是个体的差异;横向,它偏重的是群体的同一。[4]本书在使用identity 这个词,概括起来主要包含“差异”和“同一”两个层面的意思,将identity译作“身份”以彰显差异,“认同”以突出同一。“认同”在本书中更强调中文语境中的动词性,意指主体情感层面的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
第一节 认同何以在当今社会构成问题
认同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受到新左派、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的特别青睐。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对特定社会的文化的认同。这个词总爱追问:我(现代人)是谁?从何而来?到何处去?身份认同植根于西方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它具有三种倾向:第一,传统的固定认同,它来自西方哲学主体论;第二,受相对主义影响,出现一种时髦的后现代认同,它反对单一僵硬,提倡变动多样;第三,另有一种折中认同,它秉承现代性批判理念,倡导一种相对本质主义。[5]关于认同研究的缘起众说纷纭。英国学者巴克说:政治斗争、哲学和语言学研究使认同成为20世纪90年代文化研究的中心课题。[6]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则认为认同是欧美文化政治的风向标,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在美国还要早,在普遍进步与发展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层面,政治文化开始了全面转向……转向与性别、本土或种族身份相关的文化身份认同政治”。[7]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特雷·伊格尔顿进一步表示:“后现代文化是典型的身份认同政治,膜拜去中心主体。”[8]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则在整个西方哲学史、思想史中追溯了现代认同形成的根源,认为启蒙哲学同时赐予现代人以理性甘露与批判利剑,向现代主体提供了强大的反思能力。启蒙即反思,对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的反思,对自我的反思,对人的社会存在的反思。[9]据此,拉腊因教授在《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中,围绕哲学主体论的演变,考察了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的关系。
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也从启蒙哲学之后的现代知识话语入手,探讨现代和后现代身份认同的五大范式,它们分别是: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女性主义、解构主义语言中心观、福科的权利/话语分析。[10]从启蒙哲学、马克思主义,到当代少数话语、身份认同与身份主体论的流变,历经三次大的裂变从而形成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以主体为中心的启蒙身份认同。从笛卡儿在《方法论》(1637)中提出的“我思故我在”,到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区分的“自我/他者”,再到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对启蒙主体理性与精神的探讨,启蒙身份认同从启蒙时代的历史语境中剥离出来。它泛指“建立在对人的这样一种理解基础之上,即人是完全以自己为中心的同一个体,具有理性、意识和行动能力”[11]的一种身份认同模式。第二种是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身份认同。从马克思的阶级身份到韦伯对现代工具理性的批判,再到弗洛伊德从超我和心理界面对启蒙主体的进一步瓦解属于这种范式。然后,拉康以“镜像阶段”理论,福科以权利和话语探讨社会对个人的影响,社会认同强调各种社会力量的决定作用,承认身份认同过程中的自我与他者、个体和社会的相互作用。第三种是后现代去中心身份认同。后现代身份认同的特征是去中心,用霍尔的话说:“主体在不同时间获得不同身份,自我不再是中心,我们包含相互矛盾的身份认同,力量又指向四面八方,因此身份认同总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12]影响后现代认同的主要因素有相对主义、语言学转向和身份认同政治。这种认同模式从自尼采以来的相对主义开始,到后现代思想家德里达的延异、互文、解构,再发展到德勒兹和瓜塔里的“空缺”与“游牧”。
在国内,认同是最近十年(2000—2010)来文化研究最热门的话题,中文学术期刊以题名“认同”精确配置搜索,此段时间内论文题目中含“认同”字样的人文社科论文4423篇,其中博士毕业论文81篇,硕士毕业论文437篇。关于认同的词汇更是丰富多彩,有身份认同、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宗教认同、社会认同、政治认同、地域认同、自我认同、价值认同和他者认同等关于认同分类、界定的词汇。有认同感、认同意识、认同历史、双重认同问题、多重身份认同和当代认同危机等有关认同性质、内涵和境遇分析的词汇。这些论文涵盖了哲学、社会学、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文学等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有人从当下的电视、电影、广告等大众文化现象和文本入手研究政治认同、国族认同、性别认同和地域认同;有人从文学文本和具体作品入手研究当代作家表征和展示的各类认同问题;更有人把认同抽象化上升为形而上的认同理论。加拿大著名的社会学家查尔斯·泰勒以考古学的精细进一步梳理了现代认同的演化历程,出版巨著《自我认同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泰勒认为,“我的认同是由提供框架和视界的承诺和身份规定的”,也就是说,“我能够在其中采取一种立场的视界”。[13]对文学作品中的认同问题研究,就是对文学作品的一种解读立场和阐释策略。
巴尔扎克曾说“小说应当与社会身份登记处相竞争”[14],彼得·凯里正是澳大利亚社会身份登记处最有力的竞争者。澳大利亚的国家政策、民族政策、文化政策以及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不断地在作家凯里的作品中回现。凯里的创作有对殖民历史、民族主义的反思,有对澳大利亚当下幸福生活方式神话的解构,有对现代澳大利亚人自我认同的探讨。从“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到“澳大利亚人的澳大利亚”,从“白人的澳大利亚”到“澳大利亚公民的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两百多年的风云际遇在作家彼得·凯里的笔下应该怎样抒写?作为个体的澳大利亚人又有怎样的心路历程?这些问题给我们以广阔的思考空间。“我”作为一个在迥异于英语文化体系的中国文化体系中成长的“他者”,可以运用怎样的方式、采取怎样的立场,走进凯里用文学作品建构的认同世界?我(们)曾经是谁?我(们)是谁?我(们)将来能够成为谁?我(们)怎样表现我(们)自己?追寻彼得·凯里小说中的认同迷踪,可以看到澳大利亚国家认同如何从含混走向澄明、民族认同如何在危机中出现转机,文化认同如何在困境中走向超越以及凯里小说对澳大利亚人的个体自我认同探索之种种。
当下欧美学界活跃的思想家如霍米·巴巴[15](Homi Bhabha)、齐泽克[16](Slavoj Zizek)等也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给予认同以重要的位置。认同缘何如此受到当代学界的青睐?认同何以在当代社会成为问题?在这个消费主义蔓延的时代,无论是在伦敦、纽约、东京这样的大都市,还是在非洲、拉美和东亚等一些欠发达的地方,消费文化都无孔不入。琳琅满目的商品,川流不息的顾客,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全球同步上映的好莱坞商业电影,为大众量身定做的日剧、韩剧、美剧就是在“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也每天上演。的确,在全球化日趋迅速和消费涵盖一切的当今社会,神、民族、种族、家庭和地域受到了技术经济力量和各种社会运动的联合攻击,国家民族也开始受到质疑。“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正在被全球化和认同的对立趋势所塑造”,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认同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ntity)导言的第一句话即如是说。[17]对特定的个人和群体而言,认同可能有多种。然而,这种多样性不管是在自我表现中还是在社会行动中,都是压力和矛盾的源头,因此认同是人们意义和经验的来源。虽然认同这个话题被热烈讨论、有关认同的词汇使用频率很高,但是在相关理论的梳理和运用上还存在研究空间。因此,本书(1)在后殖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把认同看成一般问题研究,拓展认同研究跨学科视域。(2)将澳大利亚两百年的历史看成现代性发展过程,将其社会历史文化看成现代性的结果。(3)以彼得·凯里小说创作为例,探讨作为现代性批判建构的认同力量。
海尔曼·布洛赫说:“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这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18]在当今这样一个机会平等、个人流动频繁的时代,族裔和散居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网络联系缩小了世界,动摇了国家民族概念的时代,民族主义因而重新高涨,因此认同研究理所当然地成为热点。从社会现象本身出发,以实地调查研究为准则,从文化哲学的高度和艺术经验中去寻找认同的踪迹和认同建构,是时下学界反思现代性,进行社会文化批评的重要路径。因而,文学中所反映和表征的认同问题在这样一个后理论时代[19]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身处这种社会历史语境的澳大利亚作家彼得·凯里可作为这种研究的绝佳范本,因为他的小说发现和阐释了只有他才发现了的澳大利亚社会问题。凯里在他长达四十来年的创作生涯里,用他的4个短篇小说集、12部长篇小说和4部非小说作品建构起一个错综复杂的澳大利亚社会历史文化认同世界。本书努力做好以下工作:(1)对凯里小说中的认同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深化和超越后殖民身份认同研究,扩展凯里小说中认同问题的研究视域。(2)从整体上把握凯里的创作,探讨其构建的认同世界,把重点放在凯里构建了一个怎样的认同世界,以及如何构建上来。(3)凯里的创作与澳大利亚的国家、民族和文化紧密相连,因此本书把凯里小说中的认同问题还原到具体的澳大利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找出澳大利亚的文学、历史、政治、文化等学科之间的内在关联。
关于文学的认同建构,以下几个层面的问题尤其值得关注。[20]首先,是民族起源的神话。认同研究发现,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关于起源的神话。其次,是历史地形成的文学史经典。没有经典的民族也一定会创造和制作出经典来,这就像霍布斯·鲍姆所说的,重复是保持与过去连续性的通道。再次,在这些经典中,往往会凝练出一些典范性的人物形象,从认知心理学角度说,这些经典型人物通常具有“人格样板”的作用(例如:在《凯利帮真史》中,凯里把澳大利亚官方历史上的丛林强盗内德·凯利当成民族英雄来塑造)。假如说作品中的正面形象起到了“积极的”认同建构作用的话,那么,文学中不少否定性形象也起到更复杂的认同建构功能(例如:《奥斯卡与露辛达》中的杰弗里斯)。最后,文学中所呈现的家园空间及其生活方式,尤其是一些象征性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澳大利亚的丛林文学,伙伴关系)。家园是一种空间的归宿,家园更是一种熟悉的、亲近的和缠绕的体验,它们不断地强化人们对家园的热爱、眷恋和向往,不断地提醒人们自己的文化身份,尤其是那些挥之不去的童年经验。澳大利亚文学从大英帝国殖民时期文学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时期的文学,可以说是土生土长的澳洲白人对童年经验的澳洲式的确认。因此,我们研究彼得·凯里小说中的认同问题也可以从其民族起源神话,对帝国文学经典的重写,对澳大利亚丛林强盗的重塑以及凯里小说中展现的澳大利亚生活方式等入手来研究凯里小说中的认同问题。
第二节 凯里小说认同问题研究的缘起
认同作为一个问题,广泛地存在于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它蕴含了复杂的“差异政治”及权力关系,“从民族的、种族的文化差异,到阶级的、社会分层的差异,再到性别的差异,各种亚文化的差异,甚至区域文化地方性差异等,都可以包容在认同的范畴之下”。[21]因此,差异性成为认同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从彼得·凯里的生平和创作背景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凯里成长的年代是澳大利亚国家认同从含混走向澄明的时期;凯里步入文学创作的年代正值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第三波热潮兴起的时候;凯里开始发表作品的时期是澳大利亚民族认同陷入困境和设法摆脱困境的时期;凯里创作高峰期是澳大利亚国家、民族起源神话受到挑战的时候;凯里创作后期是澳大利亚的民族、国家、文化认同逐渐明朗的时候。以下将从作家的生活经历、作品反映的殖民历史和认同现实,以及澳大利亚历史上的民族主义三方面分析我们缘何可以从认同问题入手来研究凯里小说。
首先,彼得·凯里丰富的生活经历为建构错综复杂的认同世界提供了素材。凯里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20世纪七八十年代澳大利亚民族主义高涨时期显名于英语世界。三年多的伦敦生活、周游欧洲的经历、昆士兰热带雨林三年嬉皮士生活体验和旅居美国二十多年的域外生活,使得凯里对认同问题极为关注。这些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生活经历也让凯里能更好地理解澳大利亚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澳大利亚人个体自我认同的复杂性、含混性和待定性。
1967—1970年,凯里定居英国伦敦,一边从事广告业工作,一边周游欧洲,为以后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奥斯卡与露辛达》中的露辛达到达伦敦的感受和对英国与英国人的态度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凯里自己的体验,那种寻根之后的无根的漂泊感是在回归历史的过程中表达的现代人的感受。虽然凯里借露辛达的口表达在伦敦所看到的人,所经历的事都是不值得写的,但是凯里的《奥斯卡与露辛达》与《杰克·迈格斯》的构思和写作无不得益于他三年的伦敦生活。这两部作品中对18世纪英国伦敦的大街小巷、伦敦大桥和伦敦大雾的描写同时有着凯里的丰富想象和现代伦敦的特点。而旅居美国二十多年的经历,则为凯里作品中的美国题材、“美国梦”的描写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果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凯里作品中的美国还只是“梦”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以及以后的作品中的美国因素,则是现实中的美帝国,那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以压倒优势屹立于世的超级大国和强国。《特里斯坦·史密斯不寻常的生活》《偷窃:一个爱情故事》《他的非法自我》都是以美国为主要写作对象,探讨美澳关系的作品。澳大利亚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是在其与英国、美国的关系中显现出来的,澳大利亚人的个体自我认同是在后现代语境中参照诸多的“他者”而彰显的“自我”的认同。穿行在澳、英、美、欧的彼得·凯里以创作阐释着自身的处境及其所思、所想,也以自身的经历阐释着他的作品中的认同。
其次,澳大利亚的殖民历史与社会现实给彼得·凯里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彼得·凯里在《奥斯卡与露辛达》荣膺布克奖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以为我们的国家仍有待构造,甚至有待于发现。我们澳大利亚人还没有被塑造出来。对此,我很恼怒。谁用得着何谓英国人、何谓中国人犯愁?不过,这也是一个优势。我们没有历史的重负压在自己的肩上。我们可以自由而愚蠢地认为我们无所不能。(英人)入侵以来,毕竟只有200年啊。”[22]凯里观察到,在他成长和出道时,澳大利亚整个社会的认同都因其含混待定而成为问题,这些问题成为他的作品反映和讨论的重要问题。
虽然在澳洲这块古老的大陆上,土著人有几万年的生存史,但本书界定的澳大利亚历史为其被命名之后的两百多年的历史,即白人入侵之后的历史。欧洲白人到达澳大利亚之后,他们视澳洲土著人为“同类相食的人兽”,“在理性及有关的每一种感觉方面,他们连最低级的畜牲还不如”。[23]从1788年第一批罪犯到达新南威尔士州屠杀和驱赶澳洲土著并强占大片土地开始,到1859年英国殖民者先后在澳洲大陆上开拓了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北部地区和塔斯马尼亚六块殖民地。这一时期的澳大利亚人“首先把自己看成不列颠人,然后才是维多利亚人,南澳大利亚人或其他人,并逐渐地习惯于成为澳大利亚人”。[24]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之前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在国防、外交和发展资本方面都依赖于英国,他们的贸易和大部分移民都是靠亲属关系、文化和宪法的约束力而与英国联系在一起。[25]殖民时期的澳大利亚人说的是英语,看的是英国的文学作品,传承的是英国的传统文化,怀恋的是英国的故土。《奥斯卡与露辛达》中的奥斯卡和露辛达的母亲伊丽莎白就是这样的文学典型。
再次,澳大利亚的民族主义成为彼得·凯里小说中认同问题探讨的主要依据。19世纪90年代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社会思潮方兴未艾、工会主义的呼声响彻澳洲各地。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澳大利亚土生人口占了绝大多数,1901年联邦成立时,澳大利亚人口主要是英国血统的人,总人口中77%的在澳大利亚出生,18%的在不列颠、爱尔兰出生,最大的非英语族群是占总人口1%的德国人和占总人口0.8%的中国人。[26]打着本地印记的澳洲人,由于长期在地广人稀、荒凉多灾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逐步形成了粗犷、爽朗、乐观、幽默的独立性格,确立了以英语为基础,并吸收本地方言土语和乡音乡调的澳大利亚英语,养成了适应南半球气候条件以及自然条件的民族习惯。[27]这一时期,澳大利亚人把自己视为英国公民的情况有所改变,他们越来越反感英国殖民者鄙视澳洲殖民地,把澳洲人视为“二等公民”的做法。英国殖民者认为殖民地是培养不出主教、教授和法官的地方,甚至连殖民地的商品也一无是处,殖民地的果子酒是酸的;殖民地的啤酒是掺水的;殖民地的奶酪是腐臭的;殖民地的蜜饯是烂的。[28]民族主义者以《公报》(Bulletin)为主要阵地,发表有关民族独立、民主、平等的言论和文学作品。民族主义运动只是结果,我们要关注的是在一个多世纪漫长的殖民地生涯中,澳大利亚人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他们的认同是如何发生改变的?他们的国家、民族的认同感是如何形成的?
彼得·凯里的《奥斯卡与露辛达》、《凯利帮真史》和《杰克·迈格斯》反映的正是19世纪的殖民地时期的澳大利亚。这一时期的“澳大利亚人经常庆祝自己的国家99%是不列颠血统,这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是不成立的,但它已成为澳大利亚民族神话的一部分”。[29]《奥斯卡与露辛达》反映的是19世纪40—60年代初的澳大利亚,这一时期的澳洲各殖民地是分散的,六块主要的殖民地就是在这时候形成的。《凯利帮真史》则主要反映19世纪60—80年代的澳洲历史,以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在殖民地的遭遇,反映白澳内部的民族、族裔矛盾冲突。《杰克·迈格斯》反映的则是19世纪末澳大利亚民族意识的增强,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前夕的历史。彼得·凯里是一个历史感很强的作家,他这三部小说反映了殖民地澳大利亚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形成的全过程,这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且充满矛盾张力的过程。《奥斯卡与露辛达》主要指涉文化认同(基督教文化与澳洲土著文化)和种族(澳洲土著人)认同,《凯利帮真史》主要指涉的是族裔(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认同,《杰克·迈格斯》主要指涉的是国家认同(澳大利亚与英国的关系)。这三部小说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不同时间段澳洲殖民历史中的认同问题。
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之后,依然隶属于英国,澳大利亚没有自己的国歌,澳大利亚人出国门没有自己的护照,他们用的是英国的护照。总之,19世纪90年代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运动以联邦建立宣告结束。此后,“无论是欧洲人,还是与欧洲有近亲血缘关系的澳大利亚人,总把澳大利亚州看作是欧洲放错了位置的部分”。[30]澳大利亚联邦实施殖民时期延续下来的“白澳政策”,“什么是澳大利亚人由与不列颠或英语的联系来决定”。[31]澳洲土著人和华人等少数族裔或其他有色人种依然受到排斥和歧视,澳大利亚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在南太平洋中的“一个培养各种各样种族、国籍和宗教偏见的国度”。[32]华人在彼得·凯里的作品中一直以“他者”的身份出现,是被消音的一个群体。从《魔术师》中贩卖中华文化的神秘的、超能的“他者”,到《奥斯卡与露辛达》中开赌馆、好赌博、胆小怕事、娶了白人女子的隐身“他者”,再到《凯利帮真史》中受攻击、勇敢但不讲信用的“他者”,以及《美国梦》中的如机器般听从白人指挥的“他者”,都反映了澳大利亚历史上,华人的参与足迹以及他们被边缘化,被剥夺了话语权的生存境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的民族主义运动再次高涨。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为宗主国卖命的在战事中失败的澳大利亚人感觉到自己很勇敢的话[33],那么二战则让澳大利亚人认识到宗主国英国不是他们的上帝,他们的安全不是来自英国的保护而在于新兴帝国美国的保护。这段时间是澳大利亚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加强的时候。战后的澳大利亚受到美国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美国资本、跨国公司的涌入,美国消费文化对澳洲社会的渗透,让澳大利亚的文化界倍感焦虑。凯里小说中的“美国梦”和美国因素就是这一时期澳大利亚文化认同的表现,也暗含了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模糊和强化。经济的发展,新移民的涌入,使得澳大利亚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都发生了变化。为了吸收和同化新移民,澳大利亚的民族政策由“白澳政策”变为“同化政策”。澳大利亚政府宣扬一种“澳大利亚生活方式”,以此来规约和同化新移民。但是何为澳大利亚生活方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澳大利亚生活方式是一个人人说不清而又人人不离口的术语,它是一个模糊、散漫的概念,缺乏历史和文化的底蕴。[34]这种认同的根基是不明确的,正如一个移民所抱怨的那样,“他们老是告诉我,必须采用它(澳大利亚生活方式),但这种生活方式是什么,谁也没有告诉我”。[35]凯里的第一部小说《幸福》就是在解构“澳大利亚幸福生活”神话的同时,思考究竟什么是澳大利亚的生活方式。然而,在这部小说的新兴城市生活方式和传统澳大利亚乡土生活方式之间,凯里选择的显然是后者。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世界政治风云变化也将澳大利亚卷入其中,《他的非法自我》反映的正是处于各种思潮异常活跃、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反越战游行盛行时的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关系,凯里以此来探讨澳大利亚国家认同的加强和巩固。
加拿大哲学、人类学家查尔斯·泰勒指出,现代身份认同本质上是政治性的。[36]在政治上,彼得·凯里是左派,他主张澳大利亚脱离英联邦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因此主张澳大利亚共和的他曾数次拒绝接受英国女王的接见。在《凯利帮真史》中面对澳大利亚的殖民历史,凯里对殖民者是持批判态度的,他以赞赏的眼光把反抗殖民统治的丛林大盗内德·凯利当作民族英雄来塑造。《奥斯卡与露辛达》敢于直视曾经被抹杀和涂改过的澳洲土著问题,对殖民者在澳洲大陆这块土地上曾经犯下的滔天罪行进行批判。在《悉尼:一个作家的返乡之旅》中,凯里更是深情地思考着澳洲大陆这块土地的过去和未来,对土著人的悉尼、流放犯的悉尼和今天的新悉尼的描绘无不包含着现实社会的政治意蕴。正如特雷·伊格尔顿所说:“文学,就我们所继承的这一词的含义来说,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与种种社会权利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37]伊格尔顿用整个英国文学从起源到兴盛再到现代和后现代的诸多形态证明了,“文学在好几个方面都是这项意识形态事业的候选人”。[38]凯里在他的小说和散文作品里都不忌讳公开谈论澳大利亚政治生活中的热点问题,就是在他的采访中也不回避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态度[39],他对土著、对殖民历史、对基督教文化、对美国影响等诸多澳大利亚社会政治生活中不能回避的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可以说凯里所有的作品都有着或淡或浓的意识形态色彩。从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取材,探讨社会历史政治中的认同问题是凯里创作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研究凯里小说中认同问题的缘起。
第三节 凯里小说对认同的解构和重构
随着澳大利亚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多元文化政策”[40]的施行,不同文化碰撞中的差异与趋同、异质与同质、家园感与异在感错综纠结,使得认同问题变得越来越迫切了。认同作为一个问题,广泛地存在于澳大利亚社会历史文化的各个层面之中。同时,认同又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和未完成的过程,具有开放性和建构性。认同也是在话语实践中进行的,在种种象征认同的形态中,语言和文学无疑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文学是一种建构性的认同话语实践,其作用不可或缺。[41]彼得·凯里的创作正是这种建构性的认同话语实践。他的作品几乎囊括了澳大利亚社会的所有认同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和自我认同这四种认同问题。那么,凯里怎样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重新审视,解构澳大利亚国家神话、民族起源神话、幸福生活方式神话以及个体自我的自由神话的呢?以下将深入探讨彼得·凯里是如何通过小说这种文学形式,以多种多样的叙事手法重新建构了澳大利亚社会错综复杂的认同世界,并且指出其存在的认同问题,对之作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批判的。
一 凯里小说中的认同问题情状
在20世纪澳大利亚文学创作实践中,“所谓后现代主义,在70年代最为兴盛”。[42]当时澳大利亚文坛很少有人使用“后现代主义”一词,“我们没有什么词可以描述我们正在进行的创作,一般就叫做‘澳大利亚新文学’”[43],因此彼得·凯里等具有后现代特征的作家通常被称为“新派作家”。新派作家的代表彼得·凯里以一种先锋、叛逆的姿态走向文坛。欧美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了凯里早期的创作风格:卡夫卡式的囚禁和变形,昆德拉式的无序叙事,魔幻现实主义的恐惧与怪诞,科幻小说的想象与超常,把真实与幻想融为一体,把过去、现在和未来切入一个超现实的景象。[44]在他的短篇小说中有着卡夫卡式的战战兢兢的小人物,他们总是陷于困境,在捉摸不定、无法逃离的社会境遇和人际关系中无奈地挣扎。[45]彼得·凯里常常把他小说中的人物描写成生活的受害者和梦魇缠身的人,那是作家“羞涩的乐观主义和强烈的悲观主义的体现”。[46]曾经有评论者把彼得·凯里的作品比作但丁的《神曲》。当然凯里的作品在某些方面可能不如《神曲》的意义来得深远,但它们也确实呈现给读者一种《圣经》中《启示录》般的可怖的美丽。凯里喜欢把自己比作“专职的做梦者”“部落中讲故事的人”,努力为澳大利亚人创作出一种启示录性质的文学。彼得·凯里在创作风格上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变化过程:随着写作范围的不断扩大,作品中的感情色彩越来越浓。在他的小说世界里,读者看到感到的是末日将至的混乱、恐慌。尽管科技在进步,可能也正是因为科技的进步,文明反而走向它最终的极限阶段,野蛮正鼓动它的双翼,蠢蠢欲动。与这种外部混乱景象相映照的是人类内心的樊笼与心理上的难受。或许少数人能在世界某个幽暗的角落觅到安宁与桃源,但这不会长久,长久是梦魇般的世界,它将人们从四面包围起来。[47]因此,彼得·凯里是带有现代气质的后现代作家。
彼得·凯里的短篇小说基本上包括在《历史上的胖子》《战争罪行》《故事集》3个短篇小说集里。其认同向度主要有以下三种:(1)对社会的边缘人物、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个体身份的探讨,例如《历史上的胖子》、《剥皮》和《蟹》;(2)对现代工业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危机进行批判,例如《战争罪行》和《关于“幻影工业”的报道》;(3)对战后美国影响澳大利亚的焦虑,批评美国消费文化扰乱了澳大利亚人的认同感,例如《西边的风车》和《美国梦》。彼得·凯里借小人物和社会的边缘人解构宏大叙事中的社会大人物传略,关注边缘消解中心;对现代工业的批判表明了他对过去被发明出来的,现在即将逝去的澳大利亚生活方式的怀念;凯里对美国消费文化在澳大利亚盛行的反思与批判则是从澳美关系看澳大利亚人的文化认同。彼得·凯里的长篇小说延续了短篇小说强烈的社会批判风格,但是把目光转向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奥斯卡与露辛达》《杰克·迈格斯》《凯利帮真史》把目光转向19世纪澳大利亚的殖民历史,探寻澳大利亚社会认同问题的历史根源;《幸福》《特里斯坦·史密斯不寻常的生活》《税务检查官》《偷窃:一个爱情故事》《他的非法自我》则关注当代澳大利亚的现实,探讨认同在澳大利亚当代社会的种种情状。《魔术师》的时间跨度最长——长达一个多世纪,涉及澳大利亚的民族起源、国家建构、当下发展等诸多的问题,以家族史写国家社会的历史。《我的生活有如冒牌货》则从澳大利亚文学的历史建构之裂隙中寻找缺失的认同。
在以上提及的3个短篇小说集和10部长篇小说构成的这个错综复杂的认同世界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和个体自我认同是凯里最主要的解构和建构维度。凯里小说中的民族认同主要包括以澳洲土著人为代表的种族认同,以爱尔兰裔为代表的民族内部的认同和以华人为代表的其他族裔认同。澳洲土著人和华人在澳大利亚的历史上是最受排斥的,他们是不同历史时期种族主义和种族冲突的受害者。凯里小说中的国家认同是指澳大利亚人对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区别于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民族—国家认同。凯里小说中的文化认同指澳大利亚人对澳大利亚自己的传统文化、大英帝国的传统文化、美国的消费文化的向心和离心的认同状况。凯里小说中澳大利亚人的自我认同主要是在澳大利亚国家、民族和文化认同成为问题的境况下,个体自我认同选择的复杂性以及可能性。民族认同主要涉及澳大利亚的“白澳政策”、澳大利亚历史上的种族主义等话题,它包括凯里小说中反映的澳洲土著人、华人和爱尔兰裔的历史遭际。国家认同最主要的是涉及澳英关系以及澳大利亚的自身发展和澳大利亚民族形成过程中对国家独立的诉求。文化认同主要涉及澳英和澳美关系,英国传统文化和美国消费文化对澳大利亚的影响。自我认同是凯里在解构澳大利亚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过程中所揭示的澳大利亚人的个体心路历程。以上就是对彼得·凯里小说涵盖的认同问题的界定以及可能研究的向度。
二 凯里小说对认同问题的解构
解构(Deconstruction)是德里达在继承海德格尔的遗产之上发明的,它指德里达和他的后继者们发现并颠覆西方哲学传统中延续下来的理性/非理性、主体/客体、自我/他者、主人/奴隶、中心/边缘、东方/西方、殖民/被殖民等二元对立结构。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来一直持续和加强着这一系列的二元对立,颠覆这种二元对立结构正是德里达所要做的。他说:
在一个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中,我们所见到的唯是一种鲜明的等级关系,绝无两个对项的和平共处。其中一个单项在价值、逻辑等等方面统治着另一个单项,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解构这个二元对立,便是在一特定的契机,将这一等级秩序颠倒过来。[48]
解构主义者有志于全面置换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旧传统,颠覆等级、秩序、中心和本质。德里达和他的后继者们所做的解构一次又一次地表明,所有的边界、规则、概念、结构,所有的创造和建构,都为疑云密布的“同一”而压抑了原生的“差异”。德里达发明了用删除符号来表达他的解构策略,但是他并非是要完全粉碎这些二元对立结构使之尸骨无存,而是留下了秩序颠倒的若干踪迹。在德里达看来:
踪迹不仅仅是本原在我们的话语中和思路中的消失,它还意味着本原甚至没有消失,意味着本原除非与一个非本原相反相成,将永远没有可能建构自身。踪迹因此成为本原的本原。传统的踪迹概念,是本原的一种在场,一种初始的非踪迹,所以是经验的一种标记。而要把踪迹这概念扳离它的传统轨道,我们必须来谈一种原始的踪迹,或者说原型踪迹。有鉴于我们知道概念总是摧毁自己的名称,所以说如果一切始于踪迹的话,说到底也就没有本原的踪迹。[49]
解构主义认定的对立两项之间,还存在着大量相互渗透、相互包容的关系,因此对于德里达和真正的解构主义者来说,颠覆不是最终的目的,其最终的目的就在踪迹呈现本原在场和经验。彼得·凯里对自我与他者、殖民与被殖民、中心与边缘、白色与黑色这些帝国主义话语体系中的二元对立的解构行为留下了诸多踪迹。
后殖民的理论家们将殖民地的人民称为“殖民地的他者”(colonial other),或径直称为“他者”(Other)。“他者”这一概念,除别的意思外,主要是根据黑格尔和萨特的定义:它指主导性主体之外的一个不熟悉的对立面或否定因素,因为它的存在,主体的权威才得以确定。西方之所以自视优越,是因为它把殖民地人民看作是没有力量、没有自我意识、没有思考和统治能力的结果。精神分析学,特别是经拉康改写过后的精神分析学,也把人的“自我”视为按他人的看法建构而成的一种认识。[50]彼得·凯里的创作就是要颠覆由解构主义者首先开始,后殖民主义者、女性主义者、新历史主义者进一步解构的边缘与中心、男性与女性、宗主国与殖民地、文明与野蛮等二元对立结构。英国的殖民记录[51]和文学作品采用的全是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澳大利亚历史中对澳洲土著人和华裔的记录也是这种模式。这种种族主义在大英帝国是其殖民思想和行动的基础和依据,按当年的殖民地秘书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的说法,“不列颠是世界上所有自治民族中最伟大的一个民族”[52]。因此,彼得·凯里要解构澳大利亚基于种族主义和其他二元对立结构之上建立起来的认同,首先得解放“他者”,给予他者以说话的权利。
彼得·凯里曾这样表述过:“我认为作家有责任去说真话,从不躲闪,这个世界原本怎样就怎样;同时,作家也有责任去讴歌人类精神中潜在的东西。《魔术师》和《奥斯卡与露辛达》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们是在这两方面的张力中产生的。”[53]19世纪书写大英帝国的作家都是早已确定的象征阐释传统的继承人。当然,他们也试图运用示意系统中那些异己的然而又可以把握、可以改造的象征符号,来对浑然不清的世界进行阐释,这有点像透过奥斯卡的玻璃教堂的固定框架去看那单调得让人害怕的澳大利亚草原。[54]大英帝国的文学把澳大利亚作为异己的“他者”写进了历史。在《大卫·科波菲尔》(1849—1850)中的考伯先生就相信,澳大利亚是“一个不能以常理去衡量的春天”以及“某种异乎寻常的东西将会在那个海滩上出现”。在《大卫·科波菲尔》中,辟果提先生把失足的爱弥丽带到澳大利亚,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因为“那里没有人会指责我可爱的小宝贝”。乔治·艾略特《亚当·比德》中的赫蒂·索雷尔与爱弥丽一样,也是在出了丑闻之后被送到地球的另一端。与狄更斯的小说一样,这本小说中的澳大利亚也起着一种使社会的或男女关系上的尴尬得到解脱的作用。在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中,澳大利亚作为罪犯流放地是帝国的一个垃圾站,那里的人是有罪的甚至连他们的钱都是脏的。很显然,在帝国文学体系里澳大利亚是被当作“他者”来建构的,要在文化领域颠覆帝国的等级秩序首先得解构帝国文学经典中的“他者”形象。彼得·凯里的《杰克·迈格斯》就是解构大英帝国的这类“他者”形象,重新建构了作为澳大利亚的民族—国家起源的人物形象蓝本。
彼得·凯里以他的创作深入澳大利亚的社会历史文化现实,郑重地指出澳大利亚社会,无论是在历史还是现实生活中都充满了谎言和欺骗。凯里的小说对这些谎言与欺骗进行了揭露,长篇小说书名中的“魔术师”“冒牌货”“偷窃”“非法”就表明了他的这种解构意图。澳大利亚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发明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诸多的民族神话,这些神话包括“欧洲白人对无主土地的发现”“丛林神话”“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人的”“澳大利亚是白人的”“澳大利亚幸福生活方式”“澳新军团神话”“澳大利亚是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英勇的探险家发现了澳洲内陆”“澳大利亚人是自由、平等的,他们享有充分的民主”,等等。澳大利亚人陶醉在自己编织的谎言中颇为自得地称自己的国家为“幸运之邦”,自己是“幸运之邦的国民”[55],彼得·凯里的创作旨在解构这些有关民族和国家的神话,把澳大利亚人从谎言和欺骗的迷梦中唤醒过来。正如凯里本人在一次采访中所强调的:“我的故事大多激发于这一问题:人们是否想不按他们现在这样的方式生活?在那些试图有所改变的人身上又会发生些什么?”[56]面对澳洲土著人要求归还他们的土地,面对那些有条件的和解要求,澳大利亚的民族认同发生了危机。戳穿谎言、正视历史,当下的澳大利亚人是不是会更心安理得呢?正如凯里借拜杰葛瑞之口所说的,他们的国家是从土著人那里偷来的,但是那偷来的国家也是他们自己的国家,这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彼得·凯里小说解构之后的澳大利亚历史碎片映照出了形形色色的认同碎片。
三 凯里小说对认同问题的重构
1970年,彼得·凯里回到澳大利亚时,狂热的经验主义让他回到了短篇小说写作,渴望发出澳大利亚的声音,“把鼻子转向过去在已经死去的历史里”寻找自由。[57]就像他的生活,他的小说通常也是混杂的,交叉和混合的文体,打破了大众文学与严肃文学、高雅文学与低俗文学之间的界限。它们也僭越了像男性和女性、资本主义者和嬉皮士、殖民与后殖民之间固定的二元对立,展示了矛盾空间,模糊了正反相对的划分。[58]但凯里的创作不限于对英国帝国主义话语的攻击和瓦解,也建构了自己的话语体系,从而成为“澳大利亚文化的代言人”和“澳大利亚新神话的创造者”。从《幸福》到《他的非法自我》,凯里在解构澳大利亚社会历史现实种种神话的过程中,也在建构新的国家民族神话。从“我们是谁”“我们过去怎样”,到“我们将来会成为谁”,凯里的作品都有一种明确的未来指向。正如凯里在《悉尼:一个作家的返乡之旅》中指出的,土著人的悉尼和流放犯的悉尼那是历史是不能忘记的,但是奥运会后的悉尼才是需要当代澳大利亚人精心打造和用心呵护的新悉尼。只有揭开土著人的悉尼和流放犯的悉尼的神秘面纱,面对惨烈的历史真实,才能在今天的新悉尼的建构中摒弃种族主义、血与火、罪与欠、狭隘与偏见,建立真正自由、民主、平等的“多元文化”汇聚的现代大都市——新悉尼。
《幸福》解构了“澳大利亚幸福生活方式神话”,表达了澳大利亚人的乡土情结,彼得·凯里在澳大利亚既有的“丛林神话”的基础上,重构了乌托邦式的丛林生活方式以对抗美国化的生活方式。《魔术师》解构了“澳大利亚过去是白人发现的无主土地,现在是独立自主、平等自由的国家神话”,指出他们的国家是从澳洲土著人那里偷来的,他们的国家受到英帝国和美帝国难以摆脱的影响,要想发展民族航空工业和汽车工业举步维艰。《奥斯卡与露辛达》揭示了澳大利亚殖民时期的三个谎言:澳大利亚是“幸运的国家”;圣洁的传教士“拯救”了“野蛮的黑人”;勇敢的英雄探险家“开发”了殖民国家并使之“文明”。彼得·凯里指出白人和土著共同拥有澳大利亚的历史,上帝的事业不是天使造就的,那些“英雄的探险家”是种族屠杀的刽子手。《税务检查官》解构了“澳大利亚政府是高效、廉洁的政府”,指出其腐败的根源以及未来的希望之所在。《特里斯坦·史密斯不寻常的生活》则粉碎了“澳大利亚人的美国梦”,指出“美国梦”给民族文化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凯里塑造了澳大利亚的民族主义者形象,并指出其先天不足的特性。《杰克·迈格斯》解构了大英帝国经典文学中的诸多二元对立结构,给予殖民地人民以言说和表达自己的权利。《凯利帮真史》解构了官方历史中妖魔化的内德·凯利形象,立志于塑造自己的民族英雄,为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申诉。《我的生活有如冒牌货》揭露了澳大利亚文学传统建构中的谎言,指出澳大利亚民族文学发展中的种种问题,提出建构民族文学身份。《偷窃:一个爱情故事》解构了艺术经典的评判标准,指出艺术领域同样充满欺骗、谎言、暴力、凶杀和跨越国界的阴谋,艺术经典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他的非法自我》解构了澳大利亚人的美国梦,建构了美国人的澳大利亚梦。
对于真正的解构主义者来说,瓦解既有的二元对立结构不是目的,其目的在解构之后的踪迹。彼得·凯里的目的也不在于揭露欺骗和谎言、瓦解帝国话语体系,而在于如何以此建构全新的澳大利亚认同。凯里的“踪迹”包括有启示性的情节和特定的小说人物,如内德·凯利有机会逃到美国,但他选择了死在殖民地澳大利亚的警察手中,因此他是认同澳大利亚的。又如《偷窃:一个爱情故事》采用小说人物交替叙述,以分裂的“自我”表现复杂的人物性格特征。多样化的不断变化的人物视角以及儿童视角(例如《他的非法自我》和《美国梦》)的运用,呈现澳大利亚错综复杂的认同世界。凯里小说中的欺骗、谎言、历史、殖民等主题和玻璃教堂、水、丛林等文化意象也表征了不同的认同症候。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凯里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改变,其认同也在改变。例如,杰克·迈格斯刚来到这个世界上3个月就成了孤儿杰克,流放前是英国的窃贼杰克,刚到新南威尔士是流放犯杰克,随后成了澳大利亚的绅士杰克。再次踏上英国的土地时他是陌生人杰克,来到自己为养子亨利添置的房子中成了入侵者杰克,接着为了寻找养子成了珀西·巴克尔的仆人杰克,然后又流落成作家托拜厄斯·欧茨的犯罪心理实验对象杰克,被迫自卫杀死了捕贼队队员威尔福·帕特里基则成了杀人犯杰克,然后再次回到澳大利亚做他的绅士杰克。杰克·迈格斯的国家认同从大英帝国的子民变成了帝国的流放犯,重返帝国的杰克所有的遭际瓦解了他对帝国的认同,回到澳大利亚的杰克最终完成了自己是澳大利亚人的认同,并生下了“澳大利亚种族”的后代。
[1] David B.Guralnik,ed. 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of the American Language,New York and Cleveland: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1972,p.696.
[2] James A.H.Murray,Henry Bradley,W.A.Craigie,and C.T.Onions,eds.,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Vol.VII,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p.620.
[3]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4] 王晓路等著:《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8页。
[5] 赵一帆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465页。
[6] Chris Barker,Cultural Studies,Sage Publications,2000,p.165.
[7] Jonathan Friedman,Cultural Identity and Global Process,Sage Publications,1994,p.234.
[8] Terry Eagleton,The Idea of Culture,Blackwell Publisher Inc.2000,p.76.
[9] 见[加]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10] 赵一帆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第466页。
[11] Stuart Hall,“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in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ed.,Stuart Hall,Polity Press,1991,p.275.
[12] Stuart Hall,“Gramsci's Relevance for the Study of Race and Ethnicity”,in 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ed.D.Morley and K.Chen,Lodon:Routledge,1996,p.227.
[13] [加]查尔斯·泰勒:《自我认同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第37页。
[14] 米兰·昆德拉:《背叛的遗嘱》,孟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页。
[15] 2010年5月18—20日,霍米·巴巴在北京大学进行了系列的讲座:《全球过渡时期的人文学科我们的邻居》《我们自己:全球共同体的伦理和美学》《展示现代性——霍米巴巴与杜维明教授对话》都涉及了身份/认同问题。
[16] 2010年5月17—18日,齐泽克在中国人民大学和清华大学做了两场讲座。
[17] [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二版),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18] 见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第4页。
[19] 此说法源自特里·伊格尔顿(见[英]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20] 周宪:《文学与认同》,载周宪主编《文学与认同:跨学科的反思》,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81—195页。
[21] 周宪:《文学与认同》,载周宪主编《文学与认同:跨学科的反思》,第181—195页。
[22] Peter Carey,“In an Interview with Edmund White”,The Sunday Times(London),March 20,1988,pp.8-9.
[23] 张安德:《试论“白澳政策”的渊源、演变及其终结》,《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2期,第51—57页。
[24] Adam Jamrozik,Cathy Boland,and Robert Urquhart,Social Change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Australia,Melbourn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40.
[25] 刘丽君、邓子钦、张立中:《澳大利亚文化史稿》,汕头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26页。
[26] [澳]理查德·怀特:《创造澳大利亚》,杨岸青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页。
[27] 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7—68页。
[28] 曼宁·克拉克:《澳大利亚简史》,威廉海纳曼出版公司1969年版,第180页;转引自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页。
[29] Adam Jamrozik,Social Change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Australia,p.94.
[30] 林汉隽:《亚太经济及其文化背景》,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95页。
[31] Adam Jamrozik,Social Change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Australia,p.40.
[32] [澳]唐纳德·霍恩:《澳大利亚——一个幸运之邦的国民》,徐维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页。
[33] 加里波第战役,尽管澳大利亚损兵折将、损失惨重,但澳大利亚人认为自己很勇敢,以“澳新军团纪念日”来纪念阵亡的将士,增强民族自豪感。
[34] David Bennett,Multicultural States:Rethinking Difference and Identity,New York:Routledge,1998,p.153.
[35] [澳]理查德·怀特:《创造澳大利亚》,杨岸青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页。
[36] [加]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
[37] [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
[38] 同上书,第22页。
[39] [澳]埃德蒙·怀特:《将自己的心灵印在文学版图上——彼得·凯里访谈录》,第70—71页。
[40] 1972年,澳大利亚终止“白澳政策”,开始实施“多元文化政策”。
[41] 周宪:《文学与认同》,载周宪主编《文学与认同:跨学科的反思》,第181—195页。
[42] 麦克尔·威尔丁:《后现代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外国文学》1993年第4期,第9页。
[43] 同上书,第9页。
[44] 张明:《“新派”先锋彼得·凯里——评澳大利亚作家彼得·凯里的小说创作》,《外国文学》2001年第4期,第17—20页。
[45] 潘雯、陈正发:《都市里讲故事的人——彼得·凯里创作轨迹探寻》,载陈正发主编《大洋洲文学》,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
[46]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152.
[47] 潘雯、陈正发:《都市里讲故事的人——彼得·凯里创作轨迹探寻》,第204页。
[48] 德里达:《立场》,转引自陆扬《德里达——解构之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7页。
[49] [法]德里达:《论文字学》,转引自陆扬《德里达——解构之维》,第67—68页。
[50] [英]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韩敏中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51] [英]沃特金·坦奇:《澳洲拓殖记》,刘秉仁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52] [英]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第36页。
[53] 潘雯、陈正发:《都市里讲故事的人——彼得·凯里创作轨迹探寻》,第206页。
[54] [英]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第19页。
[55] [澳]唐纳德·霍恩:《澳大利亚人——幸运之邦的国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
[56] 潘雯、陈正发:《都市里讲故事的人——彼得·凯里创作轨迹探寻》,第205页。
[57] Bruce Woodcock,Peter Carey:Contemporary World Writers,2nd ed,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4,p.4.
[58] Ibid.,p.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