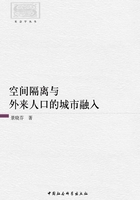
二 国内外城市社会空间相关研究及述评
(一)空间的属性
空间的研究一直是地理学、建筑学等学科所关注的,但这些学科多是将空间看作一个科学的研究对象,在研究过程中多使用的是一些自然科学的方法。在这些学科中,空间有一种不言自明的属性,那就是它的物理属性,至于空间所表示出来的社会内涵在这些学科中很少被关注,直到人文地理学的出现,在地理学科中才开始关注空间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与人有关的内容。人文社会科学对空间的关注晚于自然科学,但它们从一开始就是从社会属性的角度来论述空间的,下面就将社会科学中有关空间属性的研究做一简单梳理。
1.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空间的论述
关于城市空间社会属性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城市的论述。但马恩关于城市空间社会属性的论述多集中于城乡之间,即相对于乡村社会的城市社会特征。恩格斯将城市与乡村的分离称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这是人类社会出现的第一次社会分工和职业分化,这次分离的一个最主要后果就是城市的出现,体现在地域空间上就是城乡分离。从此,城市作为独立的、有着内部自发动力的空间形态开始存在,城乡的发展也遵循了不同的逻辑,具体表现为个人劳动方式的对立和生产方式的对立。当然,城市的出现还有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如防御、地理、政治、宗教等因素,这些因素在城市形成初期有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一旦城市形成之后,如果要持续存在的话,其内部动力只有依靠从农业中分化出来的工商业发展来维系。在城乡分离后的若干年,目前在世界的很多地方,这种分离状态依然存在,而且还将继续下去,城市和乡村的发展遵循着不同的前进逻辑,它们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物质生产方式和居民劳动方式的差别,而且是身份、地位、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对立。关于城市内部空间的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提到的比较少,相对来说,恩格斯的论述更为详细一些,他的这方面观点主要体现在《论住宅问题》文集中。这个论文集收录了恩格斯与蒲鲁东主义者关于住宅问题论战的三篇文章,在论述中他将阶级问题投射到城市空间,主要是居住空间,A.米尔柏格认为将住宅承租人对房主的关系相当于雇佣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认为通过分期付款方式使工人成为自己的住宅和宅旁小块土地的所有者,这样就可以使工人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恩格斯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这种改良主义的做法是一种历史的倒退,要从根本上解决工人的住宅问题,必须消灭私有制,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里,恩格斯是将解决“住宅问题”同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制、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根本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2.经典社会学家有关空间的论述
在社会学领域,很多经典社会学家都对空间有过一定的论及。例如,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指出时间和空间必须要通过区分才能被主体所掌握,他区分了个体所感知的空间和一般意义上的空间,但在涂尔干这里,空间问题并非其关注的重点,他只是通过时间、空间、范畴这样的概念来论述人类普遍知识是如何可能的。在社会学领域首先对空间做了专门论述的学者当属齐美尔,他在《空间社会学》一书中指出:“相互作用使此前空虚的和无价值的空间变为某种对我们来说是实在的东西,空间使相互作用成为可能,相互作用填充着空间。”(齐美尔,2002)也就是说,空间产生于人们的相互交往,如果人们只是各自占据着一定的空间而不发生互动的话,这种空间是无意义的,“……在这个位置和邻近的那个人的位置之间是未填充的空间,实际上,一无所有。在这二者进入相互作用的那一刻,他们之间的空间似乎是填满了,而且变得有生机了”(齐美尔,2002)。齐美尔还指出了空间的五种属性:空间的排他性、空间的分割性、社会互动的空间局部化、邻近/距离、空间的变动性(何雪松,2006)。相比起《空间社会学》一书,《大都市与精神生活》和大部头著作《货币哲学》中关于空间的论述就显得很不经意,如他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一书中用规模、分工、货币经济三个变量对都市空间中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精神生活特点进行了解释,这里只是将都市空间作为一个容器,研究处于其中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精神生活。在《货币哲学》一书中,提到了货币对空间的消解作用,货币使得主客体得以实现空间上的分离,从而达到个体自由。
3.列斐伏尔与福柯的空间属性
在真正意义上深刻地揭示了空间的社会属性的学者应该是列斐伏尔。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他们更多关注的是“空间中的生产”,也就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物质生产,关注的重点在于空间中的物质生产过程以及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对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中,空间本身并不是他们的直接关注对象,只是作为物质生产的一个外在容器而存在。而列斐伏尔明确地将研究转向了“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即空间本身的生产,第一次将空间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而且这种空间研究又不同于以往地理学中的空间概念,它从根本上超越了空间的物理属性。列斐伏尔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但又不完全等同,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是“时间—历史”维度的话,那么列斐伏尔则实现了由时间向空间维度的转向,他的研究方法被称为“社会—历史—空间”的“三元辩证法”。正如列斐伏尔本人所说,“辩证法不再听命于时间性……认识到空间,认识到发生了什么或在什么地方发生以及通常是指什么,这是对辩证法的恢复”(Henri Lefebvre,1978)。通过三元辩证法,将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联系起来综合分析,这是列斐伏尔在空间研究方面的第一个贡献。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研究的另一个贡献就是明确指出了空间的社会意义,“空间从来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蕴含着某种意义”(Henri Lefebvre,1991)。列斐伏尔在自己的研究中区分了各种各样的空间,如“绝对空间、政治空间、男性空间”等,对空间的这种划分实际上是表明了空间所负载的社会属性,与以往的只关注虚无的空间物理属性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转向。列斐伏尔将自己的空间思想应用于城市空间之中,认为城市是一个既包含物理又包含社会和精神的三位一体的空间存在,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他将马克思的物质资料生产过程扩展到了城市空间生产中,认为城市并不是自发而生的,而是资本按照自己的逻辑生产出来的,整个城市空间充满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资本主义在马克思时代所表现出来的危机也因为物质生产向空间扩展而得以克服。从列斐伏尔开始,人们在研究空间的时候不再将其当作一个客观的他者,站在价值无涉的立场上进行分析,而是采用了价值介入的立场。
与列斐伏尔一样,福柯也批判了在人文社科研究中过于关注时间而忽略空间的做法,他希望借助地理学中的传统概念——空间来重新解读人类社会,但与列斐伏尔的宏观分析不同,福柯(2007)更为关注微观空间层面上的意义,他关于空间的主要成果在于将空间与权力、空间与知识联系起来。权力与空间的关系主要在他的《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认为,现代社会的各种空间表现如工厂、学校等都体现了权力的运作,由边沁所设计的全景式监狱更是权力化空间的极致表现。他还论述了权力空间与知识的生产,在《疯癫与文明》中,阐明了精神病学这门学科知识如何从权力空间产生出来。
列斐伏尔和福柯不约而同地都注意到了空间的社会属性,在他们的研究里,空间不再是一个空洞的、死寂的、无生命的存在,而是一个包含着丰富内容的实体,二人共同开创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空间时代的到来,引发了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城市社会学研究中的“空间转向”。从此之后,许多学者相继对空间进行关注。
4.大卫·哈维和爱德华·索亚的空间观
哈维的空间思想直接来自列斐伏尔,同时,他继承了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将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与城市空间生产相结合,提出了资本生产的三级循环理论:资本向物质生产领域的投资是资本生产的第一循环,这一领域是马克思主要研究的;随着资本在第一循环投资机会的减少和资本投资回报的下降,资本家将投资转向第二循环,也就是城市空间,正是因为资本的投入和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创造出了城市这一“人造环境”(built environment),城市的各种景观如办公楼、房地产、商业空间等都是资本追求利润的产物,体现了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同样的,资本在第二循环也面临过度积累的危机,为了解决这一危机,资本将投向第三循环,也就是向科教文卫事业的投入,但这一循环也并非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最终出路。哈维认为,通过资本三级循环转移的“时间性修复”[1]已经无法解决当前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面临的危机,因此,资本将目光转向了“空间性修复”[2],即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但随着空间修复的进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可供投资的机会也日趋枯竭,空间修复也并不是解决资本全球危机的良策。在哈维的空间理论中,有关城市空间的叙述主要体现在他的《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巴黎的城市改造过程可以说就是资本介入城市空间的过程,在这个空间重构过程中体现了“巴黎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当新的城市空间被生产出来以后,相应的也就出现了新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体现在各类城市空间之中,如“新的宽阔大道、百货公司、咖啡馆、餐馆、剧院、公园以及一些标志性的纪念建筑”,“……阶级的区分不得不铭刻在空间的区分之上”(大卫·哈维,2006)。资本对城市空间的过度控制导致城市中空间隔离、空间剥夺以及空间异化的出现,而这一切都体现了城市空间背后所隐含的公平与正义问题。可以说,哈维的《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城市空间生产的样本,这一研究对于今日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以及急剧的城市空间变动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社会阶层关系研究仍然具有非常有益的借鉴作用。
爱德华·索亚是一位后现代地理学家,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空间传统渐渐消失,为此,需要重新审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恢复空间在其中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理论化形成主要是在法语国家,并体现出空间在20世纪法国知识传统中所重新占据的异乎寻常的中心地位”(爱德华·索亚,2004)。索亚将空间维度引入历史唯物主义,称之为“社会—空间辩证法”,他还发展出了“第三空间”理论,并将自己所创造出的方法与理论应用于实际的城市空间研究,即以洛杉矶城市为样本进行分析。
对空间属性进行讨论的学者还包括吉登斯、卡斯特、桑德斯等,本书不再一一对其思想进行综述。虽然这些学者关于城市空间的分析存在具体的差异,但其中相同的一点就是,他们无一例外地关注到了空间的社会属性,认为空间并非空洞的物质存在,而是体现了生存于其中的人与人、群体与群体、组织与组织之间社会关系、空间结构是社会结构的投射与映象。对空间社会属性的重新认识引发了城市社会学和人文地理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和人文地理学的社会转向使得这两个学科出现了交叉和对话的平台,搜索现有关于城市空间的文献,主要的成果都是来自这两个学科。
(二)西方城市社会空间研究的主要理论流派和研究方法
1.西方城市社会空间研究各流派的主要观点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和早期的社会学家在自己的研究中多多少少都涉及城市空间问题,但空间并没有成为他们专门的研究对象,即使是在齐美尔那里,对空间也只是进行了抽象的论述,缺乏具体的针对空间本身的分析。在社会学中,真正的城市空间研究始于芝加哥学派,表2—2对西方城市社会结构空间的研究进行了简单的概括和总结(唐子来,1997;刘旺、张文忠,2004;李健、宁越敏,2006;马仁锋等,2008)。
表2—2 西方城市社会空间研究的主要代表理论观点

续表

人类生态学派对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三大经典模型(见图2—1)从根本上奠定了新城市社会学产生以前城市空间研究的基础,随后的社会区研究更多的是在此基础上的深入和改进,借助统计学的技术将更多的因素纳入分析过程以发现更多影响城市空间的因素。人类生态学及其后续的研究是一种对城市空间的客观描述,在研究中所持的立场是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他们的空间研究很少触及空间背后所隐含的社会关系。新古典主义学派则将城市空间纳入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框架进行分析,这种分析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真空”立场,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基于成本和收益权衡后的空间区位选择的结果。行为主义学派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派来讲,将空间经济行为分析放到一个比较现实的环境,但其分析也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之内进行的,只不过扩展了影响变量的内容。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城市空间研究则明显持一种价值介入的立场,关注城市空间形成中的经济、政治、社会机制,将城市空间放置到整个资本主义关系下进行研究,在新马克思主义学派那里,城市空间并非只是一个客观的物理存在,而是充满了阶级斗争和社会关系的社会产物,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的城市社会学研究开创了城市空间研究的新方向,对城市社会学的空间研究贡献了新方法论、理论及具体的城市空间研究案例。

图2—1 芝加哥学派的三大经典模型
2.城市空间形成和演变的动力机制
关于城市空间形成和演变的动力机制,不同学派有不同的观点。
芝加哥学派在研究城市空间时引入了生态学的观点,认为生态学的观点也可以用于人类城市社会之中,生态学中将自然群落形成的动力归为“共生”和“竞争”,帕克认为这两个原则同样也是造成城市各类机构和群体分布于不同城市空间的原因。那些在竞争中比较有实力的机构和人口占据了城市空间中比较有利的位置,而那些没有实力的只能分布或居住于较差的地方。竞争是导致城市空间分异的主要原因,即差异较大的机构和人口分居于城市的不同空间,他们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距离。当然城市各主体之间并非只是一种竞争关系,整个城市如同自然界一样,也是一个有机系统,各要素之间还存在着相互依赖、互相依存的关系,城市各要素相互依存的基础是社会分工,社会分工越细,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就越高,体现在城市空间分布上便是那些功能相互依赖的机构和人口处于位置相邻的区域。城市空间格局形成之后并非处于一种固定状态,而是在各种力量的作用下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芝加哥学派用“集中”、“离散”、“隔离”、“侵入”和“接替”来描述这种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动。集中主要表现在那些拥有实力的竞争机构向城市中心迁移的过程,城市中心地租昂贵、通达性好,表现在空间格局上就是一些实力雄厚的商业机构和银行往往占据一个城市的中心地带;离散是指一些人口和机构出于各种原因向城市外郊迁移的过程,如一些上层人士出于对优美环境的追求,一些工商业机构为了获得地租相对便宜的城市用地迁向郊区;隔离是指某些机构和群体聚集在城市特定的区域之中,与周围其他机构和人口之间有一种相对明显的边界,如城市中少数民族、社会下层人士一般都居住在一个与外界相对隔离的区域;侵入和接替则是对空间演进过程的描述,城市不同机构和人群并不总处于自己固定的区域,它们都有可能将自己的地域扩展到其他机构和人群那里,同时也都可能被其他机构和群体入侵。如同伯吉斯的同心圆模式里所说的,当中心商业圈扩大时,就会入侵过渡区的地域,过渡区同样也有可能将自己的地域向外扩展,入侵工人住宅区。
芝加哥学派的人类生态学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城市化早期城市空间格局形成的动力机制,这一时期城市化主要是一种向心型城市化,也就是各种要素向城市中心的聚集,地租的高低和各种机构与人口对地租的支付能力之间的匹配程度决定了他们在城市空间中的区位。但人类生态学理论对于城市空间结构的解释是一种较为简化的解释,过于强调竞争力的作用而忽略了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其他因素。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继续推进,西方许多大城市出现了郊区化、逆城市化以及城市中心衰落、城市社会运动等现象,对于这些现象,人类生态学派的理论都无法予以解释。
社会区理论则着眼于一个城市中区域社会空间结构形成的影响因素,主要是人口居住空间结构。社会区是城市中具有一定同质性人口的聚居地域,社会区研究大都使用的是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因子生态分析法提取影响社会区形成的人口相关因子。经过研究,谢夫凯(Shevky)、贝尔(Bell)、莫迪(Murdie)等都认为城市社会区形成的影响因素有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状况和种族因素。莫迪还在他对加拿大多伦多城社会区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其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型。他认为,社会经济状况在空间上呈扇形分布、家庭结构在空间上呈现同心圆模式,种族因素则呈现出分散组群模式。这三类空间结构叠加起来,形成整个城市空间结构(见图2—2)。

图2—2 莫迪的城市空间结构模型
对比莫迪和芝加哥人类生态学派的城市空间模型,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社会区研究不再将单一因素作为解释城市空间结构的动力机制,芝加哥学派大都是将地租以及付租能力作为城市空间结构的决定性因素,社会区分析则将更多的人口变量纳入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因素中,不同因素所导致的空间结构呈现出不同模式,这就突破了芝加哥学派试图用一种模式解释整个城市空间结构的局限性,所构造的模型也更为切合城市空间实际。但社会区分析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大多数的社会区分析所使用的数据都来自人口普查资料,因而所提取的因子仅限于与个体有关的经济特征、家庭特征和种族特征,更多的是从微观层面上分析了影响社会区形成的动力,而关于宏观层面的经济、社会、文化因素则忽略掉了。
新古典主义学派直接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假定和理论应用于城市空间研究,主要关注家庭和公司的区位选择过程。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假定为:“经济人”假定、经济自由假定和资源稀缺假定,除此以外,还有一些辅助性的如理性人假定、信息完全假定、个体主义假定等,这些都是不同研究者在具体研究时给出的一些附加假定。在假定了这些条件之后,个体和企业行为都是在比较投入和收益之后选择的结果。具体到城市空间研究中,新古典主义学者假定城市是单核心的,所有的人都需要到城市中心去上班,而且都住在家里,需要往返于工作单位与家庭之间,距离城市越远,所需要付出的交通成本越高,但付出的住房成本越低。因而家庭的住宅区位选择是比较家庭收入、交通价格和住房价格之后折中的结果,住宅区位的选择过程是一个完全竞争过程,付出地租最高者居于城市的最佳区位。对于企业或厂商,其区位选择也是基于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的权衡,所不同的是,住宅区位选择时的交通成本被运输成本所取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和招致的批评同样也是城市空间研究中的新古典主义学派所面临的,过多的假定限制了这一模型的解释力,这种过于理想化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符合人们的区位选择行为,通勤成本是人们选择住宅区位的一个考虑因素,但很多时候并不是主要因素更不是唯一因素。古典主义学派将城市空间结构看成完全的市场自由选择结果,与现实相去甚远。区位选择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而是综合了多种力量作用的结果。
针对古典主义学派的不足,行为主义学派在研究城市空间时加入了更多人的因素,认为区位选择是区位地租与个体对区位认知共同作用后的结果,并以此为理论基础,进行了大量的购物空间选择、住宅区位选择研究。虽然比起古典主义学派,行为主义的研究更贴近现实,但仍然是一种个体主义的方法,强调个体选择对空间结构的影响而忽略了宏观社会结构在城市空间结构形成中的作用。
新马克思主义者将城市空间放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下来考察,关注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宏观动力机制。他们认为城市空间生产的动力来自资本对利润的追求,资本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了城市,城市物质景观的建立或破坏都是为了使资本的运转更有效,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新马克思主义将资本主义的城市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关系联系起来分析,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分析的是抽象意义上的城市空间而非具体的城市空间。新马克思主义者为城市空间研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思路,但也因其高度抽象,被批评者认为距离城市太远,尤其是将研究延伸到全球范围后,城市的独特性消失了。
新韦伯主义关注与空间有关的城市公共资源分配问题,如住房、交通、公共设施等,强调城市空间资源分配过程中市场机构和官僚机构中的“守门人”的作用。与其他资源一样,城市空间资源也是一种稀缺资源,个体获得这种资源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市场途径,主要依靠个人在市场上的竞争力——经济能力;二是通过国家公共部门进行分配。例如,雷克斯和墨尔(RexJ.and Moore R.,1967)认为市场和科层制决定着城市住房分配的基本过程;帕尔(Paul,1975)的城市经理人理论则认为城市空间资源在分配过程中会受到官僚制中的“经理人”的影响。
(三)国内城市空间研究
国内的城市空间研究起步比较晚,从理论和方法上一直处于学习和借鉴西方的过程中。虽然从理论和方法来讲,国内学者对于城市社会空间研究的贡献不大,但也出现了大量的具体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于丰富中国的城市空间研究资料以及以后的理论提升具有重要的基础意义。
整理国内有关城市空间研究的文献,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空间结构状态研究
国内最先对城市社会空间进行研究的是虞蔚(1986),他在《城市社会空间的研究与规划》一书中用因子生态分析法对上海的城市空间进行研究,发现对上海城市空间结构产生影响的因子为人口集聚和人口文化职业结构;接下来许学强、郑静等分别利用1984年、1985年广州居民出行调查和房屋调查数据,以及1990年广州人口普查数据在1989年和1995年对广州城市空间分异状况进行研究,发现广州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现象有加剧趋势(许学强,1989;郑静、许学强,1995);王兴中(2000)将西安居住空间结构分为六大区域,分别为知识分子居住区、工人居住区、混合居住区、干部居住区和农民居住区;吴启焰(2001)对南京市城市空间进行研究后将其居住空间分为高级别墅区、高档高层公寓区、中高档多层公寓区、中档多层住宅区、廉价多层经济住宅区和棚户区与多人廉租区,在空间分布上呈东高西南低扇状分布,在城市中心则呈围绕CBD环状分布,中心高、边缘低,东部受扇状要素影响,在外圈呈多核化现象;杨上广(2006)从住宅价格、面积和住宅类型分析了上海市的居住空间分异状态,并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探讨了居住空间分异形成的原因。此后,有学者相继对大连、深圳、兰州、厦门、济南、武汉等城市空间分布尤其是居住空间进行了研究。
在对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中,还有一部分学者将关注点集中于人口的空间分布情况,这方面的研究有张桂霞(1994)利用广州市第三次和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对广州的人口空间分布特点、变动类型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冯健、周一星(2003),黄荣清(2005)对北京的研究;周春山(1996)对广州的研究;张善余(1999)对上海的研究;李俊莉等(2005)对西安的研究;刘耀斌、张云(2004)对武汉的研究;冯健、周一星(2002)对杭州的研究。2000年以后,随着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发布,这方面的研究也比较深入,除了单纯的针对某一个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变动的研究外,还出现了将同一城市不同时期人口分布进行对比的研究,如冯健(2003)对北京、朱宇(2004)对上海的研究就是这种情形。另外一种比较研究就是将不同城市的人口空间分布进行对比,如王桂新(2003)对上海与东京的对比研究即属于这种情形。
2.城市空间分异的动力机制
关于城市空间格局形成及演化的动力机制,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目前的城市空间布局构成主要受到市场因素、政府及政策因素、历史因素、家庭及个人行为等几方面力量的共同作用,如王兴中(2000)将西安城市居住空间演变动力归为土地利用、政府和社区过滤机制三个方面;吴启焰(2001)认为政府、市场(地产机构、金融机构)、专业知识和专业机构(规划设计)是城市居住空间结构形成的充分条件,而家庭择居行为则是其必要条件,这两者共同规制了一个城市的居住空间结构;李志刚等(2004)强调历史和市场因素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魏立华、闫小培(2006)认为经济转轨后市场力量的壮大以及政府的企业化行为共同构成转型期广州城市空间结构演进的动力;邓楠(2006)认为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中各利益团体较量后的结果,主要是政府、跨国公司、企业主体、城市居民。而自然环境、交通技术和殖民化是长春空间演进的促进因子(刘艳军、李诚固,2008)。在这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不同的城市进行了研究,但从城市空间动力机制的归纳来看都没有超出以上所说的几个因素。
3.对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不同价值判断和应对策略
多数学者对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结论部分都有关于城市空间分异的价值判断,即我们尤其是政府应该以何种态度对待空间分异。一个基本一致的观点便是空间分异有它合理性的一面,在市场经济规律作用下,为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必然会造成城市空间的分异甚至极化现象,但这种分异如果不加控制的话,最终会形成城市不同群体在空间和心理上的距离,甚至会引发阶层间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因此,政府需要运用行政的力量对城市空间分异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控,使其在满足土地利用效率的同时保证不同阶层在空间分配过程中的相对公平。
通过对国内城市空间结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1)城市空间的研究对象不断拓展。从一开始的针对广州、上海这些大城市的研究逐渐扩展到国内各类城市,从大城市到中等城市甚至一些小城市。
(2)研究程度不断深入。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开始对中国城市进行城市空间研究时,因为数据的缺乏和方法上的局限,通常都是采用因子生态分析法对单个城市在某一时点上的空间结构进行研究,这种研究虽然对理解某个城市的空间结构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研究结论的解释力。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调查技术与调查手段的改进,政府和学术界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可用于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数据,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几次人口普查数据,许多学者的空间研究都是以此为基础的。另外,还有相当多的学者针对某个或某些城市的空间研究做了针对性的数据收集,这就使得空间研究不光具有宏观层面的数据,而且在微观上也有了更为生动和丰富的资料。促使城市空间研究程度不断深入的第二个因素就是统计技术的发展,统计方法进步和统计软件的开发应用使得复杂数据处理更为容易。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城市空间研究出现两个变化:一是针对同一城市不同历史时期城市空间结构的比较成为可能,如许学强在1989年和1995年对广州城市空间结构的比较;二是可以将同一时期的不同城市空间结构进行比较,如王桂新对上海与东京的对比研究。相信以后这方面的研究会更多。
(3)研究立场从价值无涉到人文关怀。一开始的城市空间研究主要集中于地理学领域,研究大都是通过因子分析客观描述城市空间结构布局;后来随着地理学研究对社会因素的关注和社会学领域对城市空间研究的介入,城市空间研究开始关注城市中的人。一开始只是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增加了个体或家庭的自我选择作用的影响;后来相当一部分学者将目光投向城市中的某些特定群体在空间中所处的区位,对他们在城市空间分配过程中所遭受的社会排斥或社会剥夺进行研究,如专门针对农民工或城市低收入群体的空间研究。在这些研究中,充满人文关怀,研究带有强烈的改变现实的目的,希望改变这些弱势群体在空间分配上的不利局面。
(4)研究方法趋于多样化。早期的城市空间研究以地理学领域为主,在方法上以因子生态分析为主,随着其他学科尤其是社会学对空间研究的关注,城市空间研究方法变得多样化,从收集资料到资料处理都呈现出一种多学科方法的综合。社会学中的抽样调查、访谈、参与观察等也被应用到城市空间研究中,这必将大大推动空间研究数据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