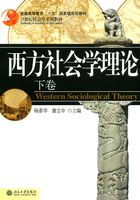
第四节 理性行动理论的影响及评价
科尔曼的《社会理论的基础》发表以后在美国社会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评论界称之为“继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发表以来又一部最重要的社会学理论著作”。在评论中,丹尼尔·贝尔认为,“这本书是当前社会学和社会理论方面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为社会学今后数十年的发展确立了新的研究方向”;默顿指出,“科尔曼教授在分析批判传统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创建了新的社会行动理论。他对法人行动者的分析是具有深远影响的新思维”。
由于这部著作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国际社会学界都受到日益关注和广泛应用。尽管每一种理论都只是从某一视角提供了一种分析和认识问题的工具,但是不同理论的影响力取决于它们在解答各种实质性问题(包括理论问题和经验问题)时是否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美国社会学家(也是理性选择学派的代表人之一)赫克特(M. Hechter)考察了1988年以来发表的社会学论文,发现受理性选择理论影响的经验研究的比例不断增多,这些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展,除了与经济行为有关的劳动力市场、企业组织、分层与流动、管理与决策等传统领域外,还扩展到家庭、宗教、犯罪、种族、性别、社会医学、历史社会学等领域。他认为,这是由于理性选择理论不是单一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如结构功能主义),而是在同一个行为假设(个人理性选择)下向不同层次发展的一组理论群,因此它适用于对各种社会现象的分析;另一原因是理性选择理论具有较强的内在逻辑性,借助这一理论视角有助于澄清原有的各种宏观与微观理论中的逻辑线索 。
。
一、理性行动理论的贡献
科尔曼的理论贡献表现在与其理论目标相联系的三个方面:(1)提供了一种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的社会行动理论。(2)借鉴经济学的理论和其他学科的成果,为建立一种分析性(规范性)的社会学理论打下了基础。(3)开创了法人行动研究的新方向。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长期存在着微观理论与宏观理论脱节的现象,这一方面是由于不同的方法论预设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理论工具和操作方法。例如,布劳在创建了微观的社会交换理论之后,曾设想将其扩展到宏观领域,但他很快放弃了这种努力,并改变了自己的方法论立场,认为宏观社会现象只与结构的突生属性有关,与个人行动(或其合力)无直接关系 。80年代以来,社会学理论领域中出现了新的整合趋势,亚历山大、瑞泽等人提出了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理论框架
。80年代以来,社会学理论领域中出现了新的整合趋势,亚历山大、瑞泽等人提出了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理论框架 。但他们都是在元理论和方法论层次进行综合。与此不同,科尔曼的理论则进入到经验分析的层次,他对社会行动的概念化和操作化使微观行动与宏观结构的逻辑关系能够得到检验(证实或证伪),使宏观现象能够在基础层次上得到解释,从而使韦伯所倡导的“以”(理解)个人有目的行动为基础的解释社会学得到丰富和发展。
。但他们都是在元理论和方法论层次进行综合。与此不同,科尔曼的理论则进入到经验分析的层次,他对社会行动的概念化和操作化使微观行动与宏观结构的逻辑关系能够得到检验(证实或证伪),使宏观现象能够在基础层次上得到解释,从而使韦伯所倡导的“以”(理解)个人有目的行动为基础的解释社会学得到丰富和发展。
从理论形式上看,理性行动理论借鉴了经济学的均衡分析和理性选择模型,但它不是简单地套用这一模型,而是将其扩展到社会行动领域,并结合其他学科的成果,以解答社会科学领域中共同的前沿课题。社会科学各学科都要研究微观行动与宏观结构(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但各学科的理论视角有所不同。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模型因其简捷性而在实证分析和解释能力这两方面优于其他学科,但在现实性和丰富性等方面则有所不足。为了扩展其解释能力,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模型经历了从局部均衡分析到一般均衡分析、再到90年代的博弈均衡分析的发展 。在博弈均衡分析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已不仅仅是个人的利益偏好和资源分布(局部均衡分析的要素),也不仅仅是补充了社会选择与决策、组织与制度、法规或产权、交易费用等(一般均衡分析和新制度经济学的要素),而且还要考虑行动者的知识结构,即由主体间性形成的共享知识或道德共识,由此而涉及众多的非经济因素,如规范、习俗、意识形态、权威、传统、文化等等。这些因素以往属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人类学关注的领域,因此经济学与其他学科在上述领域中产生了交汇,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理论形式来解答共同的前沿课题。科尔曼对规范性行动、权威性行动和法人行动的分析就是从社会学角度提供的具有独创性的成果。不仅如此,科尔曼在建立分析性的理论框架和数学模型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这些努力有助于提高社会学分析的精确性和解释能力。
。在博弈均衡分析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已不仅仅是个人的利益偏好和资源分布(局部均衡分析的要素),也不仅仅是补充了社会选择与决策、组织与制度、法规或产权、交易费用等(一般均衡分析和新制度经济学的要素),而且还要考虑行动者的知识结构,即由主体间性形成的共享知识或道德共识,由此而涉及众多的非经济因素,如规范、习俗、意识形态、权威、传统、文化等等。这些因素以往属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人类学关注的领域,因此经济学与其他学科在上述领域中产生了交汇,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理论形式来解答共同的前沿课题。科尔曼对规范性行动、权威性行动和法人行动的分析就是从社会学角度提供的具有独创性的成果。不仅如此,科尔曼在建立分析性的理论框架和数学模型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这些努力有助于提高社会学分析的精确性和解释能力。
科尔曼对社会行动理论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他对法人行动的分析上,尽管他大量借鉴了社会学的交换理论、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法学的代理人理论以及有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但是将这些成果组织在一个理论框架中,并以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来综合和发展对各种形式的社会行动(特别是法人行动)的认识,则是科尔曼的理论贡献。例如,他对法人和法规(包括制度、政策)形成的分析、关于法人权利的行使与分配(包括对代理人的监督)等问题的讨论,以及对法人组织方式的研究等等,都是当前理论界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课题,他的著作则为这些课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新社会科学与重建社会
如果按哈贝马斯的知识旨趣分类,科尔曼的理论旨趣主要在实证分析知识上,但他对法人行动的研究则既是分析性也是批判反思性的,如同韦伯对科层组织的研究。他认识到,社会科学的功能不仅仅是认识社会,而且也是为了重建社会。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的原始基础(家庭和社区)受到严重侵蚀,法人组织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由于这种“人工创立”的社会组织产生了许多社会弊病,因此迫切需要改造与重建。要重建社会就需要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科尔曼认为,以往的社会科学理论难以担负这一重任,“迄今为止,大多数社会理论家仅仅描述和解释上述社会变迁,重建社会所需要的理论基础尚未建立,因此,社会学家或从事于揭露现实弊端的对理论建设毫无价值的肤浅研究,或背离科学规律,服从意识形态的需要”。只有新社会科学理论才能指导新社会基础的创立,这种理论必须具有目的性和科学性。这是由于“创建社会组织不仅需要有关系统活动的知识,而且需要了解系统组成部分的活动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理论还必须假设个人理性行动的结合能够影响系统行动。因此,新社会科学理论的基础必然是理性行动理论 。
。
科尔曼对现代社会和大规模法人组织的批判与反思也许不如哈贝马斯和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那样深刻,但他所指出的“社会资本的流失”与后者所称的“现代性危机”都概括了共同的社会现象,即现代社会中“道德共识”或“共享的知识结构”的危机(或解体)。作为实证理论家,科尔曼并不停留在对社会的批判上,他还运用自己的理性行动理论从反思社会学的角度对理论家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他要解答的问题是:社会研究者是谁的代理人?他们提出的重建社会(或解构社会)的理论代表了谁的利益?社会理论是如何对社会现实产生影响的?
通过经验分析,他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1)尽管在现代的政策研究和应用研究中,研究者主要是一些大规模法人组织(如国家、政府部门、公司、工会)的代理人,但他们的研究结论可以反映委托人和社会的共同利益,即研究者在指导委托人如何在社会系统中更好地实现自我利益的同时,又不使社会利益受到损失,如同律师依法辩护一样。另一方面,研究者利用学科研究的独立性可以部分地摆脱委托人的支配。(2)在学科理论研究中,研究者主要是社会的代理人,这是由于理论研究不直接涉及行动领域,且研究经费主要来源于社会(纳税人或为公益捐款的基金会)。但这并不排除研究者具有个人的利益和价值偏好,这也是各种意识形态理论的产生原因。(3)新社会科学是由应用研究和理论研究这两个部分所组成的,理论部分对社会现实的影响与力学在改造物质环境时所起的作用一样。(4)新的理论应当超越各学科的传统界限,而且应当是客观的、科学的社会理论,而不是主观的、肤浅的意识形态理论。科尔曼指出,社会理论家(包括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和法学家)应当认识到,创造新社会科学既不是一种个人消遣,也不是个人主观偏好,“而是为创造一种具有生命力的社会结构提供基础,因为人们长期以来赖以生存的原始性结构已经消失” 。
。
上述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分析从两个方面发展了社会学理论:一是在科学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方面,科尔曼通过将社会研究者置于现代法人组织的系统中来分析科学研究作为一种系统行动是如何影响社会系统的,以及社会研究者作为法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代理人是如何提供一种公共物品(客观知识)的。另一方面,科尔曼从社会批判理论的角度提出了重建社会的任务,这种批判是建立在对现代法人组织的客观分析之上的。但他指出,重建社会的方案是由社会系统中的所有行动者通过集体决策制订的,而不是由理论家制订的。社会理论家不能充当政策顾问或哲学先知的角色。社会系统“需要社会理论以指导拥有法定权利控制社会政策的人,使其行使权利时以理论知识为基础。如果设想社会系统依赖于存在社会之外的顾问或哲学先知,那它的发展方向将如柏拉图或孔德所预料的,倒退至社会组织的原始形式” 。
。
三、理性行动理论的局限与潜力
科尔曼的理性行动理论发表以来也受到了许多来自社会 学界和经济学界的批评,社会学家的批评主要是:(1)这种理论的经济学色彩太浓,且忽视了许多重要的非经济因素。(2)关于人的理性选择的假设是不现实的,因为人们的许多行动不是理性的或可选择的,而是情感性、习惯性和强制性的。经济学家的批评则认为其理论模型不简捷、概念界定不明确、数学推导不严谨,而且包含了过多的非个人选择因素(如规范、结构等)。这些批评有些是恰当的,有些是出于误解。赫克特指出,许多对理性选择假设的批评是对个人理性这一概念的误解,理性选择理论只是假设个人的行动具有目的性,这种目的(或价值取向)不一定是经济目的或自私自利的,它也可以包括利他主义、社会公平、爱国主义等价值观。另一方面,理性选择理论是关注众多个人的理性行动的社会后果,而不是某一个人的理性(或非理性)选择的结果。
学界和经济学界的批评,社会学家的批评主要是:(1)这种理论的经济学色彩太浓,且忽视了许多重要的非经济因素。(2)关于人的理性选择的假设是不现实的,因为人们的许多行动不是理性的或可选择的,而是情感性、习惯性和强制性的。经济学家的批评则认为其理论模型不简捷、概念界定不明确、数学推导不严谨,而且包含了过多的非个人选择因素(如规范、结构等)。这些批评有些是恰当的,有些是出于误解。赫克特指出,许多对理性选择假设的批评是对个人理性这一概念的误解,理性选择理论只是假设个人的行动具有目的性,这种目的(或价值取向)不一定是经济目的或自私自利的,它也可以包括利他主义、社会公平、爱国主义等价值观。另一方面,理性选择理论是关注众多个人的理性行动的社会后果,而不是某一个人的理性(或非理性)选择的结果。
任何理论都有其局限性,但对不同的理论形式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在社会学理论中,科尔曼的理论不是以哲学思辨见长,也不是以广博的历史阐释或细致的现象学描述著称,而是在实证分析和解释能力方面具有优势和潜力。对于实证性理论,通常的评价标准是理论解释的有效性、内在逻辑的一致性、理论模型的简捷性和普适性(包括与其他理论的相容性)。在这些方面,理性行动理论的局限或不足之处主要是:
(1)缺乏与其他社会学理论的对话。在科尔曼的著作中,他的理论观点与以往社会学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是不清晰的,即使是在与其理论主题有密切联系的领域中(如社会交换、规范的形成、自我的内部结构等),他也没有讨论以往社会学理论(如霍曼斯、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米德的自我理论和布鲁默的符号互动论)的贡献与不足。这就削弱了理性行动理论与其他社会学理论的相容性,从而使其理论解释的有效性和普适性受到怀疑。
(2)某些基本概念的界定和操作方法还不完善,如利益和价值。尽管为克服测量“利益”的困难,科尔曼区分了客体自我和行动自我的利益,但是对后者的测量仍是像经济学那样对财富的计量(经济学假定财富是可替换物品,由此可间接衡量其他需求或偏好),这就使“效益最大化”假设转变为“财富最大化”假设,使其理论带有经济还原论的色彩。另一方面,理性行动理论是以个人的利益偏好和结构的限制这两个并列的决定因素来解释社会行动及其后果的,但是由于个人利益难以测量,因此许多经验研究都是以社会结构因素进行解释,这就使理性行动理论与主流社会学理论(如结构理论和网络理论)在经验研究中没有什么区别 。
。
(3)数学模型的不完善。由于在社会学中数学模型的应用还不普及,大多数社会学家还缺乏数学方面的训练,因此对数学模型的经验检验和理论修正还远不如经济学那样完善,这就使理性行动理论的应用受到限制。有人指出,理性选择理论有两种模型:纯(数学)模型和经验模型(thin modal and thick modal)。纯模型不考虑个体行动的具体意向,而只考虑价值偏好的一般形式和行动的基本方式。这种模型可适用于各种行动,它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却缺乏实质内容,它类似于物理学和生物学的一般理论模型 。经验模型包含丰富的经验内容,但它有很多限制条件,它只适用于某一类行动,因此很难发展成一个统一的形式化或数学化的模型,而只能采用命题或分类的形式。经验模型以韦伯的理论为代表。韦伯认为,人的理性行动有各种类型(如对财富、权力和声望的追求),每一类型有其特定的行为方式。也许在现阶段,当需要在理论模型的简捷性和形式化与模型的丰富性和适用性之间进行选择时,社会学更偏向于后者。目前许多以理性行动理论为指导的经验研究都是采用经验模型。
。经验模型包含丰富的经验内容,但它有很多限制条件,它只适用于某一类行动,因此很难发展成一个统一的形式化或数学化的模型,而只能采用命题或分类的形式。经验模型以韦伯的理论为代表。韦伯认为,人的理性行动有各种类型(如对财富、权力和声望的追求),每一类型有其特定的行为方式。也许在现阶段,当需要在理论模型的简捷性和形式化与模型的丰富性和适用性之间进行选择时,社会学更偏向于后者。目前许多以理性行动理论为指导的经验研究都是采用经验模型。
尽管有上述局限性,但理性行动理论在未来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中仍具有很大潜力,这不仅是由于它在各学科交汇的共同领域中处于前沿位置,也不仅是由于它的内在逻辑性和解释能力较强因而可广泛应用于社会学的各个领域,而且还由于它的理论框架可容纳当前各种社会学理论的洞见。例如,在综合微观与宏观、行动者与结构的各种理论中,埃默森的交换网络理论、柯林斯的微观结构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以及新经济社会学理论都与理性行动理论有一定的结合点。科尔曼关于法人行动和重建社会的观点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和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分析也有许多相通之处。当然,不同的理论形式有不同的功能。在分工发达的现代社会,没有哪一种理论可以兼备各种功能或独占垄断地位。各种知识具有互补性,各个学科具有互补性,各种理论也具有互补性。不同理论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可以相互启迪,并通过沟通而达到一定的共识。可以肯定,理性行动理论在沟通和启迪各种理论洞见方面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Coleman, J.S., The 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Sociology.Free Press,1964.
Coleman, J.S.,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U.S.Government,1966.
Coleman, J.S., Policy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General Learning Press,1972.
Coleman, J.S.,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Society.Basic Books,1974.
Coleman, J.S., Individual Interests and Collective Ac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Coleman, J.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JS.V.94:95—120.
Coleman, J.S., Free Riders and Zealots: the Role of Social Networks.Sociological Theory.V. 6:52—57.
Coleman, J.S., Foundation of Social Theory.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G.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宇、陈琪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T.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吴经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汪丁丁:《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Blau, Peter“Microprocess and Macrostructure”, In K.Cook(ed.)Social Exchange Theory. Sage,1987,83—100.
Ferejohn, J.A., “Rationality and interpretation”, In K R.Monroe(ed.),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Politics: A Critical Reassessment of the Theory of Rational Action.Harper Collins, 1991,279—305.
Goldthorpe, J.H.,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Large-scale Data and Rational Action Theory”, Eur.Sociol.Rev.12,1996,109—126.
Hechter M., Sociological Rational Choice Theory.Am.Annual Reviews.Sociology.23:215—231.
Ritzer, G., Sociological Theory, McGraw-Hill, Inc,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