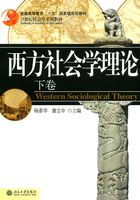
第三节 新功能主义与社会行动理论
帕森斯以前的功能主义理论都没有包含明确、系统的行动理论。把“行动”及关于行动的研究引入社会学领域,主要是理解社会学的开山祖师韦伯的功绩。而在韦伯的基础上,把“行动”及关于行动的研究引入实证主义的功能主义理论当中,则是帕森斯的功绩。帕森斯试图通过这一做法,将理解社会学对微观个人行动的强调与实证的功能主义社会学对宏观社会结构的强调结合起来,以克服传统功能主义只重宏观不重微观,只重社会不重个人的缺陷。就行动理论本身而言,帕森斯也试图通过多方面的综合来建立起一个更一般的行动理论框架,提出行动是一个包括手段、目的、规范、条件与主观努力等多种要素在内的具有多方面属性的动作过程 ,单纯把其中的某一类要素或属性抽出来对行动进行描述是不合适的。然而,尽管帕森斯试图以微观行动的理论来作为他整个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也尽管他的行动理论框架本来具有较大的包容性,但在其总的理论偏好与发展取向上,帕森斯却倾向于强调行动受规范制约的一面,偏好于用“规范性行动”或“志愿性行动”作为描述人类社会行动的基本模式。由于这种偏好,行动者为实现目标所做的各种主观努力这个对行动过程具有重要意义的方面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行动者成了一个其内部主观状态不明的“黑箱”
,单纯把其中的某一类要素或属性抽出来对行动进行描述是不合适的。然而,尽管帕森斯试图以微观行动的理论来作为他整个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也尽管他的行动理论框架本来具有较大的包容性,但在其总的理论偏好与发展取向上,帕森斯却倾向于强调行动受规范制约的一面,偏好于用“规范性行动”或“志愿性行动”作为描述人类社会行动的基本模式。由于这种偏好,行动者为实现目标所做的各种主观努力这个对行动过程具有重要意义的方面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行动者成了一个其内部主观状态不明的“黑箱” 。在帕森斯中期结构功能主义色彩最浓厚的著作中,这种内部努力状态不明的“规范性行动”过程,逻辑地被演绎成为个体通过社会化在社会规范与社会期望指引下的简单的角色执行过程。这种“过度社会化”的关于人及人的行动的形象,正是帕森斯理论受到强烈批评的一个方面。符号互动论、本土方法论、社会现象学、社会交换论等“微观社会学”理论正是针对帕森斯理论的这个基本缺陷而兴盛发达起来的,对行动者内部努力过程(理解意义、确立规则、计算得失)的探究正是各种微观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目标
。在帕森斯中期结构功能主义色彩最浓厚的著作中,这种内部努力状态不明的“规范性行动”过程,逻辑地被演绎成为个体通过社会化在社会规范与社会期望指引下的简单的角色执行过程。这种“过度社会化”的关于人及人的行动的形象,正是帕森斯理论受到强烈批评的一个方面。符号互动论、本土方法论、社会现象学、社会交换论等“微观社会学”理论正是针对帕森斯理论的这个基本缺陷而兴盛发达起来的,对行动者内部努力过程(理解意义、确立规则、计算得失)的探究正是各种微观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目标 。为了消除帕森斯理论的上述重要缺陷,许多新功能主义者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亚历山大则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为了消除帕森斯理论的上述重要缺陷,许多新功能主义者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亚历山大则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亚历山大在吸取符号互动论、本土方法论、社会现象学、社会交换论等微观社会学理论合理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更具综合性的微观行动理论模式。亚历山大提出行动总是沿着两个基本的维度进行。这两个基本维度就是解释(或理解,interpretation)与谋划(strategization)。行动不能像帕森斯想象的那样理解为高度规范化或机械化的过程。行动,正如符号互动论/社会现象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首先是理解性的;但行动并非只是理解性的,它同时也如交换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是实践的与功利性的。解释与谋划,是任何行动过程在任何时间点上都包含着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它们只能在理论上作为两个分析的要素而被区分开来,因此,绝不能把它们设想为两类不同的行动或同一行动过程的两个不同的阶段。“解释”又包括两种不同的过程:类型化(typification)与发明(invention)。对于类型化过程,舒茨的社会现象学与加芬克尔的“本土方法论”都做了详细的研究。这些研究表明,“类型化”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解释事物的基本方式。而人们之所以常常采用类型化方式来解释世界,是“因为他们充分期望每个新的印象都将是他们已经发展起来的对世界所作的理解的一个类型。这种类型化方式不仅仅是在传统的总体水平上起作用。即使当我们遭遇某些新的和令人激动的事物时,我们也期望这种新的特性和令人激动的特性是可以被理解的,它将被我们在我们已拥有的参考词汇范围之内所认识。我们无法将自己从我们的分类系统中剥离出来” 。就以“类型化”作为认知的一种基本方式而言,最现代的心智与最古老的心智之间并无重大区别。所谓的“社会化”,就是学习掌握各种类型:“每个集体的成员都必须学会给每一种可能的情境作出解释,取出名称,找出它们的类型词汇”
。就以“类型化”作为认知的一种基本方式而言,最现代的心智与最古老的心智之间并无重大区别。所谓的“社会化”,就是学习掌握各种类型:“每个集体的成员都必须学会给每一种可能的情境作出解释,取出名称,找出它们的类型词汇” 。然而,“类型化”并不是人们理解现实的唯一模式。尽管我们总是力图将遇到的每一事物都概括到我们已有的分类框架中去,但真实的事物总是每每不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用现有的分类系统无法涵盖的新现象、新性质,这时我们就需要创造一些新的范畴或类型来表示它们。这个过程就叫“发明”。归类与发明构成了解释过程的两个基本方面。我们就是通过这两种方式来达成对现实的理解。与解释过程并列,“谋划”则构成行动过程的另一个方面。“行动不仅仅是理解世界,它也改变和作用于这个世界。行动者寻求通过马克思所说的实践(praxis)来贯彻他们的意图,由此他们必须协同他人或他物一道行动,或者通过行动来抵制他人或其他事物。这种实践行动肯定只能发生于确定的理解范围之内,但在对事物清楚理解的基础上它引入了策略性的考虑:使成本最小化和使报酬最大化”
。然而,“类型化”并不是人们理解现实的唯一模式。尽管我们总是力图将遇到的每一事物都概括到我们已有的分类框架中去,但真实的事物总是每每不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用现有的分类系统无法涵盖的新现象、新性质,这时我们就需要创造一些新的范畴或类型来表示它们。这个过程就叫“发明”。归类与发明构成了解释过程的两个基本方面。我们就是通过这两种方式来达成对现实的理解。与解释过程并列,“谋划”则构成行动过程的另一个方面。“行动不仅仅是理解世界,它也改变和作用于这个世界。行动者寻求通过马克思所说的实践(praxis)来贯彻他们的意图,由此他们必须协同他人或他物一道行动,或者通过行动来抵制他人或其他事物。这种实践行动肯定只能发生于确定的理解范围之内,但在对事物清楚理解的基础上它引入了策略性的考虑:使成本最小化和使报酬最大化” 。因为实现我们的意图需要时间和能量,而时间与能量是有限的,因此它们必须根据最小费用原则来加以配置。“谋划”或“策略计划”由此便成为行动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亚历山大认为,行动中的这两大方面是相互交错又相互影响的。“谋划”须以“解释”作为基础,而我们的策略计划过程也影响了我们对世界的解释或理解过程。我们并不试图去“理解”进入我们意识中的每一种现象。我们对时间、能量、可能获得的知识、目标实现难易程度的考虑,显然会影响我们的认知过程。我们多半会选择在未来的偶然环境中估计最可能、最容易达成的目标来作为我们的优先认知对象。通过这种集符号互动论、解释学/现象学及交换论于一体的对行动理论的“解释学的重建”,亚历山大认为他揭示了在帕森斯那里处于“黑箱”状态的行动的内部过程,描述了行动所具有的偶然性与创造性本质。按照这种模式,行动不再是一种木偶式的“规范性行动”,而是一种积极的、能动的理性行动;它不再是简单地遵循文化与社会环境的压力,而是积极地去寻求改变它所遭遇的环境。当然,作为一个功能主义者,亚历山大没有忘记划清他与“主观社会学”的界限。他在将行动偶然性与创造性的思想引入功能主义的同时,也重申了功能主义关于环境对行动具有强制性的思想,指出偶然行动的思想也就蕴涵了“它所发生于其中的环境的非偶然性”; “理解偶然性就是理解它必须趋向于强制,理解偶然性的维度就是理解它在这样一种强制性环境中的变化”; “如果我正确地概括了行动,那些环境将被视为它的产物;如果我正确地概括了环境,行动将被视为它们的结果”
。因为实现我们的意图需要时间和能量,而时间与能量是有限的,因此它们必须根据最小费用原则来加以配置。“谋划”或“策略计划”由此便成为行动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亚历山大认为,行动中的这两大方面是相互交错又相互影响的。“谋划”须以“解释”作为基础,而我们的策略计划过程也影响了我们对世界的解释或理解过程。我们并不试图去“理解”进入我们意识中的每一种现象。我们对时间、能量、可能获得的知识、目标实现难易程度的考虑,显然会影响我们的认知过程。我们多半会选择在未来的偶然环境中估计最可能、最容易达成的目标来作为我们的优先认知对象。通过这种集符号互动论、解释学/现象学及交换论于一体的对行动理论的“解释学的重建”,亚历山大认为他揭示了在帕森斯那里处于“黑箱”状态的行动的内部过程,描述了行动所具有的偶然性与创造性本质。按照这种模式,行动不再是一种木偶式的“规范性行动”,而是一种积极的、能动的理性行动;它不再是简单地遵循文化与社会环境的压力,而是积极地去寻求改变它所遭遇的环境。当然,作为一个功能主义者,亚历山大没有忘记划清他与“主观社会学”的界限。他在将行动偶然性与创造性的思想引入功能主义的同时,也重申了功能主义关于环境对行动具有强制性的思想,指出偶然行动的思想也就蕴涵了“它所发生于其中的环境的非偶然性”; “理解偶然性就是理解它必须趋向于强制,理解偶然性的维度就是理解它在这样一种强制性环境中的变化”; “如果我正确地概括了行动,那些环境将被视为它的产物;如果我正确地概括了环境,行动将被视为它们的结果” 。既坚持环境对行动的强制性效果,又强调行动的偶然性与创造性,强调行动对环境的变革作用,这就是亚历山大为功能主义提供的一种新的“行动”模式。
。既坚持环境对行动的强制性效果,又强调行动的偶然性与创造性,强调行动对环境的变革作用,这就是亚历山大为功能主义提供的一种新的“行动”模式。
除了亚历山大以外,还有一些新功能主义理论家,如芒奇等也对帕森斯的行动理论作了一些新的论述 。其基本特征与亚历山大类似,也是试图改变帕森斯理论中“规范性行动”模式的被动形象,将行动的偶然性、创造性特征引入到功能主义的行动模式中去。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其基本特征与亚历山大类似,也是试图改变帕森斯理论中“规范性行动”模式的被动形象,将行动的偶然性、创造性特征引入到功能主义的行动模式中去。限于篇幅,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