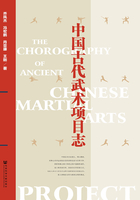
第二节 奴隶社会时期的武术
随着私有制的产生,社会上出现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原始社会开始解体。大禹的儿子启,改变了过去禅让方式,确定首领的做法,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的奴隶制国家夏(约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夏朝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从氏族社会进入王位世袭制社会的标志。从公元前21世纪夏朝建立开始,到公元前476年春秋时期结束,是中国的奴隶社会时期。奴隶社会大致经历了夏、商、西周及春秋几个历史时期。在中国奴隶社会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度过了原始社会时期的萌芽状态之后,古代武术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人体活动方式逐渐开始形成。
一 军事战争与兵械演变
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后,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军事训练,战争是武术发展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人体活动方式的主要动力。战争形式的变化发展促进了兵械的演变。车战是从商代后期到春秋时期的主要作战形式。当时军队中的兵种主要是由车兵和步兵组成,车兵是作战的主力。每一个战车上配备三名士兵,他们站成“品”字形。四马拉一车为一乘。千乘之国,指拥有1000辆战车的国家,即诸侯国。春秋时代,战争频仍,所以国家的强弱都用车辆的数目来衡量。春秋时期礼制是这样的:天子六军,每军千乘,共六千乘;大国三军;中国两军;小国一军。所以说,在孔子时代,千乘之国已经不是大国。每个战车中坐在中间的战士负责驾车,左侧的战士是射手,负责远距离射杀敌人,右侧的战士拿着长矛,负责近距离搏杀。由于战车体积非常庞大而且笨重,所以车战中武士们要用相当长度的兵器才能击刺到对方。战车上一般配置的五种兵器——戈、殳、戟、酋矛、夷矛都有令人吃惊的长度,其中酋矛20尺(约4.3米),夷矛24尺(约5.25米)(《周礼·考工记》)。正是出于这种车战的需要,那个时期武艺的训练主要是力量训练。另外,车战还大大促进了箭术的发展。与长而笨重的矛戟相比,弓箭在车战中的作用变得非常突出。习射在夏朝已成为学校的一项教育内容。至周代,“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在周代的社会和政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而“六艺”中的“礼、乐、射、御”都与武术有很大的关联。后羿,又称“夷羿”,相传是夏朝时东夷族有穷氏的首领,有穷氏这个部落十分擅长射箭技术,后羿的射技高超。当时夏王姒启的儿子姒太康不打理政事,沉迷于田猎游乐之中,后羿趁机发难,驱逐了太康。太康死后,后羿立太康之弟姒仲康为夏王,后羿于是掌握了实际的统治权。仲康死后,他的儿子相继位,后羿又把相给驱逐了,自己当了国王,这就是史书上称作太康失国和后羿代夏的故事。后羿凭借高超的射技而“代夏”,可见习射在夏代人们心中的地位。殷商时期的射礼,在经过夏代的长时间的发展之后,射礼仪式已初具规模。周朝的射礼与殷商时期的射礼相比,在礼仪程序、种类以及规模上都有很大的发展,后又经儒家的制礼作乐,达到了射礼最为鼎盛的时代。《礼记·射义》载:“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男子之所有事也。”用射天地四方来表明男子的人生志向。周朝射礼日趋大众化和平民化,逐渐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到了春秋时期,冶铁技术得到了发展,春秋末期,位于南方的吴国和越国已经可以制造铁剑了。当时有两个著名的制剑专家,一个叫欧冶子,一个叫干将,他们曾经为楚王造剑。他们选用茨山的矿石,冶炼成铁,锻制成三把铁剑,分别取名为龙渊、泰阿和工布(《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宝剑》)。奴隶社会的兵械大体上可以分为远射兵器、长兵器和近身搏斗用的短兵器等。1953年,在河南省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文物有铜矛头、铜勾、铜戚、铜刀、铜斧、铜镞等。此时的兵器不仅种类大大增加,而且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改善。铁兵器有刀、枪、剑、戟、矛、匕首、箭镞、铠甲、兜鍪(古代战士戴的头盔)等。
二 古代武舞与角力手搏
古代武舞发展到奴隶社会后,其活动形式和功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武舞大致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象舞”,文献中很早就有关于“象舞”的记载。《毛诗序》云:“《维清》,奏象舞也。”《毛诗正义》注曰:“文王时有击刺之法,武王作乐,象而为舞。”汉代的郑玄云:“《象》,周武王伐纣之乐也,以管播其声,又为之舞。” 可以看出,所谓“象舞”,就是一种模仿“击刺之法”这种军事实战之技的人体艺术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武舞已经具有一定的体育锻炼功能。第二种是“万舞”。先是武舞,舞者手拿兵器;后是文舞,舞者手拿鸟羽和乐器。“简兮简兮,方将万舞。”《毛传》云:“以干羽为万舞,用之宗庙山川”,“干舞有干与戚,羽舞有羽与旄,曰干曰羽者举一器以立言也。干舞,武舞;羽舞,文舞。曰万者又兼二舞以为名也”(《毛诗传疏》)。《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先君以是舞也,习戎备也”。显然,在当时万舞是一种军事训练手段。第三种是“大武舞”,又名武凤夜,是为武王伐纣成功而作,共分成六段,展现了伐纣灭商的全部过程。“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礼记·祭统》),“武王伐纣,至于商郊,士卒皆欢乐,歌以待旦,因称之武凤夜”(《周礼·大司农》),大武舞在后来也很流行,曾被西周以后的学校列为必学的纪念历代“先王”的多种“大舞”之一。除上述几种外,还出现了商乐《大汉》、武王伐纣时的“巴渝舞”“干戈舞”等。可以看出武和舞的结合以及武舞中对器械的应用为后来武术套路的出现打下了基础,奴隶社会时期的中国古代武术,已受到“武”与“舞”两种文化的合力滋养。
可以看出,所谓“象舞”,就是一种模仿“击刺之法”这种军事实战之技的人体艺术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武舞已经具有一定的体育锻炼功能。第二种是“万舞”。先是武舞,舞者手拿兵器;后是文舞,舞者手拿鸟羽和乐器。“简兮简兮,方将万舞。”《毛传》云:“以干羽为万舞,用之宗庙山川”,“干舞有干与戚,羽舞有羽与旄,曰干曰羽者举一器以立言也。干舞,武舞;羽舞,文舞。曰万者又兼二舞以为名也”(《毛诗传疏》)。《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先君以是舞也,习戎备也”。显然,在当时万舞是一种军事训练手段。第三种是“大武舞”,又名武凤夜,是为武王伐纣成功而作,共分成六段,展现了伐纣灭商的全部过程。“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礼记·祭统》),“武王伐纣,至于商郊,士卒皆欢乐,歌以待旦,因称之武凤夜”(《周礼·大司农》),大武舞在后来也很流行,曾被西周以后的学校列为必学的纪念历代“先王”的多种“大舞”之一。除上述几种外,还出现了商乐《大汉》、武王伐纣时的“巴渝舞”“干戈舞”等。可以看出武和舞的结合以及武舞中对器械的应用为后来武术套路的出现打下了基础,奴隶社会时期的中国古代武术,已受到“武”与“舞”两种文化的合力滋养。
这一时期,还有一种军事训练手段叫作角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人类最原始、最早的一项体育活动。《礼记》记载:“(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在《王兵篇》和《管子》等书中也提到“春秋角武,以练精材”。春秋之后,这种角力“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示)”,具有很强的娱乐观赏成分,到了秦代就演变成角抵了。除角力外,另一种体现为徒手搏斗技能的“手搏”活动也在逐渐形成。“公子友谓莒拏曰:‘吾二人不相说,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榖梁传·僖公元年》)鲁公子友与莒“相搏”,“搏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脑,是以惧”(《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且以巧斗力者,始乎阳,常卒乎阴,大至则多奇巧”(《庄子·人间世》),等等。手搏这种人体活动艺术源于狩猎和军事活动,但到了春秋时期已经成为一项相对成熟的搏击技能,并可以通过比赛来衡量搏击者的水平。
三 民间习武与武术论著
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的统治权力和威信逐渐减弱,各个诸侯国为了自身利益,相互攻伐,一个诸侯争霸、豪杰辈出的时代来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各个诸侯国都很崇尚武功,军事武艺逐渐在老百姓中普及开来。各个诸侯国采取各种措施对农民进行军事训练,农民平时耕田种地,战时编成军队,上阵打仗,一年之中“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国语·周语》)。当时不仅满腹经纶的文士可以得到统治者的重视而进入仕途,武艺高强的勇士也能得到国家的重用。用武功博取功名,建功立业,改变自身地位,这样,极大地促进了民间的习武之风,使武术活动在民间得到广泛开展。曾举起“尊王攘夷”大旗的春秋霸主齐桓公就非常重视选拔勇敢的武士,让他们为朝廷服务。《管子·小匡》中齐桓公对一位地方官吏说:“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才,其罪五。”齐国习武自国君到士民蔚然成风。“庄公陈武夫,尚勇力”(《晏子春秋·外篇》),“士民贵武勇而贱得利”(《管子·五辅》),“齐愍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汉书·刑法志》),等等,都体现了齐国人民的尚武风气,因此,后来齐国人以精通格斗技术而天下闻名(《荀子·议兵》)。吴地人“尚勇轻死”,荆楚多有“奇才剑客”。“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庄子·说剑》),“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疮)瘢”(《后汉书·马援传》)等。这一时期有很多以武技谋生的剑客,佩剑、斗剑成为流行风尚,这说明当时社会中存在浓厚的习剑风气。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曾请一位民间剑术家越女给他的士兵们传授剑术。“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越女论剑》)这是关于越女剑技的描写,剑术看起来似乎浅显而容易,但是其中的道理深邃而精妙,有门户的开合、阴阳的变化。用剑进行搏斗时,精神要充足,外表要沉稳,看上去安详平和,像一个文静的少女,一经交手才知道凶猛如同恶虎。这样的剑术家可以以一当百,以百当万。此时,剑道发展成为亮点,剑的击刺技术日臻成熟。“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腹也,诈而袭之,与先惊而后击之,一也”(《荀子·议兵》),“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庄子·说剑》),等等,说明当时剑法的完善与高超程度。春秋时期也非常重视武技的传授,开创了我国数千年来民间传授武技之风。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追述其祖先的一支“在赵者,以传剑论显”,就是指民间的私家武技传授者。这个时期,文武分途、侠士兴起。如鲁国的曹沫执匕首强逼齐桓公还侵鲁之地,吴国的专诸藏匕首于鱼腹中刺杀吴王僚等。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与武术有关的理论著作,如《庄子·说剑》《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越女论剑》等。还有一些军事著作,如春秋时期的《孙子兵法》,战国早期的《吴子兵法》、中期的《孙膑兵法》和后期的《尉缭子》。这些兵书不仅讲述了带兵、打仗、布阵这些纯军事方面的问题,还渗透了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军事与哲学融为一体,这对后来中国武术与哲学的结合,形成中国独特的武术体系产生了巨大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