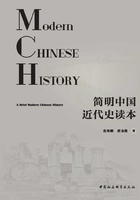

第五节 教案迭出——大规模群众反洋教斗争
近代来华传教士作为“基督教征服世界”的使者,直接参与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外国在华传教事业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宗教事业,而是列强对华侵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教案”既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的产物,也是中国传统礼俗政教与基督教文化冲突的结果。
一些传教士起到了殖民主义者进行侵略扩张的先锋队作用。美国公使田贝证实:这些传教士所搜集的有关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及其他情报,对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外国教会实际上成为侵略者的谍报机关。俄国公使伊格纳提耶夫说: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提供的精确情报,使他得以沿着真实的、正确的道路前进,同中国签订《北京条约》。俄国政府为奖赏东正教士,赐给新占中国领土中的大片土地,规定神职人员由国库支付薪俸。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说:传教士及与传教运动有关系的那些人的努力,对美国的利益非常重要。若没有他们充当译员,公事就无法处理,没有他们的帮助,美国公使在这里就简直无法履行职责。
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与列强签订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允许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且可“租买田地,建造自便”。这样一来,民教相争酿成的案件急剧增多,教案迭出。西方传教士伴着征服者的大炮,仗势欺人,中国民众则把他们当作侵略者的代表来发泄仇恨。民教相争的案件以房地产纠纷为多。传教士进入内地后急于扩展传教事业,往往强买强占民间房屋地皮,引起住民不满与反抗。传教士遂向本国公使馆告状,公使馆向清政府施压,清政府则对百姓施以弹压,使矛盾不断激化。外国教会深入中国内地后,形成一种特殊的社会势力。有洋人撑腰,官府不敢惹,一些地痞流氓也托庇入教,横行滋事。这些都成为教案爆发的导火索。
一些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兴办医院、学校、书局,同时传播了西方一些较为先进的科学文化。虔诚的洋教士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给予了善意的布施。但是这改变不了帝国主义侵略欺侮中国的大时代背景,也就不可能阻遏上述那些矛盾的发生。
《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传教士蜂拥而至,外国教会在中国势力迅速扩张。教堂、教士、教徒的数量显著增长。耶稣教差会1860年有20个,1884年增至30余个;传教士1864年有180余人,1890年达到1296人;传教士的常驻地点,1860年14个,分布在东南沿海六省的通商口岸,1894年达到238处,主要分布在沿海各省和长江流域(湖南例外),山西、陕西、甘肃、四川、广西、河南、贵州、云南等省也都有了耶稣教传教士驻地。耶稣教徒1857年仅有400人,1893年达5.5万人。天主教会1860年9个,1894年达到21个;天主教传教区,1844年10个,1883年增至34个;各教区设有主教,管辖本区的教务;天主教外籍教士1846年有100人,1885年增至488人,东起台湾,西到西藏,北达黑龙江,南至海南岛,都有天主教士的足迹;天主教徒1850年32万人,1890年增至52.5万人。 另据1877年的统计,新教传教士共有473人,差会总堂91个,支堂511个,正式教堂312个,教徒13035人。
另据1877年的统计,新教传教士共有473人,差会总堂91个,支堂511个,正式教堂312个,教徒13035人。 1865年由英国基督教传教士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第一年来华传教士3人,到19世纪末,内地会在中国约有650名传教士,270个传教站,教徒约5000余人,成为基督教在中国活动的最大差会。
1865年由英国基督教传教士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第一年来华传教士3人,到19世纪末,内地会在中国约有650名传教士,270个传教站,教徒约5000余人,成为基督教在中国活动的最大差会。 天主教每个传教区一般设总堂一座,设主教一人。总堂有的建在通都大邑,省、府、县治所,如直隶北境总堂建在北京西什库,山东北境总堂建在济南府。有的建在偏僻的村镇,如湖北西北教区设两个总堂,一个在老河口,另一个在谷城县的茶园沟;湖南南境总堂设在衡州城附近的黄沙湾。俄国东正教的团费由俄国政府提供,它的活动听从政府下达的训令。《北京条约》签订后,俄国东正教陆续在天津、哈尔滨、上海及新疆等地建立起教堂。
天主教每个传教区一般设总堂一座,设主教一人。总堂有的建在通都大邑,省、府、县治所,如直隶北境总堂建在北京西什库,山东北境总堂建在济南府。有的建在偏僻的村镇,如湖北西北教区设两个总堂,一个在老河口,另一个在谷城县的茶园沟;湖南南境总堂设在衡州城附近的黄沙湾。俄国东正教的团费由俄国政府提供,它的活动听从政府下达的训令。《北京条约》签订后,俄国东正教陆续在天津、哈尔滨、上海及新疆等地建立起教堂。
《北京条约》后40年间,中国各地共发生大小教案达400余起,反洋教怒火遍及贵州、云南、湖南、江西、四川、江苏、安徽、河南、河北、山东、福建、台湾等省的城镇乡村,其中影响最大的一起教案发生在天津。
《天津条约》签订后,法国把联军议约总部望海楼改为领事馆,又取得与望海楼毗连的崇禧观的永租权,在领事馆旁建了个大教堂,在城东区开了间仁慈堂。仁慈堂收养小孩,修女有时还给送孩子来的人一点身价钱。于是一些“吃教”的无赖,拐骗幼童去换钱的事时有发生。1870年夏,仁慈堂内收养的小孩因传染病死了不少,埋于河东乱葬岗,被野狗刨出。民众遂怀疑教堂有虐待行为。更有传闻教堂对幼童挖眼剖心的。恰在此时,一个叫武兰珍的人因迷拐幼童被乡民执获送官,审讯中供出同伙还有教民王三。天津知县刘杰审得此供,请示中央驻津的最高官员、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崇厚照会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要他帮助将教民王三送案对质。丰大业敷衍应对。
6月21日,围聚在教堂外的民众与法国领事馆人员发生冲突,向教堂抛掷砖头。丰大业要求崇厚派兵弹压,崇厚派知县刘杰及巡捕2人前往制止。丰大业持枪率秘书西蒙往见崇厚,一进门即怒言相向,开枪示威,将室内什物信手打破,口称“尔怕中国百姓,我不怕尔中国百姓” ,扬长而去。行至路上,遇见自教堂返回的刘杰,丰大业迎面放枪,将刘杰家人高升击伤。愤怒民众当场将丰大业和西蒙殴毙,接着将望海楼教堂、法领事馆、仁慈堂及洋行焚毁,又焚毁英国礼拜堂4处、美国礼拜堂两处。混乱之中殴毙或烧死18名外国人,连同丰大业和西蒙,共20人。遇害的还有中国教民16人。
,扬长而去。行至路上,遇见自教堂返回的刘杰,丰大业迎面放枪,将刘杰家人高升击伤。愤怒民众当场将丰大业和西蒙殴毙,接着将望海楼教堂、法领事馆、仁慈堂及洋行焚毁,又焚毁英国礼拜堂4处、美国礼拜堂两处。混乱之中殴毙或烧死18名外国人,连同丰大业和西蒙,共20人。遇害的还有中国教民16人。
教案发生后,美、英、法、俄、德、比、西七国联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各国军舰逼近天津海河口示威,要求惩凶赔偿。法国海军司令威胁说:不处理此案,定将津郡化为焦土。有人甚至扬言“最低要求是使用武力迫使整个中华帝国开放对外交往,从要求较高的将所有中国官吏一律斩首,推翻现政府,乃至将全国置于外国保护之下” 。清政府极为紧张,急调病假中的曾国藩赶赴天津查办。曾国藩认为“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
。清政府极为紧张,急调病假中的曾国藩赶赴天津查办。曾国藩认为“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 。他虽了解到教案发生的真实因由,却故意把迷拐儿童的情节说成“查无确据”,将天津知府和知县革职充军,判处肇事者20人死刑(缓刑4人), 25人流放,并赔款50万两白银。清政府还派崇厚专程赴法国赔礼道歉。照曾国藩自己的说法,这叫作委曲迁就,消弭衅端。事后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处理教案,“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
。他虽了解到教案发生的真实因由,却故意把迷拐儿童的情节说成“查无确据”,将天津知府和知县革职充军,判处肇事者20人死刑(缓刑4人), 25人流放,并赔款50万两白银。清政府还派崇厚专程赴法国赔礼道歉。照曾国藩自己的说法,这叫作委曲迁就,消弭衅端。事后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处理教案,“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 , “庇护天主教,本乖正理”, “内疚神明,外惭清议”
, “庇护天主教,本乖正理”, “内疚神明,外惭清议” 。清政府中也有人指责曾是“自撤藩篱,泯庶民爱国之心,禁庶民忾敌之志,杀以谢敌”
。清政府中也有人指责曾是“自撤藩篱,泯庶民爱国之心,禁庶民忾敌之志,杀以谢敌” 。他自己也以“名毁津门”而耿耿于怀。
。他自己也以“名毁津门”而耿耿于怀。
中法战争期间,当法军袭击福建水师、炮轰马尾造船厂的消息传出,全国反洋教的浪潮又起,福州、宁德、古田、厦门及毗邻福建的浙江,连续发生毁烧教堂的事件。靠近越南的两广也民情激愤,在广东有40多名传教士被驱逐到香港和澳门,50余所教堂被毁。
19世纪90年代,在四川大足、长江中下游以及直隶东北境朝阳一带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反教风潮,把反教斗争推向新的高峰。1890年9月,大足县当过挖煤苦力的余栋成聚众发动武装暴动,焚毁教堂数处,杀教民10人,发布檄文,声讨外国侵略者“欺侮中华”,号召群众驱逐外国教会势力,斗争坚持到1892年。1891年5月,芜湖万余群众暴动,冲散弹压的清兵,焚烧教士住地,与洋教士短兵搏斗。此后,长江中下游各省几十座城市和乡村,凡有教会势力的地方,都纷纷发生反教骚动。其中湖北广济县武穴千余人攻打教堂;宜昌数千人焚烧法、美教堂。直隶承德府,天主教划为东蒙古教区,主教府设在朝阳县松树嘴子村。1891年朝阳爆发了由金丹道教和在理教发动的武装起事,有众数万人,攻占朝阳、平泉、建昌、赤峰等州县,焚毁天主教堂。1895年成都教案,波及全川,数十处天主教堂、耶稣堂被毁。
教案是近代中国涉及中外关系方面一种特殊矛盾和冲突。《北京条约》签订以后,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国合法传播。由于中外文化信仰不同和建筑教堂用地利益上的纠葛,教民和非教民之间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各级政府秉公处理,这种矛盾不难解决。问题在于传教士往往庇护教民,传教士所在国家政府往往依据不平等条约压迫中国政府各级官员,甚至违法教民也获得“治外法权”的保护,政府各级官员碰到教案难以公正处理,往往担心“有碍大局”,得罪外国。即使有理,屈也在老百姓一方。这样,更大教案的发生就是难以避免的。这是中国社会在外国侵略下向下“沉沦”的表现形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