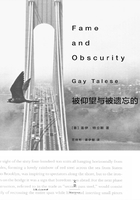
第4章 纽约——一位猎奇者的足迹(3)
但是,尽管纽约市的导游手册和商会都大肆吹捧这个城市,但她却绝不是什么旅游者的好去处。对于多数纽约人来讲,这里工作辛苦,交通拥挤,人满为患。这里生活着许许多多的无名小人物,像公共汽车司机、女清洁工以及偷偷给广告牌涂上猥亵淫秽内容却从不会被抓住的涂鸦者。许多纽约人似乎只有一个名字:女理发师、门童、擦鞋匠等等。一些纽约人一辈子都被人叫错名字,就像住在中央大街警察局对面的“面包吉米”。“面包吉米”的真名叫吉米·曼库索。在他还是个孩子时,坐在街对面的警察常对他喊:“喂,小孩儿,到街角那儿给我们买点儿咖啡和面包。”吉米总是很听话,为他们跑腿效力。久而久之,“面包吉米”或更简单的“嗨!面包”就成了他的称呼。现在吉米已是一位白发老人,有一个名叫珍妮的女儿。但珍妮从未有过自己的名字,人们都叫她“面包珍妮”。
纽约是吉姆·托培的城市,从1928年起他就为时报广场周围的广告牌播放新闻头条,多少年来从没由于自己失误烧过一个灯泡;它也是乔治·班南的城市,这位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正式计时员,曾在7000场拳击赛中举起像不死教父般的比赛计时钟,200万次摇响手中的铃铛;它也是麦克尔·麦克巴顿的城市,这位坐在时报广场附近的地铁值班室里的工作人员,总是用一种近乎于无奈和绝望的声音,冲麦克风喊着“下车时请注意脚下,注意脚下”这句话。他一天要重复这句话500遍,有时他也想即兴发挥一下,但却从未这样做过。他一直认为,在车门的咣当声和人群的嘈杂拥挤声中,没有人会注意到他的声音。他还没来得及说出一句妙语,又一列火车已从大中央车站驶来。麦克巴顿先生必须再次重复那句说过多少次的话:“下车时请注意脚下,注意脚下。”
当夜色降临纽约城,所有顾客都离开梅西百货后,十条黑色的德伯曼猎犬开始在走廊过道四处巡查,寻找可能潜伏在柜台后或隐避在衣架中的藏匿者。它们要把这座20层的大商城全部查看一遍。这些猎犬受过专门训练,能爬楼梯,跳窗框,跨栏杆,而且还会在见到诸如暖气漏水、蒸汽管道破损、烟雾甚至小偷这些不寻常的事和人时狂吠不已。如果小偷胆敢逃跑,这些猎犬就会不费吹灰之力地赶上他,在他的两脚之间来回乱蹿,把他绊倒在地。它们的叫声曾让梅西百货的保安发现了许多小隐患,但从未发现过小偷——自从1952年引入警犬之后,还没有人敢在关门后藏在商城内。
纽约城也是一座这样的城市:一只曾经穴居峭壁上的巨大秃鹰现在飞到了摩天大楼上,偶尔也会俯冲到中央公园、华尔街或哈德孙河上捕食一只鸽子。观鸟者曾看到过一些鹰隼在城市上空悠然盘旋,他们看到过鹰隼占据在大厦顶上,甚至在时报广场周围也曾见过它们。
大约有20只秃鹰在这座城市里巡游,有的鹰翅膀展开后有35英尺长。它们曾呼呼地飞过圣雷杰斯旅馆的屋顶,曾攻击过烟囱上干活儿的维修工。1947年8月,两只秃鹰曾扑倒纽约犹太盲人协会之家休息坪上的两位女居民。维修人员在河边教堂曾见过一群秃鹰在钟楼上美餐鸽子。这群秃鹰只在那儿停了一小会儿,就向河边飞去,残留在地上的净是鸽子头。秃鹰飞回时总是悄然无声,不为人们所注意,就像这座不夜城里的那些猫、蚂蚁、头颅中留有三颗子弹的看门人、为贵妇服务的高级按摩师以及许多不寻常的奇闻怪事一样,永远被人们忽视。
纽约:匿名者之城
纽约是一座有许多人工作时看不见面孔的城市。他们坐在地铁售票窗口前,迅速把一些纸片卖给人们。从周一至周五,每天有超过400万的乘客要经过这些钱币兑换者。他们似乎没有头,没有脸,也没有个性,只有手指。除了回答问路,他们的词汇往往只有两个字:“几张?”
但是,在第十四街的尽头,一个名叫威廉·德威里斯的售票员却公开对这种不为人们知晓的工作方式提出了挑战。在第八大道售票窗口外,他贴出了这样一条标语:“请给点微笑,这活儿已经够辛苦了!”
于是这里的旅客都开始微笑了。
他对每位旅客都说:“早上好!”一些纽约人对此很不习惯。他把问路回答都写在小纸条上,甚至在乘客忘带钱时,把票赊给他们。他十分健谈。窗口电话铃响时,他会抓起电话说:“早上好!这是纽约快速公共交通系统独立分公司位于第十四街与第八大道交汇处的78号售票亭的地铁公司职员威廉·德威里斯,工作证号216690。您需要帮助吗?”
作为一名地铁售票员,他可以一天八小时地观察那些纽约人:他们进进出出,互相推搡,或在车门关上的一刹那快步冲入车厢。尽管威廉·德威里斯先生不一定理解,却有机会目睹现实生活中人的一些本性。
他说:“我注意到一件事,大多数纽约人都习惯每天早晨从一个固定的转门入口进地铁,他们永远不换别的门。有的人会一次性买两张票,还有些买了套票的人,在用了一张票后,会赶快再买一张补上。”
威廉·德威里斯先生从1939年起就在地铁公司工作,他认为自己的友好行动特别成功。每天乘客读过他贴在窗口的标语后,都会微笑着离开。可一旦上了火车,他们的微笑就又消失了。他们又开始相互推搡。有的用报纸遮住脸,目不转睛地盯着某个座位;有的偷看几眼漂亮的女孩,幻想着:“我怎么才能认识她?”
他是在列克星敦大道开始注意她的。当时她从布卢明代尔百货出来过马路,他很自然地注意到了她。她下了地铁,穿过检票口,然后站在自动口香糖机与一幅巨型广告中间的站台上。广告上画的是一位通过《纽约时报》找到工作的男士。
那个女孩也许只有二十五六岁。她的腿修长,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一头剪短的金发,随意向后拢着——可能是她用手指拢的。她身穿简洁的黄色套装,戴着白手套,没有化妆。她身材苗条,线条突出,是那种经常光顾东城布卢明代尔百货,不是手里提着各种名贵食品,就是下班后乘第五大道公共汽车回家的青春健美型女孩。这类女孩一般不乘地铁,但偶尔也有一两个。当这样的女孩乘坐地铁时,他就会特别注意。
别的男人也在看她。她或许已察觉,但并不显露出来。这就是游戏的一部分。那些男人总是不露声色地在站台上踱来踱去,不时从自动口香糖机上的镜子中窥视一下她的身影。他们往往在这种游戏中会相互撞上,有时会相互尴尬地笑一笑,有时又会变得非常正经。列车进站时,他会与她保持几步距离,跟随她进入车厢,看着她在过道对面的座椅上坐下。她双膝紧靠,戴着手套的双手拘谨地放在膝上,深蓝色的双眼天真地注视着前方。
地铁列车开始迅速地切换到通向第五大道的铁轨上,黑暗中,地道里的灯快速闪过;一位手提梅西百货购物袋的胖太太像拖船一样摆来摆去;男人们的眼光透过报纸偷看着那个漂亮的女孩。她不敢与他们的目光相对,不敢破坏自己在地铁上的纯洁形象。
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地铁发生故障灯全部熄灭,或是那位胖太太摔倒,那么就会有借口与坐在过道对面五英尺外的这位女神般的纯洁女孩搭讪了。但是什么也没发生。列车依然无丝毫差错地行驶着,就像你想让列车停下时,它总不会随你心愿一样。
列车在第五大道停下。
接着,开往第四十九街。
然后,开往第四十二街。到站时女孩迅速站起,抓住扶杆停了几秒钟,下了车——就像他在纽约城里见过但从未说过话、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的所有其他迷人女孩一样消失了。
纽约市的1万名公共汽车司机每天都要在世界上最糟糕的交通状况中挣扎,同时还要忍受各种折磨:老太太的肆意谩骂,小学生耍滑少投币,计程车随便加塞,卡车冲撞抢行,等等。司机在用一只手驾车另一只手找零的同时,还要向乘客介绍换乘路线,回答各种问题。他们时而抢过绿灯,为了正点到站,时而还得躲闪地上的联合爱迪生电力公司的电缆窨井盖,还要在招呼乘客往车厢后面挪动,承受那没完没了的车铃声以及腰疼、溃疡、痔疮等疾病的折磨的同时,极力克制自己那种几乎难以控制地想把公共汽车撞到石墙上后再走开的歇斯底里的欲望。
尽管承受着这么多的烦恼和辛劳,但是纽约市的公共汽车司机大多数仍默默无闻,人们能看到的仅仅是汽车后视镜上显示出的他们的半张脸。他们从未体验过灰狗长途巴士司机驾车飞驰的那种风光;他们既不像郊区公共汽车司机,能叫出乘客的名字,并在圣诞节收到礼物;也不像包车司机,在接送人们野餐时常被邀请一起进餐;更不像那些校车司机,倘若当地的教育委员会不太激进的话,可以教训一下吵闹的乘客而不受任何惩罚。
纽约的公共汽车司机从不被人们注意。如果抬头看车内后视镜,司机眼里的乘客只是些15美分的化身:他们有的望着窗外,有的盯着脚下,还有的在偷看别人手里的报纸。一位衣冠不整的信使正在斜眼盯着一个黄色信封,一个手里紧抓着购物袋的胖女人在和一个男人瞪眼怒视,争夺车上唯一的空位。那些手抓吊环站立着的乘客在司机眼里就像两扇吊着的牛肉,当多次催促之后仍不往里挪动时,他就特别憎恨他们。
“往车厢后面挪挪,里边有地儿。”
乘客依然没有任何反应。除非他有意破坏他们的这种舒适——猛踩刹车,不回答问题,或在拉铃时到站不停——否则他们会一直没有反应。日复一日,公共汽车司机都在重复这种无休止的单调工作。面对每天乘坐公共汽车的300万纽约人,司机们知道什么时候会遇上什么样的乘客。
早上6点,乘公共汽车的净是些电话接线员、护士、家政人员和旅馆工作人员。7点钟,接踵而来的是商店雇员、码头工人、电梯工以及其他一些必须在8点钟之前赶到工作岗位且喜欢在车上读小报的人。在这几个小时里,一直能听到硬币落入投币箱里的声音。这些搭乘早班车的乘客,本身就是工人阶级,他们总想多给司机些车钱。所以说公共汽车司机的工作在8点之前还是很愉快的。到了8点钟,那些胳膊下夹着书的学生就开始在车上钻来钻去,挤着抢占座位。
早晨9点,车上充斥着秘书、接待小姐以及各种香水的味道。从10点钟起是那些不想乘出租车的经理秘书(他们一般工作到下午6点)和白领职员,还有公共汽车司机的眼中钉——妇女购物群。
“这些中年妇女钱夹里满是硬币,却给我一张五块的钞票。”巴内·奥利里说道。34年前他开始在纽约市做电车司机,现在看上去好像刚从火星探测器上下来一样,“或许她是和女友一起上车;她会说:‘唉!没关系,苏菲,我有零钱。’然后她把手套咬在嘴里,开始寻找零钱——而其他所有的人都得在车外的雨里等着。”
“当汽车驶入有许多人等车的车站时,毫无例外,拎着大包小包的女人总是排在第一。她上车时总是把包放在地板上,然后在钱包里摸来摸去地找钱。等我给她找完零钱,她又问我用三美分转车能到什么地方。这样,我就得在她这儿费两次工夫。当然,她向你打听转车的事儿时,声音特别小,几乎听不到;可她和你吵骂时的嗓门却特大,整个车厢的人都能听得到。”
“在当今的纽约,女士的表现特别差,男士已不再愿意给她们让座了。男士总是坐在公共汽车的后部,假装没有看见站在过道里的女士,或者干脆把报纸盖在脸上,或者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假装在写着什么。男士对占住他们的座位好像特别感兴趣,有时甚至坐过站。”
对于那些能承受这一切的人来说,当公共汽车司机是一份可靠的差事。算上加班费,他们每天平均能挣到120美元。司机们每天有八小时在车上度过,行驶60英里,收到约100美元的车费。他们必须为挣到的每一分钱付出辛苦。尽管有些司机像巴内·奥利里一样,一辈子都在向车后部疏散乘客,也有些司机在干了10年或15年后,开始厌倦这份工作,转行到公司里去干些不太麻烦的工作,例如去做维修人员或修理工。换了工作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非常幸福,甚至变得非常友好。在那里,他们可以远离疯狂的人群和吵闹的铃声,远离交通拥堵和投诉信,远离那些花上15美分就以为可以控制公共汽车司机命运的目中无人的购物者。
傍晚时分,纽约城里成千上万的女秘书踩着高跟鞋从写字楼里迅速走出,而另一大群女人准备涌入。从夜色降临到日出时分,这些女人似乎控制着纽约:她们将占据证交所的位子,主宰空无一人的董事会会议室,向那些看不见的广告人挥舞拳头;她们无须通告就闯进那些商界大亨舒适的办公室,站在听写机前体验发号施令的感觉;她们能让摩天大楼里的灯光彻夜不熄。从窗外看去,她们的身影和扫帚来回飞舞,就像一群女巫在施展魔法。
最后,当光明降临这座城市时,她们手中的废物筐在大厅里集中,她们的声音在楼下空旷的大理石走廊里回荡。不一会儿,她们就列队站在马路旁的人行道边,裹着大衣,笑容满面地等公共汽车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