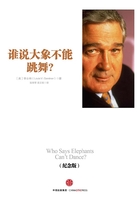
第七章
打造领导班子
1993年年底,我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整个IBM的团队建设、高层管理班子以及董事会建设上。
如果你今天问我,什么是我在IBM任职期间自认为做得最出色的一件事,那么我会说就是打造IBM的领导班子——当我卸任的时候,我的接班人是一个IBM的老员工,而且我们所有主要业务单位的负责人也必须是IBM的老员工。
我认为,如果我加盟IBM时带来一帮公司以外的人,并神奇地在IBM老员工的岗位上做得比老员工们更好的话,现在还要这样做或许太天真也太危险。我就是一个来自公司外部的人,而且是来自一个根据我的经验,你或许也能够经营得好的、一家处于相对简单的行业且经营状况良好中的小型公司。当然那时我不知道会加盟IBM,因为IBM对于我来说是一家巨大且太复杂的公司。更重要的是,IBM还拥有众多天才,他们都具有独特的经验。如果我不给这些本土团队成员一个机会的话,他们很可能就会带着他们的才能和学识另谋高就了。这样,我就不得不寻找以不同方式行事的人来充当管理班子的成员了。
我们需要做出许多关系重大的业务决策。因此,选拔一个我能信任的人至关重要。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建设一个管理班子,实际上是一个日常性的、需要逐个人和逐个业务领域予以开展的工作。我阅读他们写来的报告、观察他们与客户之间的交往、在会议中与他们座谈,并对他们的思维清晰性、是否具有信心和勇气,以及是否能够根据我的眼色灵活行事等做出评估。我还需要知道,他们是否能够坦率地与我直接讨论他们的业务问题。
在我上任之初的第一个月里,我就废除了“管理委员会”制度,这实际上就是在大声地宣告,IBM的管理文化将有重大变革。然而,我仍然需要一个高层执行委员会与我一起共同管理公司。因此,11月,我创建了一个“公司执行委员会”(CEC),包括我在内,共有11名成员。
有了“管理委员会”的前车之鉴,我宣布CEC将不允许做以下这些事:不能接受解决问题的委托,不能行使代表权或者为业务部门代做决策,只关注跨部门的政策问题。
不久,公司文化就将CEC完全视为“管理委员会”的替代机构,即把能够成为CEC的成员当作在公司中的最高荣誉。我从来没有把在CEC中谋得一席之地视为对某人价值的一种真正肯定或成功人士的象征。但有时候,你也不得不在既存的体制中工作。如果所有有能力的IBM员工都希望通过努力工作在CEC中谋得一席之地,在某种情况下这对我也没有什么不好。
同时,我还创建了一个“全球管理委员会”(WMC),以鼓励公司内部各个业务部门之间的沟通和交流。WMC有35名成员,每年召开4~5次会议,还有一个为期两天的分会,该分会主要讨论运营单位的成果以及全公司范围内的倡议。在我看来,其主要的目的还是让高级经理团队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努力工作。这些会议组织为高级经理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即他们可以在这些会议上握住另外一个高级经理的手说:“我已经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但我需要你的帮助。”
建立一个新的董事会
我初到IBM的时候,有一项最具有革命性意义但却最少被注意到的改革措施,那就是对IBM董事会的改革。当我刚到公司董事会的时候,一共有18位董事,其中4位是IBM的老员工,他们分别是:约翰·埃克斯、杰克·库恩勒、约翰·欧佩尔(在埃克斯之前,他是IBM的CEO)以及保罗·里佐。我认为,这样的董事会规模过于庞大,且内部的人员也太多,特别是这些内部人员还都是公司现任和前任的、在执行委员会中具有主导地位的人员。
显然,搜猎CEO的行动、媒体对公司公开的严厉批评,以及公司股东年会上尖锐而深刻的指责,这一切都给董事会成员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打击。在公司治理的一系列讨论活动中,我十分赞同他们中一些人的观点,尤其是吉姆·伯克和汤姆·墨菲的观点。
我想大多数的董事都对于自己在董事会的去留问题怀有复杂的心情,有些人会很愿意有一个光荣退出的机会。伯克和墨菲提出了一个精彩的建议:每位董事都自己提交辞呈,而且董事委员会将决定未来董事会的合理结构。
结果有5名董事于1993年离开了董事会,1994年又有4名董事离开了。墨菲和伯克是自己要求退休的,比IBM规定的退休时间提早了一年。他们的行动无疑是一个信号,是在告诉其他人:现在该是把位置让给新人的时候了。有些人离开是出于自愿,但也有一些人选择离开是因为他们发现公司现在的流程很令他们反感或者是出于个人的难处。但无论如何,我们顺利地解决了董事会的问题。令所有人吃惊的是,对此媒体竟显示出了少有的平静。
到1994年年底,我们组建了一个只有12名董事的董事会。我是唯一的公司内部的人,过去那个由18人组成的董事会中只有8名董事继续留任,这8个人都是在一年前才进入董事会的。
从1993年开始,我们开始引进新人,最先引进的就是查克·奈特——艾默生电气公司董事长兼CEO。当查克还是卡特彼勒公司(Caterpillar)一名董事的时候,我就已经认识他了。他是一个务实的人,也是一个对自己、对CEO以及他的董事会成员都严格要求的人,这也是我十分敬重的。他还被尊称为美国历史上最早的CEO之一,而且,他的当选也是重建IBM董事会的重要一步。
1994年,我们又将麻省理工大学校长查克·维斯特和福特汽车公司董事长兼CEO埃里克斯·特罗特曼请来担任IBM董事会成员。美国报业协会总裁兼CEO卡西亚·布莱克和美孚石油公司董事长兼CEO路·诺托也于1995年加入到我们的董事会队伍中来了,接着就是1996年进入董事会的尤尔根·道曼恩——德国赫斯特公司(Hoechst AG)董事长、1997年进入的三菱商事株式会社总裁原稔(日本商界最高层的领导人之一)、1998年进入美国运通公司的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后来是董事长兼CEO)肯·谢诺尔特,以及2001年进入的礼来公司(Eli Lilly)董事长兼CEO西德尼·陶里尔。
由这些人所组成的董事会,为我们后来所取得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有力、投入和有效,已经是公司一贯的、符合最严格的标准的治理方式。实际上,1994年,“加州公共雇员退休系统”(CalPERS)董事会——这个管理着世界最大公共补偿基金的董事会,将IBM董事会治理方法列为最优秀的董事会管理方法之一。自那以后,其他组织才认同IBM董事会的变化。
与员工的沟通和交流
就在我们改革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体制的同时,也很有必要为我们公司员工的沟通和交流打开明确而连续的通道。任何一家公司成功实现改革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就是,公开承认自己所面临的危机。如果员工不相信公司有危机存在,他们就不会做出牺牲来实施改革。因为没有人会喜欢改革。无论你是一个高级经理,还是一个门卫,改革都意味着不确定性和潜在的痛苦。
因此,危机是肯定存在的,而CEO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危机找出来与自己的员工进行沟通和交流,告诉他们这些危机的范围、严重性以及影响。同样重要的是,你作为CEO还必须能够告诉员工如何终止这些危机——新的战略、新的公司模式以及新的公司文化,即终止危机的方法。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CEO投入巨大的精力用于沟通、沟通、再沟通。我相信,如果没有CEO多年持续地致力于与员工进行当面沟通,而且是用朴素、简单易懂和具有说服力的语言去说服员工并让他们都行动起来,那么公司就不会实现根本的改革。
就我的IBM生涯而言,这就意味着,我要在某些时候,从那些在与“自己的人”进行沟通和交流时有着强烈控制欲的事业部负责人手中夺过麦克风,并告诉这些负责人,在与员工进行沟通时,如何确立他们的优先性问题、说话的声调以及个人形象问题。在某些公司,有时候这样的行为或许是恰当的,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IBM公司,这样做却并不恰当。这是一个我们都要面对的危机。为此,首先就要将我们的公司理解为一家完整的公司、一家由前后一致的思想指引的公司。在这家公司中唯一可以这样与员工进行沟通和交流的就是CEO——我。
在我上任的早期阶段,这些沟通活动对于我来说是绝对至关重要的。我所要传达的信息十分简单,我站在IBM遍及全球的员工面前——而且是没有拿演讲稿,对他们说道:“显然,我们过去所做的那一套并不管用。在3年中,我们亏损了160亿美元。自从1985年以来,已经有17.5万名员工失业了。媒体以及我们的竞争对手都把我们叫作保守而过时的恐龙,我们的客户也很不高兴而且是很生气,我们没有像我们的竞争对手那样发展壮大。难道你们不认为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尝试一些别的方法吗?”
我也发现了IBM内部信息系统的能量,因此我开始以“亲爱的同人”为称呼给员工们写信。这些信件也是我在IBM所实施的管理体制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我上任后的第6天,我就给他们写了第一封信:
董事长办公室
1993年4月6日
敬致:IBM全体同人
主题:我们的公司
上任伊始,我就在我的办公室电脑中发现,PROFS邮件是IBM的一个重要的沟通和交流工具。感谢所有给我发来道喜信、祝愿信、建议以及意见的人。
我知道你们都能理解我不可能给你们每个人单独回信,但是我的确想借此机会感谢那些在信中提到了一些经常性和严肃的公司问题的人。
你们对IBM的一片赤诚之心深深地打动了我,而且很显然你们也希望重振IBM的雄风——越快越好,让IBM重新占据电脑市场的领导地位。无论是已经离开IBM的人,还是继续留下来的人,都是这样想的。这些都有力地说明,我们的员工对成功的渴望就是我们公司的力量所在。
你们中有些人受到了伤害并为此而感到生气,因为你们在多年忠诚于公司以后,却被宣布为“多余的人”,并在媒体的有关绩效评定结果中曝了光。
我的确意识到,我是在公司正急剧走下坡路的痛苦时刻来到公司的。这对于每个人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所能给你们的保证就是,我将尽我最大的努力尽快地让这个痛苦时期成为历史,以便我们能够开始展望未来,拓展业务。
我希望你们能知道,我不认为那些离开IBM的人就一定是不太重要、不太合格或者比公司中其他人的贡献小;相反,我们都欠他们一份巨大的人情,因为他们都是给IBM做过巨大贡献、值得赞赏、了不起的人。
最后,你们在信中告诉我,重振公司的士气对于我们所制订的所有业务计划来说都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对此我完全赞同。在未来的几个月中,我打算走访尽可能多的公司营业部门和办公室,而且只要一有时间,我就会去和你们会晤以共同商讨如何巩固和加强公司的力量。
郭士纳
这封信在IBM员工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于我来说,它们无疑是我在IBM最初的黑暗日子中的一种安慰、支持和力量。有一封回信写道:
我流下了喜悦的泪水。
还有一封是这样的:
谢谢、谢谢、谢谢,IBM复苏了。
同时,IBM员工也从不害怕说出自己的反对意见。我就曾经收到过一封非常坦诚、直率和直截了当的来信——哎呀,我只能说,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可是绝对不敢给自己的老板写这样的信,就更不要说给CEO写信了。他是这样写的:
得了吧!收起你的那套噱头吧!干点实事,缩短订单的循环周期,向市场提供一些新产品,找到新的市场,倾听那些目前还不是我们的客户、但只要我们有产品他们就会成为我们客户的人。
别再做那些伤人心的事情了。干点实事会让你不至于在每6个月后就让越来越多的人痛苦。
还有一名员工在信中这样表达对我的欢迎:
欢迎你!还有,不要担心自己并不懂多少微型芯片知识,只要你不把它们和巧克力片混淆在一起就足够了。
有一名员工,即便就在他的老板面对我们竞争对手的成功而惴惴不安的时候,还抽出了时间和精力来讽刺我的走访活动:
我认为你有3个方面的态度和观点尚待改正。你如此的平易近人,且如此愿意接受信息反馈,这让我感觉与你交换意见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
1.你为IBM人制定了一个重要的长幼尊卑制度:首先是客户,其次是IBM,第三才是某人自己的事业部。这听上去就像是麦肯锡的等级制度。我给你提供一个更为合适的长幼尊卑排序——而且这也是IBM的一个传统,那就是:首先是某人自己,第二和第三都保持不变。尊重个人是个人健康成长的不二法门,不仅对于个人来说如此,一个组织或社会也不例外(麦肯锡的等级制度是这样排序的:首先是客户,其次是公司,最后才是个人。这种等级制度蔑视员工和他们的家人)。
你说我们有必要做自我检查,并对我们一直以来的运营方式做检查。我也很看重自我反思,并给出以下建议以供你参考(它们都会为你提供管理案例)。
2.你似乎既想要竞争又大力强调打击竞争的重要性。我意识到这种态度是一种文化上的认同,但是我也相信,这也是一种不必要的、不健康的和最没有生产力的社会互动形式。例如,IBM内部的竞争思维(IBM人打击IBM人)就是你所竭力反对的。你也强调了取悦客户的必要性,我同意那是一个目标,并承认它是一个与“打击竞争”不同的目标。为达到这些目标我们所要采取的方法也应该是不同的。如果不清楚自己的目标,我们将很可能找不到有效的方法去实现这些目标。
这里尤其要指出两点:你提到了“挫败某人的锐气”和“驳他们的面子”。难道这些听起来像是健康的态度吗?这些“某人”可也是有朋友、有家庭的人呀!他们甚至有可能就是你的朋友和亲戚。拥有这种想法和态度的竞争一定是一种牺牲别人以达到自己目的的竞争,就其实质来说,它就是对个人的不尊重。
就这个主题(异端文化:反对竞争的案例)我已经给你寄去了一盒录了音的磁带,并随磁带附上一个简短的说明。显然,这盒磁带和短信是被行政助理拦下了,并没有到你手中。如果你有兴趣就该主题展开进一步的探讨,我会再给你寄磁带。
你声称衡量我们是否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就是我们的每一项信息技术消费预算的百分点。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不健全的想法。百分点是有限的,最多不会超过100点。使用它来作为衡量标准,任何一家公司想要实现赢利就必须以牺牲另外一家或者多家公司为代价。如果我们能够思维开阔一些、考虑如何才能制作更大的馅饼,那么我们每个人就都能够体验成功者的感觉。比如,如果为了增加价值而在信息技术上多花点钱,这样做我们尽管会丢掉百分点,但却同时实现了公司的成长并赚取了更多的钱(我猜我们已经在20世纪80年代丢掉了太多的百分点,但是我们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实现了扩张和每个季度赚取10亿美元的利润)。相反,我们对获取100%的读卡机市场有多大的兴趣?
尽管在这封信中我所关注的是“有待改善的方面”,但我想再次强调的是,我敬佩你的为人,并尊重你已经和正在从事的工作。我期盼着能和你合作。
姓名略
又及: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真的,但我确实听说,你走访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罗利的办公地点的活动是被事先安排好了的:你所经过的路线是事先安排的,你将要参观的大厅,他们也事先重新粉刷了墙面并铺设了新地毯。我想知道,如果你知道这一切是真的,并且它就是真的,你又会怎么想呢?
有时候我不得不为我自己所说过的话感到懊悔——几乎是有一半的话都会让我懊悔。我能说的就是,有人给我回信是一件好事,但是我却因为太忙而无法给每个给我发电子邮件的来信者一一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