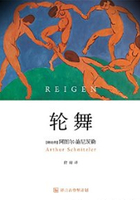
第4章 少爷与少妇(1)
晚上——施文德街上一幢房子的客厅,装潢优雅而廉价。
少爷:(刚进门,头上还戴着帽子,身上还披着大衣,就点燃了蜡烛。尔后他把通向旁边房间的门打开,往里看了一眼。客厅的烛光洒在镶木地板上,一直落到靠在尽头墙上那张有四根帷柱的床上。卧室一角的烟囱中透出一股红色的光亮,投射在床幔上——少爷打量着卧室。
他从梳妆台上拿起一个喷雾器,对着床的帷柱喷了一下,出来一小股紫罗兰香水。随后他拿着喷雾器在两个房间里走动,不停地按着喷雾器上的小球囊,整个房间里迅速弥漫起了紫罗兰的气息。然后他脱下大衣,摘下帽子。他在蓝色天鹅绒的扶手椅上坐下,点燃一根雪茄,开始抽烟。不一会儿,他又站起来,确认绿色的百叶窗是否关好了。他突然又走进卧室,打开了床头柜的抽屉。他把手伸进去,找到了一个龟壳形状的头发别针。他在找地方把它藏起来,最终把它放进了大衣口袋里。然后他打开了客厅里的一个柜子,拿出一个银杯,一瓶干邑白兰地,两个喝烈酒用的小杯子,全都放在桌子上。他又走到他的大衣前,从里面拿出一个白色的小口袋。他把口袋打开,放在干邑白兰地边上;又走到柜子前,拿出两个小盘子和餐具。从小袋子里面拿出一个用糖腌过的栗子,吃了。然后他给自己倒了一杯干邑白兰地,迅速喝光。然后他看了一眼表。他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在墙上巨大的镜子前,他站了一会儿,用小梳子理理头发和小胡子。——他现在走到前厅侧耳倾听。没有声音。然后他拉了拉紧紧挡在卧室门前的门帘。门铃响了。少爷悄没声儿地颤抖了一下。然后他到扶手椅上坐下,门开了,少妇进来的时候,他才站起身来。)
少妇:(裹得严严实实,把身后的门关上,有那么一瞬间就站在那儿,左手放在胸前,仿佛在抑制某种强烈的激动。)
少爷:(走向她,拿起她的左手,在她镶黑边的白手套上印下一吻。他轻声说)谢谢您。
少妇: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
少爷:您请进,尊贵的夫人……您请进,爱玛夫人……
少妇:再让我歇会儿——求您了……哦实在是求您了,阿尔弗雷德!(她依旧在门口站着。)
少爷:(站在她面前,握着她的手。)
少妇:我到底在哪儿?
少爷:在我身边。
少妇:这房子真可怕,阿尔弗雷德。
少爷:为什么?这房子很体面啊。
少妇:我上楼时碰到了两位先生。
少爷:你认识他们?
少妇:我不知道。有可能。
少爷:原谅我,尊贵的夫人——可是,要是您认识的人,那您肯定能认出来的。
少妇:我什么也没看见。
少爷:不过,即使是您最好的朋友——也不可能把您给认出来。我本人……要是不知道是您……这条面纱——
少妇:是两条。
少爷:您不想再过来些吗?……您至少把帽子摘下来吧!
少妇:您在打什么主意,阿尔弗雷德?我跟您说过五分钟……不,不能再长了……我跟您发誓——
少爷:所以这条面纱——
少妇:两条。
少爷:好吧,两条面纱——至少得让我看看您吧。
少妇:那么您爱我吗,阿尔弗雷德?
少爷:(受到了深深的伤害。)爱玛——您问我……
少妇:这儿太热了。
少爷:可是您还戴着皮草头巾呢——您真的会感冒的。
少妇:(终于进了房间,一屁股坐在扶手椅上。)我累死了。
少爷:请您允许我(他给她摘下面纱,把发针从帽子里拿出来,把帽子、发针、面纱放在一边。)
少妇:(任凭他这么做。)
少爷:(站在她面前,摇头。)
少妇:您怎么了?
少爷:您从没有像现在这么美过。
少妇:为什么?
少爷:单独……单独和您在一起——爱玛——(他在她的扶手椅旁边跪下来,拿起她的双手,在手上到处亲吻。)
少妇:那么现在……您让我走吧。您的要求我已经做到了。
少爷:(把头枕在她的大腿上。)
少妇:您跟我承诺过您会管住自己的。
少爷:是啊。
少妇:在这房间里要闷死了。
少爷:(站起来。)您还戴着头巾呢。
少妇:您把它放到我帽子边上吧。
少爷:(帮她摘下头巾,把头巾也放在长沙发上。)
少妇:现在——再见了——
少爷:爱玛——!——爱玛!——
少妇:五分钟早就过去了。
少爷:还不到一分钟呢!——
少妇:阿尔弗雷德,您如实说来,现在几点了?
少爷:现在正好差一刻七点钟。
少妇:现在我早该到我姐姐家了。
少爷:您姐姐经常能见到您……
少妇:天哪,阿尔弗雷德,您为什么要这样引诱我。
少爷:因为我……仰慕您,爱玛。
少妇:您跟多少人这样说过了?
少爷:自从我见到您开始,就没跟任何人说过。
少妇:我太轻率了!要是之前有人跟我说过……八天前还……昨天还……
少爷:您前天倒是已经答应过我了。
少妇:因为您老是折磨我。但是我不愿意这样做。上天作证——我不愿意这样做……昨天我下定了决心……您知道吗,我昨晚甚至给您写了一封长信。
少爷:我什么也没收到。
少妇:我又把信撕了。哦,我倒宁可把这封信寄给您。
少爷:其实这样更好。
少妇:噢不,这太羞愧了……令我羞愧。我都不能理解我自己了。再见,阿尔弗雷德,您放我走吧。
少爷:(抱住她,热烈地亲吻她的脸。)
少妇:您……就是这样履行诺言的吗。
少爷:再亲一下——再来一下。
少妇:最后一次。(他吻她,她回应着;他们的嘴唇长久地交缠在一起。)
少爷:我能跟您说点什么吗,爱玛?我这才知道什么是幸福。
少妇:(坐回扶手椅上。)
少爷:(坐到扶手上,一只胳膊温柔地环绕着她的脖子。)……或者不如说,我直到现在才知道,幸福可能是什么样子的。
少妇:(深深叹息。)
少爷:(再次吻她。)
少妇: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您想把我变成什么样啊!
少爷:不是吗——这儿其实也没那么不舒服吧……我们在这儿多安全!比光天下日之下的约会要美妙上一千倍……
少妇:啊呀,您别让我想起来那件事。
少爷:我想起这件事来倒总是会带着万千喜悦。对我来说,我在您身边度过的每一分钟,都是一场甜蜜的回忆。
少妇:您还记得工会的那场舞会吗?
少爷:我还记不记得……?用晚餐的时候我不是在您旁边吗,和您挨得特别近。您的先生在喝香槟……
少妇:(埋怨地看他一眼。)
少爷:我只是想说那香槟。爱玛,您不想来一杯干邑白兰地吗?
少妇:一丁点。不过您先给我一杯水吧。
少也:好……在哪儿来着——噢对……(他把窗帘拉开,进了卧室。)
少妇:(目光追随着他。)
少爷:(拿着一瓶水回来,还有两个杯子。)
少妇:您上哪儿去了?
少爷:上……旁边那屋去了。(斟了一杯水。)
少妇:现在我要问您些事情,阿尔弗雷德——您要向我发誓,对我说实话。
少爷:我发誓。——
少妇:这地方其他女人来过吗?
少爷:哎哟爱玛——这个房子已经二十年了!
少妇:您知道我什么意思,阿尔弗雷德……和您一起!在您身边!
少爷:和我一起——这儿——爱玛!——您会想到这种事,真是不太好。
少妇:所以您的确……我该怎么……哦不,我还是不问您了吧。我不问会更好。是我自己的错。自作自受。
少爷:啊,您在想什么?您这是怎么了?什么自作自受?
少妇:不,不不不,我不能恢复清醒……否则我就要羞愧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了。
少爷:(手里拿着水瓶,伤心地摇头。)爱玛,要是您知道您给我带来了多少痛苦,那就好了。
少妇:(给自己斟了一杯干邑白兰地。)
少爷:我有话要对您说,爱玛。您到这儿来要是觉得羞愧——我对您来说要是这么无足轻重——您要是感受不到您对我来说意味着整个世界的幸福——那您就还是走吧。——
少妇:是啊,我会的。
少爷:(握着她的手。)可您要是知道我没了您就活不下去就好了,对我来说,能在您的手上吻一下都比整个世界上全部女人的温存加在一起更重要……爱玛,我和其他油嘴滑舌的年轻人不一样——我也许太天真了……我……
少妇:您要是真的和那些年轻人一样呢?
少爷:那么您今天就不会来了——您和其他女人不一样。
少妇:您是怎么知道的?
少爷:(把她拉到长沙发上,坐在她身边。)关于您,我想了很多。我知道您并不幸福。
少妇:(高兴地。)是啊。
少爷:生命如此空洞,如此虚无——然而——如此短暂——短暂得令人害怕!只有一种幸福……找到一个人,为他所爱——
少妇:(从桌子上拿起一块用糖腌过的梨子,放进嘴里。)
少爷:给我一半!(她用嘴把它递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