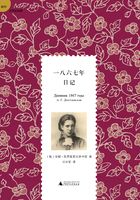
第12章 第一本(11)
早晨我很早就起床了,因为我觉得费佳今天一定会回来,就准备去车站。但不知为什么,却先去了邮局,在那里拿到了他的信。他说,收到了我的信,但银行的汇款还未收到,所以他还不能回来。【我认为,这不是实话,而只是要较长时间留在那里的借口。】他写给我的信很可笑,信中抱怨牙疼得可怕,请我稍微忍一忍[60]。有什么办法呢,我便写了一封信,就这样吧,让他在那儿多待几天吧。从这里我去了面包店,喝了一杯咖啡,吃了点奶油甜食,冒着雨就去参观矿物陈列馆原文为德语……说实在的,这里没什么好看的。陈列品很少,就摆放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在这里我未看到任何新东西,以前我都见过,也许只有拉长石除外,它是我第一次见到,还有就是琥珀中的昆虫。它们保存得很好。我在这里溜达了近半小时,铃声响起时我很高兴,这意味着规定参观时间的结束。我没能进地质厅[61],但并不后悔。从这里我去了美术馆。一般在雨天和免费日里这里人很多,——大概,在这样阴郁的日子里,谁都不知道去哪儿好,便都到美术馆来了。我带着自己的札记本,便把某些画家的出生年代和给我以特殊印象的作品记下来。从这里我去找【俄国】银行家,问他是否把信发走了。他客气得惊人,让我看了邮票,甚至像第一次那样,把我送到门口。溜达了一会儿之后,我到昨天那家糖果点心店喝咖啡,老板立刻认出了我,我们就谈起了政治,【谈纠纷,】谈普鲁士军队撤出德累斯顿。后来我回到家中,坐下来读《俄国人》报[62],补我的袜子。这双袜子已经补过许多次了。傍晚我【又】感到饿极了,便去给自己买了黄油、面包和香肠加入:(这些天我没能吃午饭,只享用了一些咖啡、茶水和小吃。这是因为房东太太认为给我提供午饭划不来,而且她的伙食很差,到饭店去吃饭又不可思议;这里看不惯没有男士陪伴的年轻女子在饭店吃饭,形形色色的德国男女放肆地瞪着眼睛看我。到糖果点心店喝咖啡则不认为反常。所以我挨饿实属无奈!)。我吩咐伊达沏茶。房东太太的妹妹到我这儿来了,她吃惊地发现我这儿这么冷,便让我到她那儿去喝茶。我喜欢去她的房间,因为很舒适。她今天在房间里生了两次火炉,所以相当暖和。我们畅谈各种事物,我发现,我说法语相当流畅,比一星期以前快三倍。这很让我高兴,那么可以指望,在国外生活几个月,我就能很好地说法语和德语了。我们喝加了樱桃酱原文为德语。的茶,这类似朗姆酒,据房东太太说,在瑞士,老年男女每天晚间都喝朗姆酒,她们也喝。(难怪我有时觉得,房东太太时常带些醉意。)后来她给了我一本《法国戏剧》,里面有两个小话剧。其中一个是《诗歌或稀粥》,里面有一位蓝袜子,非常滑稽可笑,我很喜欢。我在睡觉之前读它,后来睡得很香。清晨我醒过两三次,后来又睡着了,做了各式各样的梦,才懒洋洋地起床。我【还】忘了:昨天我又去了一次邮局,这很使邮政局长惊讶,他对我说:难道我还嫌一封信少吗?我拿到一封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加入:(·伊萨耶夫)。来的信。是写给费佳[63]的,但我认识他的笔迹,便拆开看了。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
星期六,5月25日(13日)
我想起来了,昨天邮政局长告诉我,信件清晨就到;我九点钟就到了那儿,但没有找到信。回家后想到,费佳大概今天回来。十二时我到了车站,但费佳没回来。从车站去邮局,路上我猜测这封信的内容,就是全都输掉了,请求寄钱去[64]。果然如此。我马上给他写了信,又去找银行家。可是他对我说,办事处马上要关门,三点才再开门。我在回家的路上喝了杯咖啡,【后来】拿了钱又去找他。然而,我的服装这一次也许未能引起他先前那样的尊重,他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请我坐下,也没有像昨天那样,送我到门口。
把信送到邮局后,我到茨韦格上面去散步。这里我还从未来过,可以沿着栏杆围着它走一圈。我走了一遍,然后坐在湿长凳子上写信。这一切都是为了消磨时间。后来我去了我们的图书馆,询问是否来了新书。那人回答说,还没有,但他期待着随时能到。我选了叶夫根尼娅·图尔两本书,还有一本《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札记》[65]。顺路去糖果点心店喝了一杯咖啡,然后回家,开始读书。这些书都是重复一个主题:为了姐妹或亲人,骄傲的姑娘牺牲自己和自己的爱情。总之,蠢得吓人。晚上房东太太来我这儿,【同我】聊了一会儿,祝愿我睡个好觉,就走了。
星期日,5月26日(14日)
今天我起来得相当早,因为要去邮局,然后还要去教堂。穿好衣服,见到了房东太太,答应今天在她那儿吃午饭。去了一趟邮局,收到一封信[66],信中费佳答应明天回来。然后来到教堂。这儿唱得多么好啊,简直是奇迹。信仰其他教的人,跟上星期一样,多得可怕。一开始,我在远处看祈祷仪式,后来走到了乐队旁边。在这里我看见两个漂亮姑娘:一个是金发女郎,另一个是黑发女郎。我估计,她们是情敌:其中一位穿得华丽得体,另一位穿得马马虎虎,甚至可以说,不怎么好,但两位都十分美丽。后来她们一起走出了教堂,立刻就有一位男士走过来,她们与他交谈。我回家后,马上坐下来吃午饭,吃饭当中一直劝说汤姆森小姐跟我们一起去。可是她说,只有我保证一直跟她说英语,她才肯去。我向她保证,但她还是下不了去的决心。我们一点半出发,差一刻两点到达了那里。买了票(十四吉尔布,往返票),稍等了一会儿,便上了车。同我们坐在一起的有一对夫妇。一开始我听到他们好像讲的是俄语,可后来又否定了【,因为他们讲开了德语】。还有一个德国女人,她去近处什么地方,丈夫和两个孩子送她。母亲不时与丈夫说话,可那位德国佬故意尽量不看自己的妻子。诚然,她的确上了年纪,显得比他老。火车开动的时候,两个男孩子中的一个哭了,被赶忙带了出去。
过了不到一小时,我们来到了波茨夏。我们的火车一直在易北河附近奔驰。它变得越来越窄,不比施普雷河和我们的黑溪宽,窄得吓人,但据说很深,——达十二俄丈深。我们驶过了皮尔尼茨,又驶过了皮尔纳。这是一座不大的城市,只有几条街道,很清洁。不过,我想,一定很乏味。离这里不远,在高山上,有一座精神病院,医院里有一个大花园和瞭望台。一到车站就有许多人下车,我们车厢里宽绰了不少。景色壮观。易北河的一侧到处是悬崖,高高的、阴森森的悬崖;而另一侧,我们刚才经过的那一侧,则是一堵墙,用它支撑着山崖,使其不至倾倒。原先这里是山岩,为了铺路,把它炸掉了。到处是林木。美极了。最后我们来到了[萨克森的瑞士?],大家都下车去乘船。我想,船上坐了十五个人左右,或者更多些,以致船都快要进水了。我有些担心,因为据说这里水很深,而且我根本不想落水弄湿衣服。不过还是把我们顺利地送到了,收了我们每人十二芬尼。我们上了岸。这里站着几个人,牵着备好鞍镫的马。房东太太腿疼,不想步行去。我本来想徒步去,她让我骑马,说服了我。我一开始不同意,第一,我从来没骑过马,害怕;第二,不乐意支付这么大的价钱,即一塔列尔五芬尼。后来他们让价到二十五吉尔布加入:此外,如果徒步走,我还担心落在同行人们的后面……没办法,骑吧。我上了马,把两腿分放两侧,开始抓住马鬃,保持平衡。一开始把我吓坏了,大概脸都白了,总之是一副提心吊胆的模样。房东太太提醒我注意树木。我什么也听不见,而且什么也不想看加入:为了不从马上掉下来。我的首次骑行够可怜的……不过我渐渐清醒过来,不再两手抓住马鬃了。真好哇,这个萨克森的瑞士!山岩高不可攀,层层叠压的巨石似乎随时可能向我们头顶砸来。这些山岩全都被林木覆盖着(大部分是云杉),山岩中间有溪水流淌。这一切是那么美好,简直难以想象。只有一件憾事,——费佳没有和我在一起。缺少他,什么都不能使我尽兴狂欢。有时候山岩低低地悬在我们上方,必须用力低头,才不会被碰伤。有时候巨石形成狭窄的通道,不容许两个以上的人并排而行。我们一步一步地缓缓前进。马都是驯熟了的。只有房东太太的马被她的伞吓惊了,要向一旁跳去,不过立刻就被制服了。我同我的向导聊了起来。他告诉我,我的【马】叫弗里茨,另一匹马叫利塞尔。我的是一匹老实善良的马。它有时回过头来,用它那可爱而又聪明的眼睛看我,有一次它站住,想吃青草,可是向导不允许它停下来。我想,我们走了将近一小时,终于来到了巴斯泰。
到最后我已经一点也不害怕了,而是大胆地骑在我的驽骍难得身上,【甚至】不再抓住弗里茨的鬃毛。路上我们遇到许多行人,他们惊讶地望着我们,嬉笑不止。这笑声,我想,是我大胆的愁容骑士原文为法语。的样子引起来的,后来房东太太就这样叫我。当我们到达巴斯泰以后,我们都对我的形象狂笑不已。房东太太说,她都不忍心看我那可怜样儿。当我无力再坚持下去的绝望时刻,我“嗷,嗷!”地大声号叫加入:自己还不觉得……这样的号叫声让她哈哈大笑了一个多小时。就是我自己也能想象,我在马上是何等可笑。
最后我们到了,下了马,交了钱,走进了饭店。在这里我要了一杯咖啡,她要了啤酒。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头疼得吓人。也许,这是因为我第一次骑马,吓的,或者仅仅是因为山区空气,【高度】,对我产生了影响。我头疼得十分厉害,简直到了恶心的程度。应当说明,自从到了国外,这是我第一次头疼。然后我们就去观光。我们站在被铁丝网围着的山岩上,往下面眺望易北河。一切都小得可笑。那里有一条船,也许本来不小,可是却像一个玩具。房屋,轮船,人,——一切都好像不过一俄寸大。这里可能高得可怕。(我忘记说了,我们从波茨夏渡过易北河,到了韦赫伦,从这里爬高山,过谷地,当地人称之为乌特瓦尔德·格伦德。)【此刻】火车正行进在易北河的另一侧。它显得出奇地小,不比一般商店里卖的玩具火车大。我们在这里看了好长时间,又溜达了一会儿,就开始下山。我们来到一座桥,它把三四座悬崖连接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几座小桥加入:站在桥上,周围景色一览无余,美不胜收……这一切都美极了。下面可看到苍翠与碧绿相间。这里所有的墙上都写满了各式各样的姓名,其中可以看到大量俄国人的名字。看来俄国人也努力使自己“永生”。即使在既高又大的【山岩上】也写着俄罗斯人的姓名。后来,我们下山。在路上遇到一些男孩子,他们请求我们施舍一点钱。其中一个许诺“在我们的路上撒满鲜花”,另一个想卖给我们“格卢克布拉特”,终生幸福之树叶。不过我们拒绝了,继续走我们自己的路。房东太太说,这已经成了他们的职业,这些男孩子就从事这个,这样一来,他们就要完全失去工作的能力。往山下走相当难,而且我很不习惯上山下山。这是非常陡峭的,几乎是直上直下的小路。房东太太下山的时候经常发出尖叫声,把我吓得要命。(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变得这样胆小,动不动就把我吓得一抖,这真让我遗憾。)我们到达山下后,有人从山上向我们高声呼喊。这是一些爬到山上的淘气鬼在用各式各样的声音吼叫。(我忘了:在巴斯泰上有一座塔楼,但并不比某些悬崖高。里面有一个天文台。不过我没有进去。某位先生攀到那里,开始用模仿狗吠声挑逗狗。听到陌生对手的叫声,狗沉不住气,它的对手站得那么高,让它发疯了。它那么愤怒,主人勉强才把它招呼回去。)加入:为什么要招惹狗呢,这完全是常见的毫不幽默的德国玩笑。
最后,我们来到一个小村庄,应该从这里去易北河对岸,以便到达拉滕站。船来了,我们上了船。那里有一个八口人的德国家庭,但是他们觉得最好等船回来再上,因为无法让他们都一起上这条船。我以前说过的那对夫妇也在这条船上。他们用德语同房东太太交谈。过了河,房东太太建议我吃点什么,以便缓解头疼。我要了面包、黄油和奶酪。她要的也是这些,不过奶酪是用牛乳原文为德语。做的,它有一股臭味。我们正在那里坐着,我听到那对夫妇在用俄语交谈。我立刻问妻子,他们是不是俄国人。不知道为什么,她立刻满脸通红,说她是俄国人,他们在德累斯顿已经生活了十年。除了丈夫以外,她完全没机会说俄语,丈夫在俄国生活过十五年。她告诉我,这里俄国人很多,生活在这里比在俄国更划算,她现在已经完全不怀念祖国了。她讲话有点怪口音,“O”音很重。我很高兴同人讲俄语,因为有两个来星期没说过一句俄语了。后来我又给自己要了啤酒,房东太太则要了牛奶。我们在这里等了近一小时火车才来。我们快走到车厢了,一位太太走到我面前,鞠了一躬。我早已发现她有些面熟,但不知道在哪儿见过。她一讲话我才想起来,我们同她一起从皮尔尼茨坐轮船,还说过话。我恭恭敬敬地与她鞠躬告别加入:还聊了一会儿。我对这种朴实的交往很有好感:遗憾的是,我们,俄罗斯人,从来不能这样坦诚朴实地交往,总是相互回避……我们走进车厢,与我们坐在一起的有四位德国青年,很可爱,很爱笑,可能是大学生。他们一路上都在哈哈大笑,像疯子一样。其中一个甚至还讲法语和英语,自然带有德国口音。在另一个【包房里】,背对着我们,看来坐着一对年轻夫妇。他们之间情意缠绵:他把自己的手放在她的脖子上,她则依偎着他。这一切自然很好,我赞赏夫妻幸福,不过,总还可以稍微控制一些吧,至少在公共场合别这样做加入:把温存做给别人看,这我不能接受……后来她索性把头靠在他的肩上,看样子是睡着了。我和房东太太为此笑了。年轻人们发现了,也悄悄取笑:其中一个招呼自己的同伴,建议他也这样做,也这样亲热。可那一位不顾一切地大叫道:“看在上帝分上,别这样儿!”总之,我们让全车厢都注意这对多情的夫妇,农场主们也开始窃笑。而他们,我想,也不会反对在稠人广众之中同自己的妻子温存一番的。最后,我们到站了。年轻人们先下车,然后帮助房东太太下车。一个年轻人彬彬有礼地把手递给我,帮助我下了马车。走出车站,一个带男孩子的英国男子一直走在我们前面,我们在巴斯泰和拉滕见过他。我们走到马路对面,过一段时间他也走过来了。最后他转弯去了别处,我们则往家走去。我头疼得很厉害。我立刻便在床上躺下了,担心明天不能早些醒来。
星期一,〈5月〉27日(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