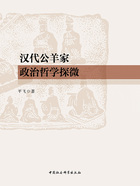
一 分裂的春秋社会与一统的汉代社会
汉代公羊家生活在已经一统的帝国,他们借以发挥思想的《春秋》中的春秋时代却是一个分裂的战争时代。远去的历史与当下的历史都不可避免地进入公羊家的思想视野,成为思考的对象。
(一)分裂的春秋社会
汉代公羊家公羊寿在汉景帝时才将《公羊传》的文本写定,“文景之治”已有升平气象。《公羊传》是解释《春秋》的,这种解释当然是一种“有字”的“经文”解释,其实更重要的是一种“无字”的“文本”解释,即《春秋》“经文”所记载的242年的春秋历史“文本”解释。这部真实的242年的春秋历史是怎样的呢?
真实的242年的春秋历史是霸道盛行,战争灭国,充满暴力。董仲舒曾总结春秋灭国的历史说:“弒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小国德薄不朝聘,大国不与诸侯会聚,孤特不相守,独居不同群,遭难莫之救,所以亡也。”(《春秋繁露·灭国上》)弱肉强食,霸王当道,不仅国内杀兄争国,而且国外相互灭并,仅仅一个齐国就并国三十五。《荀子·仲尼》载:“齐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则杀兄而争国……外事则诈邾袭莒,并国三十五。”成者王败者寇,真实的历史服从的就是权力与暴力逻辑。孟子面对着这部春秋战争史,作了这般记录与评定:“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上》)一句话说,“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怪不得孔子羡慕尧帝“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论语·尧曰》)。
真实的242年的春秋历史是礼坏乐崩,上下失和,社会无秩。按照周代的礼制,“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左传·桓公二年》)。整个社会井然有序,所有所属。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天下有道,有道与无道体现出来的秩序完全不同:“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平王东迁,周始微弱。诸侯自作礼乐,专行征伐,始于隐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于乾侯。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为家臣阳虎所囚。家臣阳虎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齐。
真实的242年的春秋历史是富国强兵,唯利是图,好货好色。《孟子·梁惠王上》载:“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像梁惠王这样见面唯利是谈的君王实在不在少数。《荀子·仲尼》载:“齐桓五伯之盛者也……内行则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闺门之内,般乐奢汏,以齐之分奉之而不足……其事行也若是,其险污淫汏也。”齐宣王更是放肆,毫无忌讳地直言自己好勇、好货、好色的毛病。《孟子·梁惠王下》载:“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梁惠王下》)王即是齐宣王,他集“好勇”“好货”“好色”于一身,任由物欲横流。孔子生在春秋时代,不无忧患地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
真实的242年的春秋历史是道术分裂,学派林立,诸子蜂起。《庄子·天下》载:“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当时各家各派,虽然各有所长,但都是一曲之士,不知“内圣外王之道”。看看《荀子·非十二子》:“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在者有人矣。纵情性,安恣孳,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它嚣魏牟也。忍情性,綦溪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陈仲史䲡也。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反纟川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只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弓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又看看《韩非子·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乐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当时各家相互批判,非常激烈,比如孟子距杨墨,就言之切切:“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扬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总起来说,在当时的思想界,一方面学派林立,每一家各有创获,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各有一曲;另一方面思想自由,各家争鸣激烈,道家《庄子》、法家《韩非子》、儒家《孟子》《荀子》以及墨家《墨子》等都在争鸣中标明自家立场,并评论各家优劣、深浅、得失,而且儒家内部、墨家内部也互有批评、争论;再一方面各家都自认自己的思想得道术之全,是真学术,并试图说服君主使自己的思想定于一尊,推行于世,救时补弊,解决现实问题。
从上面的简略描述可见,从批判的眼光可以看到这部活生生的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历史中充满暴力、充满混乱、充满物欲、充满争辩。当然,这部历史远不止这些,也有不少可以值得嘉奖的事迹。历史要向前文明地迈进,正面进步的当然要看到,并发扬光大,但负面落后的更要关注,因为救时补弊,关键在找到社会的病症,以便开出疗救的药方。《左传》是非常重视这个真实的史事记载的,读罢更能详细了解各国兴衰的历史画卷。《史记》也是非常重视这个真实的史事记载的,真实地记录了春秋时代的善善恶恶及其复杂的各种社会现象和历史事迹。哲学的思考要超越现实,超越现实必须有批判的眼光,批判的眼光必然要特别关注实然的“不是”。
面对这样一部真实的春秋历史,公羊家该如何思考呢?如何对待呢?此外,公羊家不仅要为真实的春秋历史而思,还要为书写的《春秋》而思。
再看看书写的《春秋》。先不管是谁作的,看看里面到底写了些什么。书写的这部《春秋》非常简单,近代学者梁启超按现代标准论道,以今代的史眼读之,不能不大诧异:第一,其文句简短,达于极点。每条最长者不过四十余字,最短者仅一字。第二,一条记一事,不相联属,绝类村店所用之流水账簿。每年多则十数条,少则三四条(《竹书记年》记夏殷事有数十年乃得一条者);又绝无组织,任意断自某年,皆成起讫。第三,所记仅各国宫廷事,或宫廷间相互之关系,而于社会情形一无所及。第四,天灾地变等现象,本非历史事项者,反一一注意详记。[1]我们不妨来看“隐公元年”的书写:“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娄仪父盟于眛。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书写的《春秋》非常简单地记录了一年当中的几件事,记事的要件倒是分明,有时间、地点、人物、事迹。但读起来,真的“绝类村店所用之流水账簿”。北宋宰相王安石读到《春秋》,就曾说“《春秋》漫不能通”,认为“于《春秋》不可以偏旁点画通”,还讥其为“断烂朝报”[2]。从事实来说,《春秋》如此简单,漫不能通是必然的。怪不得早在东汉时期,名儒桓谭就曾尖锐刻薄地指出:“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目思之,十年不能得知也。”(《新论·正经》)要不是《左传》详细记录当时历史实况,面对如此文本,圣人也奈何不了,十年不知又何足怪哉!换言之,要真的写史,就应该像《左传》那样。
面对这样一部已经书写的《春秋》,公羊家又该如何思考呢?如何对待呢?是把《春秋》当作一部真实的记载事实事件的史书,还是当作一部别有深意的经书呢?
(二)一统的汉代社会
公羊家的政治哲学思考,最直接的就是针对春秋与《春秋》两部历史。这是其一。还有其二是刚刚过去的秦帝国与深处其中的汉帝国。
分裂的春秋战国时代结束,就是大一统的秦帝国。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秦始皇的最大希望是:“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长治久安是一个政治大问题。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同时,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焚书非儒(后来还直接发展到“坑儒非孔”[3]),以吏为师:“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4],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由上可知,秦朝在实现军事一统与地域一统后,又实现了政治一统与思想一统。“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别黑白而定一尊”,“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法令出一”、“法令由一统”[5]、“一法度”、“事皆决于法”,“以吏为师”是秦王朝高度集权一统的标志性象征。可铁定的历史是,“万世传之无穷”不成,结果“二世而亡”。
紧接着是楚汉之争,最终楚败汉胜,汉王朝建立。为什么楚败汉胜呢?刘邦与列侯诸将的对话耐人寻味,暗藏“君道”的秘密:“高祖置酒雒阳南宫。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与天下同利”与“吾能用人杰”是刘邦打天下得天下的两大法宝,其中深藏儒家“与民同利”与“为政在人”的学理,前者“得民心”,后者“得君道”,但刘邦并不觉察这是儒家所重。
历史在反思中前进,儒家的价值也在反思中得到体现。刘邦与陆贾“马上得天下”与“马上治天下”的对话改变了刘邦对儒学的态度:“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史记·陆贾列传》)逆取顺守,文武并用是一条“长久”的政治铁律。秦始皇如果能够懂得攻守之势异的道理,“已并天下”之后,“行仁义,法先圣”,刘邦又怎么能打得了天下!陆贾的历史洞见与政治智慧非同凡响。极武而亡,极刑法易反,“皆决于法”和“以吏为师”不能德化人心,难与守成。
一旦实现军事一统后,如何实现政治一统与文化一统,是摆在汉帝王面前的首要问题。汉承秦制,政治一统暂时成为事实,但事实未必应该,还有一系列制度等着去改革,去建设。“皆决于法”和“以吏为师”的结果是“二世而亡”,按陆贾的说法,“文”更有利于治天下。文主要指礼乐制度,这是儒家所重所长。因而推行礼乐制度,就可以充分显示儒者的作用。“汉家儒宗”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为汉帝王尊儒埋下了伏笔:“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原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原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6]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汙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叔孙通与时变化,制礼进退,为刘邦找到了当皇帝的感觉。“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也真的善于“与时变化”,“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原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史记·叔孙通列传》)儒生能做官,不是简单地为了解决一个“谋食”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以做王者师,帮助帝王“守成”天下,解决一个“谋道”的问题。“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而“守成”又“知当世之要务”,“与时变化”,这样看来,儒者纳入到官僚体制内不过是迟早的事情。历史的实况是,“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史记·儒林列传》)。“征用”与“任儒”是有区别的,“征用”是储备人才,“任儒”是使用人才。直到汉武帝时,儒生才真正登上历史舞台,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公羊家公孙弘为天子三公,就是真的“任儒”行为。
历史有历史自身的逻辑。一统的汉帝国就像一统的秦帝国,也希望刘家天下能够“万世传之无穷”。“汤武革命”这种政治革命合法性的问题已经不需要再来讨论,而需要讨论的是如何论证和维护已经一统的政权,以及能提出真正可以有助长治久安的方略。[7]但哲学也有哲学自身的逻辑,总要立足现实,又超越现实。摆在公羊家面前的“两段实史”和“一本文史”,是公羊家必须面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