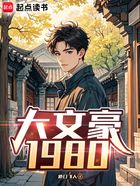
第6章 《诗刊》编辑部的争论
《诗刊》是在教员的亲自关怀下于1957年创刊的,在创刊之始,教员给首任主编臧科家的信中说:《诗刊》创刊,真好!
这本杂志后创刊之后停刊过一段时间,4年前复刊,彼时人们的思想,像洪水冲出堤坝一样,得到了解放,产生了一大批振奋人心的诗歌,比如叶汶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李发默的《呼声》,雷抒燕的《小草在歌唱》、边郭政的《对一座大山的询问》等,都发表在《诗刊》上。一位听众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呼声》时,因激动而把收音机捏碎了。
在1980年,《诗刊》是无可争议的第一诗歌杂志,发行量有五十万册之巨,举办的诗歌朗诵会,动辄就有几万人参与,影响力巨大。
可以说,如果有一个诗人有一篇诗歌发表在《诗刊》上,立刻就能在全国范围内打响名号,可以在各大高校骗吃骗喝骗睡......
不久之前,《诗刊》刊发了《令人气闷的朦胧》,这篇文章含蓄地批评了朦胧诗是故弄玄虚,故意让人读不懂。
这其实是《诗刊》编辑部对外发出的信号,他们需在支持创新与维护主流意识形态间权衡,既要发表赵振开、舒亭的先锋作品,又需刊发批判性评论......
一句话来说,涉及“改革”“现代化”等主题的作品被优先考虑。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张盐的《镜中》来到了京城《诗刊》编辑部。
日光穿过树杈,落在编辑部斑驳的木桌上,里面已经有不少人在工作,王燕生抱着一摞稿件推门而入,朗声道:
“来吧,让我们开始筛诗!”
王燕生抱着的这摞稿件是全国各地文学青年的心血:有的用复写纸,有的纸张沾着矿井的煤灰,还有的夹着粮票肉票当做编辑们的“审稿辛苦费”......
但编辑们可不会因为多塞了几张粮票就录用,在那个年代,过稿的标准很简单:
好的,留下。
差的,不要。
办公室里。
“这是什么狗屁,我爱你就像汽车爱上汽油?什么玩意都往这里寄,纯属是浪费邮票!”副主编邵燕祥摘下老花镜,审稿就是这样,要从无数的垃圾当中挑出金子,这就要求编辑们有足够的耐心与审美能力。
“‘此刻我就是叔本华,太阳也是我的高玩,月亮也是!’!纯属在哗众取宠!叔本华就一个太阳,你还月亮,你比叔本华还牛......”
老编辑吴家瑾的红笔重重划过一行来自吉省的诗,然后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发退稿信!”
“可读者来信说,年轻人就爱这种劲儿!”评论编辑丁国成翻出一沓信件,其中一封被泪水洇湿的信纸上写着:“感谢《诗刊》让我知道,诗可以不歌颂阳光......”
“......等等,都来看看这首诗,有金子了!”王燕生一拍桌子,兴奋地喊叫。
他的反应让大家都放下了手头的工作,聚了过来,编辑们都很忙,如果不是很好或者很有讨论度的作品,大家一般都不会互相打扰。
“唔,小王,难得见你这么激动,我看看......”邵燕祥戴上老花镜,七八个脑袋都凑了过来。
“白天鹅厂公用筏,看来是个工人的作品啊,《镜中》,名字还可以,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镜中》不长,读完只需到一两分钟。
于是两分钟之后,编辑部陷入了沉默,编辑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有先开口。
邵燕祥端起茶,悠哉悠哉地喝了一口,率先道:“都说说吧,什么看法?”
如同火星子落在干稻草上,编辑部霎时起火!
编辑柯岩似乎对这首诗不满意:“这首《镜中》,我反复读了,还是觉得像雾里看花。你们看看这开头——‘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这是什么逻辑?梅花落不落,和后悔有什么关联?怕不是故弄玄虚!”他敲了敲桌子,烟灰缸里的烟蒂震得跳了跳。
“还有这‘松木梯子’‘皇帝’的意象,突兀得很,像从古装戏里硬掰下来的碎片,跟现代诗的气质格格不入!而且,没有涉及到改革和开放,站位不够啊。”
吴家瑾掐灭烟头,猛地直起身:“老柯,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诗妙就妙在无理而妙!
‘梅花’哪里是实景?分明是心像!古诗里‘感时花溅泪’不也是这般?
这个叫张盐的作者不过是用古典意象嫁接现代人的精神困境——悔恨、疏离、镜花水月的人生,全被这‘梅花落南山’的意境托住了!”
“好一个梅花落啊!”
吴家瑾抓起稿纸,手指重重划过诗句,“你再细品结尾,‘梅花便落满了南山’,陶渊明的南山是归隐,张盐的南山是追悔,这是对传统的颠覆性重写!那‘皇帝’也不是真皇帝,分明是横亘在爱欲间的权力符号,是诗意的隐喻!”
“至于站位,好诗是不需要站位的!”
邵燕祥放下茶杯,慢悠悠道:
“二位争得热闹,这首诗看似支离,实则骨子里有楚辞的瑰丽、李商隐的隐晦,却又用蒙太奇手法剪碎了古典意境,拼贴成了一代人精神图景。”
邵燕祥手一指,“比如‘镜子’的意象——镜前的‘她’与镜外的‘我’,既是时空交错,又是虚实相生。这手法,倒让我想起卞之琳的《断章》,但这个叫张盐的人更狠,连叙事逻辑都打散了,只留情绪的气味。”
编辑柯岩眉头稍松,仍不甘心:“可这诗的结构像断线风筝!前脚还在‘游泳到河的另一岸’,后脚就‘回答着皇帝’,中间连个过渡都没有!普通读者怎么跟得上?”
邵燕祥大笑:“老柯啊老柯,诗要是都按起承转合写,和八股文有什么区别?你看庞德的《地铁车站》,不也是意象并置?张盐的跳跃,恰恰是诗的现代性!这‘危险的事固然美丽’,不正是青春与禁忌的张力?再说这‘镜中常坐的地方’,分明是博尔赫斯式的迷宫,镜子映照镜子,悔恨叠加悔恨——这才是高级的抒情!”
王燕生那时还是个小编辑,他试探着说,要不请严主编也看看?
于是在一群人的簇拥之下,王燕生捧着一张纸,来到了主编严辰的办公室。
严辰,是《诗刊》创刊时的元老之一,1980年代初期继续担任主编,主持刊物整体方向。其严谨的审稿风格和对诗歌艺术的坚持,为《诗刊》奠定了高质量的基调。
“呦,来干什么,要造我的反啊?”严辰放下手里的报纸,打趣道。
“主编,我们发现了一首诗,我们拿不准,您给看看。”
严辰看起了这首诗,良久之后,他才抬起头,看着一屋子大气不敢出的编辑们,坚定地开口:
“这是一首好诗,我们《诗刊》就是寻找好诗的,当然要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