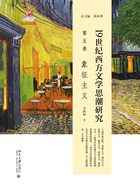
第三节 魏尔伦、马拉美与颓废派的诞生
魏尔伦在1882年和1883 年,首先在《新左岸》杂志上获得了声誉。如果回顾特雷泽尼克的文章,可以看到,他已经与“大师”的称号联系在一起了,马拉美在特雷泽尼克论科佩的文章中也已经出现,而且被认为是“原创的”1。但是真正成为大师,不仅因为他们艺术的造诣,更离不开其实际的影响力。从1883年开始,魏尔伦和马拉美迎来了新的文学地位。
一、魏尔伦的《被诅咒的诗人》
1883年8月,魏尔伦行动了。他在24日的《吕泰斯》 ( Lutèce,《新左岸》杂志的新名)上发表《被诅咒的诗人——特里斯坦·科比埃尔》一文,随后以《被诅咒的诗人》为标题刊发系列文章,并最终以《被诅咒的诗人》为标题出版成书。最早的一篇文章是该系列文章的关键,魏尔伦在这里宣扬一种反传统、反道德的主义,他称科比埃尔是“最特别的蔑视者”,是“没有任何天主教信仰的布列塔尼人,但是信仰恶魔”2。这种反道德的倾向,正是波德莱尔率先尝试的,文中的“恶魔”一词,实际上概括了《恶之花》的作者总的风格。在《恶之花》卷首的《给读者》 ( “ Au lecteur” )一诗中,人们读到了这样的告白:
正是魔鬼扯住摆弄我们的线!
我们受着丑陋的事物的诱惑;
一天天向地狱更近一步堕落,
没有畏惧,穿越臭熏熏的黑暗。3
波德莱尔表示自己不畏惧魔鬼的诱惑,但他在上帝和魔鬼之间摇摆,仍然在反思。魏尔伦的《被诅咒的诗人》的重要之处,并不在于诗人提出了什么全新的诗学理念,而在于他大胆地树起了波德莱尔主义的旗帜。时过境迁,在思想混杂、多元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魏尔伦似乎比波德莱尔有了更大的底气,他将这种恶魔主义当作积极的价值来品味。颓废从此开始告别布尔热的消极的含义,成为具有美学价值的诗歌风格。比耶特里肯定魏尔伦的书“对小社团的新来者有决定性的影响”,并且对后来颓废派的发生起到“催化剂的作用”4。
科比埃尔并不是重要的诗人,但对他的论述,给后来的文章奠定了一个基调。自1883年10月5日起,魏尔伦关于兰波的系列文章开始连载。这是兰波第一次在法国诗坛的重要场合亮相,对于后来兰波的声誉至关重要。魏尔伦并没有忘记这位远去的诗人,他想为兰波做点什么。因为他对兰波的思想和创作都非常熟悉,所以论兰波的系列文章非常成功。卡恩在这方面有发言权,他指出:“在这部书中的所有人中,兰波是魏尔伦透露最多的。”5
魏尔伦从兰波早期纯净、清晰的诗开始谈起,到了11月10日的这一期,一个颓废的兰波的形象就出现了。魏尔伦正式将兰波称作“被诅咒的诗人”,还注意到兰波与魏尔伦结识后诗风的变化:
经过几次在巴黎的逗留,经过随后多少有些可怕的漂泊后,兰波先生突然改弦更辙,他采用纯真的风格、特别朴素的风格写作,只运用半韵、模糊的词、简单的或者平常的语句。他成就了细腻的奇迹、真正的朦胧,以及因为细腻而产生的近乎无法估量的魅力。6
这里模糊、朦胧的语言和风格与颓废有不少联系,尽管兰波的诗无法用颓废一词概括尽。
魏尔伦还注意到兰波的一部手稿,“它的名字我忘掉了,它含有奇特的神秘性,以及最敏锐的心理学的观察”7。这里的手稿可能指的是《彩图集》 ( Les Illuminations) 。其中“奇特的神秘性” ,属于波德莱尔颓废六事中的第四条,它指的是兰波对超自然感觉世界的书写。除此之外,魏尔伦还提到了兰波的《地狱一季》,以及兰波的自由精神。因为魏尔伦的文章,兰波的诗在颓废派的发展中发挥了影响。
兰波之后,魏尔伦还讨论了马拉美。尽管卡恩说“魏尔伦描述的马拉美,是不全面的、陈旧的”8,但是这对马拉美的文学声誉有很大提升。马拉美比魏尔伦年长2岁,在文学生涯上却比魏尔伦失意得多。他以教书(甚至家教)为生,颠沛流离,居无定所,无奈之下曾经抱怨道:“我的天啊,讨生活是多么痛苦啊! 要是人们能讨到生活也好啊! 我们的社会让诗人们干什么职业啊!”9到1883年的时候,他在诗歌事业上也就只有一本薄薄的《牧神的午后》 ( L’Après-midi d’un faune) ,总印量为195册,仍然默默无闻。相比之下,魏尔伦则出版了6部诗集,早已成名。因为魏尔伦的评论,马拉美的命运发生了扭转,他的声望在迅速攀升。
1883年11月,魏尔伦还在《吕泰斯》推出“被诅咒的诗人”专刊。该刊这一期标题下有“ Les Poète maudits”三个大字。并印有三人的木刻肖像。马拉美坐在沙发上,右手放在书本上,夹着一只点着的烟。他的眼睛和头发比较清晰,但是胡子和嘴完全是模糊的。中间是科比埃尔,照片太小,眼睛好像下视。最左边是兰波的像,脸比本人照片要长一些,稚气的眼睛望着前方。这一期没有重要的理论和诗作,其实是为了给即将出版的书做广告。但它扩大了《被诅咒的诗人》的名气,将颓废文学的思想传到巴黎的诗坛,以至于在1884年,已经有批评家用“马拉美主义”这个词来批评《吕泰斯》的颓废倾向,认为《吕泰斯》是颓废文学的主阵地。该刊主编特雷泽尼克不得不为杂志辩护:“我们既不是自然主义者,也不是浪漫派,也不是魏尔伦派,也不是马拉美主义者,不是任何派别。”10《吕泰斯》并不是纯粹的颓废派杂志,这一点特雷泽尼克是对的,但是在1883年前后,《吕泰斯》确实是颓废诗人以及后来的象征主义诗人(比如莫雷亚斯、拉弗格)最重要的发表园地,也无怪乎报刊界有一些风言风语。
魏尔伦不仅在《被诅咒的诗人》中推出了上述几位颓废诗人,他也将自己打扮成了“被诅咒”者。这几篇文章并没有正面提及魏尔伦,但它们都是在魏尔伦的人格魅力以及颓废诗学下被探讨的。被诅咒的诗人,不能不加上魏尔伦自身。结集出版的该书中,实际的人物因而有四个。这四人可以看作是19世纪80年代最早的一批颓废诗人。但因为科比埃尔在1875年就去世了,除去他,最早的颓废诗人剩下的就是:兰波、马拉美和魏尔伦。理解三位诗人在颓废文学和象征主义思潮中的辈分,对于看清后来颓废者和象征主义诗人的论争非常有帮助。
另外,魏尔伦并不是用“被诅咒”来代替“颓废”,他对颓废也做过直接的思考。在1884年3月29日出版的《吕泰斯》中,魏尔伦说:“颓废这个词究竟想说什么? ……打倒虚假的浪漫主义,让纯粹的、顽强的(同样有趣的)诗行永存!”11在这一句话的语境中,“被诅咒”的几位诗人,在风格上被评价为是平和的、完美的。这是一个悖论。魏尔伦原本想用这个标题树立反传统的、个性的诗风,现在又用中庸的价值来洗去那些刺眼的色彩。魏尔伦是矛盾的。但是引文中的话又能说出颓废文学的一些特征。比如“纯粹的”诗行,以及对“虚假”的抵抗,它们显示出魏尔伦挖掘内在感受的决心。
总的来看,在1883年到1884年间魏尔伦的《被诅咒的诗人》已经赢得了比较广泛的关注。魏尔伦曾经回顾过自己的这部作品:“ (我的)这些诗因为在艺术上的真诚和内容上的质朴,而得到他们的喜欢。碰巧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我推出了《被诅咒的诗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科比埃尔和马拉美,尤其是为了兰波。这个小册子获得了所有人们希望的成功,以及随之而引发的一些争论。”12在魏尔伦的魅力下,颓废派的正式诞生好比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二、于斯曼的《逆流》
魏尔伦的小册子《被诅咒的诗人》 1884年3月出版,两个月后,于斯曼的《逆流》面世。于斯曼的出现,对于颓废派的成立,对于象征主义思潮的发展,都非常关键。他有力地补充了魏尔伦的影响力,让颓废的火苗烧得更旺。于斯曼原本是自然主义作家,他在当时对自然主义有些不满:“自然主义在同一个圆圈中缓慢地费力转动着石磨。每个人曾积累的观察数量,无论是对自己的,还是对其他人的,都开始枯竭。”13通过于斯曼对左拉小说的批评,可以看到于斯曼渴望抒写人的灵魂,而这种目标在他看来是自然主义无法办到的。他“模模糊糊地”把《逆流》写出来,并没有清晰的理念,但这却成就了颓废文学一时的经典。
于斯曼的《逆流》与传统的小说非常不同,它没有情节的发展,主要写人物的心情和感受。布尔热提出的“不完整的经验”说14,应该与这种特征有关系,因为感受只是人物片段的生活。这些感受又多是病态的,比如主人公德塞森特精神失常,他不止一次地发生“神经官能症”,也多次出现感官的幻觉:“一个下午,气味的幻觉一下子突显了出来。他的卧室飘荡着一股鸡蛋花的清香;他想证实是不是有一瓶香水忘了盖上盖,泄露了气味;然而,房间里根本就没有香水瓶;他走到书房,走到餐室:香气依然如故。”15这种精神上的病态,不仅是波德莱尔具有的,也是随后的颓废诗人普遍具有的。布尔德曾经讽刺这些颓废诗人,有“对疏离其他人的神经症的需要”16。这种现象确实存在。那么,能不能说明颓废的作品,就是病态的作品,进而就是不真实的作品呢? 这个思考涉及颓废文学的价值判断,非常重要。当颓废诗人(作家)们,从外在的现实退回内在的现实后,内在现实的神秘和丰富,就成为他们关注的中心,因而幻觉的写作就不可或缺了。尽管幻觉写作往往发生于神经症那里,但是文学想象、题材借用的情况是比较多的。没有必要认为颓废诗人都是精神病人,更不必主张幻觉写作就一定是不真实的。
于斯曼的小说在颓废文学史上的价值,并不只限于作品本身情调的忧郁、病态感受的渲染,它对于颓废文学的评价,也加速了颓废概念的传播。于斯曼借德塞森特的嘴,道出了他对波德莱尔的崇敬之情:
德塞森特越是重读波德莱尔,就越是在这位作家身上认出一种难以表述的魅力,在一个诗歌只用来描绘人与物表象的时代,这一位却依靠一种肌肉丰富的语言,成功表达了无法表达的东西,他的语言比任何其他语言都更拥有那种美妙无比的力量,能以表达上的一种奇怪健康,来确切指明疲倦的精神和忧伤的心灵那最不可捉摸、最战栗的死气沉沉的状态。17
波德莱尔即是德塞森特的镜子,它不仅照见自己“死气沉沉”的生活,也照见颓废文学的道路。这种道路是在对抗自然主义的过程中走出来的,所谓“描绘人与物表象的时代”,就是以自然主义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时代。而波德莱尔则“深入了心灵底层”,然后表达那些“无法表达的东西”。自然主义与象征主义思潮的对立,在于斯曼身上体现得非常典型,他就是这种对抗的代表。巴尔曾对于斯曼的意义做过思考:“ 《逆流》一书是一种反叛行为,是对自然主义开的一枪,是耗空了的文学的没落标志。”18尽管这并不是第一枪,却是1884年开的最重要的一枪。
魏尔伦的先驱地位,在《逆流》中也得到了承认。尽管于斯曼发现魏尔伦存在对李勒( Leconte de Lisle)的模仿,以及“浪漫修辞学的练习” ,但是他仍然能从这个兄长的十四行诗中发现“真正的个性”19。于斯曼是马拉美的崇拜者。马拉美的地位在他那里要远远高于魏尔伦。于是马拉美的诗作在德塞森特的书房中得到了优待:“除了这些诗人以及斯特凡·马拉美,德塞森特很少被诗人吸引。马拉美当然是例外,他特别交代仆人把马拉美的作品单搁一边,另行摆放。”20于斯曼表达了对《海洛狄亚德》( “ Hérodiade” )的痴迷,这部终其一生都没有完成的诗剧,像有神秘的魅力。甚至,于斯曼还引用了诗中的段落,仔细品味。所有这些内容,都成为布尔热“当前的文学青年受到了神秘感的折磨”一语的注脚21。
波德莱尔的感应说,在这部书中也得到了回应。这个现象是非常有意味的。魏尔伦受到了波德莱尔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主要是情调、词语和形象上的,魏尔伦不太关注那个先驱者的感应说。横向和纵向的感应,相对应的是象征和通感,这两样在魏尔伦的作品中并不多见。因而,魏尔伦给后来的颓废文学的影响,主要是情调、语言和音乐性,但是象征和通感手法往往付诸阙如。于斯曼的出现,弥补了魏尔伦的不足。象征和通感,在于斯曼的书中,被换成一个名字:类比。这一个词,就集合了波德莱尔两个词的意义:
他感觉到事物中那些最遥远的相似性,便常常以一个靠了某种类比效果,就能同时给出形式、气味、颜色、质地、光亮的词语,来表明物体或生命体,而假如这些物体和生命体只是由其技术名称简单指明的话,那他就还得使用众多不同的形容词来修饰它们,以揭示它们所有的面貌,所有的细微差别。22
这里还可以看出,如果说于斯曼是典型的颓废派作家,那么颓废派作家并不完全像魏尔伦那样,把象征留给后来的象征主义诗人。颓废派同样关注象征。下文可以看到不少颓废派诗人重视象征手法。因而颓废派和象征主义派并不是对立的流派,它们更多是圈子的不同,而不是主义的不同。如果不拿单个的诗人比较,比如用魏尔伦来比莫雷亚斯,而是将更多的人物纳入进来,那么,颓废派和象征主义派很大程度上是共通的。
三、弗卢佩的《衰落》
1884年7月,德普雷( Louis Desprez)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最后的浪漫派》 ( “ Les Derniers romantiques” )一文。这篇文章虽然没有使用“颓废”的字眼,但他讨论的却是颓废文学。德普雷注意到魏尔伦与波德莱尔的渊源:“他像波德莱尔一样,在肉欲的寻求中混入了宗教感情;像波德莱尔一样,他求助于微妙的比较,他将声音与色彩融合,沉溺在古怪的梦幻中。”23这里首先提到的是魏尔伦主题和情调上的特点,既寻求人间的放纵生活,又渴望超自然的世界。后半句中的“微妙的比较”像前文说过的那样,可换为“微妙的象征”。象征本身就是梦幻的入口。德普雷还注意到了马拉美,他认为马拉美在语言和节奏上给魏尔伦带来很大影响。这种判断失之偏颇。魏尔伦的诗很早就成熟了,在1884年他在文学上的地位也比马拉美高,魏尔伦师法马拉美的可能性不大。
11月,巴雷斯在《墨迹》 ( Les Taches d’encre)杂志上发表《夏尔·波德莱尔的疯癫》 ( “ La Folie de Charles Baudelaire” )一文。巴雷斯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分析波德莱尔的精神,也就是他内在的颓废。他发现波德莱尔有一种“秘密的直觉”,这可以生成敏锐的感受力,而波德莱尔和后来的诗人,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感觉的解释者”。巴雷斯的判断是精准的。颓废文学在当时的主要表现就是对细腻的内在感情的传达。象征就是它的工具。不过,象征在巴雷斯的文章中也像之前说过的一样,被称作“类比”:
通过类比,我们在艺术作品中做到了取消一切的构造,以便让感觉首尾相接,或者混合在一起,就好像它们呈现在诗人眼前,根据个人的性情和习惯等等,通过最古怪的联系并置在一起。理性所能做的只是这个。唯有类似性情的感觉主义者能够相互理解。24
文中说的感觉的“并置”,确实是颓废者和象征主义诗人主要的技巧。通过感觉的并置,诗人尽可能地消除诗句中的理性和逻辑的成分,尽可能地将语言与感觉联系起来。后来美国意象派( The Imagist School)提出的意象的并置理论,强调的也正是感觉的并置,其源头正在于此。
1885年4月,布尔热在《吕泰斯》上发表《当代诗》 ,称颓废文学为“年轻的文学” 。他没有使用1881 年的颓废一词,不知为何。但布尔热延续了之前的判断,认为颓废者们“依附”波德莱尔。但是在之前的研究中。布尔热的关注点在波德莱尔。在这篇文章中,魏尔伦、于斯曼的名字都出现了。他注意到魏尔伦尝试传达模糊、微妙的情调,而于斯曼则关注细微的感受。布尔热的这篇文章,并没有做出大的成绩。真正在颓废派的成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衰落》 ( Les Déliquescences)一书的出版。
《衰落》严格来看,是一个恶作剧。它标出的作者是弗卢佩( Adoré Floupette) ,实际上这个人名是杜撰的,它是两个人的集体名称,一个是博克莱尔( Henri Beauclair) ,一个是维凯尔( Gabriel Vicaire) 。这两位都是诗人,他们读过魏尔伦和于斯曼的作品,于是就有了这本仿作。康奈尔说该书“给颓废作家一个范例,又因为其风格的古怪给保守批评家一个靶子”25。但揣摩两位诗人的初衷,还是为了嘲弄颓废诗人。不过,因为这本书,颓废文学声势大涨,又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衰落》于1885年5月出版,次月又印出带序的版本。在署名塔波拉( Marius Tapora)的序言“作者生平”中提到,弗卢佩1860年出生,曾经喜欢诗人拉马丁。在1885年,塔波拉曾和弗卢佩做过诗歌的讨论。在否定自然主义后,有了下面的对话:“我变得不安了,我未经思考,大声说:‘但是,最终剩下的是什么?’他注视着我,用一种低沉带点颤抖的声音说:‘剩下的是象征。’”26这个对话倒很能说出颓废派的追求,他们渴望摆脱现实,进入象征的世界。该书的标题也能体现颓废的含义。维尔( Vir)曾说:“人们谈论衰落、没落、颓废。谈论没有价值的东西,以及荒唐的词语。”27衰落、没落,原本就与颓废是同义的。正文的诗选中,也出现过这个词,可以看作这个标题的来源:“所有我的存在/都在衰落!!”此书之后,衰落一词渐渐成为颓废的代名词。不过,书中也出现了颓废一词,有一首诗名字就叫做《颓废者》 ( “ Décadents” ) 。
维尔还提到过“荒唐的词语”,这句话在《衰落》的前言中有更具体的解释。弗卢佩曾说:
词语像你一样是活的,比你还活;它们前进,它们像小船一样有脚。词语并不描绘,它们就是绘画本身,有多少种词语,就有多少种色彩;有绿的、黄的和红的,就像药店里的大口瓶一样,那里有塞拉芬剧场梦幻的色调,药剂师可想象不到。28
这句话涉及两个“荒唐”的地方:第一个是反对描绘。第二个是词语的色彩。反对描绘即是针对巴纳斯派和自然主义作家,即是争取词语的暗示力。词语的色彩,明显是“抄袭”魏尔伦《被诅咒的诗人》中引用兰波的《元音》 ( “ Voyelles” ) 。后者写道:“ A黑,E白,I红,U绿,O蓝。”29弗卢佩将它借用过来,认为词语像色彩一样众多。最后一句中的“塞拉芬剧场”,出自波德莱尔的《人工天堂》。所谓塞拉芬剧场据说是上演皮影戏的剧场,以魔幻著称,这里则说明词语色彩的变幻无穷。弗卢佩明显放大了兰波的话,不用过多解释,人们可以明白它含有的嘲讽的语气。
词语的颓废在正文的诗作进行了实践。比如《象征田园诗》 ( “ Idylle symbolique” )中的一节:
被精神的疏懒
催眠的多情女郎们,
温存的小伙,在黑色的倒影中,
玫瑰色的放肆……30
诗中出现了不完整的句子,而且选用的词语也有了不同寻常的结合,比如“玫瑰色的放肆” 。在《颓废者》一诗中出现了这样的诗句:“我们的神经和我们的血液一文不值,/我们的头脑在夏天的风中熔化!”这首诗,与马拉美的《青空》(“L’Azur”)非常接近,都属于自我消失的主题。康奈尔认为弗卢佩诗中的句法和用词“受到魏尔伦和马拉美的启发”31,这是有根据的。正是在魏尔伦、马拉美(可能还有于斯曼)的诗学、作品的参照下,博克莱尔和维凯尔才写了这部诗集,并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
魏尔伦、马拉美、于斯曼、弗卢佩,或许他们在1885年之前,没有哪一位对于颓废派的成立具有绝对的影响力,但是当这些力量都汇合起来时,颓废的势力就形成大潮了。文学风气在1885年的巴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该年5月17日,阿雷纳( Paul Arène)发表《颓废者们》一文,见证了颓废派最初的诞生史:“颓废是一种时尚。人们不无偏颇地带着愉快的热情变成颓废者。我认识的一个勇敢的小孩,脸色红润,面颊丰满,正是十六岁的风华,自称自己是绝对的颓废者。”32虽然文中没有出现颓废派一词,但大可不必纠结术语本身。阿雷纳已经看到颓废文学的流行,而引领风潮的主要诗人有意无意就会形成一个流派。在1885年5月,颓废派已初具雏形,有了主要的代表人物:魏尔伦和马拉美,也有了重要的作品,比如《被诅咒的诗人》《逆流》《衰落》等。它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是有组织的颓废派还未出现,颓废派仅仅处于一种初级阶段。
但是形势很快就气决泉达了。在1885年8月,距《衰落》出版只有三个月,颓废派们就有了比较正式的认证了。认证者并不是颓废诗人自身,而是一位对颓废派有所非议的批评家布尔德。他在《时报》上发表《颓废诗人》 ( “ Les Poètes d'cadents” )一文,见证了一个流派的正式诞生。
四、颓废派的正式诞生
在布尔德之前,颓废诗人的名称已经出现,可是人们对它的成员并不清楚。布尔德的文章表明对颓废诗人的认识渐渐明确下来。布尔德说得明白:“尽管像从前的巴纳斯诗人一样,他们既没有共同的出版社,也没有合集,以让他们的团体显得界线分明,但这些留心于诗的人知道颓废者这个讽刺的词所指为谁。”33直到该年8月,颓废诗人并没有出版选集,也没有创办真正的机关杂志,诗人们各自为政。即使这样,布尔德说细心的读者已经明白颓废诗人“所指为谁” 。自1883 年以来,随着诗人们的不断努力,颓废派的圈子渐渐明朗了。布尔德在文中已经用“流派”来称呼他们,他列出六位他认可的颓废诗人,其中有魏尔伦和马拉美,这两位诗人被当作颓废派的两大支柱。还有莫雷亚斯。直到目前,莫雷亚斯的诗歌活动还未加以考察,不过把这个问题放到下一节,会更恰当一些。第四位是洛朗·塔亚德( Laurent Tailhade) ,这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虽然后来与象征主义思潮关系不大,但在1884年至1885年间,曾在《吕泰斯》 《黑猫》 ( Le Chat noir)等杂志上发表作品,也是活跃分子。第五位是维涅( Charles Vignier) ,魏尔伦的弟子,与《吕泰斯》 《独立评论》等杂志有些关系,也是后来成立的《象征主义者》杂志的成员。第六位是莫里斯,我们已经知道他和《吕泰斯》杂志的渊源,尤其是他与魏尔伦的不打不相识。这六位诗人,再加上弗卢佩,共是七位。按照布尔德的说法,这几位诗人就构成了最完整的颓废派。但在莫雷亚斯的回应文章中,弗卢佩被去掉——这当然好,因为弗卢佩原本就不存在——于是还是六位。这个名单还过于狭窄,但这是该流派的第一次“集体亮相”,意义重大,因而莫雷亚斯称布尔德是颓废派的“严肃的批评家”34。
布尔德还对颓废派的美学特征进行了总结。他首先看到颓废诗人精神上的病态。因为渴望精神病,所以“健康本质上是平庸的、有益的,适于粗人”,而且这种病态还带来对宗教的亵渎,尽管天主仍然存在于他们的作品中,因为“没有天主,他就不会有撒旦;而没有撒旦,他就不可能成为撒旦式的诗人”35。波德莱尔的宗教观,并不能代表所有的颓废诗人,魏尔伦出狱后,就在兰波眼中成为虔诚的宗教徒,马拉美从未亵渎过宗教。这里布尔德明显以偏概全了。莫雷亚斯曾调侃地说:“让布尔德先生放心,颓废派诗人不想多亲吗啡女神苍白的嘴唇;他们还没有吃掉带血的胎儿;他们更愿意用带脚玻璃杯喝水,而非用他们祖母的头颅,他们也习惯于在冬天阴暗的夜晚写作,而非与恶魔往来,以求在巫魔会( le sabbat)期间,说可怕的亵渎神明的话。”36布尔德对颓废派是存有敌意的,这种敌意表明颓废派在他眼中有鲜明的异端色彩。
颓废派题材和形象的古怪与反常也得到了注意。布尔德认为颓废诗人厌恶自然,在他们那里,森林不是绿色的,而是蓝色的;女人不是鲜活的,而是贫血的、惨淡的:“患精神病前妄想的性情,早早堕落的处女,正在腐烂的社会的粪堆上像霉菌一样绽放的罪恶,发臭的文明的一切娴熟的堕落,这一切对于颓废派来说,都自然而然地具有罕见事物的魅力。”37这种对新奇题材的寻求,在《逆流》和《衰落》两部作品中,确实都存在,无需争论。不过,莫雷亚斯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这就是美。莫雷亚斯引爱伦·坡给美下的定义,说明运用这些题材和形象的目的,并不是审丑,而是从中获得灵魂的狂喜。他还反驳布尔德:光明美好的事物在生活中并不常见,意谓丑陋、阴暗的事物才是真实,而所谓美好的事物往往给人“一种自我欺骗的悲伤,一种相反的悲伤”38。
布尔德还发现颓废派在诗律解放上所做的工作。他注意到巴纳斯诗人邦维尔对诗律规则的批评,以及对绝对自由诗行的呼吁,而这种呼吁等来了颓废诗人。后者不但废除了阴、阳韵的交替,要么专门使用阴韵,要么专门使用阳韵,而且有时完全不押韵。在这方面,魏尔伦的《无言的浪漫曲》成为负面的例子。奇怪的是,布尔德并没有讨论魏尔伦在诗行音节数量和语顿上的自由试验,押韵在他的辞典中与诗律是等义的。 1885年,自由诗还未诞生,这足以给布尔德短暂的安全感。
总之,布尔德在成员构成、流派特征、题材和形式上,都给颓废派做了总结。颓废派第一次清晰地呈现给世人。但布尔德并不是颓废派的支持者,他不无鄙夷地观察这个新流派,为它没有未来感到惋惜。德拉罗什( Achillle Delaroche)对它有比较中肯的评价:“这篇文章,尽管它付出认真的努力,以求理解新的思想,但对于引发一个回应来说,它含有相当多的错误和不公。”39比如它认为颓废派是“濒死的流派” ,实际上它的生命力才刚刚展现出来。
布尔德之后,颓废派迎来了流派的实质性建设的阶段。阿纳托尔·巴朱( Anatole Baju )首先在 1886 年 4 月 10 日创办了《颓废者》 ( Le Décadent)杂志,紧接着雷蒙( E. G. Raymond )任主编的《颓废》 ( Le Décadence)于该年10月1日出现。 《颓废者》1886年出了第一个系列,到该年12月4日时,已经出到第35期。 1887年改版。 《颓废》则是一个短命期刊,为《斯卡潘》 ( Le Scapin)杂志的子刊,只出了3期便消失了。这两个刊物旨在宣传颓废文学,《斯卡潘》的社论曾指出《颓废》是颓废派的“专属刊物”40。这两个刊物不仅专门宣传颓废文学的理念,也推动了颓废文学的创作和发表。更重要的是,它扩大了布尔德的颓废派六人小组的范围,又接纳了许多新的面孔。在1886年10月举办的颓废者大会上可以发现,颓废派已经成为与浪漫主义、古典派、自然主义并列的四大流派之一了。
1 Léo Trézenik, “François Coppée”, La Nouvelle rive gauche, 52 (26 janvier 1883), pp. 3—4.
2 Paul Verlaine, “Les Poètes maudits: Tristan corbière 1”, Lutèce, 82 (24 août 1883), p. 2.
3 Charles Baudelaire, Œuvres complètes, tome 1, ed. Yves Florenne, Paris: Le Club français du livre, 1966, p. 761.
4 Roland Biétry, Les Théories poétiques à l’époque symboliste, Genève: Slatkine Reprints, 2001, p 18.
5 Gustave Kahn, “Chronique de la littérature et de l’art”, La Revue indépendante, 9. 24 (octobre 1888), pp. 123—124.
6 Paul Verlaine, “ Les Poètes maudits: Arthur Rimbaud ” , Lutèce, 93 ( 10 novembre 1883), p. 2.
7 Ibid.
8 Gustave Kahn, “Chronique de la littérature et de l’art”, La Revue indépendante, 9. 24 (octobre 1888), p. 123.
9 Stéphane Mallarmé, Correspondance complète: 1862—1871, Paris: Gallimard, 1995, p. 328.
10 Léo Trézenik, “Chronique lutécienne”, Lutèce, 150 (7 décembre 1884), p. 1.
11 Paul Verlaine, “Avertissement”, Lutèce, 113 (29 mars 1884), p. 2.
12 Paul Verlaine, “Anatole Baju”, Les Hommes d’aujourd’hui, 332 (août 1888), p. 2.
13 于斯曼:《逆流·作者序言》,余中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页。
14 Paul Bourget,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Lutèce, 169 (26 avril 1885), p. 1.
15 于斯曼:《逆流》,余中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145页。
16 Paul Bourde, “Les Poètes décadents”, Le Temps, 8863 (6 août 1886), p. 3.
17 于斯曼:《逆流》,余中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187页。
18 André Barre, Le Symbolisme, New York: Burt Franklin, 1968, p. 132.
19 于斯曼:《逆流》,余中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241页。
20 于斯曼:《逆流》,余中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246—247页。
21 Paul Bourget,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Lutèce, 169 (26 avril 1885), p. 1.
22 于斯曼:《逆流》,余中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257页。
23 Louis Desprez. “ Les Derniers romantiques” , La Revue indépendante, 1 ( juillet 1884 ) , p. 219.
24 Maurice Barrès, “La Folie de Charles Baudelaire”, Les Taches d’encre, 1 (novembre 1884), pp. 16—17.
25 Kenneth Cornell, The Symbolist Movement, Hamden, Connecticut: Archon Books, 1970, p. 36.
26 Adoré Floupette, Les Déliquescences, Byzance: Lion Vanné, 1885, p. 26.
27 Vir, “La Décadence”, Le Scapin, 1 (1 sep. 1886), p. 4.
28 Adoré Floupette, Les Déliquescences, Byzance: Lion Vanné, 1885, p. 43.
29 Arthur Rimbaud,Œuvres complètes, ed. Antoine Adam, Paris: Gallimard, 1972, p. 53.
30 Adoré Floupette, Les Déliquescences, Byzance: Lion Vanné, 1885, p. 60.
31 Kenneth Cornell, The Symbolist Movement, Hamden, Connecticut: Archon Books, 1970, p. 37.
32 Paul Arène, “Les Décadents”, Gil Blas, 7 (17 mai 1885), p. 1.
33 Paul Bourde, “Les Poètes décadents”, Le Temps, 8863 (6 août 1886), p. 3.
34 Jean Moréas, “Les Décadents”, Le XIXe Siècle, 4965 (11 août 1885), p. 3.
35 Paul Bourde, “Les Poètes décadents”, Le Temps, 8863 (6 août 1886), p. 3.
36 Jean Moréas, “Les Décadents”, Le XIXe Siècle, 4965 (11 août 1885), p. 3.
37 Paul Bourde, “Les Poètes décadents”, Le Temps, 8863 (6 août 1886), p. 3.
38 Jean Moréas, “Les Décadents”, Le XIXe Siècle, 4965 (11 août 1885), p. 3.
39 Achillle Delaroche, “Le Annales du symbolisme”, La Plume, 3. 41 (1 janvier 1891), p. 16.
40 Le Scapin, “Le Sac de Scapin”, La Décadence, 1 (1 octobre 1886), p.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