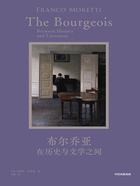
二、失调(Dissonances)
布尔乔亚文化。单一(One)文化?“五彩斑斓的(Multicolored)——[用德语说即]bunt——[文化]……方可服务于我在显微镜下观察的这个阶级”,[1]彼得·盖伊(Peter Gay)在即将结束其五卷本的《布尔乔亚经验》(The Bourgeois Experience)时写道。“经济利益、宗教信仰、思想信念和社会地位的竞争以及妇女地位等议题,都成了布尔乔亚与布尔乔亚之间争斗的战场”,在后来的一次回顾中他补充说,分歧如此尖锐,以至于“引人怀疑,它根本不是个可定义的单一实体”。[2]对于盖伊来说,所有这些“醒目的变异”,[3]都是19世纪社会变化加速的结果,因而也具有布尔乔亚史的维多利亚阶段的典型特征。[4]但在布尔乔亚文化的二律背反里,可能还有一个更为长远的视角。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有一篇关于圣三一教堂(Santa Trinita)中的萨塞蒂礼拜堂(Sassetti Chapel)的论文,取法于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在《佛罗伦萨史》(Istorie Fiorentine)中对洛伦佐的刻画——“考虑到他生活中轻松的一面和严肃的一面,就会看到在他这个人身上共存着几乎不可能调和[quasi con impossibile congiunzione congiunte]的双重人格”。[5]瓦尔堡注意到[萨塞蒂这位]——5
美第奇家族治下的佛罗伦萨公民,兼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既有理想主义者的——不管是中世纪基督教的,还是浪漫主义骑士精神的,抑或古典主义新柏拉图主义的—性格,又有世俗性的、实用性的、异教徒的伊特鲁里亚(Etruscan)商人的性格。他的生命原始却和谐,这个神秘的生灵,欣然接受一切心灵的冲动,把它们视为自己精神领地的延伸,从容不迫地开展,从容不迫地运用。[6]
一个神秘的生灵,理想主义的且又是世俗趣味的。布尔乔亚的另一个黄金时代,位于从美第奇时代到维多利亚时代这段历史的中途,在书写这个时代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所考虑的正是这种“特殊的共存”,它允许
俗世的与神职的统治者去容忍一个本来已矛盾不堪的价值体系,一场存在于占有欲和禁欲主义之间的不息的争斗……肉体上自我放纵的积习与风险投资的刺激,在荷兰贸易经济中根深蒂固,它们自身从被指定守护古老的正统的人那里,激发出所有那些警告的声音与郑重的判断……明显对立的价值体系的这种特殊的共存……使他们得以游走于神圣与世俗之间,把它们作为需要或良知的要求,而不需冒险在贫穷或毁灭之间作残忍的选择。[7]6
肉体的放纵,古老的正统:扬·斯蒂恩(Jan Steen)的画《代尔夫特的市民》(Burgher of Delft),画中人从沙玛的书的封面看着我们(图1,见右页):一个粗壮的汉子,坐着,一袭黑衣,在他的一侧是他女儿的金银服饰,在他的另一侧是一个乞丐褪了色的衣服。从佛罗伦萨到阿姆斯特丹,圣三一教堂里的那些面孔上那种率真的生命力已经暗淡了;这位市民了无欢乐,被钉在椅子上,仿佛陷身于困境之中,“道德的前后拉扯”(又是沙玛)让他无精打采:从空间上说他靠近女儿,但并没有看她;他面朝着那个女人的方向,实际上又没有跟她说话;他双眼低垂,无所关注。该怎么办呢?

图1
马基雅维利的“不可能的调和”,瓦尔堡的“神秘的生灵”,沙玛的“不息的争斗”:相较于早期布尔乔亚文化的这些矛盾,维多利亚时代呈现出的是曾经不可见的真实:一个妥协的时代,而不再仅仅是对比。当然,妥协并非一致,人们仍然可以把维多利亚人看成是某种程度上“五彩斑斓的(multicoloured)”,但这些颜色是过去的剩余物,正在失去它们的光泽。飘扬在布尔乔亚世纪的那面旗帜,不是五彩斑斓的(bunt),而是——灰色的。
[1]Peter Gay, The Bourgeois Experience:Victoria to Freud.V.Pleasure Wars, New York, 1999(1998), pp.237-238.
[2]Peter Gay, Schnitzler's Century: The Making of Middle-Class Culture 1815—1914, NewYork, 2002, p.5.[译注]中文译文见彼得·盖伊著,梁永安译:《施尼兹勒的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1815—1914》,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14页。
[3]Peter Gay, 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Victoria to Freud. I. Educations of the Senses,Oxford,1984,p.26.
[4]Ibid., pp.45ff.
[5][译注]中文译文见马基雅维利著,王永忠译:《马基雅维利全集:佛罗伦萨史》,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第400页。
[6]“The Art of Portraiture and the Florentine Bourgeoisie”(1902), in Aby Warburg, The Renewal of Pagan Antiquity,Los Angeles,1999,pp.190-191,218. 与此相似的一个将对立面予以结合的表述出现于《佛兰德艺术与佛罗伦萨早期文艺复兴》(“Flemish Art and the Florentine Early Renaissance”, 1902),在瓦尔堡论述捐赠者肖像画的那些页面:“双手保持着祈求上天保佑的忘我姿态,但目光,不管是陷于幻想还是有所警惕,望向的都是尘世中的远处。”(第297页)
[7]Simon Schama,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California,1998,pp.338,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