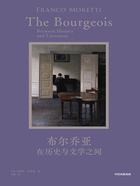
二、“这将证明我没有偷懒”[1]
但为什么要工作呢?首先,无疑,这是一个事关生存的问题:在这样一种状况里,“每天的任务……似乎就是根据需要(need)的逻辑,把它们自身展露在劳动者的眼前”。[2]但是,甚至当[他认为]“只要我活着……哪怕四十年”,[3]他未来的需要都已经无忧,鲁滨孙仍然在费力辛劳,一如既往,一页接着一页。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亚历山大·塞尔柯克(Alexander Selkirk)(据说)曾在[智利的]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Juan Fernandez)度过了四年,时而“沮丧、倦怠、忧郁”,时而又醉心于“一种持续不断的节日……亦即极度的感官的快感”,在这两种心情间疯狂地摇摆。[4]但鲁滨孙,一次也没有。曾有人做过估算,随着18世纪的进程,每年的工作日数量从250天上升到了300天;而在鲁滨孙的岛上,在这样一个星期日的地位从来都不能完全明确的地方,工作日的总量肯定更高。[5]当他处于热情最高涨的时候——“你们知道的,我现在……已经有了两个种植园……好几个房间,或者也称山洞……两片玉米地……山村别墅……饲养家畜的圈地……活的鲜肉仓库……存放葡萄干的冬季贮藏室”[6]——转身向读者高声宣布,“这将证明我没有偷懒”,人们只能点头同意,然后重提这一问题:为什么他竟(does)工作如此之多?30
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一书中写道:“今天人们几乎已经意识不到一个‘从事工作’(working)的上等阶级是多么独特、多么令人惊异的现象。……为什么它要屈从于这种强制,尽管……没有一个更高的阶级要求它这么去做?”[7]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er Kojève)分享着埃利亚斯的困惑,他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中心看出了一个悖论——“布尔乔亚的难题”(the Bourgeois's problem)——布尔乔亚必须既“为另一个人工作”(work for another)(因为工作的出现只是外在制约的结果),然而同时又只能“为他自身工作”(work for himself)(因为他不再有主人)。[8]为他自身工作,仿佛他就是另一个人:而这恰恰就是鲁滨孙发挥其职能的方式:一方面他成了木工、陶匠或面包师,用几个星期又几个星期的时间试图制成某些事物;而后主人克鲁索出现,指出所做成果的不足。而后这一循环再一次地自我重复。它自我重复,因为工作已成为社会权力新的正当化原则。当小说的结尾,鲁滨孙发现自己成了“拥有五千英镑”及其他一切的“主人”,[9]他28年不断的辛劳将在那里为他的时运声辩。实事求是地看,下述这二者没有任何的关联:他因为剥削巴西种植园的无名奴隶而变得富有——而他独自一人的劳动却没有给他带来哪怕一个英镑。但我们已看到,没有其他小说角色像他那样去工作:他怎么可能不配得到他所拥有的东西呢?[10]
有一个词语完美地表达了鲁滨孙的行为:“industry。”根据《牛津英语大词典》,这一词语大约1500年出现,最初的意思是“智慧的或聪明的工作;熟练、精巧、机敏或聪明”。随后在16世纪中叶,第二个意思出现了——“勤勉或刻苦……仔细而稳定的应用……运用、尝试”,随即又被明确为“系统的工作或劳动;习见的具有实际效用的职业”。[11]从熟练与技巧,到系统的运用;“industry”就是以这种方式促进着布尔乔亚文化:勤奋的工作(hard work),代替聪明的花样。[12]而平静的工作(calm work)与勤奋的工作具有相同的意义,在赫希曼(Hirschmann)看来,其旨趣(interest)就在于一种“平静的激情”(calm passion):稳定的、有序的、渐进的,因此比旧贵族的“狂暴(而又脆弱)的激情”[turbulent(yet weak) passion]更为强烈的激情。[13]在这里,两个统治阶级之间的不连续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狂暴的激情把尚武的等级所需要的东西——短暂的战斗“日”的白热化状态——理想化了,那么,布尔乔亚的旨趣是平静的、可重复的(可重复的、可重复的而又可重复的)日常生活的德性:较少的能量,但持续更长的时间。[每天]几个小时——“晚上那四个多钟头”,永远谦逊的鲁滨孙写道[14]——但坚持了28年。3132
在前一节里,我们审视的是开启整部《鲁滨孙漂流记》的冒险;在这一节里,我们考察的是他在岛上生活中的工作。这同样是《新教伦理》的延续:一部以“资本主义冒险家”为开端的历史,但在那里,操劳的品性最终带来了“对他的非理性冲动的一种理性的缓解”。[15]就笛福来说,从第一个[冒险的]形象到第二个[工作的]形象的转换格外引人注目,因为这一切显然不在计划之中:在小说的书名页上(图2,见下页),“奇特而惊人的冒险”——列在顶部,且用大号字体——显然被安排成了主要的卖点,而岛上的部分不过是“其他多个片段中的一个”。[16]不过,在小说的写作中,岛上生活的“出乎意料的、不受控制的扩展”必然会发生,它摆脱了与冒险故事之间的从属关系,变成了这个小说文本的新的中心。对于这一在写作的中途重新定向的行为,一个来自日内瓦的加尔文主义者(Calvinist)第一个把握到了它的重要意义——这个人就是卢梭:他的《鲁滨孙》,“清除了所有哗众取宠的空话”,将以海难为开端,然后限定在岛上的岁月里,这使得爱弥儿将不会把时间浪费于对冒险的梦想,而可以将精力集中在鲁滨孙式的工作(“他希望知道一切实用的东西,而且也只希望知道这些东西”)。[17]对爱弥儿以及在他之后的所有孩子来说,这当然是残酷的,但却是正确的:因为鲁滨孙在岛上的勤奋工作,的确是这本书最伟大的创新。33

图2
从资本主义的冒险家,到从事工作的主人(working master)。然而,当《鲁滨孙》抵近终点,第二次转向出现了:食人族、武装冲突、反叛者、狼、熊、童话式的时运……为什么呢?如果冒险的诗学曾经被它合理性的对立面所“调和”,为什么在小说最后一个句子里,要许诺还有“我个人的几次新的冒险中所遇到的一些非常令人惊异的意外事件”?[18]34
到目前为止,我着重分析了冒险文化与理性工作伦理之间的对立;确实,我毫不怀疑,这两者互不相容,而后者是现代欧洲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更为晚近的现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现代资本主义可以被化约为工作伦理,而韦伯显然倾向于这么做;出于同样的理由,“非理性投机性质,或者趋向于以武力为手段的获利”的活动不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这一事实也不意味着,它们已经从现代资本主义中消失。各种各样猛烈的、其结果不可预知的非经济实践活动——马克思所说的“原始积累”,或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最近所说的“剥夺性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在资本主义的扩张中发挥了(事实上仍然在发挥着)主要作用;果若如此,那么,广义的冒险叙事——例如,在稍后的时代里,康拉德(Conrad)的小说里那种宗主国的反思与殖民地的传奇之间的交织(entrelacement)——仍然完全适合用于对现代性的表述(representation)。
那么,这就是“两个鲁滨孙”的历史基础,随之形成了笛福叙事结构中的不连续性:那座岛为现时代的勤劳的主人提供了第一束观看的目光;海洋、非洲、巴西、星期五及其他冒险活动则给更古老的——但从来没有被彻底丢弃的——资本主义支配形式赋予了声音。从形式的观点看,对立层面之间的没有整合的共存——因此,不同于康拉德精心谋划的等级制:他又一次使用了那种平行线的结构——显然是这部小说的一个缺陷。但同样显然的是,这种不一致性不仅是一个形式的问题:它来自布尔乔亚类型自身的,来自他的两个“灵魂”[19]之间的,那未获解决的辩证法:不同于韦伯,笛福所暗示的是,理性的布尔乔亚永远不会真正战胜他的非理性冲动,也永远不会否定他曾经所是的那个掠夺者。笛福的并未定型的故事,不仅是一个新时期的开端,而且还是这样的一个开端——永远无法克服的结构性矛盾在那里有了可见的形式,因此,它仍然是布尔乔亚文学的伟大经典。35
[1][译注]丹尼尔·笛福著,唐荫荪译:《鲁滨孙漂流记》,第135页。
[2]Stuart Sherman,Telling Time:Clocks,Diaries,and English Diurnal Forms,1660—1785,Chicago,1996,p.228.谢尔曼是在引用汤普森(E.P.Thompson)的话,但作了轻微修改,见汤普森:《时间、工作纪律和工业资本主义》(“Time, Work-Discipline,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过去与现在》(Past&Present)第38期(1967年12月),第59页。
[3]Defoe,Robinson Crusoe,p.161.[译注]中文译文见丹尼尔·笛福著,唐荫荪译:《鲁滨孙漂流记》,第135页。
[4]我所引用的是斯蒂尔(Steele)在《英国人》(The Englishman)第26期(1713年12月3日)里对塞尔柯克的描绘;现见瑞伊·布兰卡(Rae Blanchard)编:《英国人:理查德·斯蒂尔的政治期刊》(The Englishman: A Political Journal by Richard Steele),Oxford,1955,第107—108页。
[5]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无情的革命:资本主义的历史》(The Relentless Revolution:A History of Capitalism),New York 2010,第106页。根据其他人的重构[例如,扬·德·弗里斯(Jan de Vries):《工业革命:消费行为与家庭经济,从1650年到现在》(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Consumer Behavior and the Household Economy,1650 to the Present),Cambridge,2008,第87—88页],在18世纪增长的并不是工作日的数量——它已经达到300天左右这样一个上限,而是每天的工作时数;然而,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这方面,鲁滨孙似乎遥遥领先于他的时代。
[6]Defoe, Robinson Crusoe, pp.160—161.[译注]中文译文见丹尼尔·笛福著,唐荫荪译:《 鲁滨孙漂流记》,第134—135页。
[7]Norbert Elias,The Civilizing Process,Oxford,2000(1939),p.128.[译注]中文译文见诺贝特·埃利亚斯著,王佩莉、袁志英译:《文明的进程》,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162页。
[8]Alexander Kojève,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Lectures on the“Phenomenology of Spirit”,Ithaca,NY,1969(1947),p.65.[译注]中文译文见柯耶夫著,姜志辉译:《黑格尔导读》,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25页。
[9]Defoe,Robinson Crusoe,p.280.[译注]中文译文见丹尼尔·笛福著,唐荫荪译:《鲁滨孙漂流记》,第254页。
[10]“他所拥有的东西”当然也包括这座岛屿:在《第二篇论文》(Second Treatise)的《论财产》(“Of Property”)一章中,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谈及未耕植土地时写道:“他的劳动(labour)把它从自然手里取了出来,从而(hath)把它划归(appropriated)私用,当它还在自然手里时,它是共有的,是同等地属于所有人的。”换句话说,通过在岛屿上的工作(work),鲁滨孙已把岛屿变为己有。John Locke,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Cambridge,1960(1690), p.331.[译注]中文译文见洛克著,叶启芳、瞿菊农译:《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0页。
[11]感谢苏·雷基克(Sue Laizik),是她第一次让我注意到这些词义的变形。当然,“industry”是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文化与社会》的关键词之一;不过,最让他感兴趣的转变,亦即这样一个事实——industry变成了“一种‘自在之物’(a thing in itself)——一种体制,一个由诸种活动组成的机体——而不仅是人类的一种属性”,出现在此处所描绘的这种转变之后,并可能是这种转变的后果:industry先是变成了任何一个人都能完成的简单、抽象的劳动(和“熟练与精巧”的独特性形成了对比),随后被第二次抽象,变成了“一种‘自在之物’”。见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Culture&Society:1780—1950),New York 1983(1958),第xiii页,以及他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rev.edn,Oxford,1983(1976).]中的“Industry”的词条。[译注]中文译文见雷蒙·威廉斯著,高晓玲译:《文化与社会:1780-1950》,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1-2页。
[12]像形容词“industrious”所显示的,勤奋的工作在英语中拥有一个伦理的光环,这是“聪明的”工作所缺乏的:这解释了在20世纪90年代,为何传奇般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Arthur Anderson Accounting)仍把“勤奋的工作”(hard work)列入其“价值表”——而这同一家机构的聪明的分支(安达信咨询公司,它曾一直炮制各种各样的投资事务)却代之以“尊重个人”(respect for individuals),后者是为追逐金融红利而提出的新自由主义的新说法。最终,咨询公司挟持着会计师事务所批准对股票价格进行操纵,导致该机构耻辱地垮台。见Susan E. Squires,Cynthia J. Smith,Lorma McDougall与William R. Yeack:《安达信内幕:价值的转换,意外的后果》(Inside Arthur Andersen: Shifting Values, Unexpected Consequences,New York,2003),第90—91页。
[13]Albert O. Hirschmann,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Princeton,NJ,1997(1977),pp.65—66.
[14]Defoe, Robinson Crusoe, p.127.“早晨”打猎要3个小时,“处理、加工、保存和烧制”又占去“一天的大部分时间”,这两者显然应该再加上晚上的4个小时,其工作时间合计起来远远超过当时大部分劳动者。[译注]中文译文见丹尼尔·笛福著,唐荫荪译:《鲁滨孙漂流记》,第101页。
[15]Ibid., p.17.[译注]作者此处标注有误,该句引文出自韦伯,中文译文见韦伯著,阎克文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60页。
[16]这一点我要归功于朱塞佩·塞尔托利(Giuseppe Sertoli)的《两个鲁滨孙》(“I due Robinson”),载于《鲁滨孙历险记》(Le avventure di Robinson Crusoe,Turin 1998)第xiv页。
[17]Jean-Jaques Rousseau,Emile(1762),in Oeuvres Complètes,Paris,1969,Vol.Ⅳ, pp.455—456.[译注]中文译文见让——雅克·卢梭著,李平沤译:《爱弥儿》(上),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71页。
[18]马克西米利安·诺瓦克(Maximilian Novak)指出,“《鲁滨孙漂流续记》(The Farther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出版于1719年8月20日,大约在第一卷面世的四个月之后”;这一事实有力地表明,笛福“在原作付印之后已在致力于续集的事务”;因此小说的末句不是一处闲笔,而是一次具体的广而告之的行动。见诺瓦克:《笛福:小说大师》(Defoe:Master of F ictions),Oxford,2001,第555页。
[19]“两个灵魂”的隐喻——受《浮士德》中那段著名独白的启发——是桑巴特(Sombart)有关布尔乔亚一书的主乐调:“每一个完全的布尔乔亚胸中都居住着两个灵魂:企业家的灵魂和值得尊敬的中间阶级人士的灵魂……企业精神是对黄金的贪婪、对冒险的欲望与对探险的热爱之间的综合……布尔乔亚精神则由计算、审慎的策略、合理性与节俭态度(economy)所组成。”Werner Sombart,The Quintessence of Capitalism,London,1915(1913),pp.20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