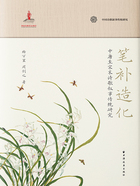
第四节 杜甫诗歌“诗史”说小议
由以上文字中转引的古人评语可以知道,晚唐宋初以来人们对杜甫诗歌叙事性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两个话题:一是杜甫诗对汉魏古诗(含乐府诗)叙事传统的借鉴(16),一是杜甫诗是“诗史”。下面分别申论之。
众所周知,《诗经》中有许多叙事性极强的诗歌,汉乐府亦然,沈德潜说“措辞叙事,乐府为佳”,(17)建安时期曹植《送应氏》、王粲《七哀诗》、蔡琰《悲愤诗》中均有相当出色的叙事部分。然而,《诗经》以至汉魏诗歌中发展起来的叙事传统,在东晋至盛唐时期的文学主潮中沉潜(非中断)了,而同时抒情性却在诗歌中昂首阔步。诗歌的叙事传统仅在民间乐府中一线潜传,至杜甫则重获生命并得以发扬光大(18)。那么,杜甫继承与发扬汉魏诗歌中叙事传统给文学史带来什么样的美学新体验?
有学者将杜甫诗中叙事概括为“事态叙写”:“它不是一定要写一个首尾完整的故事,也不是要塑造完整的人物形象。它或是一些事实片段的展现,或是某一生活场景的刻画,或是人物性格或面影的速写,是由诗人主观情感贯穿与笼罩起来的一种叙事结构。它的核心功能指向是抒情。”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杜诗的叙事走向了平凡无奇的社会生活,在采择上更注重片段、场面、细节的真实性、典型性和情感蕴含,注重对事态作深细的开掘和提炼,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手法,予以真切而传神的描绘。”(19)该文作者以为,从盛唐的意境营造到事态叙写的转变,是杜甫在诗歌艺术方面最大的贡献。用“事态叙写”这个概念来总结杜甫诗歌中的叙事性成就,正是此文最大贡献。
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可以从诗歌语言通俗化的角度对杜甫继承与发扬汉魏诗歌中叙事传统的成就进行总结。
叙事语言方面,已有论者注意到杜甫乐府诗中一改叙事作品好用陈述句的常见手法,而多用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这些非陈述句子将诗人心中的问题、思考、批判以及情绪强调出来,言已尽而意无穷,并引导读者进行同样的思考(20),极大地增加了诗歌的抒情性和批判性。同时,我们还注意到,由于叙事在再现环境的真实性(如个人经历的危险性、战争的残酷性)、符合叙述者的身份(口吻)等方面的内在需要(21),杜诗语言必然地走向了一定程度的通俗化。如《述怀》叙述自己当时的惨状:“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战乱中衣衫褴褛的诗人失去了一切,已经不需要任何华丽的、典雅的文字来掩饰自己的身份和状态了。《石壕吏》叙述老妪之语:“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符合村妇命苦善良、护犊勇毅的人物身份。《兵车行》中“行人”的话语,朴素无奇,围绕着自身从军经历、所见所想而来,绝不作肉食者之宏大思考。他们不知道国家为何会这样,更不知道如何结束目前的战乱,对于自己三十多年苦难的从军生涯没有呼天抢地的控诉,只是想到避开苦难,“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殊不知,在当时的社会,男子不存,女子焉附?因无尽的绝望而被迫短视,因长久的苦难而被迫麻木,正是社会底层“行人”的真实状态(22)。《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诗:“酒酣夸新尹,畜眼未见有……高声索果栗,欲起时被肘。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月出遮我留,仍嗔问升斗。”浅白通俗的语言,将村叟豪爽热情、粗鄙好客的特点尽写无馀,完全符合叙事对象的身份。《杜诗镜铨》评此诗:“情事最真,只如白话。”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一一引郝敬语:“此诗情景意象,妙解人神。口所不能传者,婉转笔端,如虚谷答响,字字停匀。野老留客,与田家朴直之致,无不生活。昔人称其为‘诗史’,正使班、马记事,未必如此亲切。千百世下,读者无不绝倒。”(23)刘熙载《艺概》云:“代匹夫匹妇语最难,盖饥寒劳困之苦,虽告人,人且不知,知之者必物我无间者也。杜少陵、元次山、白香山,不但如身入闾阎,目击其事,直与疾病之在身者无异。”(24)杜诗叙事语言的通俗化尝试,在当时是艺术创新。通俗化即大众化,为拓展文学表现生活的广度深度、为扩大文学的接受群体奠定了语言基础,并开中唐张王乐府、“元轻白俗”之先声(25)。
古人解说杜甫诗歌之叙事,最有名的说法莫若“诗史”说。以“诗史”论杜甫,始于孟棨《本事诗》:“杜逢禄山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意谓杜诗记录时事,故称诗史。《新唐书》杜甫传谓:“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26)意谓杜甫以格律精切之长篇诗歌记录时事,故号‘诗史’。显然,《新唐书》的说法更合理,因为它包括了“诗”与“史”两种体裁的核心要素。此后,“诗史”说愈繁,意义多歧。何谓诗史?一是得春秋笔法,下笔寓褒贬,如宋人黄彻《 溪诗话》卷一:“(《左传》)有一人而称目至数次异者,族氏、名字、爵邑、号谥皆密布其中而寓诸褒贬,此史家祖也。观少陵诗,疑隐寓此旨……诚《春秋》之法也。”二是谓客观地记录时事(且是大事),多数人持此看法。三是指学司马迁《史记》,叙事手法得体,“叙事近史”(胡应麟《诗薮》),声肖其人,话肖其人,事肖其人。总之,古人论杜甫“诗史”的要义是“叙事有法的实录”。
溪诗话》卷一:“(《左传》)有一人而称目至数次异者,族氏、名字、爵邑、号谥皆密布其中而寓诸褒贬,此史家祖也。观少陵诗,疑隐寓此旨……诚《春秋》之法也。”二是谓客观地记录时事(且是大事),多数人持此看法。三是指学司马迁《史记》,叙事手法得体,“叙事近史”(胡应麟《诗薮》),声肖其人,话肖其人,事肖其人。总之,古人论杜甫“诗史”的要义是“叙事有法的实录”。
在“诗史”概念的引导下,过去很多杜诗评注者竭力“以史证诗”,如清代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仇兆鳌《杜诗详注》、浦起龙《读杜心解》;更有甚者,以杜诗证新、旧《唐书》,以为这是读杜诗之金针(27)。那么,杜甫诗中叙事全是实录吗?实不尽然。
首先,我们要明确文学理论中的一个常识:“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学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28)换言之,杜甫之所以是诗人,关键不在于他用韵文记录时事,那样的话,他只能称之为历史学家。这是我们破除杜甫“诗史=实录”魔障的理论依据。
其次,从中国史传传统的实际情况来看,所谓的“实录”,绝不是客观叙事,而是不排除虚构成分在内。众所周知,《左传》里多记载梦兆、灾祥、鬼怪等荒诞不经的事件,不可能是真实发生的客观事实,但都记入史册了。约在东汉末成书的《孔丛子》里曾记载:“陈王涉读《国语》言申生事,顾博士曰:……‘晋献惑听谗,而书又载骊姬夜泣,公而以信入其言。人之夫妇夜处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虽黔首犹然,况国君乎?予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为之辞。’”(《答问》章)钱锺书对此评论说:“骊姬泣诉,即俗语‘枕边告状’,正《国语》作者拟想得之……《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29)柳宗元《非国语》论“越语”曰:“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金圣叹也提到《史记》里的虚构成分:“司马迁之书,是司马迁之文也。司马迁书中所叙之事,则司马迁之文之料也。是故,司马迁之为文也,吾见其有事之巨者而隐括焉,又见其有事之细者而张皇焉,或见其有事之缺者而附会焉,又见其有事之全者而轶去焉。无非为文计不为事计也。”(30)司马迁所写的介之推死前与母亲的那段著名的对话,难道还有第三者在旁听到了?显然不可能。钱锺书先生所谓“史有诗心、文心”,盖指史传中有虚构。外国学者直接将中国史传的客观性、真实性定位为“本质真实”“人情意义上的真实”。(31)史且如此,杜诗更不可能全是实录了。
既然“实录”不是杜甫诗号称“诗史”的原因,那必另有说法。杜诗不全是实录,但读起来“像”实录,奥妙何在?叙事学中的“叙事聚焦(视角)”理论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
根据叙事学著名学者热拉尔·热奈特的分类,叙事聚焦(视角)有三种基本类型(32)。第一种类型是无聚焦叙事(上帝视角),叙事者藉由全知观点来进行叙述,历史学家大多采用此视角,杜诗《前出塞》《后出塞》《悲陈陶》《悲青坂》《洗兵马》等诗歌的叙事视角即是这样。这类诗歌更像韵文版的“时事快报”,从记录时事来说它们是真正意义上的“诗史”,只可惜这类诗并不是杜诗中的精品,感染力不够。
第二种是内聚焦叙事(内视角),叙事者藉由事件中的人物(可以是一个或多个)观点来进行叙述,很多情况下叙述者就是人物(“我”)。杜诗《游龙门奉先寺》《过宋员外之问旧庄》《郑驸马宅宴洞中》《渼陂行》《彭衙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哀王孙》《哀江头》《喜达行在所三首》《述怀》《羌村三首》《北征》《潼关吏》《无家别》等即是。《无家别》记录事件中的人物“我”(老兵)战败后回到家乡的所见、所感,作者的声音绝不出现。一般来说,叙事完全从单个人物的视角出发,对事件的陈述更富有主观色彩。又由于杜甫(叙述者、人物)在写诗的时候有强烈的诗人自我意识,常常忍不住摆脱叙事的框架,插入大量的议论、抒情文字,所以这类叙事诗在字面上看抒情性最强,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呢,由于叙述者的纯个人视角加上强烈的介入叙事姿态,使得这类诗歌所叙之事的客观性大打折扣。
第三种是外聚焦叙事(外视角),在此类的聚焦中,叙事者如同一位不知情的旁观者,用不带任何主观意识的视角来客观记录事件。杜诗《新安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等诗即是。如《新安吏》:“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答)府帖昨夜下……”诗人躲在一旁,记录着“客”与新安吏的对话。《石壕吏》中“我”隐身了,全诗只剩下村妇与吏的对话。《新婚别》除了开头几句起“兴”(乐府诗的传统作法)的语句以外,全诗由第三者客观地记录新婚妻子的说话构成。《垂老别》像现代电影叙事手法:以连续镜头拍摄老兵回家的经历,伴以旁白(“子孙阵亡尽”),纯冷静客观叙事。在外聚焦叙事模式中,叙述者与作品中人物的关系相当“疏离”,叙述者只管叙述一幕幕由人物的言语和行为构成的场景,给人“中立”“客观”的感觉,读者对其所留下来的“未定点”或“空白点”须加以想象性的还原。从这个角度而言,外聚焦叙事的作品可能传达出更多丰富、复杂、微妙的深层信息。杜甫诗被称作“诗史”,主要是源于这种叙事策略带给读者的客观、中立印象,以为杜甫是像历史家一样记录着时事。这正是杜甫运用叙事手法的高超之处。
当然还可以从作者与叙事者的差异来解释上述话题。川合康三认为:“以往的自我描述方式往往将自身与前代典型人物重合,通过在类型中的融合造成自我的消失。与此相比,杜甫的自我把握因为持有将自身客体化的另一个认识主体,事实上突出显现出来的是与所描绘人物形象之间保有一定距离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这种双重结构的自我认识,虽然表面上突出描绘的是处于穷途末路的自我,另一方面却因为站在背后凝视着落魄的自己的还有另一个自我,从而能够获得一种精神上的安定。”(33)所谓“自我”与“将自身客体化的另一个认识主体”“双重结构的自我认识”云云,换成叙事学术语,就是作者与叙述者的差异。
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诗史”云云,它只是杜甫诗歌中成功地运用叙事策略而带来的一种貌似客观中立的表达效果。过于机械地理解它,会错误地将杜诗与实录相等同,其结果就是:或如清初学者朱鹤龄、仇兆鳌、浦起龙等人那样处处以唐史来解杜诗,难免穿凿;或如明代杨慎、清初王夫之那样,大谈诗、史之异同(34),实属无的放矢。
总结本章,叙事性为杜甫诗歌带来了全新的审美体验,它不仅为唐诗语言的通俗化提供了内在的必要性,也为唐诗探索出了新的表现手法,特别是《新安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等诗中“外聚焦视角”的创造性运用,开唐诗新世界,为中唐叙事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1) “叙事”是与“抒情”对举的概念,“叙事性”在本书中指向诗歌里叙事、抒情成分多少的问题。一首诗中如果能找出大致的叙述线索和叙述过程,则可认为此诗有“叙事性”。当一首诗中叙事性的分量大大地超越抒情性时,我们则认为这首诗是叙事诗。有人以叙事的基本要素(事件、情节、叙事者、人物行为者、时间、空间)为标准作过统计,现存杜甫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完全具备以上叙事要素的诗歌有五十多首,叙述单个事件的诗歌大概有六十多首,而感事抒情的诗占到全部诗作的60%以上。(曾静、郑宇:《从叙事学看杜甫诗歌的诗史特色》,《名作欣赏》2013年5月中旬,第100页)笔者按,统计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运用,误差会很明显,这与研究者对标准的理解范围和执行态度有关;其次,百分比并不能说明艺术的独创性问题,只表明作者创作时的劳动习惯和态度;更明确地说,杜甫六十首(依上统计数)叙事诗所代表的文学史意义,可能不亚于他占比60%的抒情诗的文学史意义。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孤篇横绝,竟为大家”,那些留下大量诗作的诗人们,反而在文学史上反响平平,道理就在此。
(2) [清]杨伦:《杜诗镜铨》卷一评此诗:“题是游,诗只写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3) 《杜诗镜铨》卷一引李子德语评本诗:“气体高妙,澹然自足。”同上,第1页。
(4) 浦安迪:《中国叙事学》第一章《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按,西方叙事理论更多地指向“故事”——首尾完整的情节,但浦安迪先生此处这个定义,能从中国文学的现实出发,指出中国文学的叙事特征侧重表现时间流中的人生履历(见闻),极好。
(5) 胡晓明:《释陈寅恪古典今事解诗法》,《学术集林》卷十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晓明先生将今典古典合一的诗歌写作定义为“抒情的叙事诗”(或“叙事的抒情诗”),这个命题不在本书讨论之列,此处仅借其概念的字面意义。
(6) 陈来生:《史诗·叙事诗与民族精神》,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122页。按:此说有以西方叙事概念框设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之嫌。其实浦安迪教授很早就指出:西方叙事理论建立于西方epic(荷马史诗)—romance(中世纪罗曼史)—novels(近代长篇小说)这一主流的叙事文学传统,而中国的文学主流是三百篇—騒—赋—乐府—律诗—词曲—小说这样的传统。“不难想见,如果我们简单地把西方传统的叙事理论直接套用于中国明清小说的探讨,将会出现许多悖谬之处。”(浦安迪《中国叙事学》第13页)同理,简单地把西方传统的叙事理论直接套用于中国古代诗歌的探讨,同样会出现很多悖谬。
(7) 曹植《洛神赋》有“众灵杂沓”句。“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句,“逡巡”,气盛貌;从马上直接进入舞毯(锦茵),旁若无人,粗鄙至极。“杨花覆白苹”乃化用北魏胡太后与杨白花私通典故。杨白花惧与太后私通招来杀身之祸,逃到南朝,胡太后思念他,作《杨白花歌》,有“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之句。此暗讽杨国忠(丞相)与从妹虢国夫人乱伦之事。青鸟衔巾在当时也是常用典故,西王母与汉武帝相会以青鸟为使,后世以青鸟喻两性昵戏之事。王勃《落花落》“罗袂红巾复往还”即道此景也。
(8) 古乐府诗《妇病行》《上山采蘼芜》《东门行》《十五从军行》《陌上桑》等,都运用了对话叙事的手法,特别是《孔雀东南飞》中用了三十次对话,“大大增加了诗歌的客观性、形象性和戏剧性”(沈文凡、周非非:《杜甫叙事诗言语对话艺术略论》,《华夏文化论坛》2007年9月)。
(9) 陈伯海:《唐诗汇评》上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928页。
(10) 同上。
(11) (托名)[唐]王昌龄:《诗格》,见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凤凰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页。
(12) 为什么初盛唐人有那样的天真乐观情绪,而中晚唐及宋人则普遍深沉忧虑?根本原因还在于国家的整体生存环境。初盛唐时期恰逢北方游牧民族普遍衰落,唐代前期趁此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大力开疆拓土,征服地纷纷来朝,那种万国来仪的文化融合,造就了盛唐气象,诗亦随之。而安史之乱后至整个宋代,情形则相反,先是地方军阀混战,继而是北方游牧民族重新强盛,如契丹、女真、蒙古先后崛起于北方。边防压力大则经济压力大、阶级矛盾激烈,相应地,则民众生活压力也大,同时对外交流中断。我们可以看到,自安史之乱起直至宋朝,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了内生式发展,思维单一而体系严密,这就是自韩愈起直至南宋时期读书人所呼吁的“重建道统”的历史。
(13) 梁启超:《情圣杜甫》,见《杜甫研究论文集》第1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页。
(14) 《岘傭说诗》评曰:“《羌村》三首,惊心动魄,真至极矣。陶公真至,寓于平淡;少陵真至,结为沉痛。此境遇之分,亦情性之分。”(转引自《唐诗汇评》上册,第962页)
(15) 谢思炜:《杜诗叙事艺术探微》,《文学遗产》1994年第4期。
(16) 有研究谓:“叙事上,杜甫综合了《诗经》与乐府两大不同的叙事传统,一方面以《诗经》传统为精神内核,记述重大历史事实,展现诗歌的史学批判价值;另一方面,向着被忽视的乐府叙事传统回归,强调叙事的虚构性、情节性、传奇性等娱乐特质,最终创作出一批写人叙事与伦理价值完美融合的杰作,并深深影响了中唐叙事诗的繁荣。”(辛晓娟博士论文《杜甫七言歌行艺术研究》提要语,正文第五章第三节《杜甫歌行对乐府传统的继承》则是对该论点的展开论述。见第125—161页,北京大学2012年。)笔者按,将《诗经》叙事传统与记述重大历史事实相联,将汉魏汉府传统与虚构性、情节性、传奇性等娱乐特质相联,这种归纳过于理想化。杜诗叙事,很多情况下是向日常生活回归;而他的叙事中,情节性诚有,但虚构性和娱乐性恰恰是最缺少的。
(17) [清]沈德潜:《说诗晬语》,《清诗话》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32页。
(18) 谢思炜:《杜诗叙事艺术探微》,《文学遗产》1994年第4期。
(19) 邹进先:《从意象营造到事态叙写——论杜诗叙事的审美形态与诗学意义》,《文学遗产》2006年第5期。
(20) 于年湖:《杜甫新乐府诗语言的文化批判功能》,《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21) 宋人张端义《贵耳集》上卷:“项平斋自号江陵病叟,余侍先君往荆南,所训‘学诗当学杜诗,学词当学柳词’。扣其所以,云:‘杜诗柳词皆无表德,只是实说’。”杨按,“表德”大约即今天所谓议论抒情,“实说”庶几叙事纪实之意。
(22) 《兵车行》旧注多以为是针对玄宗征吐蕃而作,《杜诗详注》引黄鹤注认为是针对天宝十载杨国忠遣鲜于仲通征南诏败于泸南而作。杜甫此诗中的叙事,正好可与李白咏泸南之败的《古风》诗相对照看。李诗云:“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困兽当猛虎,穷鱼饵奔鲸。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显然,李诗只是高度概括现实,更多地在表达个人的哀伤同情。在表现战争给百姓带来的广泛的人道主义灾难相比,李白诗的表现力远不能与杜甫《兵车行》诗相比。
(23) [清]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92—893页。
(24) [清]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65页。
(25) 顺便提到,杜甫诗中语言的通俗化,在他晚年创作中已基本消失。与此同时,诗歌叙事性在他晚年创作中也同样快速消褪。晚年的杜甫,诗歌创作回归到盛唐时以近体诗为主流的状态中来了,并在声律方面采取最严格的姿态,“晚节渐于诗律细”,是他自己在《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诗中的自道。黑格尔论历史进步总是螺旋式上升,余谓人生进步何独不尔?
(26) 《新唐书》杜甫传又谓:“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盖此论甫之见识不高,不如其诗艺之杰出。
(27) [清]杨伦:《杜诗镜铨》毕沅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28) 亚里士多德:《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6页。
(29) 钱锺书:《管锥编·左传正义》,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册,第165—166页。
(30) [清]金圣叹:《金圣叹批<水浒传>》第二十八回回前评,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545页。
(31) 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
(32) Gerard Genette,Narrative Discourse:An Essay in Method,Cornell University Press(August 31,1983)pp.186—189,243—247.
(33) 川合康三:《杜甫诗中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表述》,《杜甫与唐宋诗学: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九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里仁书局2002年版,第89页。
(34) 杨慎谓:“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见《升庵诗话》卷十一“诗史”条。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68页。
王夫之谓:“诗有叙事叙语者,较史尤不易。史才固以檃括生色,而从实着笔自易;诗则即事生情,即语绘状,一用史法,则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此《上山采蘼芜》一诗所以妙夺天工也。杜子美仿之作《石壕吏》,亦将酷肖,而每于刻画处犹以逼写见真,终觉于史有馀,于诗不足。”王夫之评选、张国星点校:《古诗评选》,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