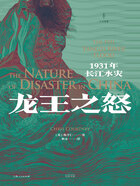
1931年洪水的六个历史画面
本书分为六章,每一章都提供了关于1931年洪水的不同历史视角。虽然个别章节可以作为对特定主题和方法的阐述而单独阅读,但作为一个整体,它们为读者提供了多维的视角,可以从不同的时间和地理尺度以及利用一系列史学方法来看灾害。第一章描绘了湖北自人类早期定居以来的洪水环境史。该地区以治水为主题的史料丰富,很大程度上阐明了人类是如何通过修筑堤坝和排干土地来改变环境的。[39]如果我们要理解洪水问题,这种方法至关重要,但它也创造了一种水利范式。这种范式鼓励我们从堤坝建设者的角度看待洪水,从根本上将洪水视为技术失败。本章对定期洪水淹没景观如何成为区域生态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给出了不同的看法。过去两千年来,在湖北乃至世界大部分地区盛行的防洪风尚并非历史常态。地方群体找到了多种与水共存的方式,在适应而不是简单地抵御洪水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复杂的湿地文化。随着农业的发展,自然属性的洪水成为自然灾害。农业开发不仅让河流变得更加危险,而且为洪水之后的饥荒和流行病创造条件。湖北近代灾害现象并非单纯源于自然,而是几千年来随着人类聚落与河流生态系统相互作用而出现的。
在第二章,我们缩小研究范围,考察单次洪水脉冲的生态史。为了解1931年人类经历了什么,我们必须考察水是如何影响居住在其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物种的。洪水的历史研究往往集中在单一的生态影响上——可食用植物损失。这种以营养为中心的方法要求我们只关注农业和粮仓,而这扭曲了我们对灾难的理解。对于洪水受害者来说,很少会死于纯粹的饥饿,而更多的情况是由于饥饿和疾病的共同作用而死亡。1931年的死亡危机也不例外。可获得食物急剧减少,再加上经济权利的丧失,导致了一场严重削弱人类个体和集体的生存危机。然而,事实证明,席卷洪泛区的瘟疫才是最致命的。认识到疾病在灾害中所起的导源性角色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屈服于一种病原决定论——在这种论调中,人类只不过是细菌和病毒的不幸受害者——而是必须要认识到自然、社会和微生物生态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第三章探讨了在武汉被淹没街头出现的各种描绘洪水历史的宗教和哲学解释,是当地人用来解释天气和调节自然力量的民间气象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最强大的神灵之一是龙王:负责控制降雨和江河的神。而洪水前不久,武汉市政府做出了重大决定,拆除一座供奉这位神灵的寺庙。许多本地人将随之而来的洪灾解读为对这种毁坏圣像之举的宗教报复。媒体迅速抓住这一宗教理论,嘲笑它是老百姓愚昧迷信的表现。他们其实没有意识到,洪水期间老百姓游行不仅仅是因为龙王。请龙王除有其特定功能外,仪式和游行本身还充当了民众抗议的工具。宗教在致灾机制中扮演着复杂的角色,作为一种“话语”,受灾地区通过这种话语来呼吁他们的领导人承担责任。
第四章通过描绘武汉水灾的感知史(sensory history),使我们更接近水灾的即时体验。目击者经常提到身体的创伤景象、受惊吓的难民的声音和暴露在自然环境中的不适以及无处不在的死亡和粪便的恶臭。学术研究往往会忽略这些令人生厌的细节,而更喜欢根据静态的定量数据来分析灾害。本章恢复在历史研究中被剔除的感性描述,通过对灾害的感观和情感叙述,不仅能丰富对历史的体验认知,还能深入了解人们在危机中的行为方式。要了解人们在洪水期间做了什么,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尝试了解他们的感受。许多被记录下来的感观史料成为观察难民行为的关键切入口,而这些难民行为也是任何致灾机制都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本书的最后两章对比了两种形式的专业知识:精英救援人员的技术知识和难民的乡土知识。第五章描绘的是应对洪水的政府机构及制度史。它描述了救援组织是如何被一种孤立的意识形态主导的,而这种意识形态的基础是关于饥荒原因和贫困性质的共同假设。这造成反对者的声音被屏蔽,并掩盖了救援工作的诸多实效。尽管他们的努力后来被誉为近代国家的胜利,但在现实中,救援机构受到财政和政治困难的困扰。随着日本的入侵,中国陷入更大的经济困境之中,国民政府开始向美国申请小麦贷款。这些贷款以慈善的形式让贷方获利,也是美国政府稳定其疲弱的农村经济的方式。这种双边救灾模式似乎预见了后殖民世界将出现的国际秩序的某些新特征。中华民国作为一个名义上的主权国家,竟运行在一个财富和权力严重不对称的国际体系中。随着粮食在中国仓库里腐烂,难民们发现自己在吃世界另一端种植的小麦。
类似的不对称界定了武汉洪水的地方经验,尽管是微观的形式。第六章介绍了这座城市发生的难民危机的社会史,关注难民自身的专业知识,而非将难民看成一个需要专家治理的问题;考察他们如何应对灾害,如何应对治理。与公认的观点相反,许多难民不想被国家收容,更愿意选择自救。而不幸的是,市政当局几乎总是将难民的自主应对策略解释为社会问题:水上拉客被认为是一种公害,乞讨导致贫穷,卖淫是不道德的,而贩卖儿童则等同于贩卖奴隶。尽管这些社会问题引起了官方的特别关注,但地方当局首要关心的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威胁。由于害怕政治上的“阴谋”,军事长官对这些流离失所的难民进行残酷镇压。在武汉郊区的一个难民收容所,难民们在枪口下被仓促安置,在那里,他们有许多人死亡。像所有洪水中丧生的人一样,难民收容所中的死者不仅仅是大自然的受害者,他们被锁定在一个由水文、气象、经济、生态、文化和政治相互作用而定义的致命的致灾机制中。
注释
[1]管雪斋:《水上三点钟》,《亚细亚报》,《湖北省一九三一年水灾档案选编》(以下简称HSSDX)。
[2]此处叙述基于该记者在1932年1月13日《武汉日报》上的报道。
[3]刘思佳:《汉口中山公园百年回看》,《武汉文史资料》2010年第9期,第39—45页。
[4]吕学赶、唐仁民:《汉口中山公园动物园的片段回忆》,《武汉文史资料》2006年第9期,第4—8页。
[5]刘思佳:《汉口中山公园百年回看》。
[6]这是关于这场灾难的第一本专著。中国有几篇文章和专著的章节描述了此次洪水,包括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章博《论政府在灾荒救济中的作用——以武汉1931年水灾为个案的考察》、孔祥成《民国江苏收容机制及其救助实效研究——以1931年江淮水灾为例》。英语世界读者可以在李明珠(Lillian M. Li)《华北的饥荒》(Fighting Famine)、曾玛莉(Margherita Zanasi)《拯救国家》(Saving the Nation)、艾睿思·布罗维(Iris Borowy)《大思维》(‘Thinking Big’)、李慈(Zwia Lipkin)《于国无用》(Useless to the State)等论著中找到一些简单的描述,而目前为止英文著作中描述最全面的是皮大卫(David Pietz)《工程国家》(Engineering the State)的一章。
[7]《全国抗洪救灾委员会1931—1932年报告》(以下简称RNFRC),第7页。
[8]包括安徽、湖北、湖南、江苏、浙江、江西、河南和山东。有关洪水地理范围的描述,参阅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第203页。
[9]参见《武汉已成沧海》,《国闻周报》1931年第8卷第33期;F. G. 昂利(F. G. Onley):《书信节选》,1931年8月28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档案(以下简称SOAS Archives),10/7/15;胡玉森:《书信节选》,1931年8月28日,SOAS Archives,10/7/15。
[10]RNFRC,第3页。
[11]同上,第5页。
[12]《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1931年11月。
[13]RNFRC,第7页。
[14]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第231页。
[15]见附录。
[16]巴雷特(William E. Barrett):《红漆门》(Red Lacquered Gate),第265页。
[17]卜凯(John Lossing Buck):《中华民国廿年水灾区域之经济调查》(The 1931 Flood in China: An Economic Survey),第8页。
[18]RNFRC,第3页;《教务杂志》,1932年11月;巴雷特:《红漆门》,第274页。
[19]参见一些学者的研究,如威斯勒(Ben Wisner)等人的《置身险境》(At Risk)、奥利弗——史密斯(Anthony Oliver-Smith)《关于危险和灾难的人类学研究》(‘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on Hazards and Disaster’)、班考夫《灾难文化》(Cultures of Disaster)、菲斯特(Christian Pfister)《从自然灾害中学习》(‘Learning from Nature-Induced Disasters’)等论著。
[20]如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尘暴》(Dust Bowl)、莫里斯(Christopher Morris)《大沼泽》(Big Muddy)。
[21]李明珠:《华北的饥荒》;魏丕信(Pierre-Étienne Will)、王国斌(R. Bin Wong):《养民》(Nourish the People);魏丕信:《官僚制度与荒政》(Bureaucracy and Famine)。
[22]这是研究发生在帝国主义或其他独裁政权下的灾害的普遍主题。比如戴维斯(Mike Davis)《维多利亚晚期的大屠杀》(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霍尔——马修斯(David Hall-Mattews)《印度西部殖民地的饥荒与国家》(Peasants, Famine and the State)、惠特克罗夫特(S. G. Wheatcroft)《解释苏联饥荒》(Towards Explaining Soviet Famine)。
[23]参见德瓦尔(Alex de Waal)《饥荒犯罪》(Famine Crimes)、穆盛博《战争生态学》(Ecology of War)、穆克吉(Janam Mukherjee)《饥饿的孟加拉》(Hungry Bengal)。
[24]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贫穷与饥荒》(Poverty and Famines)。有关权益法的讨论,请参见奥·格拉达《饥荒》(Famine)。
[25]这种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比如威斯勒等《置身险境》、奥利弗——史密斯《关于危险和灾难的人类学研究》。有关脆弱性话语的批判性评价,参阅班考夫的《灾难文化》。
[26]见阿马蒂亚·森《贫穷与饥荒》等。
[27]相关论述请参阅瑞斯(Seth R. Reice)《一线希望:自然灾害的好处》(Silver Lining: The Benefits of Natural Disasters)。
[28]班考夫:《灾难文化》。
[29]例如艾志瑞《铁泪图》(Tears from Iron)、安特利雅·扬库(Andrea Janku)《帝制中国晚期的天灾》(‘Heaven-Sent Disast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斯奈德·莱因克(Jeffrey Snyder-Reinke)《旱魃》(Dry Spells)、富勒(Pierre Fuller)《饥荒重现华北》(‘North China Famine Revisited’)、穆盛博《战争生态学》、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农村社会》;还可参见弋玫(Kimberley Ens Manning)、文浩(Felix Wemheuer)《吃苦》(Eating Bitterness),塔克斯顿(Ralph Thaxton)《灾难与争论》(Catastrophe and Contention)等。
[30]魏丕信、王国斌:《养民》。
[31]戴维斯:《维多利亚晚期的大屠杀》。
[32]李明珠:《华北的饥荒》。
[33]“机制”(regime)一词的使用受到两方面的影响。首先,生态学家将环境中的物理危害概称为“干扰机制”(disturbance regime)[参见德尔·莫拉尔(Roger Del Moral)和沃克(Lawrence R. Walker)《环境灾难、自然恢复与人类应对》(Environmental Disasters,Natural Recovery and Human Responses),第123页]。其次,研究城市火灾的历史学家会描述城市物质和政治关系的配置如何有助于创建“火灾机制”(fire regimes)[见班考夫等人的《易燃城市》(Flammable Cities)]。
[34]杰克逊(Jeffrey H. Jackson):《水下巴黎》(Paris Under Water);罗扎里奥(Kevin Rozario):《灾难文化》(Culture of Calamity);克兰西(Gregory Clancey):《地震之国》(Earthquake Nation)。
[35]沃森(Philip Watson):《大运河、大江:十二世纪中国诗人的旅行日记》(Grand Canal, Great River: The Travel Diary of a Twelfth-Century Poet);伯德:《长江流域及以外地区游记》(The Yangtze Valley and Beyond)。
[36]罗威廉(William Rowe)的经典两卷本汉口史仍然是研究该地区的学者和城市史学者最好的参考书之一。参见罗威廉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和《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796—1895)》(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最近有两本书聚焦武汉城市:拉哈夫(Shakhar Rahav)的《政治精英的崛起》(The Rise of Political Intellectuals in Modern China)、麦金农(Stephen Mackinnon)的《武汉·1938》(Wuhan, 1938)。爱德华·麦考德(Edward A. McCord)在他的战争史中经常提到这座城市,参阅麦考德《现代中国形成过程中的军事与精英力量》(Military Force and Elite Power in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a)。当然,这座城市还有许多中文研究著作,如皮明庥的多卷本《武汉通史》和田子渝的《五四运动史》。
[37]伊懋可(Mark Elvin):《谁是天气的罪魁祸首》(‘Who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Weather?’);扬库: 《帝制中国晚期的天灾》。
[38]随着天灾一词进入现代词典,它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即经历了刘禾(Lydia Liu)所说的“关系转变”,但用法保持不变。刘禾:《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第41页。
[39]刘翠溶(Ts’ui-jung Liu):《荆州大堤的建设》(‘Dike Construction in Ching-chou’);魏丕信:《中国水利周期》(‘Un cycle hydraulique en Chine’);魏丕信:《国家干预》(‘State Intervention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a Hydraulic Infrastructure’);濮德培(Peter C. Perdue):《耗尽土地》(‘Exhausting the Earth’);罗威廉:《治水与清政府决策程序:樊口大坝之争》(‘Water Control and the Qing Political Process: The Fankou Dam Controversy’);张家炎:《应对灾难》(Coping with Calamity);高燕:《马的撤退》(‘Retreat of the Hor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