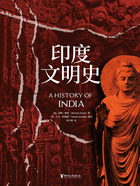
南部半岛
除了面积更小和环境更多样化外,南部半岛也因距离海洋更近而受到影响。内陆地区往往彼此更加孤立,而沿海地区则很早就与外界接触。甚至有可能,地中海地区的移民在远古时代就通过海路来到这里定居,当然,在公元前,文化和经济商品肯定都是双向流动的。在公元前1000年早期统治半岛东部的泰米尔国王具有持久的影响力,这在很久以后的柬埔寨吴哥王国以及斯里兰卡和马来半岛的遗址中得到证实。中国的记录提到甘吉布勒姆是公元前2世纪重要的贸易中心,罗马人也提到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海岸的其他贸易中心。
马拉巴尔海岸或西部沿海地区的贸易更为久远。在公元前5000年中叶之前,雪松被出口到埃及法老王朝和美索不达米亚,而硬木似乎在公元前3000年时就已被运到古老的乌尔。古吉拉特邦(Gu-jarat)至少有一处哈拉帕文明遗址表明其四千年前与西亚有海上往来。到公元初年,贸易商们将货物存放在西部港口,以便通过陆路将它们运往东部——这一点仍然可以通过所发现的大量积存的罗马硬币来追踪。来自中东的犹太商人定居在马拉巴尔海岸的科钦(Cochin),直到最近,他们的后代仍然生活在那里。
然而,到13世纪,印度人的这种海上贸易基本上已经结束。那时,穆斯林贸易商主宰了印度洋贸易路线,而半岛的内部贸易则变得更有组织、更重要。从大约9世纪开始,由“行会”联系在一起的富有商人协会并入当地的商人团体,这些商人团体已经融入发达的农业社群,并且彼此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对外贸易对印度南部的重要性有所减弱,直到欧洲占主导地位后这种重要性才得以恢复。事实上,到了13世纪,印度人似乎认为出海是一种只有贪婪才能引起的愚蠢行为,那个时期的王室铭文提到“那些人[外国人]在海上航行中承担了巨大的风险,他们认为财富甚至比生命更有价值”。[2]
无论如何,半岛的环境,以其分离的河流流域和干燥的高原内陆,催生了历史上持久的社会和经济组织形式。印度人自己也认识到他们生活环境的多样性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泰米尔人在其早期诗歌中确定了五种“地貌景观”,每一种都与通常的诗歌主题、性和暴力的特定方面有关。与海岸相关联的往往是低种姓渔民,他们与妻子经常分离,并群殴激战。山丘往往是婚前求爱和抢牛(cattle raids)的场所。同样,旱地、森林和耕地有它们自己的与爱和战争的关联。
到13世纪,在农业环境中,有三种基本类型,每种类型又有各自不同的形式。这些都与居民的经济和社会模式密切相关(尽管不那么浪漫),分别为:基于严格控制且稳定的水井或蓄水池灌溉模式;仅依靠降雨进行灌溉的模式;以及将两者结合的灌溉模式。只有在西海岸才有可靠而且很强的季风,能保证单个农户种植水稻所需的充足水分,那里不需要跨地域性的合作或监管。与此相对应的另一个极端是,在干旱地区,贫瘠的土壤和稀疏的降雨只能养活那些种植小米、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畜牧业为生的散居人口。
那些水分充沛的地方,养活了大量的宗教祭司和军事专职人员(婆罗门和武士-国王),在那里,分工和地位等级最严格繁复。相比之下,在干旱地区,分工最简单,地位和等级差别很小,很少能找到婆罗门或寺庙:这些地区处于一种通常被称为“部落”的生存状态中,那里每个人都很贫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中,实际生产过程都已被高度程序化,种植者几乎没有掌握技能或发挥主动性的机会。然而,半干旱或混合式的生态形式确实为流动、独立和技术熟练的农民[他们被称为“sat”,即清洁的,首陀罗(shudras)]提供了机会;那里的商人和工匠也享有较高的地位,与占主导地位的有地农民有联系。这三种基本类型及其相关的社会模式一直延续到19世纪。
随着17世纪欧洲人的到来,印度的地貌开始从新的视角被审视。对欧洲人来说,热带地区既代表着天堂,也代表着危险。至少从古典时代晚期开始,尘世间的伊甸园经常被西方人想象为位于恒河谷(恒河被认为是来自天堂的河流之一)或在南部的科摩林角。热带气候对北方人来说在身体方面和精神方面都充满了危险,但同时也给人以轻松自在的希望。在令人能量衰竭的气温下,各种疾病肆虐流行。此外,降雨的季风性分布意味着水和土壤的定期流失,而水和土壤正是实现最大生产力所必需的。洪水、地震、干旱和饥荒也频繁发生。
欧洲人最初是贸易商,后来又是殖民者,他们希望从农产品中获取最大利润,同时也要确保劳动力不仅不会挨饿而且还能够不断地繁衍生息。这些利益冲突的程度取决于他们认为自己作为贸易商、伐木商、种植者或收税人的任期的保障程度。为了保护欧洲人的健康和利益,许多被远派到有希望带来巨大财富的热带伊甸园行使调查和管理任务的官员和雇员都经过了医学培训,因此也可以算是接受了科学培训。他们还沉浸在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哲学思潮熏染中,常常被美丽和具有异国情调的动植物所吸引而着迷,以致他们有时采取的立场与其商业雇主的宗旨背道而驰。最终,一旦殖民政府感到自己已地位稳固,他们实际上就能够对所在国家施加相当大的影响力,以支持他们眼中的对森林和野生动物的“保护”。因此,帝国主义的商业和政治目的有时会不同,后者需要稳定和长期的权力和收入,而前者则需要快速和最大化的利润。
总体结果是,“保护”这一概念往往被扭曲为是要保护森林免受当地居民及其行使利用森林资源的传统权利时所造成的伤害,而其实,当地居民的做法往往对环境有益,但是没有被认识到。相反,“保护”被当作一种借口,使国家能掌握共同财产的控制权并任意利用它为当时的政策服务——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印度独立,并且仍然在继续。因此,总的来说,也许早期植物学家和自然保护主义者在壮大西方环保主义的根基方面比对热带森林、土壤和水源供应提供任何实际保护方面更为成功。在英国殖民时期,印度北部和南部的一些森林地区被彻底损毁,取而代之的是茶叶、咖啡和橡胶的种植园,而在农业人口日益增多的压力下,甚至更大范围的土地上的野生植被被清除。其中许多这样的政策和态度在印度独立后一直被延续下来,并导致了当今的环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