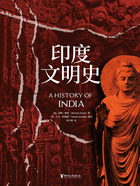
社群和国家
描述中世纪政治的特征至今仍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当中大多数争辩这个问题的人都同意,有必要同时考虑正式的国家结构——不管我们如何划定它们——和仍然是地方化的公民社会,或者,正如我想要说的,“社群化”方式,大约在笈多王朝时代,我称之为“族群和国家”的这种政治体制,似乎已经变得普遍。
查托帕迪亚雅注意到,在中世纪早期的状态下,类似单一的次大陆国家这样的技术基础显然是不存在的。他指出,直到11世纪末,次大陆有大约四十个王室。婆罗门所做的工作是进行有关“国家社会”理论的传播,即国家在社会之中,是其一部分,同时又处于社会外部并对其进行管理。从事这些工作的是教派领袖、礼仪专家和中世纪早期开始存在的众多宗教中心的祭司。婆罗门还参与了另一系列社会变革,这些变革与宗教变革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即:扩大种姓制度和定居式耕种生产。
社群与国家存在着平衡的关系。有时,就像拉杰普特人和奥里萨邦(Orissan)的小国君主们的情况一样,国家直接从以前的氏族/社群中产生;有时,就像朱罗王朝的情况,类似帝国的国家从地方部落崛起,并在不消除他们原生阶层的情况下延续。我认为这是一种主导印度政治的形式,直到18世纪,差异化的现代国家出现在次大陆,随之而来的是社群逐渐沦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外壳。
这是一个渐进的发展。在莫卧儿时代,氏族、教派和种姓等本地化社群机构众多,往往都包含数以万计的被以各种方式划分等级的人,反映了神圣和王室荣誉、种姓和血缘关系的观念形态。当地族群也是多种多样、相互交错、相互分割的,以赋予宗族和集体财产的个人分享者以多重身份。大量的交换关系遵循了按不同的“荣誉”和“地位”进行再分配的逻辑。地方社群履行被认为是适合他们的司法和政治职能。
南印度中世纪的政体无法进行自上而下的集权和改变,即使是对于强大的莫卧儿王朝来说也是如此,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发展起一个官僚机构,以包容和制服其基层的世袭组织。相反,莫卧儿政权本身也因下层的发展而改变,地方与区域机构和统治者与皇权发生冲突,并使后者的权威受到削弱。在印度南部、西部以及某些东部地区,有一个明显的特征,也许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晚期,不过到了17世纪才变得更加清晰,那就是,地方“领主”或“小国君主”从社群机构中的崛起。
在北部,情况则大不相同,莫卧儿王朝在这里安营扎寨,以掠夺性拉杰普特战士的氏族结构为基础,来巩固和利用先前的王权。由于这些结构从未被莫卧儿当局所废除,因此,以社群为基础的政治的重新出现并不令人惊讶,而这种政治最终改变了莫卧儿王朝。我之所以说“最终”是因为政治发展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被无数的突发事件所扰动。在这种体系的几个不同层面上存在着君主制的倾向,在区域和地方的准国王之间制造紧张和冲突,由此产生的紧张局势和冲突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模式出现。
从17世纪后期开始,大批轻装、快速行进的中亚骑兵流入南亚平原,或寻找军事工作,或建立自己的王国。他们被想要成为霸主的人广泛雇用(有时随后又取代这些人)。他们的军事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削弱了以前莫卧儿中央军队重型骑兵和攻城装备的优势。骑兵部落的涌入提供了新的军事前沿技术,使得通常以社群为基础的领主们有可能进一步摆脱莫卧儿统治的终极制约。
到18世纪,从这些进程中产生的国家,在权力和财产权方面与从前截然不同,尽管它有时试图回到莫卧儿式的过去。也许,国家权力最有力的巩固发生在地区文化和政治传统植根于前莫卧儿领地的省级统治或尚存的中世纪印度教王权的地方。那里的统治者试图加深和扩大他们对族群机构内部以及这些机构所维持的当地权贵们的权利和资源的主张。对税收和贡品的实际需求不断升级,皇家机构试图以新的规模支配并攫取商业资源,尤其是要为统治者现在所依赖的雇佣军买单。
到18世纪中叶,所有这一切对财产和国家概念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国家以前所未有的努力试图集中权力并对资源进行掌控,没收或要求支配以前归社群掌握的资源。然而,在实现“专制君主统治的梦想”过程中遇到了两个问题[也许最理想化的是迈索尔王国(Mysore)的铁普苏丹(Tipu Sultan),他提议建立彻底的国有经济制度]。第一个问题依旧是,缺乏官僚机构。因此,“王权”往往外包给社群机构内的商人、银行家和当地知名人士进行管理,通常以现金支付,这是一种“王权的商业化”。寻找愿意接手的金融代理人几乎没有什么困难:王室权力的新的和不断扩大的主张,除了提供丰厚可观的酬劳之外,还可被富有之人用来从社群机构手中夺取对权利和资源的控制权,并将由此产生的现金流从再分配途径转移到自己的口袋里。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在17世纪见证了行政管理者“大家庭”的兴起,其中包括蓬斯尔(Bhonsle)家族的沙吉(Shahji)和西瓦吉(Shivaji),他们将来自“国王”和社群机构的权利汇集在一起。所获得的权利是在各个家族经济中混杂管理的。最近对孟加拉、印度南部和旁遮普的研究也表明,这些地方也有类似的发展。
西瓦吉和铁普苏丹的17世纪和18世纪的世界,标志着在印度漫长历史中社群和国家之间辩证对立的最后阶段。正是在这个时期,“社群”被剥夺了所有目的和意义,只保留了意识形态:为此,需要在阶级框架内对社会和政治关系进行情境化处理,而这项任务在此只能用最简短的术语来勾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