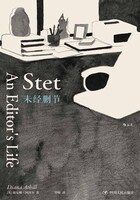
第2章 推荐序
李孟苏
年轻时,戴安娜·阿西尔美得凛然,如一尊古希腊时代的雕像。面部线条清晰,勾勒出有棱有角的下颌,五官俊朗,鼻梁高挺,眼睛跳跃着两朵火花,目光似乎永远看向远方;表情温和,少有脂粉气,多的是坚定舒展,带着一种她成长的年代极少被提及的中性美。到了老年,她脸上的刚毅愈发明显,显著到甚至影响了她的容貌——人老了会被岁月打磨成低分辨率的影像,面目模糊,很多时候难以分出性别——但很少见到一位老太太像阿西尔这样仍保有坚毅的下巴,高高的、光洁的额头。英格兰人推崇“坚硬的上唇”,视之为民族性的特征之一。看啊,她的双唇紧紧抿住,坚定、不畏缩、不妥协,就像她的一生——这辈子她基本上做到了按自己的想法生活。不由感叹,时光竟能在一个女人的面庞上烙下如此鲜明的睿智、沉静、友善、宽容的印记。
我第一次看到戴安娜·阿西尔的文字,第一次知道这位英国出版界的权威编辑和作家,是在2008年。这一年,阿西尔91岁,她的回忆录《暮色将尽》获得英国重要的科斯塔文学大奖,成为畅销书。她做了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编辑,并不缺乏领奖的经验,不过都是陪着她的作者,开奖前说些宽心的话,很理解地看着他们脸上努力绽出淡定的微笑。轮到她自己,她大概是英国文学史上年纪最大的获奖者,如此高龄才拿到平生第一个文学奖,想必书中内容也像消息本身,有不同凡响之处。
《暮色将尽》是阿西尔的第六本回忆录,薄薄的一本,很快就看完了。合上书,感慨她活成了诚实坦率的人精。按说有资格写传记的人精会写出传奇,阿西尔没有。她的回忆录由一篇篇独立又连续的短文组成,没有成型的故事,只有事件的碎片,这样的结构,可以随手翻,翻到哪页看哪页,读起来倒也轻松。碎片折射出她对“老年”的种种思考。
老年是和肉体衰败、对伴侣既照护又希望逃避、婚姻的责任、性欲消退、被社会遗忘、病痛、死亡等个人体验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话题在今天即使不再是禁忌,也很少拿出来公开讨论。衰老让她每天早晨起床变得不甚愉快:“你必须强打精神,挪下床,干点什么。”她每天为穿衣戴帽颇费心思,尽可能藏起多一点发皱的皮肤,绝不会有一点不妥当。“我的头发剪得很短,我也没剩多少头发了,它们就像一张蜘蛛网罩在粉红的头皮上,不过发型师说还没到戴假发的地步”。说自己状态好需要自欺欺人的精神,毕竟人生的绝大部分是越来越糟……阿西尔谈起来,毫无多愁善感的小情绪,倒是颇多“刺你一下”的想法和言辞,似乎这些禁忌在她这儿就是散步时被树篱中的刺扎了一下,没什么大不了。
人老了也有好处,一个可取之处就是性欲开始退潮,人生减去了一项负担。老了没有情欲,其实是“挣脱了套在疯子身上的锁链”。“变老”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不必再考虑未来。死亡是人生的一部分,每一种生物都会死。人生之旅,死亡是最伟大的一段旅程:“莎士比亚说过,懦夫在死之前已经死过很多回了。”
她写回忆录的初衷是给老人们看的,落笔比较温和,她说怕惊到读者。实际上因为写得太真实,仍不乏惊人之语。看她对老年人提出了何种忠告:“一个老人永永远远不应该期望年轻人渴望他的陪伴,或声称自己是他们的同龄人。享受他们(年轻人)慷慨的付出吧,但仅限于此。”
阿西尔一向鼓励她的作者“尝试写出真相,无论它们有多么不雅”,她在写回忆录时也遵守了这一戒律。她自己的写作始于45岁。写作之初,阿西尔一度围绕自我经验打转,写着写着,她越来越认为,写自己的事毫无意义,写作是为了弄清自己和生活的真相:“一旦你不用‘I’(我)而用‘eye’(眼睛)看事物,就摆脱了‘自我’。”诚实地写作,是一个重新自我认识的过程,帮助她度过了精神良好的晚年。她“这辈子从来挣钱也不多,没什么积蓄”,回忆录的成功增加了她的收入,她欣喜地说,她从未有过这么简单的乐趣。百岁生日前夕,她调侃,我想象不出来这世上还有几个百岁老人仍要靠动笔杆子生活。
做了一辈子图书编辑的阿西尔个人著述并不多,其中以回忆录为多。这一本本回忆录,就是一位聪慧的女性,一辈子以书为伴,泰然自若、幽默温和地讲述独属于她自己的乐观和坚持。在她生命的后半程,这些回忆录成就了她的文学声望,尤其是《未经删节》和《暮色将尽》,是英国书店里的常销书和畅销书。
“编辑永远不要期待感谢。偶尔收到时,应该将其视为意外的收获。”
在《暮色将尽》中,阿西尔几次谈到早前出的《未经删节》这本回忆录。《未经删节》出版于2000年,不妨看作是她的工作小结。
阿西尔生于191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在BBC工作。她通过BBC的同事,认识了安德烈·多伊奇。英国出版业的每个人都知道,约翰·勒卡雷的小说《锅匠,裁缝,士兵,间谍》里的特工托比·伊斯特哈斯,小个子,说一口中欧腔,“什么话都说不好,但他都会说。在瑞士的时候,吉勒姆听他说过法语,有德国口音,他的德语又有斯拉夫口音,他的英语尽是小毛病和元音错误”(董乐山译)——这长相和独特的说话方式,活脱脱就是多伊奇本人。
多伊奇是匈牙利犹太人,战争爆发前为了避难,辗转来到英国学经济学。战争爆发后,他却因为被视为敌方外国人,被拘留在英国马恩岛,无意中进入出版界谋生,很快他就显示出自己是“天生的出版商”。战争结束,他决定创办自己的出版社,便邀请阿西尔与他一同创业。他们曾经短暂地成为恋人,很快双双发现他们“缺乏充分的理由持续风流韵事”,不可能成为长久的恋人,于是理智地把关系归为“知己”。多伊奇浮夸、喜怒无常、难缠,开工资时十分吝啬,虽然阿西尔说他是“全伦敦最难相处的人”,但感念他给了自己最大程度的编辑自由,因此仍与他保持了终生的友谊和合作关系。
多伊奇先后创办了两家出版社,阿西尔与他共事,直到1993年以76岁的高龄退休。她有着极其敏锐的文学嗅觉、非凡的写作鉴赏力和无可挑剔的编辑判断力,擅长发现写作新人,第一个出版了奈保尔、莫迪凯·里奇勒和布莱恩·摩尔等人的作品,第一个把约翰·厄普代克、菲利普·罗斯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人的作品引进到英国。她还为波伏娃、凯鲁亚克、诺曼·梅勒、劳里·李、英国女诗人斯蒂夫·史密斯、女性主义哲学家玛丽莲·弗伦奇等作者出版了早期的作品。在她的关爱、鼓励下,沉寂了几十年的简·里斯和莫莉·基恩,在晚年分别出版了新小说《藻海无边》和《品行良好》,再次绽放出才华的光芒。这些编辑经历让阿西尔堪称英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学编辑之一,也帮助独立出版社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在英语文学出版业有了不可小觑的重要价值。
阿西尔打过交道的作家中,她最喜欢爱尔兰女作家莫莉·基恩,她认为最好的男人是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而奈保尔最缺乏个人魅力——每当她需要通过感恩来振奋自己的精神时,都会告诉自己:“至少我没有嫁给维迪亚(奈保尔)。”奈保尔曾向她求爱,在一次吃晚餐时亲吻了她,阿西尔和他“短兵相接”几个回合,看到奈保尔严重自大的那一面,拒绝了他。
半个世纪的出版生涯,“年老的前编辑的故事”,阿西尔趁自己没有完全遗忘,记录下它们,取名《未经删节》。回忆录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她的编辑日常工作,一部分是她为六位作家,莫迪凯·里奇勒、布莱恩·摩尔、简·里斯、阿尔弗雷德·切斯特、V.S.奈保尔、莫莉·基恩写的人物小传。
希望或已经成为图书编辑的读者,不妨重点看回忆录的第一部分,那揭开了出版业赤裸裸的真相,完全可以当作行业指南,每句话都是阿西尔最个人的经验与心得。
她一句棒喝,说明白编辑应具备的基本修养:“编辑永远不要期待感谢(偶尔收到时,应该将其视为意外的收获)。必须永远记住,我们只是‘助产士’,如果想要听赞美,就得自己去生孩子。”她很享受这份工作。做图书的助产士“就像从一个形状笨拙的包裹中取出一层层皱巴巴的棕色包装纸,然后慢慢将里面的漂亮礼物展示出来”。而且,这份工作扩大和延展了她的生活,让她每天有事可干,能赚到足够的钱维持生活,并且遇到非常有趣的人。
一个好编辑往往通过一个细节就可以判断出一本书的好坏,阿西尔正具备如此天赋。美国作家诺曼·梅勒的成名作《裸者与死者》是阿西尔出版的。这部战争题材的小说“因语言淫秽”被伦敦六家大出版社拒稿,阿西尔收到书稿,感慨在文字上设置禁忌是多么愚蠢,并注意到一段描写:“那是关于疲惫不堪的士兵在深深的泥沼中挣扎着举枪的段落”。这个细节让阿西尔坚信她看到的是杰作,冒着极大的风险坚持出版了这本书。这本书奠定了阿西尔和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在业内的地位和盛誉。
她紧接着又提醒,某些细节是作者玩的花活,是故弄玄虚,编辑看到,会受到一种神秘的牵引:“我无法理解这个,这超出我的理解范围,或许反而非常特别。”阿西尔不以为然:“这种因为抓不住重点而产生的惯常反应有一种感人的谦逊,但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是一种对智慧的背叛,这种背叛允许大量垃圾伪装成艺术。”
阿西尔入行之际,正逢英国战后文化复苏的时代,图书短缺,一本文学图书哪怕明显卖不出去,只要阿西尔“宣布这书不错,我们就会立刻不假思索地发行”。那真是出版业的黄金时代啊。20世纪70年代之后,图书制作成本不断上升,像多伊奇这样的小型独立出版社生存得越来越艰难,不得不把股份卖给跨国传媒集团。美国时代公司旗下的“时代生活”接管了多伊奇出版社,要求出版社按大公司的模式运营,比如交出未来五年的出版计划,比如参加富有异国情调、华而不实的销售年会。多伊奇出版社的会计写信给“时代生活”的财务说:“我们在五年内要出版什么,取决于某些坐在阁楼不知名的人们脑子里在想什么,而我们不知道那个阁楼的地址。”此后,多伊奇出版社经历了多次转手。
编辑们力图弥合出版商认为有趣的内容与普罗大众认为有趣的内容之间的差距,减少小说,多出非虚构类作品,阿西尔感到大脑一片空白:“要么不得不内心痛苦地拒绝一些好作品,要么自欺欺人地出版一些亏本的东西。”
阿西尔退休后反思,在她的职业生涯里,出版业从业者属于知识精英阶层,我们认为的“好书”往往也只是这个社会阶层观念中的好。“阅读和吃饭其实是一样的,最大的需求永远是快速、容易、简单、能立即识别的口味——比如糖和醋。”这种需求一直存在,只是当下的出版界“更奢侈地迎合了这种愿望”。
多伊奇出版社遇到的困境、挣扎和努力,在中国的出版人、读者看来,有令人熟悉的沮丧。
对残忍,他们从不感到惊讶
《未经删节》全书的华彩是第二部分,阿西尔写下了她与六位作家的交往。那是六篇杰作。
编辑和作者的关系,阿西尔原本抱着佛系的态度,认为“双方都没有义务努力建立亲密的私人关系”。当然,“如果真的由此开出了喜欢的花朵,也是一种自然的发展。”她用耐烦的心培育出花朵。
作者普遍有种心理,“无论他们的书挣了多少钱,都应该完完全全属于自己”。于是,作家看编辑就是给自己做衣服的裁缝,“工作干得还不错的令人愉快的人,允许一定程度的亲密感”。因为裁缝必须了解某些私密的尺寸,但绝不会被做衣人请吃饭。反过来,阿西尔对作者的奉献,润物细无声。
有的作者依赖编辑,就像网球明星依赖自己的父母,这时候阿西尔不得不扮演保姆的角色,简·里斯的小说《藻海无边》可以说是她哄出来的。她从人海深处把里斯打捞出来,给予里斯极大的理解和同情。阿西尔鼓励她写下去,在生活、精神乃至法律上援助她,那是扔给了她一个救生圈,让衰老、脆弱的她有一丝力气“迎着艰难的命运”,游出酗酒、孤僻、贫穷、偏执、不切实际和精神崩溃的苦海。里斯创作《藻海无边》用了九年时间,漫长又艰辛,如果没有阿西尔持续的悉心呵护,里斯会怎样?她还能完成这部人生最后的长篇小说吗?
阿西尔不惜笔墨描写了与里斯紧密相连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她的出生地多米尼克,这个加勒比汪洋中的岛屿被火山和雨林填满,极其孤绝,却是她的心灵属地;一个是她晚年生活的凄凉陋舍,“位于一排连在一起的单层棚屋的最后一间,是一间掩映在树篱之后蜷缩着的灰色建筑,很不起眼的权宜之所。看起来好像由瓦楞铁皮、石棉和焦油毡搭建而成……厨房……大约十英尺见方……唯一的取暖设备是一种电暖器……除了烧焦人们的小腿,几乎无法温暖空间。房间里放着简工作兼吃饭的小桌子,两把直椅,一个食物柜,一个餐具柜,这些,就是全部的家当,这里,就是简度过每一天的房间”。在这平房里,里斯完成了《藻海无边》,阿西尔“清晰瞥见了简·里斯的核心奥秘,一个如此无能的人,一个承受了混乱、灾难,甚至毁灭的人,内心是钢铁般坚强的艺术家”。
只有理解了里斯生命起初和终了的两个地方,才能真正看懂里斯的小说。
阿西尔同样写了奈保尔的家乡特立尼达,力图帮助读者理解奈保尔的作品。她一丝不苟地描述了奈保尔的冷酷、自大和残忍,自嘲与他相处时的勇气和自欺欺人。在她去特立尼达旅行过后,终于明白奈保尔要逃离什么,以及他为逃离家乡付出了何种代价,那是贯穿他一生的绝望和焦虑。他们曾经谈到如何渡过生活中的难关,阿西尔说,靠简单的快乐,比如水果的香味、泡热水澡的温暖、干净床单的触感、花朵应和着生命轻颤的方式、鸟儿轻快的飞翔。奈保尔悲伤、困惑地回答:“你真幸运,我就不行。”阿西尔直言不讳地评论,奈保尔的作品缺乏这种被称为动物本能的东西,所以是“褪了色的”,它们确实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并不吸引人。
阿西尔的性情坚定、活泼,行事坚决、明智,她却奇怪地被悲剧人物吸引了。她以近乎痛苦的诚实观察每一个迷失的灵魂,同情地写出他们沉沦在那种被定义为“疯狂”的漩涡里,赞扬他们的美德,不带一丝说教。
一个女性主义者自觉的一生
戴安娜·阿西尔生于1917年,于2019年去世,享年101岁。
阿西尔的母亲爱丽丝,出身于书香馥郁的家族。爱丽丝的父亲威廉·卡尔(William Carr,1862—1925)是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外公詹姆斯·弗兰克·布莱特(James Franck Bright,1832—1920)曾担任牛津大学大学学院的院长,在历史学和传记写作方面颇有建树。两位先辈让阿西尔知道了,“读书也可能成为一份工作”。
卡尔家族在诺福克郡乡间有一座迪钦厄姆庄园(Ditchingham Hall)。庄园原本属于某世袭男爵家族,红砖建的主楼建于1710年,卡尔家族在1885年买下来后,扩建了宅邸,足有20间卧室。庄园里树林茂密,风景清幽美丽。在这里,阿西尔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她和弟弟、妹妹一起骑马、打猎,听外婆朗读毕翠克丝·波特、吉卜林、沃尔特·司各特的作品。大宅里,抬眼望去,到处都是书。“阅读是人们在室内做的事,就像骑马是在户外做的事一样,这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一种乐趣”。成年后,她相信文字的力量,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书籍:“书本能带我远远超出自身经历的狭隘界限,极大地扩展我对生活复杂性的认识:它充满了黑暗,以及,感谢上帝,还有那一直艰难跋涉的光明。”
相比起来,阿西尔的父系家族乏善可陈。她父亲是一名军官,没有什么家业,甚至“没能拥有让我们得以扎根的土地”,以至于小家庭要依附于妻子家族的庄园。也因此父亲家族的男人视自己谋生为理所当然,这是她受到的另一种家庭教育:你必须脚踏实地,自己谋生,此法则也适用于女儿。
阿西尔很早就认识到,时代已经不允许女人把婚姻当作“绝对靠得住的谋生手段”。她成长为英国最早的一批职业女性,思想独立,反抗传统,从不自负自夸,不自怜自恋,更不自怨自艾。当时髦的社会思潮涌来,她不会随波逐流,观察和见解清晰得令人不安,哪怕这些清晰暴露了她情感上的弱点和缺点。她归结于自己“是个典型的英国人,喜欢清醒”。
精确、清晰和沉着,不仅是她观察世界的方式,也是她行文的风格。读者或许感到某种冷淡疏离,奇怪的是,不会感到寒意。
阿西尔终生未婚,只短暂地订过婚。未婚夫与别的女孩发生一夜风流,阿西尔痛苦之余,开始思考占有和忠诚:“有人以为那表明对一个人的爱,并非要控制对方。但对有些人来说,(不控制对方)根本是不可能的。”她认识到“女人其实也能不谈爱,仅仅因性就可以燃烧”。而婚姻对当事人提出了“占有和忠诚”的要求,可她的天性不喜欢占有,忠诚也非她的美德,“夫妻关系里,善意和体贴才是最重要的”,而非不对等的忠诚。她尊重别人的忠诚,但以为“如果在性事上天天盘旋纠结忠诚问题,就有些无聊了”。
同时她意识到自己“非同寻常地缺少母性本能”,不愿为了丈夫和婚姻而生孩子。她心中有些重要的事,是不该被别的事打扰的,显然儿女之事不在重要名单上。她竭力要摆脱婚姻这一游戏规则的束缚,于是主动放弃了婚约。后来有男人愿意和她结婚,阿西尔形容,这就像上流阶层的俱乐部终于接纳了某位出身较低的名演员:那是带着不屑和傲慢的恩赐。她不需要这种恩赐。
摒弃了婚姻,却在偶然间促成了阿西尔事业的成功:她必须工作,这是她独立的经济来源。
阿西尔成为编辑的年月,女性在出版社的位置通常被安排在营销部门,而非董事会。她在多伊奇出版社担任执行董事,但收入并不高,她敏锐地注意到了男女没有同工同酬的问题,并进行了反思。在《未经删节》里她写道,“出版业都由许多收入微薄的女性和一些收入更高的男性经营着,女性当然能意识到这种不平衡,但她们似乎认为这理所当然。……我想部分原因一定在于后天养成:在很大程度上,我所处的环境将我塑造成取悦男人的人”。
她承认自己没有为不公正的对待争辩过什么,也钦佩那些积极争取女性权利的活动家。她坦率地剖析自己,做编辑这份工作,是因为自己喜欢,它能带来做好工作的满足感;加之天性“懒惰”,不愿为金钱操心,不愿意为了钱去做任何自己不想做的事,只乐意花钱,在出版这门复杂的生意中,她“唯一真正身心均想沉浸其间的,只有对书籍的选择和编辑”,所以她选择做花钱的编辑,而不是负责赚钱的出版商。她的真实想法是,“安德烈(多伊奇)确实利用我的天性占了我的便宜,忽视了我的感受,廉价使用了我,但就这份工作而言,还谈不上伤害了我的感情。”她确实没有感受到男女薪酬不平等带来的痛苦,因为她“正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她不内疚自己在争取平权上的惰性,指出,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同时受到后天环境和天性的影响,“为什么一个女人做了同样的选择,就应该认为她被洗脑了呢?”
她把自己看作是“人”,而不仅仅是“女人”。她不是激进的女权活动家,她是温和的真正的女性主义者。别忘了,是她出版了波伏娃的书。
阿西尔最欣赏简·里斯的文风。里斯常常说,文字要“删,删,删”,阿西尔对此非常认同,“精确的写作意味着精确的思想”。文如其人,阿西尔这一生都不曾拖泥带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