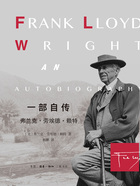
The Boy
男孩
在维多利亚时代[1]的威尔士[2],有一个身材魁梧的帽子匠。他做的帽子是一种尖尖的黑色圆锥,就像骑着扫帚的巫婆们戴的帽子。威尔士人也戴这种奇怪的帽子。这个帽子匠对他的手艺格外自豪。在集市上,每当有顾客在他的摊子前驻足,他都会把自己做的帽子扔在地上,说道:“踩上去试试!”
每逢星期天,他都向周围的人布道。胸中永远有一团火焰,他总是瞪着黑黑的眼眸,执着地追问人如何才能真诚地面对上帝。然而,身边所有人的答案都不能令他信服。
他名叫理查德·琼斯,一个热情却又孤僻的唯一神派[3]教徒。有一位来自古老的威尔士家族的姑娘玛丽·劳埃德,听过他的布道,爱上了他。
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享长寿。
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行恶过分。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4]
于是,她不顾父母的反对,追随自己的信仰,也追随了他。即使她富有的家庭看不上这个倔强的汉子,那又何妨。她爱他,所以信赖他。
他们在一起有了七个孩子,这个家庭的姓氏改成了“劳埃德-琼斯”。
后来,他的自由直言触犯了周围保守的人,因此,这个唯一神派教徒想到了美国这片乐土。他带着娇小的妻子和七个孩子漂洋过海,向西来到这个崭新的世界。在那里,他要凭借强健的体魄耕耘一块自己的土地,建起自己的家园。在那里,他可以自由地信仰和表达,因为人是生而自由的。
五十三岁那一年,这位也是布道者的帽子匠带着他的托马斯、约翰、玛格丽特、玛丽、安娜、詹金和南妮,成了威斯康星[5]土地上的拓荒者。
小南妮在旅途中夭折,被孤独地留在了陌生的地方。
他们乘木船顺运河而下,再坐汽船驶过大湖,途经密尔沃基,到达艾霍尼亚。在那里度过的六年,迎来了四个新的小生命:爱伦、简、詹姆斯和伊诺斯。然后,这个大家庭找到了威斯康星河[6]畔的这座山谷。
“山谷”,是日后全家人对他们钟爱的这片沃土的爱称。它依偎在两座舒缓的山丘之间,谷内地势较高的一端被另一座山丘分成两个更小一些的山谷,各有一条溪水从中流出,在他们的农场附近汇成一条更宽的溪流,再一路向前汇入威斯康星河。从附近的小山丘上望去,山谷里地势较低也较为开阔的一端,是溪流冲积成的支汊交错的沙洲。这片不生树木的沙石地,曾经是远古时代威斯康星河的河床。
当外祖父和他的孩子们开垦这片处女地的时候,友善的印第安人还常常在周边出现。
家里的长子托马斯是个木匠,他在山丘向阳的缓坡上盖起一座小屋。外祖母领着孩子们在小屋四周和门前的小路旁,栽下一株株挺拔的香脂白杨和伦巴第白杨。橡木板钉成的曲尺形状的围栏,沿着小路两侧一直延伸到山顶和山丘北坡的树林深处。
向阳的南坡过于干燥,除了裸露出岩石断层的地方之外,基本上没有植被生长。他们房子的屋顶仿照威尔士的传统样式铺着茅草。墙面是托马斯和弟弟们一道钉起来的木板和木瓦,俭朴却很“现代”。厨房是倚在屋后的一间棚子,一段露天阶梯通向厨房下面石头砌成的地窖。屋子不远处另有一个小储藏室,部分埋在地下,部分露出地面被草地覆盖着。
在这片“山谷”里,威尔士来的拓荒者理查德·劳埃德-琼斯,带着他的十支血脉和一道伤痕,在他憧憬过的美国大地上扎下了根。如今,这里是他安居的乐土。
无论是船行在运河上还是大湖里,还是全家暂宿在客栈里,所到之处,他从未停止过布道。他身边总有心怀崇敬的听者分享他的激情和虔诚。虽然他朗读《圣经》时带着独特的语调和浓重的威尔士口音,但是没有人误解他的意思。听者常常会从他布道的言语里感受到新鲜的含义,重新思考他们的信仰。他不仅仅是在土地上拓荒,也是在愚昧的地方点燃精神之火。
在艾霍尼亚,他加入了一个教会。但是又一次,他所信仰的“人生而自由,所以自由地信仰”受到压制。当教会要对他进行审问,他说道:“不必劳神。若是冒犯了诸位,我自会离开。但是我的思想不会屈服。”
他把古老的德鲁伊教[7]的圣符 用作家族的徽纹,它象征着“与世界对立的真理”。外祖父的布道秉承着先知以赛亚的意志:“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8]他的孩子们都要反复颂读《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直到熟记于心中。
用作家族的徽纹,它象征着“与世界对立的真理”。外祖父的布道秉承着先知以赛亚的意志:“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8]他的孩子们都要反复颂读《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直到熟记于心中。
他的一个小外孙渐渐长大,萌生出对以赛亚的怀疑。难道因为注定会凋谢,鲜花就不配更娇艳地开放吗?对于山谷里这些以耕种为生的人而言,草是多么的不可或缺啊!如果没有晒干的野草喂养牲畜挨过寒冬,连外祖父自己也难以生存。
自从以赛亚听到“我们神的话”,千百年来,永远有鲜花在星光下合上它们的眼睛,又在阳光下睁开,再把种子撒进大地善意的胸膛。鲜花的生命似乎永不褪色,以赛亚听到的“我们神的话”却被口口相传,经过了无数次篡改……
或许最初并非如此。这些必将枯干的草和必会凋残的花,也同样蕴含着上帝的真理。在这一段如雷霆般自负的话语里,似乎流露着卑鄙的忘恩负义。
黑云滚过环抱着山谷的一座座山丘,狂风暴雨抽打着树林,吞没弱小的花草。风暴过后留下一片扭曲和毁灭的景象,让那个男孩看到了以赛亚的“审判”。
看呐!以这位先知的名义,地狱肆无忌惮地张开了“她”的巨颚。
祸哉!祸哉!这个词在男孩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沉重的一击——“祸哉!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9]即便是“所怀的胎”[10]也难以幸免。孩子们将被踢倒在脚下,遭到践踏。
以赛亚所敬畏的神无情地鞭挞着渺小的芸芸众生,从不抹去四溅的血污,从不满足于面前的累累伤痕,而是不断用可怕的巨掌更加无情地猛击。
然而,以赛亚告诫世人,若你胆敢与“他”(谁也无从判断“他”指的是以赛亚自己还是他的神)论理争辩,你的罪孽必将像雪地那样洁白。为什么呢?
这位被奉作先知的神圣斗士,以他自己的理解来描摹上帝的意志,以他自己的欲求来界定美德,因为他的欲求恰恰是痛苦而不是快乐。
把这些注入一个孩子的头脑,这是何等的诅咒啊!对于一个孩子,还有什么样的鞭打比这更恶毒?对于一个孩子,还有什么样的教导比这更可怕?
小外孙时常看见他敬畏和热爱的外祖父,像一个威武的酋长,须发皆白,腰板挺直地坐在那匹名叫“提摩太”[11]的马上。他双脚踩在马镫里,左臂挂着牧羊鞭,腋下紧紧夹着那本寄托着他信仰的《圣经》。这位以赛亚的信徒纵马奔驰,从来不曾掉落那本圣洁的书。
从星期一到星期六,外祖父信奉的福音是辛勤的劳动。他毫不留情地教他的孩子们,如何在早已筋疲力尽的时候,为了更多的劳动流淌更多的汗水。他率领着子孙们伐倒大树,在亘古以来蛮荒的丛林中,开辟出人烟的生机;为造化的表情,填上一抹人间的笑容。
有时候,路过这里的印第安人会在他的家门口留下一些鹿肉。他会放一些烟叶作为交换,因为他自己也抽烟斗。他的烟斗让他饱受全家人的责怪。外祖父对孩子们一向严厉。如果某个孩子不小心在盘子里多倒了高粱糖饴,外祖父会毫不偏袒地要求他全都吃光——你的“眼睛不能大过胃口”。这种严厉得到全家人的尊重,但是他们难以谅解也无法容忍他的烟斗。
最终,外祖母用她的爱缓和了外祖父的倔强。她教会他如何利用烟斗缓解他的哮喘。[12]
他克服了哮喘,而烟斗也陪伴着他直到生命的终点。
外祖母的慈爱交织着外祖父的倔强,把他们的十个儿女永远牢固地维系在一起。
在山谷里安家十年后的一天,外祖母安详地离开了。外祖父亲手搭起一座亭子,供她的遗体下葬前暂时安放。虽然失去了自己生命中的光辉,但是外祖父仍然坚强地领着孩子们,站在亭子前为她祈祷。多年以后,那一次祈祷依旧萦绕在孩子们脑海里,依旧是他们听过的最美丽的祈祷。
又过了十一个年头的某一个夜晚,八十七岁的外祖父在他的床榻上安然睡去了。他的精神,依旧没有“屈服”。
外祖父的精神在美利坚的处女地上生生不息。这片崭新而广袤的国土,是他和许多远道而来的人心目中的自由。他在其中的一角种下一个来自威尔士的小部落,让它在土地里生根发芽,与周围生长的万物为伴。
土地!它给予理查德·劳埃德-琼斯这样的拓荒者无所不包的深厚、宽广和美丽。他与田间的石头立约,[13]他自己仿佛就是葱绿的山崖下露出的一块岩石。他建起一个自己的小世界,外面是一重重更大的世界。重重叠套,永无止境。
他不在意那些百合花如何生长。[14]
瘦小的外祖母就是他心中的一切。
美向所有坚强的人走近,虽然有时候带着伪装,不易察觉。
他的子孙后代继承了他的秉性,但是温柔的外祖母给他们心中添了一份在意“百合花”的温情,教会他们对“花必凋残”的同情,对“草必枯干”的感恩。
山坡的草地上有一株“母亲的松树”,那是她疼爱的另一个孩子。这个小生命被瘦小的外祖母种在那里,却被粗心的割草人划伤了。看到有人要把树苗拔起来扔掉,她赶忙拦住:“不要拔,把它留给我。”她取来针线筐,跪在树下的草地上。先用松脂填平树干上的伤口,然后用一块厚实的粗布把树干裹紧,再细细地缝好。
今天,那株白松已经长成七十五英尺高!虽然被雷电击中过两次,但是和众多因人类而消失了的同伴相比,它始终巍然屹立,像一件高贵的标本。
外祖母心爱的伦巴第白杨,曾经沿着小路连绵地爬上山坡,如今只剩下零星几簇。她栽下的香脂白杨,其后代已经遍及山谷周边你想不到的地方。
还有她种在家门前的丁香和石竹花,已经繁衍成一簇簇茂密的花丛,装点着大路两旁。
在这片充满着劳动、歌唱和祈祷的威斯康星原野上,有一个劳动者的身影,属于安娜姐姐。她的儿子就是那个对以赛亚心生疑惑的小男孩,约翰舅舅用雪地里的脚印教导过的小外甥。
安娜是劳埃德-琼斯家的第五个孩子。离开威尔士那年她刚刚五岁,却像男子汉一样走起路来昂首阔步。她有着俊俏的鼻子和满怀梦想的深栗色眼眸,饱满的额头前飘动着同样深栗色的秀发。在她的沉静和优雅下面,埋藏着热情和力量的火焰。
从很小的时候起,安娜就深爱着教育。整个家族都把教育视为救赎之路。唯有教育才能使人摆脱野蛮,有别于兽类。并且,唯有教育能够打开枷锁,把美从宝库中解放出来,融进生命的点点滴滴——在这一点上,她错了。她相信教育是上帝直接的显现,指引世人靠近美,但是她也热爱美的事物自身。
长大以后,她成了一名乡村教师,每天骑着马翻过一座座山丘,穿过一片片树林,往返于家和学校之间。时至今日,已经老态龙钟的乡邻们提起他们的老师“安娜姐姐”,依然满怀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