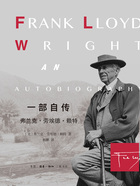
译者序
一位读完了本书译稿的朋友,认为这是“一个精彩的电影剧本”。这种评价出乎我的意料,但是仔细想来,的确非常恰当。
很显然,作者借鉴了他所崇拜的雨果惯用的笔法。雨果的每一部小说,都像带有完整分镜头的电影剧本。这部自传和《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一样充满鲜活的人物、精彩的对话,当然也屡屡出现雨果式的大段抽象议论。
如果把这个剧本搬上银幕,你会看到男主角的形象在令人目眩地变换:顶着烈日锄草放牛的少年,校园舞会上出丑的大学生,在东京的陋巷里搜买浮世绘的艺术商,三次婚姻中的丈夫,七个子女的父亲,涉及私奔、火灾、谋杀、诱拐和破产而频频见报的社会名人,监狱铁窗下熬过寒夜的被告,驾驶着敞篷轿车横穿半个美国的花甲老者……
这就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人生吗?
是的,赖特用他长达九十二年的人生,验证了他喜爱的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诗句——“丰盛即美”(Exuberance is Beauty)。
当然,他“丰盛”的人生还有另一部分内容。以上种种形象终归只是他的“客串”。他的主业是从事世界上最伟大(没有之一)的艺术种类。在六十多年的建筑师生涯中,赖特总共设计了一千一百座建筑,其中约五百座建成。包括“流水别墅”和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的二十五件作品,被美国政府列为“国家历史名胜”(National Historic Landmark)。赖特被他从未加入过的美国建筑师协会,评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美国建筑师”(the greatest American architect of all time)。他的八件代表作(六座住宅和一座教堂、一座博物馆),作为一个系列项目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当七十五岁的赖特为洋洋洒洒的《一部自传》画上句号时,他正准备迎来事业的又一个高峰。此刻,他所有建成作品中的大约三分之一尚未开始设计。很可惜,这一神奇的事实也是本书最大的缺憾。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赖特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于攀登建筑的新高峰,无暇增补他的文学遗产。因此,我们无缘看到他描述“古根海姆博物馆”等杰作诞生的过程。
赖特本人未必认为这是多么严重的“缺憾”。
毕竟,他生命中最后的十几年里一片坦途,荣耀与成功如潮涌来,生活似乎不再那么“丰盛”了。而丰盛的生活才是他追求的终极目标。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部自传》里长篇累牍地介绍他野餐带了哪些美食、他如何被记者和律师们纠缠,却没有更详尽地描述他的更多建筑杰作。
他最引以为豪的或许不是任何一件作品,而是他享受(某些时候是忍受)的丰富人生。
话虽如此,这毕竟是一位建筑师的自传。作品仍是这棵大树的主干。
值得注意的是,名震寰宇的“流水别墅”在数十万字的《一部自传》里,居然只占据寥寥几行,一笔带过。而另外几座知名度较低的作品,各自都有七八页的详细描述。我推测,那是因为“流水别墅”在他自己心目中无足轻重。如果让晚年的赖特给自己的作品排座次,“流水别墅”未必能进入前二十位。在山清水秀之处,没有任何限制的豪华民宿,只是他抖抖袖子的戏作。他晚年的事业重心,是解决“尤松尼亚住宅一号”这样的难题。在街边狭窄的用地里,为手头拮据的普通的三口之家,建起能长久生活的小房子——并且是全美国最早拥有地板采暖的住宅。
《自传》里提到的大多数代表作,都得到了妥善的维护。例如,“统一教堂”历经百年中的多次维修,仍在正常使用。他的长孙埃里克(建筑师劳埃德的儿子)也是建筑师,参与了包括“统一教堂”的多个赖特作品的维修。“巴恩斯道住宅”(蜀葵)已经开放为博物馆。约翰逊制蜡公司(在中国的名字是“上海庄臣”),像大教堂一样的总部大楼依然身体健壮,目前它的主要角色已经不是办公,而是这家跨国公司最宝贵的企业文化遗产,每年迎接数以万计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
令人遗憾的是,现代建筑史上最重要的杰作之一,赖特极为得意的拉金办公大楼,因拉金公司破产,于1950年被拆毁——原址成为一个停车场。在自传中占据篇幅最多的作品——东京帝国饭店,于1968年被拆除——原址建成了十七层的新帝国饭店。拆除的主要原因,是它地处东京的核心区,只有不到三百间客房,无法满足商业需求。此外,赖特当年把帝国饭店设计得像一条大船浮在泥塘上,曾帮助它抵抗住了关东大地震,但是也造成建筑整体持续向下沉降。所幸,日本与赖特还有一段缘分未了。饭店精美的大门厅和建筑前方的水池,被细心地拆解,在爱知县犬山市的露天博物馆“明治村”原样重建。
赖特本人最钟爱的作品,还是他自己的家。这一点也是他在现代建筑大师群体中保持鹤立的原因之一。按照常理,建筑大师自己的家,应当都是建筑杰作。事实却并非如此,有谁知道柯布西耶、密斯的家是什么样子呢?
赖特的三处家园,目前都是游人如织的博物馆,一切都像是他留下的样子。橡树园的家里,壁炉上刻着“Truth is Life”(真理就是生活)。山谷里的塔里埃森,小剧场的门楣上方刻着贝多芬《悲怆奏鸣曲》第一乐章的几行曲谱。沙漠里的西塔里埃森,粗糙的石墙上,挂有一块铜板,刻着:“The reality of the building does not consist in the roof and walls but in the space within to be lived in。”这是《老子》第十一章中“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的意译。
赖特的另一件重要作品,就是《一部自传》。
在有关赖特的上百本学术专著当中,它享有极其独特的地位。尽管时常思维跳跃、有时刻意地闪烁其词,但仍它不啻为探究赖特的思想和人生的最佳线索。
从1926年起的数年时间里,经济大萧条与赖特“臭名昭著”的私生活产生叠加效应,造成他几乎没有建筑项目可做。这时的赖特接受了夫人的建议,开始写作《一部自传》。相当于本书前四卷内容的第一版于1932年发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随即于1933年和1938年再版。而后,经历了“复苏”的赖特补充了第五卷,并且对前四卷加以删减,1943年发行了最终的“定本”。其英文版于1945年、1957年、1977年和1998年,由不同出版社多次再版。中文版所依据的是美国石榴出版社(Pomegranate)的2005年版本。
每一卷前面的插页都有赖特亲自设计的线条图案,抽象地体现该卷文字的主旨。前四卷序曲的主题,是按照冬、春、夏、秋顺序排列的四季,这些都是建筑师用心良苦的布局。
想必很多读者会注意到书名里的“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为何写上这么啰唆的全名?书店里的英美名人传记,大多是类似《华盛顿传》或者《托马斯·爱迪生传》这样的书名。某些传记的英文原著可能包含中间名(middle name),但是中文版为了简洁起见,则极少保留。实际生活中,美国人的中间名,一般也只在少数场合或正式文件里出现。赖特则有所不同。他在各种场合做自我介绍,总是报上全名,中间名“劳埃德”永不离身。一部分原因,恐怕是老先生故作鹤立鸡群之势;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强调他母亲一方的威尔士血统。“劳埃德(Lloyd)”是典型的威尔士姓,也是他外祖父的复姓“劳埃德-琼斯”的一部分。相对于外来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威尔士人是不列颠群岛的土著凯尔特人的后裔。直到现代社会,威尔士人仍保留着某些鲜明的文化特征。威尔士语和英语的差异,远大于英语和德语之间的差异。“劳埃德”相当于赖特的文化名片,表明他和盎格鲁-撒克逊气质的美国文化主流划清界限。
本书第一卷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赖特采用了第三人称。这种别致的写法,是效仿他的恩师路易·沙利文。沙利文的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An Idea,目前尚无中译本,从童年写到中年,全书都采用了第三人称。在第三卷里,赖特饱含深情地描写他去探望垂危的沙利文,沙利文激动地把他的自传样书题赠给这位著名的弟子。
迄今为止,这部书的译本包括德语(1955年出版)、法语(1955年与1998年出版两种不同译本)、意大利语(1957年、1998年出版两种不同译本)、日语(1988年出版)以及韩语(2004年出版)。
在赖特的有生之年,数以百计的年轻人从美国各地,从墨西哥、意大利、中国和印度,来到他身边充当学徒。其中有些人并没有建筑专业的基础,也不甚了解赖特的作品,只是因为读了这本自传,就毅然做出改变自己一生的决定。
仅举两例。1932年,从密歇根州某社区学院英语系毕业的青年约翰·劳特纳(John Lautner,1911—1994)接受了他母亲的建议,来到塔里埃森学习建筑。日后,劳特纳成为赖特的“有机建筑”最重要的继承人之一。他于九十年代去世的时候,已经是美国现代建筑史不可忽略的人物。而当年母亲的决定,直接来源于她刚刚读完的《一部自传》。
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印度。1945年,即将从孟买建筑学院毕业的曼辛·拉纳(Mansinh Rana,1921—2012),在学校图书馆读完了《一部自传》,随即决心远赴重洋,于1947年加入赖特的学徒会。在大师身边的几年,塑造了这位日后尼赫鲁非常器重的著名建筑师。
我之所以有勇气将这部书译成中文,正是因为我坚信自己有限的语言能力和学识,也无法削弱它蕴含的力量。作为一个蹩脚的建筑师,我从这本书里学到:只有思考整个世界,才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建筑师。如果仅仅思考建筑,即使你的作品能够体面地建成,它多半只是对于模仿品的再模仿,你本质上仍然只是一个出色的绘图员。
作为人口两千万的大都市中的一个原子,我发现书中写于八十年前的预言已经成为现实:行人无路可走而汽车只能慢慢蠕动、拥挤的地铁和公共汽车剥夺人们起码的尊严。这究竟是人类进步的标志,还是大家都有幸分享的耻辱?作为一个父亲,我甚至可以从书中汲取教育孩子的经验。
我在此感谢世纪文景出版社的多位编辑,把这本书引进中国并使之于2014年顺利面世;也感谢三联书店的编辑刘蓉林促成了它的再版。
我在此感谢赖特基金会(Frank Lloyd Wright Foundation)的玛戈·斯蒂普(Margo Stipe),她帮助我破解了原文中的许多掌故与难点。我的美国朋友庞博(Peter Bandonis)和日本朋友百町新歌,也在翻译过程中给予我热情的帮助。
感谢维基百科,使我能够足不出户就查到大量极有价值的资料,为没有任何注解的英文原著补充数百条注解。它无处不在,却又无影无形。世界上各个角落里互不相识的人共同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赖特理想中的“广亩城市”。
感谢我的父母、我的妻子和儿子悠悠。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让我在利用两年的业余时间翻译的过程中,虽然饱尝艰苦但终未放弃。
最后,还要感谢美国歌手保罗·西蒙(Paul Simon)。他的那首歌So Long,Frank Lloyd Wright,也是我在疲惫中坚持下去的动力之一。歌中唱道:
Architects may come
and Architects may go
and Never change your point of view.
When I run dry
I stop awhile and think of you.
杨鹏
2012年5月
北京双桥
2017年3月
增补于北京三义庙
2021年10月
再补于北京三义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