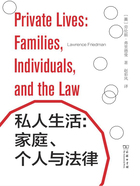
一、普通法婚姻
普通法婚姻是一种协议婚姻,男女双方只要彼此简单地订立缔结婚姻的契约,婚姻即告成立。尽管历史上以及宗教术语中,婚姻被认为是圣事,但在美国法中婚姻(用一个高频短语来说)是“民事契约”——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如此称谓婚姻,美国法学家和法院亦如是。注43当然婚姻是一项极为特殊的契约。假如两人签订一个马匹买卖合同,他们可以合意取消整桩交易;但缔结婚姻“民事契约”的双方必须持守他们的协议,除非他们遇到离婚的麻烦——离婚在美国的大部分历史上并非易事。而且如一位作家所述:签订普通契约的双方“可以确定适合他们自己的条款”,但双方一旦缔结婚姻契约,“则完全由法律来确定其条款”。注44
于是,婚姻是一种身份——无疑是通过协议确定的身份。普通法婚姻原则把协议的理念贯彻到了一种合乎逻辑的极致。一男一女只要彼此互说永结同心之语,就足以缔结合法婚姻;不需要见证人,也不需要任何仪式,双方即时起互相连为一体。他们的孩子是合法子女,且如同所有夫妻一样,他们对彼此有同等的财产诉求权利——同那些在教堂举行婚礼、见证人上百、宾朋满座、华妆盛服并由牧师主持仪式的结婚相比,其权利毫无二致。
在英国,秘密婚姻、非正式婚姻也曾经是普遍实践,这也是其他国家(如法国)的情形。注45毕竟对于穷人来说,婚礼是一桩极为破费的事情。1753年《哈德威克勋爵婚姻法》(Lord Hardwicke's Marriage Act)出台以前,英国的法律似乎认可这些婚姻。这部重要立法摧毁了非正式婚姻的法律基础。该法的标题就是“一部旨在更有效地阻止秘密婚姻的法令”。此后“结婚预告”必须以一种“与众知悉的方式在教区教堂或公众礼拜堂”连续公示三个礼拜日。所有婚礼必须由(英国教会)公认的牧师主持,结婚必须“当着两个或两个以上可靠证人的面举行”并进行登记。凡试图违反该法律结婚的行为将被判重罪,违法者可能被“发配到英王在美洲的种植园”。注46
今天的美国在当时是大不列颠的集中殖民地,在《哈德威克勋爵婚姻法》通过二十余年后才取得独立。但非正式婚姻在美国有截然不同的命运。1753年的英国法不适用于“在海外缔结的婚姻”注47,实际上哈德威克勋爵的道路并非美国的道路。曾被赶出英国本土的普通法原则在美洲殖民地得以幸存并繁荣发展。美国独立革命后,在一系列重要案件中,独立的各州总体上承认普通法婚姻是完全合法有效的。
为何如此?普通法婚姻的观念从何而来?为何得以存续?在某些方面,这个问题不难回答。非正式婚姻在若干社会是常态,深深植根于习惯和实践。殖民时期的人们缔结非正式“婚姻”显然司空见惯。结婚者的邻居似乎接受这一观念:他们的婚姻即使不合乎法律,在道德上也是正当的。据说马里兰州的一位牧师认为,如果这些婚姻没有效力,那么在他所在的地区出生的人十有八九是私生子。注48“非正式”婚姻并不总是完全非正式的,有时有必要的习惯和仪式——如打破一枚钱币。无论法律是否认可“破钱”为婚姻形式,该社群的人们都认为这是一种缔结婚诺的标志。注49得克萨斯州有一种叫作“保证金婚姻”的制度。男女双方签订一份书面协议,其中包含通常的结婚誓言。这份文件有证人做见证,实际上是一种订婚形式,它经常有一项没收条款:任何一方如果反悔,必须支付保证金。注50无论人们怎么评价保证金婚姻,它与哈德威克勋爵所设想的婚姻基本上是两码事。
在得克萨斯州以及美国其他地区(尤其是西部),神职人员严重短缺。这无疑是接受普通法婚姻及其他非正式类型结合的原因之一。1766年,英国圣公会牧师查尔斯·伍德梅森(Charles Woodmason)前往南卡罗来纳州的落后乡村,旨在将宗教福音传播到这个相当野蛮的地区。他的报告称:“由于缺少牧师主持结婚,由于那些百姓的放荡不羁,数百人过着同居生活,他们将妻子当牲口般进行交换,处于自然状态,比印第安人更没有规矩和节操。”注51伍德梅森可能是夸大其词了,这些夫妻中的许多人可能并不认为他们处于“自然状态”。但牧师短缺确实助长了非正式的结婚方式。
得克萨斯式的保证金婚姻是一种明确的习惯,具有很强的礼仪性;连打破钱币也是一种仪式或典礼。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婚姻也是公开的行为。然而大多数州认可完全非正式的婚姻——没有证据支持它们,没有人证实这对夫妇确实私下里交换过好合的吉语或誓言。但是与所有重要的法律原则一样,普通法婚姻不是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因此我们应当问:普通法婚姻有什么作用?其目的何在?公开报道的案件对该问题做出了非常清晰的回答。钱财、土地和继承,这些才是问题所在。普通法婚姻是一种解决财产权利诉求的机制,当婚姻由于一方死亡(通常是“丈夫”)而终止时,它保护非正式结合的“妻子”及其子女,这是其主要功能。注52
在某种意义上,美国是第一个中产阶级国家。没有任何因素可以更好地解释美国法律的诸多曲折以及整个19世纪美国社会的性质。美国是第一个普通人拥有一些资产——一个农场、一块土地、一栋房子——的国家。产权、继承和抵押的问题不会出现在那些一无所有者(农奴、佃农等)的生活中。人们一旦有了财产,一旦拥有什么,他们就变成了法律制度产品的消费者。现在,家庭法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一个男人过世,他拥有一个80英亩的农场,他的女人是他的遗孀吗?他们的子女是合法继承人吗?
普通法婚姻原则保护与一个男人以稳定关系共同生活的妇女的权利,也保护他们子女的权利。由于普通法婚姻完全是非正式的,几乎从来没有任何实际婚姻证明,所以法官只是假定存在婚约。如果一男一女共同生活并育有子女,过着体面的生活,所在社区认为他们结婚了,则从实践来说他们的确已婚。这些事实引发了普通法婚姻的推定。否则谁能证明婚姻关系的存在呢?在婚外性行为是丑闻的时代,该原则还保护了配偶及其子女的声誉。事实上,19世纪在大多数州,婚外性行为都是犯罪。基于这些原因,美国大多数州都接受了普通法婚姻原则;有些州怨声载道,不接受该原则,但这显然是少数。
承认这一原则有效的一些案例可说明其社会功效。19世纪初的一个重要案例开启了妇女领取抚恤金的权利。原告声称自己是一个名叫威廉·里德(William Reed)的男子的遗孀,里德加入了一个为其成员的遗孀提供抚恤金的社团。事实如下:原告之前与一个名叫约翰·盖斯特(John Guest)的男子结过婚。盖斯特失踪了7年,人们推测他已死亡,于是原告改嫁了里德。没想到盖斯特再次出现。显然里德太太已经受够了盖斯特,她仍与里德在一起。盖斯特对此似乎没有异议。从法律上说,该妇女与里德的婚姻无效。她是重婚者,在她与里德举行婚礼时,她的首任丈夫仍健在。但后来盖斯特亡故,随后里德也过世。盖斯特死后,她可以自由地和里德结婚,使一切合法正当化。但没有证据表明她这样做过——没有婚姻仪式的证明。法院仍判给她抚恤金,推定存在一桩有效的普通法婚姻。法院称,婚姻可以从情境“推断”出来:本案当事人“作为夫妻同居”,他们拥有已婚的“声誉”,这就足够了。注53
随后在1918年俄克拉何马州的一起案例中,法院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一位名叫密苏里·A.托马斯(Missouri A.Thomas)的妇女要求对约翰·托马斯(John Thomas)的遗产享有权利。约翰·托马斯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婚姻生了一个女儿——正是这个女儿反对该“遗孀”的请求权。第一段婚姻结束后,约翰以通常的、举行婚礼的正式方式娶了密苏里。后来他们闹翻了,离了婚。但显然离婚数周后旧情复燃。约翰搬到其前妻密苏里的住处,两人以一个独立家户一起生活,直到约翰过世。社区的居民认为他们是已婚夫妇。法院称,这一事实和他们的行为“足以证明推定为有效的普通法婚姻”;密苏里·托马斯是约翰的遗孀,有权分得其遗产份额。注54显而易见,在这个案例以及若干类似案件中,如法院所说,“婚姻”只是始于同居——一种“不正当”关系(“不正当”是指称非法的法律术语)。但即便如此,如一位评论者所说,一些“不正当”关系“不知不觉地发展为永久的结合”;“合理的公共政策”应当“接纳其最终的合规性”而非“起初对法律的漠视”。注55
在大多数案例中,法院运用普通法原则保护“寡妇”和孩子。但有一次该原则却反其道而行之,如1850年纽约州一起案例的情形那样。注56一个名叫乔治·梅瑟维(George Messerve)的男子在他父亲设立的一项信托中享有终身财产权益。根据信托条款,乔治过世后,其份额归他的子女所有。乔治娶了一个名叫萨拉·玛丽亚·扬(Sarah Maria Young)的女子,并和她生了一个女儿凯瑟琳·安(Catherine Ann)。凯瑟琳·安对这笔信托财产提出权利主张。但信托执行人拒绝给付,理由为她是非婚生子女。事实证明她的母亲曾有某些不检点的过去。萨拉·玛丽亚十六岁左右时从一个名叫理查德·申克(Richard Schenck)的男子受孕。“根据《私生子法》规定”,理查德被捕,但从未被起诉。孩子出生后,他与萨拉·玛丽亚住在一起(孩子不到一岁夭折),人们以为他们结婚了。后来分手时,他们制订了一份称为“分居协议”的文件,文件述称他们为夫妻。两人分道扬镳后,萨拉·玛丽亚嫁给了乔治·梅瑟维。
显然,假如萨拉·玛丽亚已婚(若她与理查德·申克存在普通法上的婚姻),则她与乔治的“婚姻”根本不是婚姻,而是重婚,因此无效。这里的情形是,一对男女共同公开生活,至少有一次他们声明结婚了,且人们认为他们已婚。通常这些事实会让法院有充分理由以普通法方式认定他们的确已结婚。但在本案的特殊情况下,这样的裁判结果会很糟糕:它将使凯瑟琳·安成为私生女,并剥夺其遗产。纽约法院拒绝这么判。法院称,证据可否定前桩结合。理查德与萨拉·玛丽亚是“不正当”关系,而她与乔治的婚姻是合法的,凯瑟琳·安有权获得她的财产。
该案显然使一些法官感到困扰,其中三名法官投了反对票。撰写赞同意见的法官评论道:“非法同居生活”是一种“道德沦丧”的情形,“在所有文明社会”这种人都被“排除于同体面人的结合之外”。因此,假如两人公开共同生活,正确的做法是推定其关系的“纯洁性”。但本案情况不同,因为推定第一段关系合法的话,会使第二段关系的女儿成为私生女。注57
这些案例转向了钱财问题,它们由土地和金钱激发,是土地和金钱促使这些案件进入法院。但是性、婚姻和同居不仅仅是决定某人死后谁获得农场的方式;它们是亲密无间的关系,宗教律法试图对其进行规制,社会规范试图对其进行评估、裁判和教化。即使道德不驱使这类案件进入法庭,它也从未远离它们。在1860年佐治亚州的一起案例中,注58焦点是程序问题:詹姆斯·杜普雷(James Dupree)和他的妻子尤赖亚(Uriah)对一个名叫尤赖亚·艾斯丘(Uriah Askew)的男子提起诉讼。原告指控男尤赖亚对女尤赖亚父亲的财产管理不当。男尤赖亚提出一个技术层面的异议:他主张詹姆斯和女尤赖亚没有真正结婚,因而詹姆斯不能成为这起诉讼的当事人。詹姆斯和女尤赖亚认为(或一度认为)他们已结婚,婚礼是由一位自称是“福音派牧师”的A.巴克纳(A.Buckner)主持的。但据称在他们结婚前,巴克纳已经“被教会革职”,他的证书被吊销并被“逐出教会”。因此,被告向原告尤赖亚辩称,她的婚姻无效,她所认为的丈夫根本不是她的丈夫。
书写判决书的伦普金(Lumpkin)大法官支持女尤赖亚的主张。巴克纳诚然无权为其主持婚礼,婚礼仪式无效;但(法官说)她与詹姆斯具有合法的普通法婚姻,虽然没有证据支持这一点。同时伦普金也承认,他说“从来不知”有“自我合法化”的婚姻。但普通法原则是一个明智之举,尤其对于“女性……她的名誉得以挽救,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甚至超过生命本身”。法官称,毕竟(当时)佐治亚州法律允许年满14岁的男孩和12岁的女孩——(法律意义上的)“幼儿”——“缔结有约束力的婚约”,这有悖于一般规则,即法律不认可“幼儿”缔结的契约有拘束力。其原因何在?在这样的年龄阶段,“性冲动通常已发育”;法律以其智慧“防范由私通导致的多重罪恶,宣布即使幼儿也有能力形成婚姻关系”。显然对于伦普金来说,普通法婚姻具备同样的有益效果,它将男女从“私通”中拯救出来;它只是通过简单地重新贴标签,将“私通”标为“合法结合”,就做到了这一点。这种做法似乎没有困扰伦普金。但他生活在一个非常注重面子的时代。威胁社会的不是苟合本身,而是对规范嗤之以鼻的苟合,是蔑视、攻击和试图破坏传统道德的苟合。传统道德能够在不计其数的隐恶之下幸存,但它无法存活于公开的反叛之中。
普通法婚姻也挽救儿童,给予他们农场和金钱,这非同小可。它保护了孩子父母的声誉,用这种方式拯救孩子以脱离私生子的可怕标签。斯特朗(Strong)大法官在联邦最高法院1877年的一起案件中指出:婚姻是“一项普通权利的事务”,“鼓励”婚姻是国家政策。如果没有普通法婚姻,“很多没有意识到违法的父母的孩子”将会成为“非法子女”。注59当然我们不知这些父母是否“意识”到“违法”。但这一考虑无关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