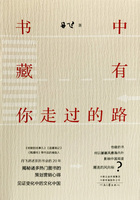
第4章 网络文学+,+什么?怎么+[1]
“网络文学+”一方面是政策制定(对网络文学实践的归纳总结和适度预见)和从业者共谋的时髦和策略——并被网络文学消费者广泛接受和深度消费、反刍、反哺。另一方面又在中国大地上切切实实地发生发展着,风起云涌,又暗流滋长。语义层面,“网络文学+”是“互联网+”句式的合理移用;语用层面,“网络文学+”进行得如火如荼,其边界或说“‘+什么’媒介”尽管已近乎穷尽,其维度或说“‘+什么’IP”和“怎么+”却永无穷尽之时。笔者结合自身浸淫近20年、专职从业14年的网络文学生产、运作经历,简笔建构“一个人的网络文学史”,就网络文学+什么、怎么+,以期形成某种程度的“洞见”,发现和勾画网络文学的边界和内在的现实和可能性,并启发业界和读者诸君思考。
序章 文学是什么?“镜子”抑或“鞋子”
谈论文学的本质在这个时代多少有些不合时宜。问题的核心是,任何事情穷究到底,开枝散叶,溯本求源,必然会摸到树干直至树根,好比著名的人生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必然会问到本质。追问本质太重要了,文学的本质决定了文学的功能,并最终决定文学的路向和命运。借用找笔者写电影《翻译家》的“顽童”型企业家裘冲先生的口头禅,这种追问叫“找根”。
找文学的“根”,这让笔者想起在正式踏足网络文学或文学产业之前的2001年的一档节目。因为1999年重返清华念完编辑出版学双学位后保研,边治中国现当代文学边被破格委任为首次对外招生的编辑出版学双学位班一百多人的班主任,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一档节目找到笔者,希望笔者带队参加一档知识竞技节目。近水楼台,笔者自然从所带学生中选出数人组队参与。节目开题就是“文学是什么”。不出意外,文坛“宿将”组成的评委们点赞北大队,因为他们给出了标准答案——镜子。而笔者的学生们给出的答案是“鞋子”。
文学的“镜子”说实在不新鲜,其远端就有古罗马西塞罗的“人生的镜子”说,达·芬奇(论画)、塞万提斯、莎士比亚、“英国小说之父”(司各特语)亨利·菲尔丁、列宁也有相关表述。在中国,南宋严羽论诗有“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主张。明朝谢榛延续此论,称“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可也”。文学的“生活的再现”说固然不差,但由此上升为标准答案,目为文学的本质,如此论者盘踞文坛挥舞大棒,就有些让人替中国文学的未来担忧了。
好在文学IP化、产业化、“文学+”的崛起和勃兴正是以固守一隅的“文学老干部”的边缘化和“失乐园”为表征。甚至可以说,这个“独孤求败”因而“高处不胜寒”的小插曲无意中成了笔者文学之路的一个转捩点,决定了笔者在路的起点就与文坛相“望”于江湖,走了一条野路子——笔者至今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坛”的交集只在做了梁晓声《政协委员》等小说、都梁《百年往事》等文学剧本,帮出版社老书新做贾平凹、余秋雨、文坛总舵主铁凝的散文,请曹文轩挂名总策划《文昙》,自己的诗歌和小说作品在“严肃文学”期刊发表等有限的几个小切口——也构成了本文遥远的缘起和回响。相较于“镜子说”,笔者更认同心理分析学派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判断。他在《精神分析引论》中说:“艺术家利用艺术返回现实。”他认为艺术是创作者对“昼梦”(白日梦)、“幻想的观念”的“润饰”“加工”和“处理”,所谓“他知道如何润饰他的昼梦,使失去个人的色彩,而为他人共同欣赏;他又知道如何加以充分修改……他又有一种神秘的才能,能处理特殊的材料,直到忠实地表示出幻想的观念……”
“鞋子说”也许更顺应“网络文学+”时代:所谓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脚知道。如何检验好的文学或者说时代需要的文学,就看文学作品(鞋子)是否为文学生产、消费链各环节(脚)所需,这种需求可以外化为文学的变现能力,更多的是内化为文学创作者、其他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深层次的心理需求。
消费升级倒逼产业升级,文学从三要素到六要素
笔者对作家、编剧和部分影视公司老总“讲经”时,常提及文学三要素——人物、故事、语言。笔者曾在手机上写过给作家、编剧的“写作课”,如今看来不算过时,照录如下:
一是每个角色类型化充分,每个角色都出彩,每个角色都(对推进故事情节)有用,没有一个废角色;
二是故事吸引人,设扣解扣,让人一直追看,欲罢不能;
三是塑造人物、讲故事需要恰当的能勾人阅读欲的语言。
这三方面是小说的三大支柱。
而要写出改编成影视后能成大热现象剧/片的长篇小说,还要做到:
一、讲究基本的逻辑但不拘泥于逻辑,小说/影视只需要遵循艺术逻辑。如《琅琊榜》《花千骨》《欢乐颂》等武侠、奇幻、古言、都市言情等(基本上所有畅销小说、大热剧/片都如此)的人设和情节推进。如《欢乐颂》中,安迪获得的待遇,故事“讲不下去了”,立马安排一个角色出点事,轮流出现问题、解决问题,一个长篇/一个剧就成了。
二、角色、情节、桥段要有新意但又不是要百分百新意。故事母题有限,从古至今的文学作品百试不爽,常用常新。对于懒人,一个捷径是对现有大热国产剧/片、美剧、韩剧及其他国大热剧角色、情节、桥段的合理借用、改装使用、拆分组合,实现应用层面的新意,不要掉进“创新”的坑里出不来。
三、要会读心,读读者和观众的心,具体来说就是以90后为主体,适当兼顾其他代际。让“自来水”在微信、微博上主动转发、评论、私聊、点赞、吐槽,效果好于花几千万几个亿的“炒作”。因此,必须写出角色、情节、桥段的“痛点”、槽点。角色的多元化(如《欢乐颂》中白富美安迪、曲筱绡,草根樊胜美、邱莹莹、关雎儿(隐形官二代),同学、师兄,高富帅奇点、包奕凡、谭宗明,等等;他们的社会属性、性格、富法穷法、为人处世截然不同)、每个角色的成长性(如《欢乐颂》中奇点表面是万能暖男关键时刻变㞞,女主安迪的心理、家庭之痛,樊胜美由伪装到撕去伪装),有角色、情节、桥段被读者/观众爱、粉、追捧,有角色、情节、桥段被读者/观众骂、吐槽,就成功了。手段是有时迎合读者/观众的预期,有时故意不满足读者/观众胃口(如《欢乐颂》让安迪选奇点,偏不选谭、包)。
这一课强调文学三要素的同时,贩卖了方法论、“成功学”。从中至少可以解析出:文学的创作术、生产术、消费术。文学要素增加两环:生产和消费。文学写心,又怎能不秉持万变不离其宗——精神内核?大众认知上有一个概念约略与精神内核同义反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三观。当内容产业的“守门人”——立法者、决策者——高举“三观正”大旗,难免让观者动容——产生天生的应激性生理反应。然具体到文学产品,举凡图书、电影、电视剧、网络剧、动画、游戏……“三观”不正的产品必然行之不远。不信参详那些在全民圈层造成现象级影响力的爆款产品,无不“三观”正,绝无例外。至此,文学六要素浮出水面:精神内核、人物、故事、语言、生产、消费。笔者17年前提出的“鞋子说”即强调了文学的正反馈功能。这一正反馈功能包含了文学创作者、文学生产者、文学消费者的共谋和同构。文学消费者的反刍间接或直接反哺文学创作和文学生产,并最终左右文学“创作—生产—消费—传播”链条的走向。文学现状的丰富和多元决定了人物、故事、语言三要素已经不足以支撑文学表达及阐释体系。精神内核、生产、消费要素的引入既是现实吁求,也是策略,更是工具本身。
言及文学生产,不能不提“限娱令”。限娱令一方面拨正影视行业若干乱象,另一方面又给影视生态带来多层面的震荡和冲击。戴着镣铐跳舞是宇宙法则,没有绝对的自由,只有限制的、部分的自由,具体到艺术领域,更是真理。“法则”的形成,为艺术得以生发保驾护航,也是艺术生发的副产品。在自律和他律的前提下,影视业在更能提振人心的若干题材上精耕细作,精品力作的出货率也许会更高——不能拍《摄影机不能停!》,可以拍《摔跤吧!爸爸》啊。消费升级倒逼文学生产——含创作和生产两极。本质上,文学创作是文学生产的源头;实操上,文学创作与文学生产又没办法二元割裂,交融、互动、相互补益和建构成为文学生产的现实图景——升级,形成良性循环的合理闭环。传播学的“KISS法则”颇有意味。越简单粗暴,越直接,越不用受众群体过脑的信息越能得到最强有力的传播。所谓Keep it simple&stupid(让事情变得傻傻的简单)。这也是符合人体大脑构造和认知心理学的,文字、符号、画面、声音、影像等任意信号、信息的重复,会强化人群和个体认知。所以一个怪象是,我们一边强调作品如何“烧脑”,一边被大众吐槽在“秀智商下限”。国内学者喜欢讲述斯拉沃热·齐泽克的一个段子。齐泽克被视为拉康学统继承人和“黑格尔式的思想家”,致力打通弗洛伊德、康德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长期在法国任教的斯洛文尼亚籍学术明星,他曾带着幼子经过一个报亭,父子二人都被一张海报吸引,只不过齐泽克感兴趣的是骑在哈雷摩托上的美女,他的儿子感兴趣的是美女胯下的哈雷摩托。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者的认知偏差总有一条肉眼可见的鸿沟。
网络文学+,“影动游”是终极大杀器吗
某种程度上,院线电影、电视剧(近来也称“台播剧”)、网络剧(时兴称“剧集”“超级网剧”“超级剧集”)、网络大电影(简称“网大”)、动画电影、动画长片(或称“长篇动画”)、真人动画电影、真人动画长片、网络游戏(简称“网游”)、终端游戏(简称“端游”)、页面游戏(简称“页游”)、影视动画游戏衍生品(也称“周边”)、其他文化创意产品(简称“文创产品”)、话剧、舞台剧、舞剧、音乐剧、特技和后期制作公司——有时也算上角色扮演(Cosplay)、视频节目、再生视频、漫画、绘本、基于影视动画游戏及其周边的体验园、产业园、特色小镇构建的文化旅游地产(简称“文旅”)——与简称“文创”“文创产业”的文化创意产业同义复指,其核心板块可概称为“影视动游”或“影动游”。由于“网大”尚处于“狗血”“雷人”“山寨”“十八线”“草台”段位,未能爆出不管是市场层面还是艺术层面的任何爆款产品,短期内也看不到翻身的可能;本土动画尽管出现了市场封神的《大圣归来》、获得市场成功和艺术口碑的《大鱼海棠》、通过动画长片及周边的培育出现的喜羊羊、熊出没系列爆款动画品牌,一度破本土电影票房纪录的真人动画《捉妖记》(动画元素在该产品成功因素中占比几何是个未知数),但本土动画仍将长期在按播放平台和播出分钟数拿政府补贴圈钱养懒的低空徘徊;话剧、舞台剧、舞剧、音乐剧的成功又是小概率事件,“影动游”的核心缩窄为真正有市场抗压能力并因此有搏出生天可能的院线电影、电视剧、网络剧和(网络)游戏。
与数字阅读(含电子书)从纸质图书到以手机、电脑、Kindle(一种电子阅读器)为代表的纸书阅读器(“电纸书”)等终端显示器,有声书(曾称“听书”,如今一般通称“音频”)从文字到语音传播介质的一级转化(笔者称之为“翻译”或“转译”)不同,院线电影、电视剧、网络剧、(网络)游戏存在从传播介质到传播内容、表现手法的多级转化、“转译”和跃迁,即内容和形式的再生和创生,因此其IP转化的权利称为“改编权”。不得不注意的另一个维度是,依托中国移动的咪咕有着毋庸置疑的国企背景和国企基因,其身影见于多类别主流和新媒体传播领域。因为含着金汤匙出生,视频业务板块已经可以介入世界杯转播这类一线流量业务。而因其电子阅读基于庞大用户群获得的市场占有量俨然成为规则制定者,他们近期出台了严苛的版权方合作资格认定规则(内称“接入流程”),版权采购业务由内容部门转为由法务部接手。“新政”出台半年,此前负责版权采购业务的某“小编”称很多机构吐槽过该接入流程,原有对接的机构只成功接入一家。以音频切入市场的蜻蜓FM在喜马拉雅和重资本背景的企鹅FM的版图上稳扎稳打,杀出一条血路,已完成多轮巨额融资。在多行业自我唱衰的背景下,“网络文学+”似乎呈现出一片利益蓝海——现状可喜,前景可见,回报可观,长尾可期,通过利益“全民”利益业态。作为文创“鄙视链条”最底端的纸质图书出版发行业,年年都有人唱衰,图书业从业者和作者也带头唱衰,却仍有大批新生力量持续涌入,图书公司的数量和规模不降反升,不少公司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如磨铁、漫友等先后引入多轮投资,新经典、博集、先锋、联动、壹力、含章等老牌出版机构或长于国外经典引进,或精于放大头部内容效应,或有影视策划、图文书、经典名著、连锁书店等增项,都各有各的“杀器”。一方面,纸质图书总体在衰落;另一方面,纸质图书又永远不会消亡,不排除会出现短期回温甚至在未来某个节点逆势反弹的可能。一方面,图书公司及国有出版企业担负着出版这一古老的文明传承行当的“执火者”角色;另一方面,图书公司及国有出版企业又向我等IP经纪人、版权经纪平台输血——部分版权来源。之所以加以“部分”修饰,以笔者个人而言,笔者仅有不足一成的IP来自出版的“反哺”;笔者从2007年卖给郑晓龙导演《后宫·甄嬛传》影视改编权起,11年间售出的70余个影视游IP中,超过半数IP远在出版之前已经售出,正由《鬼吹灯之寻龙诀》美术设计师徐天华担纲美术设计的超级剧集《白泽图》、谍战剧《牺牲者》、婚恋剧《婚姻扣》等多部小说甚至在还差几万字才完结之时就售出了影视改编权;而在出版后卖出影视改编权的《匈奴王密咒》《婚姻门》《娶我为妻》《房比天大》《我想结婚了》《第101次逃婚》《兰陵缭乱》《84号公路》《杀八方》《楼兰绘梦》《老少爷们儿拿起枪》《草莽》《荡寇》《寻龙记》《爱神的黑白羽翼》《我的国》等IP,很难说纸质图书的出版在其中起到了多少作用。如今我掌握近千个IP, IP池每月都有增补,其中包括共青团中央和腾讯合办的Next Idea全国大学生文化创意大赛(麦然,青年编剧一等奖)、全国大学生征文比赛(欧阳德彬,首奖)、一等奖新浪原创文学大赛(阿闻,最佳长篇小说奖;千里烟,一等奖)、搜狐原创文学大赛(翁想想,一等奖)等重要赛事的魁首。不难看出,现实题材、红色题材、幻想文学构成笔者个人IP版图的三极。尽管这是一句“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或“正确的废话”,但还是得说:“网络文学+”尽管上游来自选题、创作(或可加上纸质图书出版),下游延展到依托影动游生长起来的周边、文旅的长尾,影动游这个可口“红烧中段”仍将长期是“网络文学+”的终极大杀器。这个事实真令人伤感。
被“超级IP”和“大数据”驱赶的影视业
一个时期内,影视业者言必称《余罪》《白夜追凶》,是《余罪》《白夜追凶》《无证之罪》等网络剧的爆红、《延禧攻略》“吊打”《如懿传》的必然余波。反观台播剧,尽管不少电视剧频频抛出挑战人类认知常识的“迷之数据”,《楚乔传》《扶摇》《莽荒纪》《武动乾坤》《斗破苍穹》等“超级IP”冠冕头上的光芒因此暧昧不明。良知蒙尘构不成影视业的主流,台播剧不一定优于网播剧,网播剧不一定劣于台播剧却已成为事实。其中,创建之初对标You Tube却最终办成了中国版Netflix(美国奈飞公司)的爱奇艺、优酷、腾讯领头的视频平台功不可没——视频平台经过几轮洗牌,大浪淘沙,形成了如今爱、优、腾(戏称“哎哟疼”)三足鼎立的局面——动摇和补充了院线发行、电视台分发的影视发行、传播柱基。好莱坞面临的是将影片投入院线“赌命”还是卖给Netflix圈钱的二元选择,同样,本土视频平台至少在电视剧领域已经尝了鲜,视频平台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用户的观剧习惯(以及由此带来的“小剧场”、横幅、角标、贴片等花样翻新的图文或富媒体广告收入)做底,在与电视台分别发行电视卫星频道(原“一剧四星”改为“一剧两星”后,唯有进入江苏、浙江、湖南、东方、北京五大卫视中的一家或两家首播,一部剧才有成为爆款剧甚至仅仅是收回成本的可能)和网络平台的常规打法下,多了与卫视竞争“独播”权的底气,卫视、视频网站联播和网站独播两种打法竞价,本着价高者得的商业规则,部分电视剧有了甩掉卫视而交由视频网站独家首播的可能。
《如懿传》起点更高,有前作《甄嬛传》的金字招牌打底,理应“吊打”口碑欠佳的“于正剧”《延禧攻略》而不是相反。孰知于正此番从创作者身份抽离出来,担任总策划和总制片人,祭出连服、化、道都被封推的精工细作。配色都能被网民追捧归类为“莫兰迪色”,更有专业画者纠正说压根没有莫兰迪色什么事,而是清初就确定下来的服饰配色体系。
相较而言,尽管亦演亦导的导演汪俊有过执导封神之作《苍穹之昂》的成绩单,同样是拍清宫戏,同样是与《延禧攻略》一样拍摄乾隆的后宫,《如懿传》的成色与《甄嬛传》《延禧攻略》或汪俊自己的名作《苍穹之昂》相比稍显逊色。另以故事的呈现、选角和演员的演技论,《延》的成功在每个角色都各得其所,无一人掉链子,影像流与影像流之间产生了流动和勾连效应,推波助澜,追云逐月,有机地融合成一部相对自洽的影像作品——笔者是提出聂远演技炸裂在前半段的“润”、后半段的“枯”的第一人;被网民追捧的神演技“继后”撕破脸、“尔晴”瞪眼是该剧不多的演技败笔,网民诟病的“璎珞”“傅恒”的“面瘫”“性冷”式表演恰恰是角色本身赋予的个性和做派;惜乎《延禧攻略》之得正是《如懿传》之失,包括笔者欣赏的周迅、张丰毅在内的主演、配角、群演的个体演绎、角色互动与角色之间存在的“隔”如此扎眼,台词也因为经由角色之口说出成了大片“水词”。演技也是有传染效应的,要么如《甄嬛传》《苍穹之昂》《延禧攻略》一样带上山,要么如《如懿传》一样带进沟,就连老戏骨张丰毅也不能幸免,演帝王也演成了“霸王”范儿。
迷信“超级IP”和“大数据”是影视圈的一股汹汹潮流,及至发现原作作者、编剧、导演、演员、班底、类型的“大数据”不是万灵药,“超级IP”的倒掉有如推翻了多米诺骨牌,人们这才会恍然悟到“超级IP”不一定靠谱,“大数据”是数字游戏,影视艺术是个案的艺术,没法类比,没法类推,必须如郑晓龙导演等电影人一样下苦功夫、笨功夫的真理。
被简称为“网生”的网络生态特点、被简称为“网感”的互联网传播特性是文学传播和文学消费的倒逼,但如果小说创作、影视创作以“网生”“网感”为保命符咒,就失却了小说、影视艺术的本真,可谓忘了来路,也终将迷失归途。何时审慎看待这一对伪概念,文本和内容本身而不是“超级IP”和“大数据”构成注意力经济的主旨和归依,才标志着网络文学产业真正成熟。
+什么?怎么+?作品IP和创作者IP
在谈论“网络文学+”+什么和怎么+之前,有必要对IP进行正本清源,厘清IP的内涵和外延。IP是Intellectual Property的缩写,字面意思是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一般称为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版权)、专利权、专有技术权等创造性成果权利和商标权、商号权、服务标记、货源标记、原产地名称等识别性标志权。知识产权是“私权”的一种,赋予创造人在一定时期内的独占权,如著作权的署名权为永久,著作权的授权使用和获得报酬权延续到创造人死后五十年——这个年限也称为版权保护期。出版界有一个怪象:每年都有出版社或民营出版公司拉出名人清单,处心积虑地算计哪个作家的作品几月几日超过版权保护期,那样就可以不经著作权继承人授权、不用支付版权使用费,随意使用其作品(此类图书则叫公版书)。殊不知,老赵这么想,隔壁老王也是这么想的,不是传承人类智慧成果的冲动而是省去稿费或版税的贪欲造成了公版书的泛滥。网络文学、影动游业所称IP一般指拥有著作权的相关智力成果,即文学作品、影视动画游戏等作品(整体或部分内容,更严苛的版权保护还包括作品名称、角色和剧情的衍生、延展、再创作、改编权)自动产生的无形资产相关权利,含人身权利(精神权利,如署名权、发表权、修改权等)和财产权利(经济权利,即获得报酬权)。是以利用金庸武侠人物创作的“同人小说”《此间的少年》、《宫锁连城》与《梅花烙》故事架构、人物关系和人物功能的相似,引发了版权战。
作品作为IP自不待言,作家、编剧、导演、主演、制片人等主要创作者的续作、同人作品、后续同类作品甚至任意后续作品因此沾了已取得市场或口碑、艺术、奖项等成功的前作的光,也在情理之中。创作者作为IP其来有自,只不过在网络文学爆发式成长阶段得以“发现”、昌明和利用。南派三叔、天下霸唱、流潋紫、唐家三少、天蚕土豆、猫腻、我吃西红柿等起家于网络的一批作者,占据了IP时代的半壁江山,某种程度上,正是网络文学促生了“IP剧”“大IP”概念的成形。流潋紫以小说、剧本的著作权作价参股,南派三叔、天下霸唱小说、编剧之外深度参与制片,江南则早早以“运动员”(作者)兼裁判员(世界观统摄、IP运作)身份介入IP名利场,网络文学自创生之时起就注定了会搅动一池春水。收割市场的同时,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还都蹲伏着两只小兽,一只叫体制化(如匪我思存、蒋胜男当上省级作协副主席或网络作协副主席,当年明月当上处级干部),一只叫经典化(如安妮宝贝等人向《收获》等文学期刊的靠拢,几乎所有网络作家都有诺奖、茅奖、鲁奖情结)。然而对于网络文学产业群的从业者来说,+什么和怎么+,现下的“网络文学+”业态虽多元立体,却远未穷尽可能性,想要到达边界,探路和试错没有穷时。武断一点说,网络文学可以+一切内容、形式、信息和能量存在与延展的任何维度和形态,网链上的任意一极(级)或一环或一域,传播和交互和反馈、读取、写入、敲除方式。约百年前的前代“文青”和“网络作家”鲁迅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相似的判断依然成立:“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网络文学+’有关。”“网络文学+”的未来会怎样?充满可能性又几无悬念。
网络文学的主题虽富,或为共情,或为奇观,最大的要旨乃在人性;类型文学的富矿和同质化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细究起来每个IP都无外乎权、钱、美的对垒——“打怪升级”升的是权位,“王子灰姑娘”反转的是“钱”途命运,“杰克苏”“玛丽苏”苏的是美的移置、倾斜;借用“乡”的概念,不外“异乡”“望乡”“在乡”三端。异、望、在的“乡”可能是现实图景,也可能是心灵图景;人物行动和故事进程的第一推动力是美(孔子说的色)与好(孔子说的德)的角力,构建文学的共同想象,在现实和心灵困境下用美来解救真、好被囚之困。广为我国影视从业者推崇的《摔跤吧!爸爸》的淬炼之旅也许提供了一条似曾相识的“新”路,据说写这部电影的并非职业编剧,她看到报纸上一则新闻,于是到故事发生地蹲点了六个月,为了三万来字的剧本,花了两年半时间。这个年方24岁的印度姑娘所做的不就是我国老文学工作者、影视工作者习用的“采风”“踩景”“田野调查”和“体验生活”吗?艺术反映生活的同时也要高于生活,借用弗洛伊德的说法,艺术还必须实现“生活中所不能满足的欲望的代替满足”。网文常说的“YY”近似于弗洛伊德所说的“代替满足”,但后者无疑正面得多,也就有更强的指向性和实操的指导性。世界很公平,谁用了心,谁的心用在正路上,必将回报以果实。我们需要做的是重新捡起丢掉的用心,不把媚俗和眼前的利益放在首位,只关注讲好故事,写好人物,凸显那些即使置于暗处也会兀自发光的精神内核。“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鲁迅《呐喊》自序)“网络文学+”的未来也许就在有“别样的人们”所在的“异路”“异地”这种别样的远方。
结语“网络文学+”,“终极”出路也许在于做减法
实际上,“网络文学+”方兴未艾的同时,不乏“醒客”报以辩证的审视。《甄嬛传》总发行人曹平对笔者表示,她和郑晓龙导演挑选IP的标准从来都不是各大文学网站上拿数据、流量和粉丝说话的“头部IP”,他们只看内容。更进一步,她认为仅仅在网文状态或者仅仅到了纸质图书出版阶段,一部小说还构不成IP。只有当经过精密的设计、改装,变成部分受众人群甚至全民喜闻乐见的影视动画游戏作品,传播度和影响力的广度和深度形成从量变到质变级别的升级,才可称之为IP。在内容端,以笔者的操作手法为例,除非在被笔者发现之前作品已在网络上发表、传播,笔者一般都会选择影视化、纸质图书出版先行,电子和音频降格为营销手法,附带小额变现。此举基于笔者对网文市场的基本判断:(1)精神内核要么缺失要么不入流;(2)同质化严重;(3)注水成为下意识,当然也是谋生手段,无法想象一个动辄百万言的口水文通篇都是干货;(4)抄袭门槛低。一个好的题材和创意公开,无异于向嗅觉灵敏的文抄公们敞开大脑和钱袋。驱使抄袭的力量表面看是作者,更多是文学生产各链条的暗示和明示,甚至有人别有用心地宣称作者在抄袭排行榜上独占鳌头“省了宣发费用”。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于中国文学的判断同样适用于网络文学:“但即便只是描绘画面,很多中国当代小说家笔下的画面也是千篇一律,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根本无关紧要。他们毫无节制。”“把语言的熟练程度和精神上的追求排除在好作品的判断标准之外。”顾彬认为,好的长篇小说必须“拥有一流的、创新的语言以及深刻的思想和寻找独特形式的能力”。“正是商业利益和对娱乐功能片刻不停的需求,决定了文学的命运。”一针见血。
与世间事一样,起作用的是减法不是加法。“网络文学+”行当环节繁多,彼此相应相扣,你折半我折半,结果不是50分加50分得100分,而是5折乘5折成了2.5折,环环折扣最终得到的是断崖式崩坏。古斯塔夫·勒庞在传播学名作《乌合之众》中断论:“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如何引领大众而不是去曲意迎合大众,“网络文学+”大潮裹挟下的每个行当、每个群体和个体都应保持警醒。当然,影动游有个现象应该引起注意:大量创作者、生产者花大力气砸重金在宏大场面、特技特效的渲染上,以主创核心导演为例,不去努力讲好故事,洞明人性,以为靠“奇观”一技便可以收割受众,从导演降格为动作导演或特效导演、特技导演。讲不好故事,不能通过影像语言烛照忍常人所不能忍、为常人所不能为的人性,黄金比例、中国风、水墨美学、暴力美学等影像美学、电影法则用得越神乎其技越坏事——“网络文学+”归根结底要+人性和故事,而不是任何层面的炫技。夜阑听“鞋”的诸位不妨耐心期待郑晓龙、曹平等一大批真正耐得住寂寞的“别样的人们”,如同期待17年前笔者设定的那只“鞋子”,在你不经意间掉到地板上。在别的创作者被资本和效益或者仅仅是急功近利的“三观”驱使年出数作的大背景下,他们舍得投入数年磨出一部大众叫好又可以传之后世的好作品,这样的苦心孤诣可以不是爆款,但一定是精品。“网络文学+”最应该+的正是这样的精品,正是这样只问耕耘的“傻子”。毫无疑问,这样的耕耘者最终收获更多。有趣的是,我们本意在苦苦追问“网络文学+”出路何在,最终找到的“终极”解决之道是创意创新和工匠精神,而创意创新意味着对“注水”“大路货”“行活”说不,工匠精神意味着对粗制滥造、“60分万岁”、“流量至上”的彻底摒弃,而其实质恰恰是走窄门、做减法。
注释
[1]本文首发《科技与出版》2018年第10期“特别策划”栏目,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出版工作》)索引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