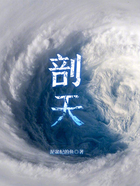
第37章 那过去的事情(一)
一切好的和使人感到舒适的事物都是简单而自然的。
这句看起来格外美好的格言曾经让陈相特别费解。在他看来,好和舒适都是人穷极一生也不一定能摸到的东西,怎么可能来得那样容易。但如今,他终于明白,所谓的好不是挂在天上看得见摸不着的那轮金日,而是能填满世间所有空隙的阳光,只要想,就有千百种方式捕捉到它。
离开气象台后,他住进了高梵的家。那是一套朴素的三居室,位于赤坎老街附近的一栋破败的居民楼,尖顶小二层,露天阳台,红砖砌成的护栏已松散到让人不敢触碰,外墙上有淡黄色的漆痕,已斑斑驳驳。
这栋房子的房龄50年朝上,在它附近立了一棵差不多同样年纪的法国枇杷。它被种在双向两车道水泥马路的绿化带里,向道路和居民楼倒伏45度角,苍老又茂盛。
陈德球为陈相收拾出一间闲置的屋子,搬出随意堆放的画板、颜料、沾满灰尘的布偶和发霉的童话书,搬进新打的桌子、衣柜和床。那些被驱逐的杂物一看就是高梵的童年回忆,但她丝毫不在意,毫不留恋地让陈德球帮她扔掉。
结束了无尽自我内耗和无休止的夜班后,陈相在这里迎来了久违的安稳生活。
每天清晨,他都会和高梵一起到永远热闹的老街里买一袋水井油条,拿回家就着陈德球做的生蚝粥一起吃。早餐结束后,闲不下来的陈德球推着一个带轮子的小冰箱到老街摆摊卖凉粉草,陈相和高梵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各自用功。
陈相泡在力扣和面经里,高梵则沉浸在PS和PR里。两人都很忙碌,忙碌到陈德球做好午饭后谁都不来吃,只在不定时歇息头脑的时候,从屋里跑出来狼吞虎咽一番。
晚上,是高梵用来放松的时间,她会陪在陈德球身边看一些欢乐的综艺,一边看一边在手机上回复粉丝的留言。而这时,陈相依旧在用功,比学生时代更加用功。
7月到9月,一共两个月的时间,这是陈相给自己划定期限。他的目标依然是大厂的算法工程师,但由于没有相关工作经历,只能尝试和快毕业的应届生在校招里抢初级职位。校招通常都有机考,考数据结构,这是非科班出身的他,最为薄弱的一部分。
从副高职称唾手可得的中级工程师,到一张白纸的萌新,说是天渊之差都不为过,但这是他的选择。他选择用安稳换富贵,以人生中最宝贵的十年在最热门最有钱途的行业里闯出一番天地,去实现他的诺言,实现他期许给张瑾玥红红火火的未来。
选择永远比努力重要,行业的上下限完全能够决定一个人的上下限,同一座城市里,气象局正研高工的年薪丝毫不抵互联网大厂给应届本科生开出的白菜价,那些诱人的数字完全值得他拼命。
校招9月份便会开启提前批,在那之前,他必须弥补好自己欠缺的一切。因为混得一个机考只是一个开始,他还必须在后续的面试流程中表现得比科班应届生更为出色,才有可能求到一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他相信自己能够做到。结束夜班的两周后,他就成功把自己的作息调整正常。在这座喧闹又僻静的老城区,他总能睡得安稳,一夜无梦沉沉睡到天亮,一整日都头脑清明。
原先忙里偷闲时永远学不懂的抽象知识开始变得既清晰又容易,他学得丝毫不艰辛,甚至还有余力去处理其他琐事,比如拜访和陈波有关的所有人,拾取他们的记忆碎片,把谜一般的拼图拼凑完整,还原26年前那个雨夜的全貌。
他选择从拼图的最边缘开始,从二横巷开始。这并不是由于他内心怯懦不忍直面事实,而是单纯因为那条最让他刻骨铭心的小巷即将不复存在。
风暴潮为霞山区的低洼地增水220厘米,虽然居民撤离及时,房屋也没有垮塌,但灾后房屋安全自查时,有好几户人家发现墙体有裂缝,砖柱有位移。经测量,二横巷7成以上的房屋结构受损,被评估为危房。
二横巷就要被整体拆除了,浓缩他整个童年最为牢靠的记忆载体即将不复存在。在那之前,他想用力抓住暂未遁形的一切。
7月下旬,在夏季里最炎热的时候,他终于被允许返回阔别已久的家。那条从40年前繁华至今的老巷被深蓝色的瓦楞彩钢板围得死死的,附近的居民楼也难逃一劫。危房拆除自外向内进行,他是第一批被允许短暂返回家中取回重要物品的幸运儿,有幸最后看一眼二横巷的全貌。
被灾难洗劫后的景象并不如他想象得那样触目惊心。房子的外观都是完好的,只是外墙相较之前略显斑驳。道路上没有聚集碎裂的砖石、水泥块或其他建筑垃圾,只粘黏几簇未被清理干净的淤泥和海草。
终日不见阳光的暗巷里,已闻不到小苔藓的气息,也找不见它们的身影,石板缝里嵌的是贝壳渣和小鱼骨头。他站在连接主巷和居民区的这条暗巷口,目光被尽头处二横小卖部露出的招牌一角吸引,想走过去看看,却被一个洪亮的嗓音叫住。
“喂!不能往前走了,你是被通知回家拿东西的吗?过来登记!”
陈相扭头看,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细长脸光头眯缝眼,是丁小幺。
丁小幺穿着蓝色短袖制服,帽子脱在手里,一个劲地给自己扇风,汗流浃背。另一只手也没闲着,把捏在手里的纸笔衔在嘴里,腾出的手用来打手势招呼陈相。
陈相应声走过去,给丁小幺看了身份证,又被后者催促着往居民区走。
“3号楼3单元101的啊,已经排到你了,快去,快去啊,别墨迹。大概有十五分钟时间让你收拾,可能更长,也可能更短,看现场工程师的安排,让你进你就进,喊你走你就走。别墨迹,否则有可能给你埋里面。”
丁小幺似乎对陈相的举动起了疑心,一直把陈相送进楼里才离开。3号楼附近的景物稍稍有些破败,粉煤砖砌成的花坛已不见踪迹,花椒树还在,但是秃了也歪脖了。张瑾玥的小花坛被黑色的淤泥盖得严严实实。
楼里楼外都被架上了杂乱的脚手架,二楼的砖砌护栏破了个洞,正好破在王奶奶家门口。王奶奶的家门一如既往紧闭着,她家已经空置三年,她被在国外安家的儿子接去养老了。
陈相还想再看几眼,但被戴黄色安全帽的监督员催促,只好先进了自家的门。
和这座无比珍贵的记忆载体相处的15分钟里,陈相并没有手忙脚乱。这里的绝大多数物品早在几年前就被搬入新家,只留下基本的生活用具,供陈相躲开赵栋梁,也供张瑾玥偶尔回来和老邻居叙旧。他没有什么好拿的,也没有什么能拿的。两米多的增水,可以把这里的一切化为腐朽。
在淤泥、破碎的玻璃和扭曲的家具里兜兜转转一阵后,他来到了张瑾玥的卧室。如果说这座记忆的空壳里能遗留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那么最有可能在卧室门头吊柜的第二格。他在某一次轮回中有幸得知,这是张瑾玥藏存折的地方,是她心中最隐秘最安全的地方。然而费力找来踮脚物,站在其上抠开扭曲的塑料板,却发现那里空空如也。
监督员已经在吹哨了,这趟试图在记忆沙河里掘金的旅程就此结束。他一无所获。
走出家门时,陈相发现丁小幺立在不远处,看到自己后立刻迎了上来。丁小幺把帽子松散地扣在头上遮挡阳光,眯着眼睛冲陈相说,“走吧,送你出去。”
“这么些人来来往往的,你为什么只盯着我?”陈相费解地问,心中十分不满,他还想偷偷到别处转转。
丁小幺把帽子戴正,仰着下巴理直气壮,“不为什么,就是看你可疑。大太阳晒着不赶紧回家吹空调,非要在这齁热的地方瞎胡转悠,你图什么?”
陈相听后没有反驳,只默默跟着丁小幺走。和某个风雨夜里发生的一样,这位长得一点都不像好人的警官再一次让他无言以对。
两人无言地并排走,陈相撒谎自己从巷西的出口出去方便乘车,并且故意压慢脚速,好多拖延一些时间。不舍张望间,他的余光扫到了丁小幺胸前的警号,紧接着一股不安从心底升起。
丁小幺的胸前别了上下对齐的两串警号,根据记忆,下面那串是丁小幺自己的,上面那串是黄龙的。警号是独一无二并且跟随一名警官终身的,同一串警号出现在两个人身上,只有一种可能:一人因公牺牲后,他的孩子也成为一名警官,重启父辈的警号。
丁小幺继承了黄龙的警号,说明黄龙牺牲了。可天气评述里明明记录着26年前那次风暴潮中湛江市区只有一人遇难。很明显,那一个人就是陈波。难道是自己记忆有误?或者陈波的死另有隐情,陈波并没有被判定为在风暴潮中遇难,真正遇难的是黄龙?
还未被完全解开的疑团一下子变得更加凝重,于是陈相毫不掩饰地把疑问脱口而出,“黄龙在风暴潮中牺牲了?”
丁小幺一下子愣在原地,脸上的神情由慵懒换为惊异,眼里闪过一瞬间的哀伤,“你认识黄龙?”
陈相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自己与黄龙的关系——那令人刻骨铭心的一面之缘。但丁小幺并不是很在意,反而换上一幅惊喜的神情。
因一个能牵起无尽回忆的人名,两个陌生人的关系被瞬间拉近。丁小幺不再驱赶陈相,反而邀他到办事处坐坐。一个非常临时的办事处,坐落在集装箱房里,专门为拆迁建立的。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空调桌椅档案柜和床一个不落,丁小幺招呼陈相坐下休息,并为他端出一盘芒果。
覃斗蛋芒,青里透黄,果香浓郁。于婶生病后二横巷就没人卖芒果了,这香味闻得人眼睛发酸。
“吃吧,是洗好的。”丁小幺向陈相手里递一个,还给他一把小水果刀,“我对这东西过敏,没有口福。这是黄龙最喜欢吃的东西,一把年纪把血糖吃到八点几都不舍得停嘴。”
陈相没有接,只把心中的疑问问出第二遍,“黄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丁小幺渐渐把头垂下来,收回芒果和小刀,细细地削着皮,口中吐出陈相未曾知晓的故事。
“黄龙死了,但不是死在风暴潮里。
26年前,有个特别厉害的台风登陆这里,还带来无穷无尽的潮水。
那天我值夜班,睡得正香被黄龙一脚踹醒。他让我跟着其他同事一起去撤离群众,他不跟我一起,他要到赤坎河河道旁协助炸堤。
我一听就不乐意了,觉得他这是看不起我。他一个老胳膊老腿的人去到随时能淹死人的河边上淌水堆炸药,我一个年轻力壮的举个轻巧的小喇叭上大街上吆喝人。哪有这个道理嘛。
他就是看不起我,觉得我成不了事,宁愿自己拼上老命去凑个没用的人头也不让我有这么个干实事的机会。他是我师傅,快退休了还只是个二级警员,每天干点城管的活儿,什么都不教我,我其实更看不起他。
我跟他理论,他却威胁我说要让我滚回老家种地去。我一下子就怂了,我家里兄弟姊妹一共五个,省吃检用供我一个人上学,让我回去还不如让我淹死。
我从了他的命,一边上街上吆喝人躲家里,一边挂念炸堤这事。
那天炸堤的时间特别紧,一共给他们半个小时,半小时炸200米,根本就不可能完成。但好巧不巧西头有个要搬家的发电厂准备定向爆破拆除两个冷却塔,炸药运到厂里了,工人也来了好几拨,准备第二天施工。于是河堤和电厂通力协作,一边挖埋炸药的孔,一边组织个敢死队冒雨送炸药,生生把时间赶上了。
老黄是去埋药的。据说特别惊险,他们还在接线的时候,水就已经漫上堤,河下游的入海口凭空长出一座大山朝他们移过来,越移越近,吓得人腿脚发软。
按理说炸堤的时候人是要撤到50米之外的,但他们没有时间,起爆前一分钟才屁滚尿流往远跑。老黄跑得最慢,被气浪狠狠拍了一下,拍进刚泄出的水里。好在他水性够好,闷了一会儿也就挣扎出来了。
我见到他是在第三天,他唤我去他家给他送膏药。他本来就有风湿病,冷水里一泡,腰啊腿啊都彻底废了。
那天他特别神气,说这事他干完,一辈子都值了。他直挺挺躺在床上,一边疼得嗷嗷叫,一边跟我吹牛,别提有多气人。牛吹累了居然还支使我给去他削芒果,我嘴上答应,但撒丫子就跑。我才不给他削,他抢了我的功,还要用芒果折磨我。
之后的两天,我都没再见他,他也没再托人唤我。再后来,他邻居交给我一封信和一个存折,说他死了。
他是直挺挺硬在床上的,枕头边放着写好的信。信里他把我唤作儿子,说棺材本和房子都留给我,让我给他收尸,还让我烧芒果给他。
堆在灶台上的芒果已经发霉了。他临走都没吃上口芒果。”
丁小幺说完时,手里的芒果也刚好削完。金黄色的果肉,纤维很少,水光光的,像是高档的树熟果。他埋着头,啃得狼吞虎咽。
“死后才认的儿子,不算直系血亲。我没法继承老黄的警号,只能单纯要过来,自己给自己别衣服上。这是不规范的,但反正我就只干点城管的活儿,乡里乡亲的都没意见。”
丁小幺吃完,抬起头,嘴唇周围起了密密麻麻的红疹,肿成一片。他望着陈相,眼里没有悲伤,“老黄说,吃包子比吃刀吃枪吃汽油弹强,睡床板比睡车屁股睡草窝睡棺材强,跟着他除了享福其它什么都不用考虑。
我跟着他享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