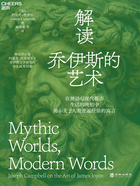
艺术之翼
当你翻开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一句拉丁语映入你的眼帘,“et ignotas animum dimitit in artes”,意思是“他全心全意投入晦涩无名的艺术中”。这句箴言出自奥维德的《变形记》,它指的是希腊神话中在克里特岛建造迷宫的伟大工匠代达罗斯(Daedalus)。迷宫的奥义就是他的作品,在古典传统中他被视为艺术的保护神。传说中,克里特岛的暴君米诺斯国王试图让代达罗斯成为农奴,但代达罗斯决意带着儿子伊卡洛斯(Icarcu)一起从克里特岛逃走。为此,代达罗斯将他的注意力“投入晦涩无名的艺术中”,制作了两对蜡质翅膀,让他们真的飞了起来。因此,开篇的箴言是指乔伊斯决定制造艺术之翼。此后,这个关于飞行和艺术之鸟的主题成了贯穿乔伊斯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它甚至出现在《芬尼根的守灵夜》的结尾——乔伊斯是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这段文字写下很多年以后才写的《芬尼根的守灵夜》。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在谈论艺术家的飞行时总是提伊卡洛斯而不是代达罗斯。伊卡洛斯飞得太高,离太阳太近,翅膀上的蜡融化了,于是掉进了海里。大多数人对此的看法似乎是艺术家是做不到的。可是,代达罗斯做到了。乔伊斯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认为一个有能力的艺术家拥有实现自由飞翔的能力。
那么这句箴言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寓言是代达罗斯从克里特岛逃到了大陆,乔伊斯从爱尔兰的地方文化逃到了它伟大的大陆源头。但是,乔伊斯还在进行另一次逃亡,从罗马天主教会的象征主义逃到了共相(19)(也就是荣格所说的“原型”),基督教意象是其中的一个转折。可以说他逃脱了自己精神上的地方主义进入了完全的人性,这是我们内心深处共同的遗产。
作为一名天主教徒,乔伊斯从小就被荣格原型的天主教色彩所包围。当你走进一个天主教家庭时,你会看到什么挂画?你会看到圣母玛利亚,会看到十字架,你还会看到利奥波尔德·布卢姆所说的“基督喜怒形于色”。天主教的孩子是在这些神话形象面前长大的,是原型形象方面的专家。例如,他们知道母亲和父亲只不过是圣母和父神这些伟大原型的地方性变化。然而,这个天主教青年在成长过程中,却一直纠结于如何将现实世界与他所接受的形象联系起来,而这些形象某种程度上却显得格格不入。乔伊斯所做的首先是从他身后的那些形象和外面的世界出发,然后他把意象伸展开来,伴着随处可见的联想的变化,最后把意象交还回去。
以我为例,我也是在罗马天主教的环境中长大的,在阅读乔伊斯之前,我已经对这些形象的力量失去了所有信念。而通过乔伊斯,我了解了一个人如何能够将局部的象征打开,拓展为更大的象征,以及这个过程中心理层面会发生什么变化。我认为乔伊斯的作品对其他人来说也有这样的影响,它不仅适用于基督教的意象,也适用于拥有其他神话遗产的任何一个人。
关于乔伊斯小说的艺术,这里还有另外一点需要说明。詹姆斯·乔伊斯继承了十九世纪后期自然主义小说的传统,而《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开篇的箴言“他全心全意投入晦涩无名的艺术中”,暗示着他的飞行不仅是从爱尔兰到大陆、从罗马天主教到伟大的神话原型,而且还是从自然主义小说到神话的原型。只有生活的细节被送上舞台呈现出来,我们才能感受到原型在它们幕后的演奏。
乔伊斯并不是当时唯一一个以这种方式创作的人。我发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文学界最有趣的一件事,那就是许多作者从自然主义传统出发,逐步进入神话思想的领域。在这方面,我能想到与詹姆斯·乔伊斯最近似的人是托马斯·曼(Thomas Mann):乔伊斯是一个抛弃了天主教的天主教徒,托马斯·曼是一个抛弃了新教传统的新教徒,他们的第一部作品在几年内相继问世。两人的第一部作品都是自然主义的,但都带有一种美学上的呼应,开始将情感指向超越自然主义的层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两人虽然彼此不知道对方在做什么,但都推出了一部重要的作品,表面上是自然主义的形式,但却进入了神话的领域。托马斯·曼的《魔山》于1924年出版,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于1922年出版,在这两部作品中都有对神话的刻意呼唤,有意并直接引用了英雄进入黑暗世界、坠入深渊后归来的神话故事。当我们谈到《尤利西斯》时,我将展示乔伊斯是如何处理这个神话旅程的。他们的最后一部作品,1939年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和托马斯·曼的“约瑟夫”系列(1934—1944)都放弃了人间,彻底投身神话世界。乔伊斯本打算再写一部作品,可以说,这部作品本来可以结束他的神话旅程,但他在这样做之前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