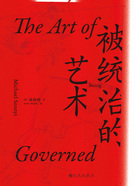
导论
悲苛政一门入军户 叹凄凉三子死他乡
明代中国的日常政治
如果“规训”(discipline)之网确实处处变得更加清晰、将更多人牢牢套住,那么对以下问题的求索便显得愈加迫切:整个社会是如何反抗堕入此规训之网的?众人是通过哪些惯用的(亦即日常而“微不足道”的)手段操纵规训的机制,以求在顺从中加以规避?最后,又是怎样的“运作方式”构成了组织社会经济秩序的缄默过程的对应之物?
——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日常生活实践》
凡是国家,必有军队,用以保卫国土、攘外安内。很遗憾,这一历史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1军事制度普遍存在,从这里入手做研究往往卓有成效。我们不仅能通过该制度了解国家如何运作、如何动员和分配资源,而且能以之探索国家与其人民如何互相作用、互相影响。这是因为,国家拥有军队,自然意味着拥有士兵。动员民众参军是国家不得不面对的最常见的挑战之一。在历史上的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一部分人或自愿,或不自愿地以当兵的方式为国家服务。如何动员民众参军?国家的抉择,对军队的方方面面——从指挥结构到军事战略,从筹措军费到后勤补给——均意义重大,2亦深刻地影响着在伍服役的士兵。
本书讨论的是:在明代(1368—1644)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国家的军事动员决策所带来的影响。重点不在于相关决策造成的军事、后勤或财政后果,而是其社会影响,即军事制度如何形塑普通百姓的生活。我将在本书中讲述一个个明代平凡家庭与国家机构之间互动的故事,并考察这种互动如何作用于其他社会关系。明代百姓如何因应兵役之责?他们的行为引发了哪些更广泛的后果?这两个简单的问题,占据着本书的核心位置。
万历年间(16世纪晚期)生活于泉州近郊的颜魁槐,为我们留下了一段翔实的记述,从中可以看到他的家族是如何回答上述两个问题的。“伤哉!”他以哀叹开篇,接着写道:
勾伍之毒人也,猛于虎。我祖观田公六子,三死于是焉。弟故,兄代。兄终,弟及。在留守卫者一,毙于滇南者二。今朱家自嘉靖六年着役,抵今垂八十载,每回家取贴,万里崎岖,子姓待之若平(凭)空开骗局者。然曾不稍加怜恤,窃恐意叵测,我家未得晏然安寝也。故纪伍籍谱末,俾后人有所据,稽考从戎之繇、勾清之苦,与二姓合同均贴始末,得先事预为之备焉。
洪武九年抽军,本户颜师吉户内六丁,六都朱必茂户三丁,共合当南京留守卫军一名。先将正户颜丁应祖应役,乃观田公第四子,时年一十四岁,南京当军病故。勾次兄应安补役,逃回,称作病故。勾长兄应乾补役。洪武十四年,调征云南,拨守楚雄卫,百户袁纪下分屯种军。在卫二十八年卒,今有坟墩在。生子颜关、颜保。永乐八年勾军,推乾第五弟应崇起解补,在途不知日月病故。
至宣德三年,称作沉迷,将户丁颜良兴寄操泉州卫,至正统三年戊午故。勾朱必茂户丁细苟补操。至景泰三年,将细苟起解楚雄,本户贴盘缠银二十二两五钱、棉布三十匹。细苟到卫逃回,册勾将朱末初起解,本户又贴银二十二两五钱、棉布九匹,到卫逃。册勾将朱真璇起解,又贴银一十两。至弘治间逃回,仍拘起解,又贴银十两。正德十一年,又逃。嘉靖六年,册勾逃军。本府清理,审将朱尚忠起解,颜继户内津贴盘费银三十八两。二家议立合同:“颜家四丁当军百余年,俱各在伍身故。朱尚忠此去,务要在伍身故。发册清勾,颜家愿替朱家依例津贴盘费银两。”
至嘉靖廿一年,尚忠回籍取贴布匹银两,本家每丁科银一钱,计三十四两,余设酒呈戏,备银送行。至戊午,尚忠称伊行年六十有余,退军与长男,代我家当军焉。立合同,再年每丁约贴银三分。尚忠回卫,父子继殁。
至万历壬午,孙朱邦彬回籍取贴。计二十五年,每丁依原谣出银七钱五分,除贫乏、病故、新娶,实只有银四十二两。彬嫌少,欲告状退役,又欲勒借盘费。故会众与立合同,每丁年还银六分。癸巳,朱仰泉取贴,本族还银不上四十两。朱家以代我当军不理,除往来费用,所得无几。大约朱邦彬既长,子孙在卫,退役虽非本心,无利亦岂甘代我家?若一解顶,买军妻、备盘缠,所费难量。若再来取贴,处之以礼,待之以厚利,庶无后患。3
颜魁槐笔下的悲惨故事,要从颜家在明代户籍制度中的身份讲起。颜家被朝廷编为军户。在明代大部分时间里,人口中的这一特殊群体构成了军队的核心力量。后文将对军户制度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目前,我们只需要知道,军户必须世世代代为军队提供军人。并不是说军户中的每一个人——准确地说,每个男丁——都要当兵,而是说他们有义务为军队提供一定数量的人员。通常而言,每户一丁。颜家的情况有些复杂。他们和朱家——当地的另一个家族——共同承役。换句话说,两家须联合派出一名士兵,其中颜家负主要责任。颜朱两家组成了所谓的“正贴军户”。4洪武九年(1376),颜朱两家被征入伍,颜氏家长颜观田率先出丁,以确保两家履行义务。他选择让第四子颜应祖服役。应祖当时不过是个十四岁的男孩,就被遣往远方的南京戍卫。他在伍时间很短,到京师后不久便因病身故。颜家随后派出另一名幼子接替应祖。这个孩子也没服役多长时间,就当了逃兵,不知所终。颜观田别无选择,只得继续出丁。这次他态度一变,命令六个儿子中的老大应役。
洪武十四年(1381),颜家长子被调往千里迢遥的西南边疆,戍守云南楚雄卫。他在那里终身服役,再未回乡,于永乐八年(1410)去世。勾军官吏第四次登门。颜观田已是风烛残年,却不得不再择子顶补。新兵甚至连驻地都没见着,就在长途跋涉中不幸病故。颜观田去世时,他六个儿子中的四个服过兵役。三人入伍不久即离世或逃亡;唯一的“幸存者”,则远离家乡,在西南丛林卫所里度过余生(图1)。
之后的十多年,颜朱军户没有再派人当兵。这可能要感谢负责相关文书的书吏粗心大意,未及追查。到了宣德三年(1428),明军兵力严重短缺,朝廷重新清理军伍,勾补逃军,力图填满缺额。部分官员认为,士兵驻地远离本乡是军队失额的原因之一。有些新兵在漫漫长途中患病、死亡,颜观田的两个儿子就是如此;有些则如同颜家的另一个儿子,宁当逃兵,也不肯和家人天各一方、永难再见。军队的对策,可被称为“自首政策”:若负有补伍之责的男丁主动向官府自首,他将得到清勾官吏的保证,不会被送回本户原来服役的远方卫所,而是在家乡附近就地安排。5颜良兴,这名年轻的颜氏族人借机向朝廷自首,成功改编到不远的泉州卫服役。他于十年后去世。至此,颜家已经服了六十多年的兵役。
颜良兴身故后,颜家再无役龄男丁。于是乎,替补军役的责任就转移到“正贴军户”的另一家人身上。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朱家先后派出四名族人参军。

图1 颜朱两家正军的旅程示意图
随着边防所需兵员有增无已,“自首政策”最终破产。朱家的第一名士兵又被遣回颜朱军户原本的驻地——西南丛林中的楚雄卫。两家人都十分希望他能恪尽职守。逃兵屡禁不止,是明朝军队的大问题。对军户而言也是个大麻烦,因为他们必须找人顶补。为了阻止本户士兵逃亡,颜朱两家精心安排,为每位新兵准备银两和棉布。表面上,这是“军装盘缠”;实际上,两家希望以此说服新兵留在军队。可是这个如意算盘落空了,在役士兵一次又一次地逃亡,官吏便一次又一次地上门,勾取两家的替役者。
时至嘉靖六年(1527),颜朱军户服役已超过一个半世纪,对其中的不确定性深恶痛绝,想要找到长远的解决方案。他们共同拟订了一份简明的合同,其内容迄今仍留在颜氏族谱中。当时正在服役的朱氏族人是朱尚忠,他同意毕生服役。(合同上赫然写道:“务要在伍身故。”)颜家为求放心,同意替朱家支付朱尚忠的军装盘缠,以确保他坚持履行两家的共同义务。
事与愿违,该方案未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嘉靖三十七年(1558),朱尚忠自云南归来,提出一个新方案。他已经六十多岁了,想要退役,并希望达成一笔交易:朱尚忠承诺,自己的直系亲属和后代子孙会永世承担兵役,作为交换,两家人须定期支付银两。尚忠的儿子和孙子相继补伍,这将使颜家免于世代当兵,转而以金钱代役。只要持续付钱,颜家就再也不必担心会有官吏将颜氏族人推上战场。
颜朱两家起草的新合同比旧合同细致得多。其条文——同样被录入族谱——不仅包括两家的族际安排,还包括颜氏自家的内部协议,即如何筹钱给付朱尚忠及其后代。近两百年前,颜家被征入伍;而此时,颜观田的后代子孙很可能已有数百人之多,他们构成了所谓的“宗族”。合同明文规定,宗族中的每名男丁须逐年缴付一小笔款项,组成累积基金。准确地说,就是按丁摊派的人头费。而远在西南边疆的正军,将会定期收到来自本基金的报酬。
终于解决了一个旷日持久的难题,两家成员肯定如释重负。但故事尚未结束。新合同订立二十五年后,朱尚忠之孙回到家乡,抱怨酬劳太少,要求重修条款。颜家自度别无他法,不得不答应。他们提高了人头费,以应付新的、更多的军装开销。
颜魁槐的记述止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他呼吁族人凡事要通情达理,满足朱家后人的全部要求。如果正军回来索取更多盘缠,族人务必“处之以礼,待之以厚利,庶无后患”。颜氏族人也许没什么机会遵行颜魁槐的嘱咐,因为半个世纪后,明朝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清王朝,在军队动员问题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法。
颜魁槐受过良好的教育,科举及第,仕途得意。6但是,他的记述不是站在学者或官僚的角度写下的。它既非哲学沉思,亦非政策分析,只是一份家族内部的文书,被录入族谱,主要供族人浏览(我们将在后文的讨论中发现,颜魁槐也意识到,有朝一日,这份内部文书可能会作为呈堂证供交由判官过目)。它阐明了颜家为满足朝廷要求而做出的各项安排,并证实这些安排的合理性。它的时间跨度逾两百年,几乎与明王朝相始终。
军户与日常政治
像颜魁槐的记述这般,由家族成员出于自身动机撰写、继而被抄入族谱的文书,能够为本书的两个核心问题提供答案。这些文本,由普通民众写成,旨在处理、评论日常问题,或许会成为我们研究明代平民历史的最佳史料。在我们能找到的各种资料中,它们很可能最贴近百姓的心声。这些文本,不是从主导动员的国家的角度,而是从被动员的民众的角度,揭露了明代军事动员的方方面面。它们诉说着生活在明代的百姓,如何一方面苦苦应对来自国家的挑战,另一方面紧紧抓住国家提供的机会。我撰写本书的主要动力,就是要将百姓的巧思和创意告诉读者。我将努力论证,他们的策略、实践、话语构成了一套政治互动模式。这套模式,不仅见于士兵之中,而且遍布社会的方方面面;不独属于有明一代,亦曾显迹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期。甚至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可寻见其身影。
给这类互动贴上“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标签,不见得错,但这是对历史的“后见之明”,有简化问题之嫌,而且将国家和社会人格化了。社会由社会行动者——个人或家庭——构成,但每个社会行动者都在做着自己的选择。大部分时候,他们既不代表社会,也不以社会公益为目的,甚至不会产生这类想法。相反,他们追求的是个人利益,是认为对自己有益的事物。国家也非有意的,乃至协调一致的行动者。国家并不与民众互动,或者更准确地说,民众极少感觉到国家在和自己互动。民众的互动对象是国家的代理人:官员和胥吏。民众照章办事,造册登记,缴粮纳赋。我们可以从自身经验得知,在这类互动中,人们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我可以不折不扣地遵循政府官员的指示,一丝不苟、尽心尽责地登记各种文书簿册;我也可以拒绝服从这套程序,如果对方施压,我兴许会逃之夭夭,或者干脆揭竿而起。当然,民众和国家的绝大多数互动介于上述两个极端之间,对我们来说是这样,对古人来说也是这样。
此外,虽然有些政治活动没有涉及与国家制度或国家代理人的直接互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对这些活动而言无关紧要。无论其代理人是否在场,国家的影响力都无远弗届。国家的制度和管理结构,是世人生活背景的一部分。在颜魁槐的记述中,军队将领和征兵官吏均未现身。如果我们就此认为国家缺席了颜朱两家的族际交涉与内部磋商,那就未免太天真了。征兵制度是他们一切互动行为的背景。国家或许没有直接介入两家人的协商,但肯定是其中的利益相关者。这类协商很难被归入某一常见的政治行为范畴。可是,若无视其政治属性,将大错特错。
其实,很多政治行为往往只是一种平凡而日常的互动:介于被动服从和主动反抗之间,不直接牵涉国家或其代理人。在这个中间地带,百姓间接地而非直接地与国家机构、规管制度及国家代理人打交道,反客为主,移花接木,以求其得以任己摆布、为己所用。百姓为了应付与国家的互动,琢磨出许多策略,我们该如何描述这些策略呢?显然不能简单地按照官方文书的说法,给它们贴上“犯上作乱”或“行为不端”的标签。为了突破“顺从”“反抗”二元对立的局限,我选择了“日常政治”(everyday politics)这个术语。7正如本·柯尔克夫烈(Ben Kerkvliet)所言:“日常政治,即大众接受、顺从、适应、挑战那些事关资源的控制、生产或分配的规范和规则,并通过克制的、平凡的、微妙的表达和行为完成这一切。”8
日常政治的“策略”,是一种本领和技巧,可以被掌握或传授;或者说,它是一种“被统治的艺术”。这一概念的灵感,显然来自福柯笔下的“统治的艺术”以及斯科特所说的“不被统治的艺术”。正如福柯对“统治的艺术”之重心变化的描述,本书希望刻画出“被统治的艺术”的历史。9本书与斯科特的大作在书名上仅一字之差,希望读者不要以为这只是在玩文字游戏。我想借此表明一个严肃的观点:明朝(及中国历朝历代)的百姓和斯科特笔下的高地居民(zomia)存在本质差异。前者的“被统治的艺术”,不是一道简单的要么“被统治”,要么“不被统治”的选择题,而是就以下问题进行决策:何时被统治,如何被“最恰当地”统治,如何让被统治的好处最大化、同时让其弊端最小化,等等。对明代百姓来说,日常政治意味着不计其数的权衡斟酌,包括掂量顺从或不顺从的后果、评估各自的代价及潜在的益处。10强调这些权衡斟酌,并不意味着把百姓的所作所为简化为在理性选择驱使下的机械行事(相反,他们是目标明确、深思熟虑的行动主体,通过有意识的努力,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时,也不意味着将他们的努力矮化为“操纵体制……把自身损失降到最低”11的一个实例。操纵体制的现象很可能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但是,百姓如何操纵体制,为何要这么做,为此动用了哪些资源,对体制的操纵如何重塑了他们的社会关系……这些都是历史研究中有意义的,乃至亟须探索的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承认百姓有能力知悉自己与国家的关系,并应付自如。换句话说,他们有能力创造自己的历史。
本书将通过军户的故事,考察明代的日常政治。我们会结识彰浦郑氏一家,他们通过修改族长遗嘱,解决了怎样在家族内部定夺参军人选的问题;福清叶氏一家,他们通过维持与戍边族人的联络,化解了地方恶徒的刁难;福全蒋氏一家,他们仗着自己在军中的地位,参与货品走私和海盗活动。此外,还有很多很多人家,以及他们精彩绝伦的故事。
表1 被统治的艺术:百姓与国家互动策略之类型

上述家族应对国家的一系列策略,可分为四类,如表1所示。我已经提及从服从到反抗这一光谱(“服从”与“反抗”的措辞相反相成,实则皆是从国家角度而言的);另一光谱则关于策略运思的程度:一端是随机应变的权宜之计,另一端则是蓄谋已久、井然有序的运筹帷幄。
军中的极端反抗行为的表现,莫过于逃兵和哗变。明军士兵不是未曾造反或逃跑,但本书不会对它们详加讨论,原因并非在于它们不属于明代日常政治的范畴,而是因为士兵很少留下相关的书面记录。明王朝深受逃兵之害,作为对策,朝廷越来越倚赖募兵。募兵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通常被视为压倒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12然而,几乎没有任何史料是从士兵的角度讲述逃兵现象的。
军户肯定还有很多别的策略,因时制宜、灵活自如地应对挑战。“日常反抗行为”包括小偷小摸、故意拖延、冷嘲热讽、溜之大吉,等等。通过这么做,各地军户百姓竭力维护自身利益,对抗上司和朝廷的种种要求。13人们一般也不会记下这类随机策略。要说从实践者的角度理解它们,历史学家可比不上人类学家和民族志学者。因此,我也不会在这类策略上徒费笔墨。
最适合历史学方法大展拳脚的,乃是对“日常政治策略”的研究。所谓“日常政治策略”,是指那些合乎规矩且被朝廷视为服从(或至少不是反抗)的策略。实施者一般都会将其用白纸黑字记下来。其实,每每正是这样的记录,才使策略得以奏效。本书着重探讨的就是这一领域的策略。
制度、解域化和社会遗产
军事体制将人员调往四面八方。为了发动进攻、组织防御、传递信号或其他目的,士兵从一地来到另一地。军队让士兵脱离熟悉的社会环境,切断原有的社会关系。这使得士兵“脱离原境”(decontextualize),或借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说法,士兵被“解域化”(deterritorialize,德勒兹和瓜塔里或许会将军队称为“解域化机器”)。14然而,军事调度又催生出“再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反作用力。一种流动性得到加强的同时,另一种流动性则受到削弱:军官既要提高队伍的机动性,又要限制士兵开小差。士兵自己也能产生“再域化”的反作用力。当他们带着家眷来到远离本乡的卫所,原有的社会网络已支离破碎。但是,他们很快就会着手跟周围的人——卫所中的同袍和卫所外的民户——建立起新的纽带。15由此可见,军队实际上还是一个催生社会关系的机构。这些由国家政策与民众对策无心插柳而成的新社会关系,正是本书的第二个主题。它们构成了又一类日常政治,虽然看起来不太像“策略”,但潜在的重要性不遑多让。
本书关注的制度——明代军户制——随着明王朝的覆灭走入历史。然而,我们将会看到,明代军事政策意外创造的社会关系在改朝换代之后依然存在。它们熬过了实行军户制的明王朝的灭亡(1644),熬过了帝制本身的倾覆(1911),甚至熬过了接替清朝的中华民国的溃败(1949)。制度似走马灯一般更替,其孕育的社会关系却生命力顽强。制度的历史可以洞烛迄今犹存的社会关系背后的历史进程。只要到福建省莆田市平海镇走一走,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平海镇位于泉州以北,前身是明代的平海卫。每逢农历新年,镇民都会举行盛大的节庆仪式。正月初九,他们抬出城隍,绕镇巡游。庆典热闹非凡,人们燃放炮竹,现场烟火弥漫。抬神之人在前,数百骑手在后,他们五颜六色的服饰在浓厚的香雾中时隐时现。妇女们一边念念有词、喃喃祈祷,一边为游神队伍清扫开道,从沉重的香炉中取走点燃的线香。平海卫的城墙早已毁弃,但游神队伍仍然仅在昔日城墙限定的范围内活动,不会进入周围的村庄。年复一年,城隍巡游平海辖境,接受信众的供品,为新年赐福驱邪,在平海和周围村庄之间划下一道界线。卫所已消失了数百载,仪式却依然例行不辍。
中国很多地方的城隍无名无姓。没人知道他叫什么,也没人知道他何以成为本地的守护神。平海则有所不同,城隍的身份和事迹不仅家喻户晓,而且令人生畏。他曾是历史上一个真实人物,名叫周德兴,死后化身神明。作为明朝开国功勋,周德兴早年投奔朱元璋,成为其亲信,最终受封江夏侯。当朱元璋需要一位可靠的将军,负责建设帝国东南地区的海防体系时,周德兴成为不二之选。洪武年间(14世纪80年代),周德兴率部经略福建,行垛集法,按籍抽丁,操练成兵,士兵家庭被编为军户。此举令福建数万男丁背井离乡,置身行伍,筑造城池,尔后留守其中。平海卫便是新城之一,建城之人即现今镇民的祖先。卫城始建,就有了一座城隍庙,供奉着城隍神。百余年后,镇民将周德兴追尊为城隍。如今平海人高抬城隍巡游,为来年祈福,并不只是传统习俗的简单重复,而且还在纪念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数百年前本地社群的诞生。进入21世纪的游神,既讲述着地方认同的形成,又显示着历史传承的非凡,是历史造就了这项仪式。巡游的神明娓娓道出本地先祖和明代国家互动的往事,这正是游神活动所拥有的诸多意义之一。
关于明代历史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1368—1398年在位),乃元末乱世崛起的一代枭雄。平定四方、一统天下后,他大展宏图,着手重建历经数十载外族统治和内部纷乱的中国社会。他与朝臣以元代之前的中原王朝为样板,革故鼎新,旨在与元朝划清界限。然而,明代制度实则广泛倚赖元朝旧制,包括世袭军户制度的某些部分。16
明王朝的第二个主要特点是,整个帝国深深烙上了朱元璋的个人印记。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开国皇帝,朱元璋执政伊始,便拟定了本朝的社会政策——一份“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的宏伟计划”。17朱元璋的愿景不只是设立或恢复运行良好的政府体制,他还希望创建(或重建)一套乌托邦式的乡村秩序。在该秩序下,百姓生活在自给自足的村庄,过着安于现状的日子,亲属和邻居之间相互监督,无须朝廷官吏插手管理。
所有领袖都会担心自己的政策能否在身后继续实行,朱元璋也不例外。他下令,自己与大臣设计的治国纲领和原则(或许可称之为明代的“宪法”或“祖宗之法”)必须永远贯彻下去,后世不得违逆。历史学家通常将这份指示视为明朝的第三个特点,据此解读本朝何以无力应对外部世界的改变。可是,“宪法不可变”并非明代独有。18也许明人格外强调这一原则,但体制终归有能力通过各种方式适应时代的变迁。若非如此,大明国祚又怎能延绵近三个世纪之久?在国家的实际运行方面,大体上,明朝的制度惯性或路径依赖与其他政体并无本质差别,甚至近似于现代国家——当然,造成惯性的根本原因和制度结构大不相同。毋庸置疑,朱元璋的“祖宗之法”影响了明代历史,但我们不能仅从字面上理解这一“祖宗之法”的含义。
在朱元璋的乌托邦中,乡村社群将主要采取自治模式。然而,要实现他的愿景,实需同时落实高度干预的方针。若不考虑技术方面的能力,仅就其中的勃勃雄心而论,朱元璋政权和其他政权是一样的。20世纪以降,明朝被视为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顶峰,当代的部分学者依然这么认为。19但随着我们对明中期经济迅速增长、社会充满活力的事实有了更多了解,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则已发生改变。其时,全球对中国产品需求强劲,大量白银涌入中国,加上农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共同促成了明代经济的市场化,这对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造成了翻天覆地的影响。现今很多学者指出,明末社会——尤其在富庶的城镇地区——基本不受朝廷控制。部分学者甚至将之描述为“自由社会”。20由此可见,明史的主导叙述模式已从以国家为中心转向以市场为中心。21
在这里,我将尝试提出一种全新的明史叙述模式。这种叙述模式的主体既不是国家,也不是市场;既不是皇帝,也不是白银。本书认为,无论是早先的“专制独裁论”,还是与之对立的“自由社会论”,都言过其实。明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可以更好地从国家角色及其在场效果之变化的角度,而非国家退出和消失的角度讲述。
关于本书
图书管理员大概会把本书放到明代军事史类别的书架上,但军事并非我在这里着重探讨的内容。本书虽然和明代军队有关,但是没有描述任何战役,对战略、后勤或武器等军事史的经典主题亦鲜有涉及。相关研究成果浩如烟海,大多聚焦于明王朝建立或覆灭的历史。换句话说,军事史学家主要关心朱元璋如何打下江山,而他的子孙又如何将天下拱手让人。22对明王朝衰亡的叙述往往以明军战斗力低下——作为国运衰颓、本末倒置、党同伐异或财政崩溃的表征——为中心。23但是,部分研究明代军队的学者则超越了狭隘的军事课题,探索外交政策、战略文化、民族或暴力等议题。和他们一样,研究军事机构并非我的目的,只是我研究其他问题——明朝百姓的日常政治——的手段。24
本书将讨论明代军队这个特定机构,但我的目的不在于阐述该机构的正式条规及其在不同时期的运作情况。本书建基于其他学者对军户制的研究成果之上。譬如张金奎,他是大陆学术界在该领域最权威的专家。但与之不同的是,我主要把军事机构放在社会史的领域进行研究。本书亦受益于于志嘉的著作,她是张金奎在台湾地区的同道。但与之不同的是,我尝试将研究课题放在特定的地方生态环境中进行考察(平心而论,我往往唯有借助她关于军户制的综合性研究,才能够了解地方案例。而且她的一些近作,也是围绕某个特定地区展开论述的)。25我研究体制,依据的不是朝廷在设计体制时的种种构想——尽管这些构想是必不可少的背景知识——而是与体制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百姓,看体制如何塑造人,又如何反过来为人所塑造;看百姓如何反客为主,操纵体制乃至扭曲体制。换句话说,本书致力于勾勒出制度的日常政治,以及在一般的日常政治中制度所扮演的角色。本书将探索百姓对制度的体验如何因时而变,探索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是或不是在自我强化,而影响它自我强化程度的内在和外在因素又有哪些。
本书是一部区域史著作,但却不是某个地方的历史。确切地说,本书是在特定区域微生态的背景下探讨历史现象。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曾经写下“人类学家不研究村庄,而在村庄里做研究”的名言。26同样地,本书不是中国某个地区的历史,而是利用来自一个地区的证据写成的中国日常政治史。我的“村庄”远离北部和西部边疆——它们是明朝重兵驻防的地区,也是此前大部分研究者的关注焦点。一个地区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它会受到社会史研究者的青睐。我的“村庄”要比格尔茨所想的大一些:本书的地理范围——以福建沿海地区为主,并向北延伸到浙南,向南延伸到粤东北——与我的研究目的有关。我希望将制度放到它被体验的特定的政治、社会和生态背景下进行考察。27
海洋是东南沿海地区生态最突出的特征。对该地区的居民来说,海洋是生计的来源。他们出海捕鱼、在浅海养殖贝类,并在海上进行贸易和走私。他们乘风破浪,足迹遍及台湾岛、琉球、日本和东南亚。和其他边疆地区一样,情势危急时,百姓会选择逃离,而海洋则提供了逃生通道。沿海居民——士兵和平民——可以逃到台湾岛或某座离岸小岛。有时,他们的确是这么做的。
海洋既蕴藏危险,又带来机遇。该地区曾多次遭受来自海上的攻击,本书登场的军户家族的主要军事职责便是抵御这类攻击,确保海疆靖晏。但是,相比于帝国的其他边疆,沿海地区的局势要安宁平静得多。与北部和西北部的驻军不同,有明一代,沿海地区的军队从未长期面临严重而紧迫的军事威胁。既然东南沿海地区的防务不是帝国首要的军事问题,该地区的驻军也就没有受到朝廷的持续重视。
该地区第二个值得关注的要素是沿海和内陆的关系。通过内河航运,内陆丘陵与滨海平原相连,丘陵地区成为沿海卫所的主要粮食供应地。远洋贸易推动的市场化渗入丘陵地区,使该处比深入腹地的其他州县更加繁荣,其经济的商业化程度也高得多。
其他学者已经讲述过该地区的地方史。28如同本书涉及制度方面的内容主要受益于制度史家对明代军队的研究,近几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地方史著作,极大地影响了本书对该区域的论述。我将制度史和地方史这两个领域的文献结合起来,撰写出这部区域制度史著作,揭示军事制度中的日常政治如何受到区域自然和社会微生态及其遗产的影响,又如何反过来对后者产生影响。
本书大部分研究取材自福建沿海的二十多个明代卫所,但有时我也会将范围扩展至更北或更南的地区(图2)。在一些卫所的原址,我们还可以看到明代遗迹,虽然它们已被现在的居住区域完全包裹起来。举例来说,虽然明代永宁卫的遗址只占据欣欣向荣的石狮市的一个小角落,但其格局依然清晰可见,昔日卫城那铺满石子的长长的窄巷,连接着两座城门,蜿蜒近两公里。有些明代军事基地遗址,例如位于偏远半岛、坐落在悬崖峭壁之上的镇海卫,几乎没有受到近年来经济发展的影响。镇海卫的寺庙最近一次重建于清末,现在依然完好无损。

图2 东南沿海卫所示意图
兼顾现实情况和学术考量,本书讨论的卫所大多位于农村地区。一些大城市(如福州)当然也有卫所分布,但受限于我所掌握的资料,此类卫所极少出现在本书中。我将在后文进一步说明,包括颜家在内的军户家族的族谱是本书运用的主要史料。走访曾经的卫所,寻找军户的后人,是搜集这些族谱的最佳方法。在许多曾是卫所的村镇,当地相当一部分人口依然由明代士兵的后裔构成。在福建那些人口数百万的大城市,这种方法不可能奏效。不仅如此,和位于农村地区的卫所不同,位于城市中心的卫所从未在当地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当然,这不是说卫所对城市社会一点影响都没有)。29因此,为了确保在不受其他因素干扰的情况下研究明代军事制度的影响,位于农村地区的卫所是我们的优先选择。如果我们将通过军户考察普通百姓如何与国家制度打交道视为一场自然科学实验,相较而言,远离城市喧嚣的卫所显然实验条件会更好一些。
本书之所以是一部区域史著作,原因在于它极其依赖于田野调查——不是指那种长期参与某一社群生活的人类学家式的田野调查,而是指使用从田野搜集到的史料,并在当地背景下予以解读。尽管中国历朝历代都致力于将全部历史档案收归国有,但这个目标从未真正实现。研究者只有花时间前往历史文本的创造、使用和流传之地,才能获得数量巨大且独一无二的原始资料。30本书使用的大量史料并非来自图书馆或官方文献,而是从个人手中或资料所在地发现的。搜集这类史料是田野调查的最大乐趣:你要找到乐意分享自家历史的人(一般是上年纪的人);多数情况下,你唯一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成为他们的座上宾。毫不夸张地说,我写本书所需的历史档案,是由田野调查创建出来的。
其次,跑田野意味着我们要在当地背景下阅读新制作的档案,要格外关注生产这些档案的地方条件,同时尽量利用今人——通常是文献作者的后人——所拥有的与档案相关的地方知识。这很简单,譬如,去追查地契上罗列的田地的实际方位,好知道买田卖田的农民究竟都做了什么;或者,搞清楚税收记录中的方言土语,好理解老百姓的实际税负。此外,还有更多事可以做,譬如,将乡村寺庙中的碑铭和当地族谱进行比对,从而明白寺庙施主之间的亲属关系;又或者,如第六章和第七章所示,我们可以跟着游神队伍一起绕境巡行,从而描绘出本地社群活动区域的界限范围。
本书研究范围较小,且着重探讨地方性经验,因此使用的方法在某些方面近似于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等人所实践的微观史学。微观史学的滥觞,挑战了效法社会科学、抹杀人的实践经验和主观能动性的史学研究进路。和微观史学家一样,我在这里的目标是,在“突破,但不推翻”大结构之局限的前提下研究人的作用,“在小地方问大问题”。31本书和西方微观史学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虽然我讲述的故事确实是“微观”的,但所用的史料很少是百姓在非自愿的情况下接触国家代理人或机构的产物。书面证词、拘捕记录或审讯报告很少出现在本书中。我参考的地方文书,绝大多数是百姓带着明显的策略意图自愿创作而成的。这意味着此类文书更适合研究社会史而非文化史。本书的故事展现的是人的行为而非精神状态,是人的行动而非解释框架。它们侧重叙事而非结构,能帮我们增加对政治策略而非政治文化的理解。
综上所述,本书是一部基于田野调查搜集而来的史料,在地方语境下讨论明代军事制度的社会史著作。本书提出了一个在特定微生态中的日常政治策略分类模型,并以此为基础,就明代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日常政治,提出了一个更具广泛性的论点。
本书由四部分组成,每部分的空间和时间背景各不相同。第一部分的时间设定在明代军户制度创立伊始的14世纪末,地点则是明军士兵原籍所在的乡村。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时间则来到15世纪和16世纪,主要探讨明代军事制度在进入成熟期后的运作方式。第二部分的故事发生在士兵戍守的卫所,第三部分的故事则发生在士兵垦辟的军屯。到第四部分时,我们会回到卫所,看看明朝灭亡后的情况。
本书的第一部分将探讨募兵和征兵制度。第一章以郑家的故事开篇,他们采用创造性的方法,解决了如何挑选族人应役这一难题,从中我们可以一窥军事体制中的家庭如何通过成熟的策略应对兵役之责。军户在规章制度中的定位简单明了——一个军户必须为军队提供一名士兵——但是他们实际的处境可能十分复杂。他们精心制订出各种策略以处理两者间的差异,使应负的职责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从而减少未知的风险,使更多族人享受到身在军籍的好处,同时将需要付出的代价降到最低。
编为军户,干系重大,远不止于为军队提供士兵这么简单。它既会带来大量的赋税豁免,也会招致邻居的恐吓敲诈。军户家庭怀有强烈的动机,希望和在伍的亲人保持联络,因为他们可以证实自家谨遵军户体制的规定。福清叶氏即是一例。叶家最有名的成员——内阁首辅叶向高——为我们留下一段文字,记述了叶家为与戍守在北部边地的亲人重新取得联系而付出的百般努力。
本书的第二、第三部分将焦点从军户原籍所在的乡村转移到士兵驻守的卫所,并从明初进入明代中后期。我们将在第三章遇到担任福全所世袭千户的蒋家。蒋家至少有一名族人曾既担任军官,又干着走私和海盗的勾当。他的故事揭示了军户如何利用他们在卫所中的特殊地位浑水摸鱼,从事非法贸易。他们靠近国家,利用自己的身份斡旋于军方和商界之间,在海上商贸中占尽优势。卫所军士不得不适应一个全新的环境,让自己扎根其中,建立新的社群。我将在第四章考察卫所军户的婚配嫁娶,他们祈福的寺庙,以及就读的卫学,这些都在展示士兵及军眷如何一步步地融入卫所的地方社会之中。
本书第三部分将目光从卫所转向为军队提供补给的军屯。军屯军户垦殖农田,供养着戍守在卫所的同袍。麟阳鄢氏的不幸故事,告诉我们军屯士兵如何熟练利用军田与民田之间的不同渔利。经济的市场化催生出复杂的土地所有权模式和土地使用模式,军屯里的家庭则设法用这些模式为自身服务。军屯的日常政治远不止于摆布土地制度。一如卫所军户,军屯军户也不得不融入当地社群。本书的第六章旨在探索这一过程。有些人游走于不同的规管体制之间,左右逢源。其他人则设法加入现有的社会组织,乃至反客为主、取而代之。湖头的一座小庙将告诉我们这些新的社会关系如何得以持续不断的发展。
进入第七章,我们将返回卫所,但此时已然明清易鼎。明代的军事制度虽不复存在,但依然影响着曾身处其中的普通百姓。有的人试图挽回旧体制,从而可以延续他们在体制中享有的特权。有的人则发现,改朝换代之后,自己依然要承担前朝的一些义务,于是不得不继续应付。还有人努力通过调整前朝旧制的某些元素,使之适应新的处境。他们想方设法让清王朝了解自己,使用清代官员能够接受的语言来实现此目标,尽管经他们描述的社会制度与其真实的情况往往南辕北辙。
本书四部分中的一则则故事,讲述着明代百姓如何利用各种策略应对国家力役。在前面讨论的基础上,我将于本书结尾处,就中华帝国晚期及其后的“被统治的艺术”提出一些更宽泛的思考路径和思考方法。
脚注
1 持该立场的人喜欢引用韦伯的名言:“国家者,就是一个在某固定疆域内(在事实上)肯定了自身对武力之正当使用的垄断权力的人类共同体。”(“Politics as a Vocation”,78)
2 部分学者甚至认为,军事动员的手段形塑了现代国家形成的本质。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言:“战争创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42;亦可参见Roberts,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1560-1660。Levi, “Conscription: The Price of Citizenship”是对国家征兵方式的类型学研究,但主要讨论的是现代国家。
3 “纪伍籍”,《颜氏族谱》, 119页及其后。在可能的情况下,族谱的注释都会包括所引文章或段落的标题。
4 关于“正贴军户”的详情,请见本书第一章。
5 《明宣宗实录》卷三十六,宣德三年二月甲寅, 892页。本书所引《明宣宗实录》,来自《汉籍全文资料库》。
6 万历三十二年(1604),颜魁槐乡试中举,然后出任了一系列官职,最高者乃楚雄府同知。楚雄动荡不安,有军队驻扎。有趣的是,不少驻军来自泉州地区,是他的老乡。
7 福柯试图用“反训导”(counter-conduct)这一术语处理类似的两难问题,但我认为该词难以令人满意,因为它依然过度强调反抗的一面。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260. 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有“不像那样和不付出那种代价而被统治的艺术”以及“不被统治到如此程度的艺术”等表述。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些表述方式也不够好。 “What is Critique?” , 45.
8 Kerkvliet, “Everyday Politics in Peasant Societies (and Ours), ” 232.
9 Foucault, “Governmentality”;Scott,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10 继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之后,罗森塔尔(Jean-Laurent Rosenthal)和王国斌(R. Bin Wong)提出,生活在中华帝国晚期的百姓如果对现状实在感到不满,就会试着通过“退出”(exit)和“发声”(voice)等策略组合,重塑自身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我将在下文论述,这种对潜在策略的思考方式过于狭窄。对自身与国家之关系的重塑一直都存在。当百姓相信运用某些策略可以满足个人利益的需要时,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做。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 211.
11 Hobsbawm, “Peasants and Politics, ” 7.
12 关于明代逃兵规模的估算,可参见许贤瑶:《明代的勾军》,139—140页。
13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Sivaramakrishnan, “Some Intellectual Genealogies for the Concept of Everyday Resistance.”
14 Deleuze and Guattari, Anti-Oedipus, 34-35; Nomadology, 65-68.
15 中国学者经常使用“地方化”或“本地化”指代我称之为“再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过程。参见林昌丈:《明清东南沿海卫所军户的地方化——以温州金乡卫为中心》。“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另一个主要含义——在当代全球化的条件下,诸如金融交易在内的多种互动行为并不在某个特定地点发生——和此处的用法不同。Scholte, Globaliza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17, 75-78.
16 Taylor, “Yuan Origins of the Wei-So System.”
17 Farmer, Zhu Yuanzhang, 10.
18 Farmer, Zhu Yuanzhang, 16-17; Tackett, “A Tang-Song Turning Point,” 3;邓小南:《祖宗之法》,第四章;关于该现象的影响,参见《祖宗之法》第六章。
19 譬如,有学者就认为:“明代建立的第二个相关意义是:在皇朝体制内,权力被进一步集中,形成‘明代专制’。”参见Farmer, Zhu Yuanzhang, 100。至于中国史学界的相关研究,参见范文澜、蔡美彪:《中国通史》,第八卷,尤其是第一章。
20 想了解学者关于该立场的学术背景的讨论,可以参见Struve, “Modern China’s Liberal Muse: The Late Ming”。
21 这激起学界对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新兴趣:有些学者致力于在明末社会寻找中国本土的“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却收效甚微;有些学者则致力于研究社会行动者与国家代理人之间的互动协商,譬如探索社会网络如“毛细管”一般影响国家的方式,或者追问社会领域“殖民化”国家制度的途径,相关研究进路成果颇丰。Brook, The Chinese State in Ming Society; Schneewind, Community Schools and the State in Ming China; 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
22 Dreyer, “Military Origins of Ming China”;李华彦:《近三十年来明清鼎革之际军事史研究回顾》。想了解中国史学界的相关研究,可参见张金奎:《二十年来明代军制研究回顾》。想了解日本史学界的相关研究,可参见川越泰博:《明代军事史的研究状况》。
23 相关的大部分中文研究著作都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批评明代(尤其是明末)统治者重文轻武、军备不修、目光短浅。石康(Kenneth Swope)近年来以修正主义的进路挑战了这类强调明军衰弱的论述,指出16世纪末明朝对日作战的胜利表明,即便在王朝末年,明军也根本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参见Swope, A Dragon’s Head and a Serpent’s Tail。
24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Robinson,Bandits, Eunuchs and the Son of Heaven; Waldr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25 于志嘉:《卫所、军户与军役》,以及她的其他作品;张金奎:《明代卫所军户研究》。于氏的《卫所、军户与军役》虽然是以明清江西地区为中心的研究,但在我看来,该研究并没有真正立足于江西的地方生态。不少有关明代军队的著作选择将焦点集中在庞大体制的某一部分。对“开中法”的研究即一显例。在该制度下,朝廷给商人发放食盐运销许可凭证(盐引),作为交换,商人则需为边地驻军提供补给。黄仁宇:《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五章“盐的专卖”);Puk, The Rise and Fall of a Public Debt Market, 13-18,评论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26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22.
27 如果参考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影响深远的中国大区概念,拙作的地理范围和东南沿海大区的核心地带几乎完全重合。
28 例如:Clark, Community, Trade and Networks;Billy Kee-Long So, Prosperity, Region and 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China;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
29 研究城市卫所的一篇高水平作品是Luo, “Soldiers and the City”。
30 现存文本中,只有极小部分能在图书馆等公共资源库(其中上海市图书馆藏书量最大)找到。举例来说,收录家谱(族谱)最多的目录,即王鹤鸣主编的《中国家谱总目》列举出安溪县四十七部家谱,而上海市图书馆只藏有其中一部。我于2012年前往安溪县搜集史料,当时停留时间不算长,在该县二十四个乡镇中的湖头镇,就拍摄了超过二十部家谱。这些家谱中,只有四部出现在王鹤鸣主编的总目里。附近的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已经从湖头镇搜集了一百多部家谱。既然连该研究中心的收藏都没能囊括所有现存家谱,这意味着家谱总数大约比总目记载的数量还多出两个数量级。
31 Joyner, Shared Traditions: Southern History and Folk Culture,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