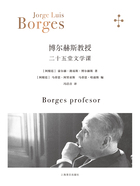
引言
这些讲课记录由几位英国文学课的学生录音,为了让其他因为工作需要而不能前来上课的学生也能作为教材。这些录音的文字版由同一批学生抄录,构成了本书的基础。
原始录音带已经遗失,也许被用去为其他科目的课程录音。这样的草率马虎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不可原谅,然而,我们应当理解在一九六六年——讲授这门课程的那一年——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尚未像今天这样被视为无可争议的天才人物。鉴于阿根廷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他对当时事件的评论比他的文学作品获得了更多的公众关注。对于他课堂上的许多学生而言,博尔赫斯——尽管已经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和国家图书馆馆长——大概也只不过是一位教授而已。因此,这些课堂录音笔记是作为学习教材而制作的,很可能仓促而成,为了应付考试。
实际上我们也许应该为此而心怀感激:无人尝试去修饰博尔赫斯的口头语言,也没有修订他的句子,我们拿到手的是免不了重复和套话的原始记录,这种忠实性可以通过对比博尔赫斯此处的语言与其他口头论述文本的语言——例如他的许多讲座和公开访谈——而得到证实。抄录者在每一堂课录音笔记的结尾都标注有这样的话:“原文照录”。幸运的是,这种忠实不仅表现在记录博尔赫斯的陈述,而且表现在记录了教授对他的学生说话时的偏题话和口头用语。
另一方面,因抄录者受限于时间且缺乏学术训练,每个专有名词、标题或者外语用词都用注音标注,因此大部分作者名和作品标题都写错了;原始记录中的盎格鲁——撒克逊语和英语原文摘录以及顺带的词源解释均完全无法辨识。
出现在文中的每一个名称都必须详细核对。要辨认出“Roseti”是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并不难,但是要猜出“Wado Thoube”实际上是诗人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则花费了更多时间。抄录者每次提到哲学家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的时候都将其写成“Bartle”。许多这样的名称需要花费大量精力查找,例如十八世纪耶稣会士马丁·多布雷兹霍夫(Martin Dobrizhoffer)——在原始记录中写作“Edoverick Hoffer”,还有利文斯顿·洛斯(Livingston Lowes)教授,他的名字被写成一本书的名称,“Lyrics and Lows”。
显然许多情况下抄录者不熟悉课上谈到的文学作品,像杰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这样尽人皆知的名字在原始记录中有着奇怪的拼写,几乎可以将角色可怕的双重身份变成多重身份。例如,杰基尔博士(Dr.Jekyll)分别写作“Jaquil”“Shekli”“Shake”“Sheke”和“Shakel”,海德先生(Mr.Hyde)则是“Hi”“Hid”和“Hait”,这些变异有时出现在同一页上,甚至同一段话中。有时很难确定是否所有的变异指的是同一个人。因此英雄亨吉斯特(Hengest)在上一行里拼写正确,在下一行里就变成了“Heinrich”;哲学家斯宾格勒(Spengler)躲在“Stendler”“Spendler”这样的名称后面,甚至跑得更远,变成了“Schomber”。
博尔赫斯列举的诗歌内容也同样难以分辨。有些分辨出来后,结果令人觉得很有喜剧性。也许最值得一提的是出自《草叶集》的一行诗,原本是:“Walt Whitman,un cosmos,hijo de Manhattan”(“沃尔特·惠特曼,和谐一体,曼哈顿之子”),结果在原始记录中变成了“Walt Whitman,un cojo,hijo de Manhattan”(“沃尔特·惠特曼,瘸子,曼哈顿之子”),这样的变异肯定会让诗人感到不安。
在课堂上,博尔赫斯经常要求学生全神贯注大声朗读诗歌,学生朗读时,博尔赫斯会对每一节诗加以评论。在原始记录中,学生朗读的原文被省略了,在缺乏原文的情况下,博尔赫斯对每一节诗的评论上下连续出现,完全无法解读。为了恢复前后一致性,我们找到了这些学生朗读的诗歌原文,将博尔赫斯的评论穿插在其中,这的确是一项费力的编辑和复原工作。
这样的工作要求恢复先前按照原文发音抄录的古英语的原文摘选内容。尽管有很多舛误,这些还是可以辨识的,我们用原文替代了。
博尔赫斯文本的标点符号在仓促而成的原始抄录中必须全部更改,原则上总是令其符合上课说话的节奏。
这项编辑工作要求修订所有的事实,纠正抄录错误,在必要时进行更正。大部分文本的原始资料都已经找到,我们还添加了尾注,提供了诗歌原文(如果简短的话)或者片段。
在有些情况下,为了方便读者,做了一些必要的小修改:
一、添加了遗漏的词(连接词、介词等等),博尔赫斯说话时肯定会用到的,尽管在原始抄录中没有出现。
二、有些连接词的确出现在口语中,但会使书面文本更难理解,则予以删除。
三、有几处地方有必要使主语和动词更加贴近彼此,因为博尔赫斯有时会热情洋溢地长时间偏题——这在口语中是可以接受的,但在书面文本中,讨论的线索就会完全中断。我们改变了一些句式中词语的顺序,但没有删去任何说过的词。
鉴于这些修订并未改变博尔赫斯讲课的用词和主旨,我们没有注明这些修订之处,以免打扰读者。在其他情况下,如果添加博尔赫斯没有说过的词,则将其置于方括号内,以方便理解。
尾注大多提供有关作品、人物或事件的信息,为了充实阅读材料。我们基本上没有试图将这些课程中的主题与博尔赫斯的其他作品相关联,否则作家博尔赫斯与教授博尔赫斯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紧密,会需要几乎无限量的注释,何况,我们的目的并非对文本进行批评或分析。
许多注释都只是生平简介。篇幅的相对长短并不反映我们对人或事的价值评判,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均由两个因素决定:一、具体所指不为人所知的程度,二、与课程的相关程度。因此,例如乌尔菲拉这位哥特神职人员,还有冰岛历史学家斯诺里·斯图鲁松有几行文字介绍;而年代更近或更加为人所知——或者只是顺便提到——的人物的注释则只包含生卒年份、国籍以及便于读者识别的少量事实。
读者将会发现许多这样的短小生平注释对应著名人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读者不熟悉他们。考虑到博尔赫斯常常在不同世纪、不同大陆之间来回跳跃,进行对比和比较,这些注释有利于读者对具体人物进行历史定位。
我们不知道博尔赫斯是否知晓存在这些教材笔记,但是可以肯定,他会很高兴得知有这些纸张来传承他作为教师的工作。无数读者现在可以加入那些学生的行列,博尔赫斯曾经多年满怀深情兢兢业业地亲自向他们面授英国文学。
衷心希望读者也像我们享受编辑本书一样,在阅读中获得享受。
马蒂恩·阿里亚斯
马蒂恩·哈迪斯
布宜诺斯艾利斯
二〇〇〇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