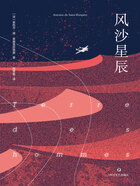
第一章
航线
1926年,我以年轻飞行员的身份进入拉泰克埃尔公司,这家公司在邮政航空和法国航空之前承担着图卢兹到达喀尔航线的飞行。我也是在那里学习了有关飞行员这个职业的一切。和所有的同行们一样,在有幸驾驶飞机前,我经过了那么一段新手的实习期。试飞,从图卢兹到佩皮尼昂的来回旅行,冰冷的停机库里令人抑郁的气象课程。我们生活在对陌生的西班牙山脉的恐惧中,以及对前辈飞行员的某种敬畏的情感中。
这些常常在餐厅中与我们擦肩而过的老飞行员,看起来粗糙而冷漠。他们时常有点高高在上地给我们这样那样的意见。当他们其中的某一个,从阿利坎特或者卡萨布兰卡飞回来,穿着被雨淋湿的皮夹克来到我们中间时,总有一个新飞行员,会忍不住腼腆地向他询问关于旅途的一切。他们简短地回答着,向我们叙述着在空中所遭遇到的风暴。这一切的讲述对我们来说,构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世界。那是一个充满了陷阱与圈套,四处皆是悬崖的世界。狂暴的气流能将雪松连根拔起。在这个世界里,黑色的长龙守卫着山谷的入口,千万束的闪电好像花环一般覆盖着山顶。老飞行员们以他们精湛的技艺让我们敬佩。然而迟早有那么一天,这种尊敬将会变为永远的怀念。他们当中的某一个,会消失在茫茫高空中,再也无法回到我们中间。
我还记得某一次比里飞行归来的场景(比里后来丧生于克里比耶山脉)。他当时坐在我们中间,一言不发地大口吃着饭。他的肩膀好像被旅途中的辛劳挤压着,难以抬起。那是一个天气恶劣的夜晚。从航线的这一头到它的那一端,天空是腐烂的。飞行员穿越在山脉中,如同旧时帆船上被切断了绳索的大炮,在甲板的污泥上,前后左右地震动着。我看着比里,咽了口口水,然后小心地问他旅途是否顺利。比里似乎没有听见我的问题,皱着眉头,身体向面前的盘子倾斜着。当天气恶劣的时候,驾驶敞盖飞机的飞行员为了清晰地观察外部的一切,必须将身体探到挡风玻璃外。机舱外的寒风毫无遮挡地涌入双耳,久久不散。比里终于抬起了头,像是听见了我在跟他说话。他尝试着在回忆着什么,然后忽然爽朗地笑了起来。他的笑声顿时点亮了我。比里很少笑,而他短暂的笑容似乎也立即甩掉了脸上的疲倦。他并没有对自己的胜利做任何的解释,微笑散去后,就又低下头,无声地咀嚼着。在这个灰暗的小餐馆中,在一群群努力驱赶着白天疲惫的普通公务员中,这个肩膀沉重的同事却显得如此高贵。在他粗犷的外壳下,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天使如何战胜凶猛黑龙的场景。
终于有那么一个晚上,主任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简单地对我说:
“您明天出发。”
我站在那里,等待着他允许我离开的指令。一阵沉默后,他说:
“所有的相关条例,您都已经了解了吧?”
那个时期的引擎并不具备如今的安全性能。引擎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失灵,发出一阵盘碗被摔碎般的响声,是飞行员经常会遇到的事故。这种情况下,向岩石盘踞、没有任何避难所的西班牙大地举双手投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当引擎报废,飞机也无法支撑太长的时间。”但飞机坏了是可以替换的,最重要的是不能盲目飞入岩石区。因此航空公司以最严厉的惩罚,禁止飞行员在山区的云海中飞行。遭遇引擎故障的飞行员,常常会进入这一片白茫茫的海洋,然后在完全看不清楚周围的情况下,一头撞在山尖上。
这就是为什么这天晚上,一个沉重而缓慢的声音再次向我重复着相关的条例:“在西班牙,跟随着指南针的指示飞越云海,那是非常美丽而优雅的。但是……”
那个声音变得越发的缓慢:“但是请您记住,在那层云海下隐藏的,是永远的消失。”
一瞬间,这个静谧、平坦而简单的,当你从云海中浮出的那一刻探索到的世界,对我而言忽然拥有了一种完全陌生的意义。那种温柔变成了一个陷阱。我能够想象得出,在我脚下铺展的这片白色海洋,隐藏着如何致命的骗局。那里既没有属于人的喧嚣与骚动,也没有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占领它的,只有无边的、绝对的寂静。对我来说,这个白色的海洋变成了一条界线。它分隔着现实与幻境,让已知的世界与未知的一切遥遥相望,无从聚首。我猜想,一种景观本身也许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通过某一种文化、某一种文明,或者某一种职业来诠释它的时候,它才拥有属于它的内涵。就好像那些山里人,他们也一样见过白色的云海。然而他们永远不会发现,云海下那层无与伦比的幕帘。
当我走出主任办公室的时候,一种幼稚的骄傲占据了我的内心。黎明来临的那一刻,我就将载着乘客和邮件,成为飞机上的指挥者了。但是在骄傲的同时,谦卑之情依然在我心中无法挥去。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完全做好准备。西班牙是一片缺少避难所的土地。我担心如果在飞行中真的遇到严重机械障碍,我会难以找到迫降的平原。我反复查阅着地图,然而它除了一遍又一遍地将那片贫瘠的土地呈现在我面前,并没有给予我任何我需要的信息。怀揣着混杂骄傲与担忧的情绪,我决定与纪尧姆一起度过这个初航前夕的紧张夜晚。纪尧姆是我的同事,他已经在我之前飞越了这条航线。他握有打开西班牙种种秘密的钥匙。而此时我需要的,正是来自同行的经验与引领。
当我走进他家时,他微笑着对我说:
“我已经听说了,你高兴吗?”
他走到壁橱边,从里面拿出一瓶波特酒和两只杯子。然后依旧微笑着走到我身边:
“我们把这瓶酒喝了。你等着瞧,这可管用哪。”
纪尧姆一身的自信,好像那点亮整个房间的灯泡一样,挥洒得遍地都是。而正是他,在几年以后,打破了往返于安第斯山脉与南太平洋的飞行纪录。但那天晚上的他,穿着衬衫,脸上带着无比祥和的笑容,双臂交叉在胸前,站在灯光下,简洁地对我说:“无论是狂风、大雾还是下雪,当所有阻碍你飞行的因素出现的时候,你只要想一想在你之前,已经经历过这一切的同事们,然后对自己说,‘别人能成功的,我也一样能完成。’”但在他说完这些以后,我还是摊开了地图,请他好歹和我一起再看看这场旅行的飞行路线。坐在台灯下,弯着身体面对着地图,倚靠着前辈的肩膀,我仿佛又找回了中学时深夜读书的宁静一刻。
那个晚上,纪尧姆给我上的是一堂多么奇妙的地理课啊!他并未教授我关于西班牙的知识,而是试图把西班牙变成我的一个朋友。他既不跟我讨论水文地理学,也不谈当地的人口、畜牧这些问题。他不跟我讲瓜迪克斯这个城市本身,而是向我讲述它的附近,某一片田野边的三棵橙子树:“你要当心这些树,在地图上做个记号……”于是,这三棵树立即就比内达华山脉更显重要。他也对洛尔卡不感兴趣,倒是跟我讲了一大通洛尔卡附近的某一个农庄。那农场很普通,但生气蓬勃。农庄的主人,一个农夫与一个农妇,是如何经营这片被外面世界所遗忘的、一望无际的、一千五百公里之外的土地。他们栖身在山谷,如同一座灯塔的守护人。在那片星光下,这两个守护人随时做好准备,如果有什么人遇到了危险,他们就会立刻挺身救援。
我们从被淡忘的记忆和难以想象的远方中挖掘出了被地理学家忽略的细节。因为令地理学家们所感兴趣的,通常只是那条穿越各大城市的埃布罗河,他们并不关心莫特里尔西部的草地下还隐藏着另一条水流,而正是这条小溪,滋养着三十几朵野花。“你要小心这条水源,它侵蚀了用作飞机降落场地的田野……记得在地图上做一个记号。”我当然记得莫特里尔的那条小河。它看起来普通无常,在它轻微的低语中,栖息着几只青蛙。可它也并非毫无力量。那天堂般的紧急迫降场地长有青草,小溪就在这两千公里外的草丛中等待着我。只要我稍不留意,它就将把我化成一束火焰……
我还做好了与三十只绵羊斗争的准备。它们聚在山坡上,随时准备发起冲锋。“你以为这片草地空无一人,然后呼啦一声,那些绵羊就会向你冲来……”听到这个如此狡猾凶险的威胁,我报以一个惊讶的微笑。
灯光下,西班牙在我的地图上,一点一点地变成一个充满童话的国度。我在地图上做了各种十字记号,哪里充满了陷阱,哪里将会是我的避难所。农庄、三十只绵羊出没的草地、那条水流,统统被记录下来。
与纪尧姆告别后,我觉得自己有必要在这寒冷的夜色里独自行走一段。我竖起大衣的领子,带着一种莫名的热情,行走在陌生的人群中。与这些素不相识的人擦肩而过,我装满了秘密的内心无比自豪。这些“野蛮人”不认识我,而他们的烦恼、冲动,将在太阳升起的那一刻,一齐被装进邮包,由我来为他们传递。他们的希望与梦想,将会通过我的双手抵达目的地。我被厚重的大衣包裹着,在人群中迈着好似守护者一般的脚步。可是,人群是无法了解我的这份关怀 的。
人群也不会收到那些我从黑夜中得到的信息。天空中某处也许会有一场风暴,它将令我的首次飞行变得有点复杂。天上的星星一一暗去,可是人群怎么会知道这所有的一切呢?我是这个秘密中的独行者。在战斗开始以前,我已经知道了敌人的位置……
但是,当我收到那事关生死的重要命令的时候,我正站在摆放着圣诞礼物的明亮橱窗前。黑夜之中,好像世上一切财宝都陈设在那里。我面对着这一切,骄傲地品尝着置身事外的那种陶醉感。我是一个面临威胁的战士,这些在我面前闪烁着的、用来装点节日的水晶、灯罩、书本,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好像已经置身于云层中,作为飞行员,品尝着属于夜间航班的独特的苦涩滋味。
我被叫醒时是凌晨三点。我推开百叶窗,窗外下着雨,我心情沉重地穿上衣服。
半个钟头后,我坐在自己的小行李箱上。潮湿发亮的人行道上,我等待着公共汽车的出现。所有的同伴,在他们的第一次飞行前,都带着焦虑的心情经历过这样的等待。汽车终于出现在了街道的拐角处。那是一种响彻着铁轨般叮叮当当杂音的老式公车。我和还没睡醒的海关工作人员以及几个普通办事员一起,挤在汽车狭窄的座位上。车厢里充满沉闷腐朽的气味,好像布满了灰尘的行政机关里,一个暗淡的办公室,将一个男人的生活一点一点地吞蚀掉。汽车每隔五百米停一次,于是车上就又多了一个秘书,一个海关办事员,或者一个检查员。那些已经蒙蒙眬眬睡着的乘客,当新的乘客上车的时候,他们会努力打起精神,与对方打个招呼。然后,又立即被浓浓的睡意侵占了。这阴郁的老公车,就如此缓慢地行驶在图卢兹凹凸不平的石板路上。飞行员与所有的人混坐在一起,没有人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一路上路灯林列,离机场越来越近。这辆颠簸的老公车,它不过是你和我,是所有的人在变成蝴蝶飞翔在天空中以前,不得不栖息在里面的灰色虫茧。
所有的同伴,都已经经历过这样一个早晨。在谦卑地服从那令人有点恼火的检查员的同时,内心由衷地升起对西班牙和非洲邮航的责任感。也正是在这么一个早晨,三个小时后,一个敢于穿越奥斯皮塔莱特区域的闪电的飞行员诞生了。四个小时后,他会义无反顾地决定绕海飞行,或者在暴风雨、山川与大海的夹攻中,直接向阿尔科伊山脉进 攻。
所有的同伴,都曾经在图卢兹冬天灰色的天空下,挤在公车上的人群中。但也正是在这么一个早晨,一种帝王般的力量与勇气在他们身上诞生了。五个小时后,他将把属于北国冬天的雨点和雪花抛在身后,减缓引擎动力,在阿利坎特耀眼的阳光包围下,一路向着夏天降落。
老公车早已消失不见了,然而它的严厉和不舒适感一直生动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它多少象征着在飞行员的职业中,艰难却又不可或缺的铺垫。一切都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朴素和认真的方式进行着。我还记得在我正式成为飞行员的三年后,在这辆公车上,如何通过一场不超过十个句子的对话,获知同事莱克里万在飞行中丧生的消息。莱克里万是这条航线的一百个同事中的一员。就像其他人一样,在某一个白天或者是夜晚的浓雾中,他永远地退出了这个职业。
那天一样是凌晨三点。一片寂静中,坐在阴影里的主任对检查员说:
“莱克里万今天晚上没有在卡萨布兰卡降落。”
“啊!”检查员回答道。
刚刚从睡梦中醒来的检查员,努力着让自己的思绪变得清晰。为了表示关切,他继续问道:
“啊,是吗?他没能成功降落?又掉头飞回去 了?”
坐在公车最后面的主任,只是简单地回答了一句:“没有。”我们等待着下文,主任却没有再说过一个字。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所有的人都明白了,这句“没有”后面,是没有下文的,这句“没有”就是最终的判决。莱克里万没有在卡萨布兰卡降落,他也不可能再在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降落。
在我第一次起飞前的那个黎明,我与所有的人一样,经历着踏入这个职业前所必须经受的神圣洗礼。透过玻璃窗,我看着碎石子路上倒映出的路灯,感觉不踏实。路面上的水洼里,风不时地将水面吹动得涟漪起伏。我心想:“说真的,这将是我的第一次邮航飞行,我的运气真不太好……”我看着检查员:“这是不是说,天气非常糟糕?”检查员疲惫不堪地看了一眼窗外:“这个证明不了什么。”我于是问自己,判断好天气还是坏天气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昨天晚上,在谈到那些老飞行员不断灌输给我们的关于所有不好的预兆的迷信说法时,纪尧姆用他轻描淡写的微笑将它们统统否定了。可是它们还是无法阻挡地占据了我的思绪:“对那些没有掌握所有飞行线路中一山一石的人,要是碰上风暴,我真同情他……真的!我同情这些人!……”通常他们在说完这句话以后,为了显示他们的资历与优越,会习惯性地摇摇头,然后用充满可怜的眼神盯着我们看,好像是在对我们天真的热情表示无限的怜悯。
是啊,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曾经把这辆阴冷晦涩的老公车当作自己最后的栖身地?六十个?八十个?同样是被那沉默寡言的司机引领着,行驶在下着雨的黎明中。我看着自己的周围,阴影中闪动着几点光亮,香烟的火光让人的思绪停顿破碎。抽烟的是些上了年纪的公务员。他们又曾经陪伴过多少飞行员,作为他们最后的守卫者?
我不时捕捉到这些人低沉的交谈声。他们谈论着疾病、金钱,还有令人伤心的家务事。这些谈话勾勒出那堵暗淡的监狱的墙,无情地将人们关闭在里面。忽然之间,我的眼前出现了命运的脸孔。
坐在我身边的公务员,你从来都没有从这堵墙翻越出去的机会。这不是你的错。你只是用尽全力,像白蚁一样,用水泥封死了所有的光线来源,好营造内心的平静。你在那布尔乔亚的、一成不变又令人窒息的外省生活方式中,舒适地将自己就这么安顿下来。你筑起这道谦卑的墙壁,用它来抵挡狂风、海浪与星星。你不再想为那些严峻的问题而操心担忧了,因为你好不容易才摆脱了昔日沉重的生活负担。你不是生活在某一个游荡的星球上的公民,你也不会去提出没有答案的问题:你只是一个生活在图卢兹的小布尔乔维亚。在曾经还来得及做些什么的过去,从来没有人抓住过你的肩膀,对你说些什么。如今,你自己堆砌成的黏土早已经风干变硬。你身体里曾经沉睡着的那音乐家、诗人或者天文学家的心灵,再也没有人能将它唤醒了。
我不再抱怨天空中飘洒的雨点。这神奇的职业即将向我打开一扇门。两个小时以后,我眼前舞动着的,将是黑色的长龙与笼罩着山顶的蓝色闪电。我一路要阅读的,则是闪烁在天上的星星。
这就是我们在正式地成为飞行员以前,所经受的洗礼。从此以后,我们便踏上了征途。大部分的时候,旅行都平安顺遂,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我们像职业的潜水员一样,平静地潜入深不见底的大海。今天,这个海洋已经被人们掌握研究得很透彻了。飞行员、机械师、通信员不再将每一次出发当作一次探险,而是走进了一个实验室。他们遵守的,是指针上显示的各种数据,而不是窗外一片接一片的风景。机舱外的山川被黑暗笼罩着,可它们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山川,而是某种需要精确计算的看不见的力量。通信员在灯光下记录着所有的数据,机械师在地图上画着标记,而飞行员如果看到山脉位置发生改变,他本想从左边绕过去的山峰突然悄无声息地、秘密地出现在他面前,他就得纠正飞机路线。
至于地面的通信员,他们则每时每刻、一丝不苟地记录着来自同事们的消息:“零点四十分,230航道,机上一切正常。”
这就是今天全机组人员在旅途中的状态。他们或许都不觉得他们正处在某种行动中。他们离所有的坐标点都无比遥远。然而引擎的呻吟声响彻明亮的机舱,赋予这看似平凡的一切特殊的质地与意义。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在那些数据表里、无线电中、指针间,却正进行着人眼看不见的炼金术。那些神秘的手势,欲言又止的话语,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为奇迹的发生做准备。当那一刻终于来到时,飞行员也终于可以舒口气,将额头贴在窗玻璃上。黄金长于虚无中,它在中途停靠点的红绿灯下闪烁着。
我们也都经历过,离下一个停靠站只剩下两小时的时候,因为窗外某些特殊的风景,叫人突然感觉置身于一个全然陌生世界的体验。这种陌生感哪怕是在去印度的途中,我们也并没有感觉到。而在那场旅途中,当时大家连能顺利返回的期望都不抱有。
当梅尔莫兹驾驶水上飞机,第一次穿越南大西洋,在太阳即将落下之际抵达热带辐合带时,情况就是如此。他眼看着龙卷风的尾巴在自己的面前收得越来越紧,好像砌起了一堵墙一般。然后夜色慢慢地降临,将这片场景遮掩起来。一个小时以后,当梅尔莫兹钻进这片云层时,他走进了一个现实中不存在的幻想世界。
海面上,龙卷风卷起的水柱层层叠叠地堆积在一起,好像庙宇里黑色的柱子。它们支撑着阴暗风暴的拱顶,让它看上去更加壮大。透过被撕裂的顶端,某种光线洒落下来,那是柱子间闪耀着的满月。梅尔莫兹在这片荒无人烟的废墟中穿行着。从一道光束倾斜到另一道,绕过那些巨大的、怒吼着叫大海向天空翻滚过来的黑色柱子,沿着月色倾斜流淌下来的银光,继续飞行了四个小时,直到走出那座海上庙宇。眼前的场景用一种难以形容的力量震撼着他,以至于从这片热带辐合带走出来以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当时连害怕的念头都还来不及有。
我还记得那些行走在真实与幻觉边缘的时刻。来自撒哈拉的各停靠站的信息,一个晚上都是错误的。我和通信员内里犯下了严重的判断错误。当我透过浓雾的裂缝看见隐约闪烁的水面,我立即将飞行的方向往海岸边调整。因为错误的信息,我们不知道已经在公海上飞行了多久。
我们并不确定飞机还剩下足够的汽油将我们带回海岸。即使能抵达海岸,还必须找到可以着落的停靠站。然而当时,月亮正在慢慢地落下。在没有任何飞行角度信息的条件下,加上一片漆黑的天空,飞机几乎是盲目地在空中飞行着。月亮在一层苍白如雪的雾气中,像一堆木炭似的逐渐熄灭了。头顶上的天空,立即被云层遮盖了起来。我们行走在云层与雾气中,一个全无光影的空洞世界。
停靠站无法给予我们关于飞机当前所处位置的任何信息:“没有数据显示,没有数据显示。”我们的声音对他们来说好像来自四面八方,又好像无迹可寻。
就在我们已经绝望时,左前方一个闪烁的亮点,撕下了隐藏在雾气中的地平线的面具。我感觉到一种近乎狂乱的喜悦。坐在边上的内里,则唱着歌,身体朝着我倾斜过来。这点光亮并不来自某个停靠站,它应该属于某个灯塔。因为夜晚的撒哈拉,一切停靠站的灯光都是被熄灭的,像是一片死亡的土地。那光线继续闪烁着,片刻后熄灭了。我们于是朝着另一处闪着光亮的地方继续飞行。那光线仅仅在地平线上出现了几分钟的时间,就在雾气与云层之间。
只要某处有光亮,我们就抱着某种盲目的希望,一次一次地向着灯光的方向飞过去。假如那亮光持续着不熄灭,我们立即企图证明它来自某个灯塔。“前方有灯光,”内里同锡兹内罗斯站联络着,“请关闭灯塔灯光,连续三次亮灯。”锡兹内罗斯站按照内里的要求操作。可是我们面前的灯光极为耀眼,没有熄灭,闪亮得如同一颗星星。
尽管燃油正在一点一点地耗尽,我们却一次次地朝着金色的诱饵咬去,每次都以为它真的是导航灯的亮光。因为灯塔于我们来说,是停靠与生还的机会。但是很快,就又要向着下一处光亮飞行而去。
我们似乎是在这星际旅途一般的航行中迷路了。这一片难以走入的星际中,我们寻找着属于我们的那颗星球。只有它,藏着我们所熟悉的风景、朋友们的房子,以及各种温柔。
只有它,拥有我们所寻找的……我会向你们讲述,当时出现在我眼前的一幅幅画面,也许有人会觉得那很幼稚。即使是在这种极端的危险中,我们仍然有着和普通人一样的烦恼与牵挂。我当时又饿又渴。我想,如果我们能找到锡兹内罗斯停靠站,就能把飞机加满油,然后在卡萨布兰卡降落。凉爽的早晨,工作结束了!内里和我一起来到市中心,小酒馆已经开门营业了……我们两个找了一张桌子坐下来,面前摆着牛奶、咖啡和热可颂面包,嬉笑地谈论着昨天晚上的危险情景。那将是属于我和内里的来自生命的礼物。对一位年老的农妇来说,一幅简单的神的画像、一个奖章或者一串念珠,就能让她与神相会:必须用一种简单的语言向我们诉说,我们才能感受到。而我,那第一口炽热的、混合着牛奶与咖啡滋味的芬芳,就足以让我沉浸在活着的喜悦中。也正是当牛奶、咖啡与小麦在口中融合的那一刻,我能感觉到同静谧的田野、同异国的植被之间的交流,同脚下的大地神奇的相知相通。在所有的星光中,只有那么一颗,能给予我们黎明时分那顿早餐独特的温柔。
然而阻拦在我们与那陆地间的距离,却是如此难以逾越。似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财富,都聚集在一粒迷失了方向的尘埃上。内里这个天文学家,只能祈求着众多的星星,帮助他找到这粒迷路的尘埃。
他突然在纸上写下了些什么,递给我。“一切情况正常,我刚刚收到一条你难以置信的消息……”我的心狂跳着,等待他告诉我,究竟是什么消息救了我们的命。终于,我等到了来自上天的“恩赐”。
这是一条来自昨天晚上我们的出发地卡萨布兰卡的信息。飞机当时因为交接而延迟了起飞的时间,随后我们就在空中偏离了航线两千公里,迷失在云层与雾海中。这条消息代表官方,从卡萨布兰卡机场发来。“圣埃克苏佩里先生,由于您在卡萨布兰卡起飞时,旋转地靠停机库太近,我不得不向巴黎要求对您处罚。”我当时的确是将飞机靠得离停机库太近了,这位恪尽职守的先生因此而生气也是完全正常的事情。我已经在机场的办公室里,非常谦卑地听从了他一大堆的责难。而他此时的这条消息,在这片浓厚的雾气与充满威胁气息的大海中,显得如此不协调。我们手中驾驭的,是这架邮航与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正困难无比地为此搏斗着,这个男人却在这个时候,清算他对我的怨恨。我和内里完全没有因为他的消息而觉得生气或者懊恼,反而感到一阵巨大的喜悦。在这架飞机里,我们两个才是唯一的指挥者,这位先生让我意识到了这一点。他难道没发现,从坐上飞机那一刻开始,我们袖子上印着的“下士”级别,已经变成了“上尉”的头衔?他正在打扰着属于我们的梦境。当我们从大熊星飞到射手星时,当我们此时唯一关心的是背叛了我们的月亮时,他不合时宜地打扰着我们……
这个男人应该立即执行的义务,也是此刻他唯一的义务,是提供给我们正确的数据,好让我们计算不同行星之间的距离。而他提供的所有数据都是错误的。所以暂时,这颗“星球”最好还是闭嘴。内里在纸上写道:“他们有时间折腾这些蠢事情,不如动动脑子,想想怎么让我们从这片虚幻的世界走出去……”这个“他们”概括了这个地球上存在的所有的人,他们的议会、参议院、军队和皇帝们。读着这条来自某个荒唐的、自以为和我们有什么关联的人的消息,我们转向了水星的边缘。
我们被某种最奇怪的偶然拯救了:当我们不再抱有找到锡兹内罗斯停靠站的希望时,我决定垂直地向海岸线方向转,一直到燃油耗尽为止。我做好各种准备,让飞机不在海面上坠落。不幸的是,不停地在欺骗着我的灯塔,把我引到了不知道什么地方。更不幸的是,四面阻碍我们的浓雾,让我们很难平安地到达陆地。可是,我已经没有选择 了。
眼前的局势已经再清晰不过了。我忧郁地耸了耸肩膀。内里这个时候又递给我一张字条,上面的信息如果在一个小时以前传达到,也许还能救我们的命,眼下我只能无奈地耸耸肩。字条上写着:“锡兹内罗斯站找到我们目前的位置了,两百一十六,但是不能确定……”锡兹内罗斯不再是隐藏在黑暗中而无法触及的,它在我们的左边。但是,它离我们究竟有多少距离?内里和我在短暂地讨论以后,一致认为,已经来不及了。现在往锡兹内罗斯站方向飞行,我们将冒着错过陆地的可能性。内里回复着:“还剩一个小时的燃料,维持九十三方 向。”
此时航线的停靠站,却一个接着一个地醒来。阿加迪尔、卡萨布兰卡、达喀尔站,都纷纷加入与我们的对话中。所有的无线电通信站都向当地的机场做了报告,所有机场的负责人都通知了相关的工作人员。他们慢慢地走到我们身边,好像是围绕着一个重病的病人一样。那是一种无用的温情,但它至少是温暖的;那是一种枯萎的建议,但它至少是柔和的。
忽然之间,传来了图卢兹站的声音,那远在四千公里以外的航线总部。图卢兹站问道:“飞机的型号是不是F……”(具体型号数据我已经不记得了。)
“是的。”
“这样的话你们还有两小时的燃料,该型号的蓄油装置与标准型号不同。请调整方向飞往锡兹内罗斯。”
就这样,航空飞行这个特殊行业,它所苛求的一切,正在改变、丰富着这个世界。它让你领会到这一出出重复的剧目中,每一次蕴含着的不同的意义。对于乘客来说单调重复的风景,却对机组人员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地平线上堆积的云层,对掌控飞机的人来说,早已不是一幅单调的装饰画。它刺激着他们的肌肉,时时地向他们提出挑战。他们意识到这一点,观察研究着它,用一种真正的语言维系着他们之间的关系。一个又一个的山顶,离得还很远,它们的脸庞在显示着些什么?在满月的照耀下,它们是最适宜的方位坐标。但是如果飞行员盲目地在空中翱翔着,无比困难地纠正着自己的偏航,对自己所处的位置并不确定,那这些山顶就变成了危险的水雷。它将夜晚变成海洋,只要有一个尖顶露出水面,海水立即变得危机四伏。
大海亦是如此。对普通的乘客来说,从高空中望下去,波流并没有显现出多大的起伏,一簇簇的浪花也仿佛静止不动。一大片白色的浪花泡沫铺展着,展露着断裂的痕迹与纹路,如同被封在冰层中。只有机组人员才了解,这片白色浪花意味着水上迫降是不可能的。它们对飞行员来说,如同有毒的巨型花朵。
即使是一场令人愉快的旅途,飞行员也无法以一个观众的身份欣赏一路的风景。天空与大地的颜色、海面上风吹过留下的痕迹、黄昏时金色的云彩,他都不能好好观赏,这些只会引起他的沉思。他好像一个开垦土地的农民,时时要分析掌握着春天的来临,霜降的危险,下雨又会给他带来些什么。飞行员要破解那云、雾与欢乐的夜中,隐藏着的种种信息。飞机看上去是让飞行员有了安全的栖身之处,实际上身处其中,只令人面对着更严酷的来自大自然的种种问题。当飞机行走在暴风雨组成的法庭中,他所要面对的是山川、大海与风暴,这三个神灵将与他争夺手中掌控的那架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