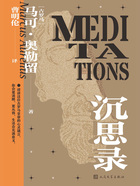
卷一
1.1 从我祖父韦鲁斯[1]那里,我学会了宽容和温良。
1.2 据人们对家父[2]的回忆和追述,我学会了正直和刚毅。
1.3 家母传我虔诚之心、慷慨之气;教我不做坏事,甚至不起恶念;还教我生活节俭,摒弃有钱人的恶习。
1.4 我曾外祖父没让我上公立学校,而是为我聘了优秀的家庭教师;老人让我懂得,在这种事上应舍得花钱。
1.5 家庭教师让我明白:观战车竞赛要保持中立立场,观角斗竞技也不要据武士轻装或重装而支持某方;要吃苦耐劳,清心寡欲;凡事要自己动手,管好自己的事;对流言蜚语要充耳不闻。
1.6 狄奥涅图斯[3]教导我,别热衷于无聊之事,要怀疑所有江湖骗子和冒牌庸医的胡吹神侃、驱邪咒语,以及诸如此类的谎言;切莫参与斗鸡走狗,莫以此类寻欢作乐为乐;要允许别人直言不讳;要亲近哲学,先听巴切修斯的扬榷,再听坦达西斯和马尔西努斯的演讲;要从年轻时就开始写随笔文章;要喜欢行军床、皮裹毯,以及希腊人训练体格品行用的其他所有器具。
1.7 因了鲁斯蒂库斯[4],我意识到自己的品格尚需修炼矫正;不要沉迷于巧言诡辩,不写没有根据的文章;不要自不量力地说教,别把自己装扮成苦行僧或慈善家;说话要避免高谈阔论、华而不实、自命不凡;别身着盛装在自己家里晃荡,要避免其他任何类似的不当言行;写信就要像他从锡纽萨[5]写给我母亲的信那样,真挚自然,不矫揉造作;对自己冒犯过的人或冒犯过自己的人,只要他们有和解的意愿,就要欣然与之和解;读书要用心领悟,融会贯通,既不要满足于一知半解,也不要轻易接受书中的浅陋之见;因他之故,我有幸读到了爱比克泰德[6]的《谈话录》,而且我读的就是他从自己藏书中推荐给我的那本。
1.8 阿波罗尼乌斯[7]让我懂得,要追求精神自由,不受命运摆布,任何时候都只能从理性的视角看待问题;要坚持始终如一,面对突如其来的痛苦也依然故我,哪怕是遭遇丧子之痛或顽疾之苦;他让我清楚地看见了活生生的范例,一个人可以刚柔并济,诲人不倦;一个人可以洞明世事,挥洒自如地讲经传道,却几乎不将这些经验和技艺视为自己的天赋;他还教会我如何去赢得朋友明显的好感,既不对他们轻易妥协,也不要漠视他们的拒斥。
1.9 从塞克斯都[8]身上,我看到了一种仁慈和善的性格,一种由父系家长做主的家庭模式,一种循自然之道生活的人生观;为人不卑不亢,待友关怀备至,对平庸无知者、言之无物者或固执己见者都很宽容;他与任何人都能怡然相处,听他闲聊比听恭维话还令人愉悦;他所到之处,人人都会向他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他善于发现并理清生活的基本原则,而且总是心中有数;他从未给人留下愤怒或大喜大悲的印象,总能把全然避免动情和人之常情巧妙地融为一体;赞美他人而不失于吹捧,自己博学而不流于炫弄。
1.10 从文法学家亚历山大[9]那里,我学会了不要吹毛求疵,或者说见别人在词法、语法或读法上犯错时不必当面纠正;不必揪着措辞本身,而要就其反映出的问题,通过回答、确证、讨论,或其他适当提醒的方法,巧妙地向人介绍某特定表达的正确形式。
1.11 弗龙托[10]让我明白,要了解独裁统治下之猜忌、伪善和反复无常所产生的影响;通常说来,我们称之为“贵族”的那些人多少都缺点人情味儿。
1.12 柏拉图主义者亚历山大[11]让我明白,若无绝对必要之理由,说话写信都要尽可能少对别人说“我太忙”;也别提前使用“情势紧迫”这种类似的借口来回避与朋友同事的礼尚往来。
1.13 从卡图卢斯[12]那里我学会了,哪怕朋友的批评可能只是无理取闹,也千万不可置之不理,而要想方设法使朋友恢复常态;要像记载中所说的多米提乌斯和雅典诺多托斯[13]那样,言及师长要满怀感恩之心,谈到孩子要满怀怜爱之情。
1.14 从塞维鲁[14]那里,我懂得了要热爱家庭,热爱真理,热爱正义;多亏他帮助,我才理解了色雷西、赫尔维乌斯、小加图、狄奥和布鲁图等反对专制暴政的英雄,才想到了要构建一种均衡政体,一种基于人人平等、言论自由的联邦政体,一种把国民之自由看得比什么都重的君主政体;也是从他那里,我学会了对哲学给予一种恒定而坚定的尊重,学会了乐善好施,慷慨大度,乐天知命;他信赖朋友的友爱之情,对他所责备者总直言不讳,所好所恶都溢于言表,所以他的朋友从不需要揣测他的心思。
1.15 从马克西穆斯[15]那里,我学会了自我克制,不为任何突发的奇想所左右;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心情愉悦,连罹病犯疾时也不例外;我还养成了沉着镇定的性格,温和而不失威严,对必行之事必任劳任怨;他让众人都相信他心口如一,所作所为都出于善意;他遇事不慌,临危不惧,既不仓促行事,亦不优柔寡断;他绝不会束手无策,绝不会自馁退缩,而在另一方面,他既不会动辄发怒,亦不会疑神疑鬼;他乐善不倦,仁慈宽容,待人真诚;他给人的印象是:其循规蹈矩与其说是出于他自己的选择,不如说是出于世事所迫;事实上,没人会在他面前觉得自己相形见绌,也没人会觉得自己比他高出一等;他也会幽默风趣,谈笑风生。
1.16 父亲[16]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温文尔雅,做决定之前都深思熟虑,拿定主意后则坚定不移;从不妄求世人所谓的尊荣;做事韧劲十足,持之以恒;乐意倾听对公众有益的任何建议;褒奖公正,凡有功者皆有其赏;张弛有度,深谙何处该紧,何处该松;他终止了青年男子同性恋的不良风气[17];还废除了朝臣时时陪他用膳的庸俗礼仪,免除了属下随同他出城的义务,而那些被解除了其他种种专责的人都无一例外地发现他对待他们的态度并无异常;开会议事他总是聚精会神,穷竭心思,既不轻信第一印象,亦不草率地搁置问题;他在意与朋友保持友谊,但从不过分偏宠友人;凡分内事务都亲自料理,且从容应对,深谋远虑,对细枝末节亦处置自如;他在位期间不允许臣民对他歌功颂德,制止了各种形式的阿谀奉承;他始终关注帝国的需要,对其资源财力均严格管理,因此而遭某些人责怪也达然容之;他不会出于迷信而畏惧诸神,不会为笼络民意以曲意取悦民众,而是清醒而稳妥地对待一切,既无纡尊媚俗之癖好,亦无好奇骛新之嗜欲。
对有助于生活舒适的用品什物(此类东西命运给了他不少),他喜而不夸,受之无愧,能享受时则坦然享受,没有之时也不觉遗憾;实际上,从不曾有人说他是欺世者、冒牌货,或书呆子,反而夸他是智慧之人、练达之士,能不为阿谀所动,能治己亦能治人。
余外,他极其敬重真正的哲人——对另一类哲学家也无恶言相向,不过能轻易将其识破;他亦善交际,风趣幽默,但不过分;他显然关心自己的身体,但既不无病忧病,过分担心健康,也决不置健康于不顾,所以,他对身体的自我关注使他很少需要就医服药。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对有一技之长者,对那些在文学创作、法律研究、赋税征收或其他方面有特殊才能者,他都给予充分尊重,都亲力亲为予以扶持,让他们在各自领域都获得应有的地位。他始终按惯例行事,但并不以因循守旧为公然目标;此外,他不好变化无常,不喜侥幸撞运,而习惯在同样的地方做同样的事情;他患有偏头痛,但发作之后又立即恢复常态,又精神矍铄地继续工作;除少数例外,他几乎没有不可言之于人的秘密,而那少数例外皆关乎国家大事;对竞技表演安排、市政工程签约,以及救济物资发放之类事情,他都能做到合理而适度——他做事只着眼于实际需要,从不在乎博取虚名。
他不爱经常去浴场[18],也不爱大兴土木;他不挑剔饮食,不讲究服装的颜色和质地,他家的奴隶也不必年轻貌美;事实上,他穿的衣服都来自拉努维乌姆的洛里姆堡[19],来自他家在乡下的那座庄园;拉努维乌姆还流传着他在那里生活时的许多故事,比如他如何作弄从图斯库鲁姆[20]上门认错的税务官员,以及诸如此类的行为细节。
他待人绝不苛刻,做事从不冲动;你永远不可能说他忙得“汗流浃背”,因为他做事就像一个闲人,凡事都由着自己的时间,依着自己的想法——他行事之道乃不慌不忙,有条有理,魄力十足,有始有终。凡对苏格拉底的记载也都适用于他;对众多意志薄弱者不肯绝弃或沉迷于其中的享受,他都能做到弃之而不以为苦,受之而绝不逾度。
此等性格力量(依情势而定的忍耐力或自制力)展现了那个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就像马克西穆斯在病中展现的那种精神[21]。
1.17 幸亏众神护佑,我有体面的祖父母、体面的父母、体面的妹妹[22]、体面的老师、体面的家庭,以及体面的亲戚朋友——几乎一切皆好;我不曾莽撞地冒犯过他们中的任何人,虽说我的性格注定若机缘凑巧就很可能冒犯他们,但感谢众神保佑,始终没给我显露那种性格的机遇。我庆幸自己由祖父那个女人养育的时间并不太长[23],这让我保住了自身清白,把对性的体验留到了适当的时期,实际上还稍稍有所延迟。我庆幸之后养育我的人具有皇帝和父亲的双重身份,他努力消除我所有的狂妄自负,让我懂得身居皇宫也可以觉得并不需要卫兵、华服、雕像、枝状大烛台,以及诸如此类的奢侈铺张;皇帝也可以纡尊降贵,让自己活得尽可能像个平民,而且并不会因此丧失尊严和权威,同样可以为公众利益而行使统治者的职权。
我庆幸自己有了个弟弟[24],他的品格总能提醒我时时检点自己,而他对我的尊敬和爱戴也让我时时感到喜悦。我庆幸自己的孩子出生时都既不痴愚也没有残疾。[25]我庆幸自己没在修辞、诗歌和其他方面有更大的进步,因要是我当时觉得那是适合我的正道,我很可能会沉溺于其中。我庆幸自己很快就把教过我的那些老师都提升到了他们所希冀的位置,而没以他们当时还年轻为由而推迟他们的委任。我庆幸自己认识了阿波罗尼乌斯、鲁斯蒂库斯和马克西穆斯。
我庆幸自己对依自然之道生活意味着什么有了清醒而始终如一的认识,故而现在谈到众神,谈到神的帮助、启示,以及来自那个世界的神灵感应,都无碍于我依自然之道生活;[26]我多少尚有不足,但这应归于我自己的过错,是我未能领悟诸神的暗谕,甚至明确的指令。
我庆幸过我这样的生活身体居然还能撑到今天。我庆幸自己未曾碰过贝内狄克塔或狄奥多图斯[27],庆幸后来的一次性经历没给我留下后患。我庆幸自己虽经常冲鲁斯蒂库斯发火,但却从没达到过让我后悔的地步。虽然我母亲未能尽享其天年,但我庆幸她在世的最后几年是在我身边度过。
我庆幸自己在想帮助那些因贫穷或其他原因需要帮助的人时,从没发现自己手边没钱;我也庆幸自己不曾陷入过需要别人用金钱帮助的境地。我庆幸自己有一个贤妻,那般柔顺,充满深情,不矫揉造作[28];我还庆幸自己的孩子们从不缺少合适的老师。
我庆幸自己从梦中得到神助,尤其是知道了如何避免大发雷霆,如何消除阵发性头晕,以及对加埃塔神谕所那道“恰如汝用自身”的神谕如何回应。我庆幸,虽然我热爱哲学,但却没撞上任何一个诡辩家,也未曾把自己的时间用来研究文学或逻辑学,或沉湎与对宇宙的猜想。这所有幸运都需要众神相助,都需要命运女神垂青。
[1] 奥勒留的祖父曾三度出任罗马执政官。
[2] 奥勒留的生父也名叫韦鲁斯(Marcus Annius Verus),他在奥勒留3岁那年(124年)早逝。
[3] 狄奥涅图斯(Diognetus),教奥勒留绘画的家庭教师。
[4] 鲁斯蒂库斯(Quintus Junius Rusticus)是一位斯多葛学派哲学家,是他让年轻的奥勒留把兴趣从修辞学转向哲学,并培养他对斯多葛学派哲学产生了兴趣。
[5] 锡纽萨(Sinuessa),罗马帝国海滨古城,其遗址在今意大利拉齐奥区和坎帕尼亚区濒海交界处。
[6] 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生活于公元前一世纪时的古罗马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奴隶出身,一生清平,其学说由其学生阿利安(Plavius Arrian)记述在《谈话录》(Discourses)和《手册》(Enchiridion)二书之中。
[7] 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一位来自博斯普鲁斯海峡东岸小城卡尔西顿(今卡德柯伊)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及职业教师,安东尼·庇护专门邀请他到罗马指导奥勒留。
[8] 塞克斯都(Sextus),来自希腊中部维奥蒂亚地区的哲学家、散文家及传记作家,普卢塔克之外甥;奥勒留成为皇帝后仍继续去听他的演讲。
[9] 此亚历山大(Alexander)乃奥勒留的家庭教师之一,来自小亚细亚的弗里吉亚,当时以研究荷马著称;著名的雅典哲学家阿里斯提得斯(Aelius Aristides,约120—约180)也曾是他的学生。
[10] 弗龙托(Marcus Cornelius Fronto,100—166),罗马著名演说家、修辞学家、语法学家,尤以演说著称,曾与加图、西塞罗和昆提利安等大贤齐名于古代讲坛;安东尼·庇护即位后即聘任他为奥勒留和卢奇乌斯·韦鲁斯的导师,惜其作品大多散佚,唯有他写给奥勒留和韦鲁斯这两位学生的一些书信存世。
[11] 此亚历山大(Alexander)系来自小亚细亚塞琉西亚的哲学家及修辞学家,曾担任奥勒留的希腊语秘书。
[12] 这位卡图卢斯(Cinna Catulus)也是个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奥勒留曾聆听过他的演说。
[13] 这位多米提乌斯(Gnaeus Domitius)可能曾教过雅典诺多托斯(Athenodotus),而雅典诺多托斯则是本卷第11节(1.11节)中提到的那位弗龙托的老师。
[14] 应该指奥勒留一位女婿的父亲克劳狄乌斯·塞维鲁(Claudius Severus),一位对政治哲学有浓厚兴趣的政治家,146年曾任罗马执政官。
[15] 马克西穆斯(Claudius Maximus),罗马政治家,斯多葛学派哲学家,曾任元老院元老、罗马执政官等职,在担任阿非利加总督时曾主持对著名作家、《金驴记》作者阿普列乌斯(Lucius Apuleius, 约124—170以后)的审判。
[16] 此处指作者的养父(亦是他姑父)、罗马皇帝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86—161;在位期138—161)。
[17] 古罗马男人同性恋风气源于希腊,共和国时期(公元前264—前31)元老院曾颁布法令禁止,但直到帝国早期此风气依然盛行,哈德良皇帝(在位期公元117—138)与美少年安提诺乌斯的同性恋故事甚至被传为佳话,迄今仍见于西方的绘画雕塑。
[18] 古罗马人酷爱去浴场沐浴,当时的浴场都修建得富丽堂皇,人们去浴场不单是为洗澡,还可以在那里商量买卖,谈论政治和解决诉讼争端等等。王政时期罗马城内浴场多达数百,有的可容上千人同时沐浴,帝国时期的大型浴场还增设了图书馆、讲演厅、竞技场、散步道、健身房和商店等设施。
[19] 拉努维乌姆(Lanuvium)即今罗马东南方约30公里外的旅游胜地拉努维奥(Lanuvio),是安东尼·庇护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洛里姆堡(Lorium)即今天的旅游景点圭多堡(Castel di Guido)。
[20] 图斯库鲁姆(Tusculum)即今罗马东南方约16公里处的山地小城图斯科洛(Tuscolo)。
[21] 参见上节(1.15节)第二分句“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心情愉悦,连罹病犯疾时也不例外”。
[22] 指作者唯一的胞妹安妮娅·福斯蒂娜(Annia Cornificia Faustina),她生于123年,于152年早逝。
[23] 生父于124年去世后,作者由祖父收养,直到138年被姑父安东尼·庇护收养。“祖父那个女人”指作者祖母死后祖父的继室。
[24] 指与作者一道被安东尼·庇护收养的卢奇乌斯·韦鲁斯(参见“作者年表”138年),他比作者小4岁。
[25] 奥勒留与妻福斯蒂娜于145年结婚后共生有14个儿女(包括两对双胞胎男婴),但大多夭折或早逝,奥勒留于180年去世时存活的儿子只有继位者康茂德(时年18岁)。
[26] 此句和本节末段中的“梦中得到神助”都说明,作为一名斯多葛派哲学家,奥勒留当时的宗教信仰已超越了传统的虔诚。
[27] 贝内狄克塔(Benedicta)和狄奥多图斯(Theodotus)可能是安东尼·庇护家的两个奴隶,当时主人与之发生性关系(不管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并非耻辱之事,反而被认为合乎常情。
[28] 但据史料记载,这个皇后不仅轻佻而且淫荡,曾把好几个奸夫推上高位;不过也有史学家对奥勒留赞美妻子给予充分理解,爱德华·吉本就说:“如果一个妻子存心耍花招,丈夫是没有不受骗的。”(参见黄宜思、黄雨石译爱德华·吉本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第81—82页,商务印书馆,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