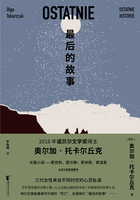
第一部 净土
1
冬日里,乡村公路上的白色标识线不再清晰可见,只有被扫到两侧的积雪为道路勾勒出粗犷而不规则的轮廓。车灯的光融化在形状模糊的路边积雪上,照出一个寂静的剧场:那里只有车轮投射在地面形成的半圆形影子不断向前滚动,仿佛所有人都在期待一个演员会从这黑暗中出现。远光灯变得无用——只能在黑暗中照出一片奶白色的冬日蒸汽,笼罩在这个世界上。
“冰冷的死人的呼吸”,开车的女人想到,“死人的呼吸”,这是矛盾修辞法,一个词推翻另一个词,凑在一起却又构成了某种意义。再过一会儿,她就会开到一个大一点的十字路口,在那儿右转,再向南开,然后在大路上一定能找到一家汽车旅馆或家庭旅店。这里有好多家庭旅店,黑暗中不断有广告牌跳出来:“免费房间”“客房”“农家乐”,涂着这些字的木板被钉在路边的篱笆或大树上。车载广播发出嘶嘶啦啦的杂音,里面夹杂着一些懒洋洋的讨论,但女人并没有在听。
突然,浓雾中有一个黑影,从道路右侧映入眼帘,在雪地中很是显眼。她小心翼翼地放慢速度,扭头看向那边——一只狗侧卧在路旁一个平缓的、覆满了雪的浅坑里。狗儿的四脚放在身前,脑袋微微抬起,仿佛躺在枕头上休息。它的前爪微微弯曲,毛茸茸的尾巴像一个散开的羽冠垂落下来。这应该不是什么名贵的品种,大概是狼狗,不过体型较小,毛色棕黑,应该是“苏台德杂种狗”,这里的人都这么叫。它看上去好像在睡觉,仿佛正在路边散步时被一阵突然袭来的困意击中——就在这儿,现在,立刻马上——支持不住立刻躺倒。所以它必须靠向一边,将路边积雪压成一个临时的窝,这个窝离那些心不在焉的汽车车轮只有一米的距离。
车灯照亮了这只路边狗,只那么一会儿工夫,揭示出了它突然睡着的秘密。然后,狗儿的秘密就又一次被淹没在黑暗之中。女人加快了速度,其实这并不必要,因为她正开始下坡。汽车在公路上漂移起来,好像浓雾中一架马上就要从巨大跑道上起飞的夜航班机。这种下坡的感觉很棒——心都提了起来,轻飘飘的,没有一点重量。女人微眯了眼睛,享受着这愉悦的时刻。
黑暗中,路的右侧突然跳出一个路标,写着“巴尔多-博什库夫”,就像一个夜间搭顺风车的人展开双臂,强迫路过的司机做出选择。左转还是右转?鱼还是熊掌?立刻做出决定!快点,就是现在。
没什么大不了,我的上帝,她想。道路笔直,方向正确,而且就像童话里写的那样,这是一条最最安全、最少障碍的路线,肯定能到达目的地。
而她马上就会走上一条坚硬的黑色柏油大路,路上撒了融雪盐,路中间有整齐的白色标识线。
下午,当她离开旅馆,绕着山谷里的盘山道下山的时候,在一个又滑又危险的急弯处被迫停了下来。那里的柏油路上撒了厚厚的融雪盐。一群奶牛挡住了去路,舔着地上的盐,看上去温和、安详又幸福:它们垂下那柔软的、毛茸茸的眼皮,将目光隐藏在漂亮的睫毛下面,慢慢地、悠闲地、不慌不忙地品尝着地上的盐。在金属般冰冷的冬日黄昏,站在道路中间的它们不再是动物。它们好像成了一种存在,在经年的冥想中越来越超脱。这时有一个人,一定是它们的主人,惊慌失措地想把它们从盐上驱赶开。他挥舞着棍子,抽打它们骨头凸出的屁股。可是它们并不害怕他的叫声,或者压根没听到。汽车已经排起了长龙,有人在队尾不耐烦地按起喇叭,而另一个人从车里下来,看到眼前发生的一切,点根烟抽了起来。“牛群舔路呢。”他向后面的司机传递着讯息。人们十分理解地接收了这个消息,对啊,为什么不呢?他们略带嘲讽地笑着,相互看向对方说道:“母牛在舔盐。”接下来,人们擦起了车窗玻璃,或者拿出手机煲电话粥,开关后备厢的咔咔声此起彼伏。过了好一阵子,动物们才清醒过来,甚至好像为自己突然不受控制的行为造成的混乱感到羞愧,于是它们迈开蹄子,一阵小碎步向山下跑去,都没等等自己的主人。
驾车的感觉舒服得就像奶牛正在舔撒了盐的柏油路。车子现在飞快地前进,正经过一个最大的洼地。女人看到一个个从雪包后面冒出来的刷了反光漆的路障,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这里有个急转弯。没有任何预兆!没有指示牌,或者指示牌被雪盖住了。她猛地向左打方向盘,可汽车根本不听话,继续向前飞驰,甚至有那么一瞬间,她觉得车已经离开了地面。她感到汽车有一股不受控制的力量,心下奇怪——她一直以为是自己在控制汽车,却从未想过,其实这些汽车所走的路、所去的方向,都被一个共同的坐标无形地牵引着。一种巧合使得这些汽车奔赴同一个方向,停在同一个加油站,可现在它们分道扬镳——她的银色小本田像滑翔机一样从高高的“起跳坡”上飞了出去,带起一片雪雾,仿佛在抗议着什么。车载收音机里正播放着新闻。女人并没看到车飞起来的样子,她更多是感觉到的。车灯照向天空,地面上的任何东西都看不到。这状态持续了挺长时间,直到小汽车开始不耐烦就这么一直飞着,毕竟这不是它的目的。她还知道,自己的头撞上了方向盘,她听到了脑袋里一种令人难受的声音,和拔牙时的那种声音一样。不过这种感觉只持续了一小会儿。
她没费多少力气就解开了安全带,径直从车里爬了出来——但是她站不起来,跪落在了雪地上。她用手背擦了下嘴唇,满是温热、黏稠的液体,她猜一定是撞击时咬到了舌头。小汽车的后轮扎进了雪地里,看起来像是要用车头去够那高处的树枝,结果是,机器由于对人类发动无理性攻击而阵亡。车灯无情地照亮了松树的树冠。车前盖大开着,发出了无声的愤怒的尖叫。车轮无力地在空中转动,越来越慢。收音机里播放着天气预报。
她拖着沉重的身体爬进车里,忍着晕眩把车钥匙拔了下来。刺眼的车灯熄灭了。四周突然陷入一片黑暗、寂静和冰冷。她觉得,这片黑暗中是无边无际的光秃秃的荒野,冷风打在她的身上,没有任何树木,哪怕是低矮灌木也能够为她遮挡。她感觉得到,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她的脸。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朝着上方的公路走去。
浓雾消散,黑夜显得澄澈而清冷,远处的星光清晰地透过天幕。女人站在勉强可见的公路上,抬头望向天空,寻找着天上的星座,就像父亲教她的那样——前面是北斗星,接着五颗距离相似的小星星延伸上去——那是北极星,紧接着则是小北斗的斗柄。“在斗柄的转弯处,你有没有看到大星星旁边有一个小星星?就像女儿靠在爸爸身边,你看到了吗?”“是的,我看到了。”“所以你可以去当兵了,”父亲说,“阿拉伯人都是用这种方法检测士兵的视力的。”
她还看到了猎户座和仙后座——那些明亮的星星排成了漂亮的几何图形,一行行大大小小按照笔直的规律重复排列,突然形成了三角形、多边形和摇摇晃晃的梯形、菱形……这还不够吗?还需要给这些漂亮的星群杜撰出各种晦涩不明的故事和传说吗?
她顺着公路边,朝着昏黄微弱的灯光走去,看到了她最喜欢的星座——后发座。那是一个由星星组成的小小的花冠,并没有什么发辫[1],充其量是一束假发辫,或者一个假发套。这个星座看起来比其他星星离地球更远,好像童年时的风筝,一不留神就飞到了高空。
拐过一个弯后,道路两侧的松林消失了,女人看到了一片城郊的灯光,起初只是星星点点,渐渐地越来越浓稠,形成了一片褐色的光芒。烟囱和一幢幢细高、老旧的楼房在这片光芒中透了出来。
当她走进第一片楼群,看到了道路两侧细长、低矮的库房。那是一些批发站,上面的招牌模糊不清,到处是坡道和宽阔的大门。她发现这里静悄悄的,没有一辆车经过,仿佛已是深夜。
一条小路从一片批发商店里伸出,拐向另外一边,朝着树林的方向。路上矗立着高高的路灯,仿佛卫士守护着街道。与其他路灯不同,它们泛着紫色的光。路上的积雪被清扫得干干净净。远处有一栋房子,窗户反射着微光。她一边琢磨着后发座,不知道贝勒尼基是谁,为什么她的发辫会跑到天上,一边不假思索地转过弯儿。当紫色路灯在她身上投下蓝紫色的光晕,她听到了那座亮着灯的房子里传出的犬吠声。于是她循声走了过去。
这房子并不是那种乡间小屋,倒更像一个被遗忘在乡野的度假别墅。房子只有两层,窄窄的,四周又搭建了一些棚子。也许起初房主打算在这儿建一溜儿房子,形成一片富人住宅区,但某些事打断了他——只留下了这么一座孤零零的房子,瑟缩在山丘和树林下面。远处一些难以辨认的低矮、破败的建筑和一些外形简单的仓库、平房、厂房正在遥遥打量着它。铁轨在这些房子中间穿过——女人两次越过铁轨,走进一片开阔的小广场——不过铁轨已经被废弃了,大雪阻隔了它们的用途和方向。只有一个个道岔和零星的信号灯,显示着白雪下一条条平行轨道的存在。那些信号灯就像一些单臂的雕塑,长久地矗立在这里,向过往行人打着招呼。
窗户里透出微弱的灯光,这正是她不喜欢的那种灯光,总令她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忧伤。灯泡高高地挂在天花板上,最多四十瓦。这简直是一种让人想要自杀的灯光。
不知从哪里跑来一只大白狗,背上有几块黑色的斑点——之前一定就是它在叫,现在倒是安静了下来——它例行公事地、仔细地闻了闻她,呼呼地喘着粗气,领着她走到了门口。女人走进黑黢黢的玄关,寻找着电灯开关,狗儿抓挠着里面的门。
“你回来了?不是才刚刚出去吗?”一个女人带着抱怨的语气说道。
灯光在地板上打出一条细细的影子,正好照在客人的脚上。
“哎哟,”她低声惊呼,“你是谁?”
女人试着挤进细窄的光线里。
“很抱歉,我走错了路,迷路了。我刚刚开车前往柯沃兹科,突然掉进沟里受了伤。我想,如果我找到人帮忙,这一切就会好起来……”
“请进吧,外面冷。”
这是一个宽敞的厨房,正中摆着一张桌子,靠墙放着一个大大的白色橱柜。一个年老的男人不情愿地从桌边站了起来。他穿着睡衣,上面套着一件条纹马甲。他的前面站着一个瘦骨嶙峋的矮小女人,穿着一件面料发光,但已洗得发白的浴袍。客人又一次前言不搭后语地讲述着自己的遭遇,说的都是一样的话:她把车扔下,掉进了沟里,开车前往柯沃兹科,美丽的夜色,最后还说到了后发座。他们看着她,面露异色——他们读不懂她的语言:忧伤?平静?还是疲倦?
矮小的妇人站在女人面前,就像一名卖票员,马上就要把入场券递给她。妇人小小的脸庞被门口的寒风吹得红通通,又或者是在厨房被通红的炉灶烤红。她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面巾纸。
“您请坐,”她说,“您的嘴上都是血。”
她轻轻地替女人擦拭着血迹,动作快速而坚定。
“您没事吧?要不要喝点茶?”她问道。
“好的,当然。茶,或者随便什么。”
男人帮她把外套脱下来,仔细地把她的围巾叠成一个方块。
“您怎么样?有没有哪里觉得疼?”
这些简单的问题,对她来说似乎复杂又难以理解。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想要说话,没想到却哭了出来。
“我撞伤了自己,车掉进了雪里。我好不容易爬了出来,然后走到了这里。我可能没什么事,看不出来我有什么事,对吧?我的胳膊腿都能动,您看!”她笑着动了动胳膊腿,像个提线木偶。
矮个子妇人端了杯水,放在她面前。水杯外侧装饰着金属花纹。他们在桌子对面坐下。
“这天气就是这样。让人迷失方向。”男人一边说,一边打量着窗户。窗玻璃上反射着那个只有四十瓦的灯泡的影子,灯泡上罩着一个白色的半圆形灯罩,看上去像个月亮。
“这冬天长得没个头。”
“明天我孙子会过来,让他给您看看。我们在楼上有房间,您就住在我们这儿吧。今天太晚了,什么也干不了。只要把电炉打开取暖就行了。”矮个子妇人一边说,一边看着丈夫。
男人披上一件厚厚的毛衣开衫,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他的脚步声在楼上响起。玻璃灯在天花板下面毫无意义地晃动着。
矮个子妇人两手交叉放在桌上,有些出人意料地高兴地说道:
“我的记性有些问题,所以如果您有什么要紧事,就和他说。”她用下巴指了指天花板。“我能记住很久以前的事情,比如战争时期的事,或者我们如何来到了这里,我甚至记得刚解放的时候面包的价钱。你知道多少钱吗,孩子?我就知道, 20个格罗什[2]。可是我记不住昨天发生的事情。这不是那个‘阿’什么症,就是大家都得的那个病。我就是老了。”
“好的,我记住了。”
老妇人从橱柜里拿出一瓶开封了的伏特加,倒了一点在女人的茶杯里。
“快喝吧,喝了就暖和了。”
老妇人接着说,“我叫奥尔加,他呢,”她看向楼上,“他叫斯特凡。”女人喝了一口热茶,想要回答;她已经张开了嘴,却突然意识到,她的脑袋里充满了冰冷的浓雾。她用手指指向自己的胸口,感受到了指头的触感。她知道应该集中精神,那样她就能想起来。思绪在翻腾、涌动,像许许多多不安的蝌蚪。一定是撞击造成的,所以她才会觉得怪异,仿佛是在睡觉,在梦游,她一定是得了脑震荡,所以思绪才如此纷乱,像冰雕一样破碎、倒塌。她知道,她马上就能想起来,只是必须集中注意力。老妇人仔细地看着她,等着她的回答。可是她很累,还在努力地整理思绪。谢天谢地,奥尔加的注意力被什么东西从那个并没有提出的问题上转移开来,她站了起来,向墙角走过去。那儿立着一个平顶的木头箱子,箱子上盖着一块深灰色的毯子,毯子上卧着一个黑色的毛茸茸的家伙。那是一只狗。它那长长的毛就像羊毛绳索,又好像又厚又乱的头发,特别是脑袋和臀部。它喘着粗气,发出低低的声音。女人和奥尔加一起俯下身去看这个黑绒球。一股酸臭味扑上脸颊。狗儿好像感觉到了她们的存在,睁开眼睛,短短地瞄了她们一眼。这目光黑黑的,难以穿透,就像深深的井底,仿佛从这个井底就能看到地下水的表面。
女人在楼梯上踉跄了几步。他们扶住了她,把她带进一个有点冷的空荡荡的房间。这里立着一个低矮的柜子,上面放着一个陶瓷半身像,是一个女孩,金色的头发用蓝色的丝带绑起来。房里还有一张铁架床和一把柳条编的破椅子,以前应该是白色的,现在已经斑驳。地板上的油漆一块一块,就像家具上长出了头皮屑。窗下,在一些打开的报纸上放着一些苹果,尽管现在已是二月底,果皮不过微微发皱。空气顺滑而湿润,就像他们的皮肤。电暖器的热度渐渐将她包裹。
他们两人还在一边说着些什么,一边打开了柜子(里面净是些陈旧的、光滑的、没有套被罩的被子),拉上窗帘,挪了挪水壶,整理了一下桌布。女人没有听他们说话。她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躺在床上,好像她是个金贵的瓷娃娃,只能平放在用来防撞的麻线团里。过了一会儿,老妇人带着浴巾和洗过的绒布睡衣走了回来。
“浴室就在楼下。”她低声地说,消失在黑暗中,和男人说着些断断续续的话,继续发出些窸窸窣窣的声音,把椅子挪来挪去,又开开关关电灯,把门锁扭来扭去。
她仰面躺着,闭上了眼睛。她应该吃一片安眠药,用耳塞把耳朵堵上,侧躺着等待安眠药发挥作用,等待着美梦慢慢从湿润静谧之中冒出芽来。可是她没有助眠胶囊,也没有耳塞。她把双手放在胸前,像平常一样,看看自己的心脏是不是还在跳动。她的身体很僵硬,对抗着手掌的压力。“硬得像木头”,她仿佛听到、看到了自己,从山上跑下来,那时她可能只有十三岁,穿着一件印花布做的连衣裙,上面满是罂粟花,那裙子后来穿烂了,妈妈拿去做了抹布,她和玩伴们在河边的废墟里相约,她们的名字她都想不起来了,是叫波热娜?还是雅佳?
有人教过姑娘们这个游戏,但是不知道是谁,一定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然后年纪大的姑娘再接着教年纪小的。周而复始,从未失传。
大家跪在地上围成一个圈,谁都不说话,就这么一直沉默着,直到所有人都觉得这很自然,很平常,直到谁都不想再开口说话。这时候每个人用手指头比画一个数字,大家一起数。数错的那个人就要躺在圈里,闭上眼睛。
接下来大家用手指尖碰这个人,一开始只是轻轻地点,然后越来越用力,并且不断重复:“硬得像木板,冷得像冰块,轻得像羽毛。”然后从头开始,直到最后这个人的身体上布满了手掌。然后大家把这个躺着的身体使劲地往土里面推,不停地说着同样的话:“像木板,像冰块,像羽毛。”然后,突然——一切都自动地再来一遍——大家发现应该继续念叨:
轻得像羽毛,
硬得像木头,
我们把你送进坟墓,
我们的睡美人。
硬得像木头,
冷得像冰块,
我们把你埋进土里,
这样就能永久冷藏。
硬得像木头,
轻得像羽毛,
你的房子,
就是那地上的一个洞。
一排小姑娘的指尖上,一个僵硬的、没有生气的、吓坏了的身体毫不费力地站了起来,就好像她是个空心的用塑料泡沫做的小人。
不,不,最好永远也别进入这个圆圈;最好自己动,而不是被别人动来动去;最好施魔法,而不是被别人的咒语控制;最好做个活人,而不是死人,哪怕是装死。万一她们中的某一个人没能从恍惚状态中醒过来,变成了僵硬的、紧闭双眼的、不死不活的好似不存在的人,那该怎么办呢?万一这个人无法从那个梦游中回来,成了其他人眼中和断了的树枝、小溪里的石头一样的物件,又该怎么办呢?不过每个人都回来了。她们坐在那儿,眨着眼睛,被远远地隔开。
那一幕挺可笑,所以其他人都笑了起来,然后游戏就这么结束了。圆圈里的那个姑娘排在最后回到村里,隐约觉得自己被耍弄了,就像剧场里被催眠师随机选中的一名观众,被拉到舞台上,被要求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她有些不高兴,动作也磨磨蹭蹭,不过当大家一起下山回到村里,一切都恢复如常,她强迫自己把一切都忘掉。
女人在这游戏中从没被轮到过成为圆圈中间的那一个,所以她不知道躺在圆圈的中间,失去重量是一种什么感觉。她把它想象成做梦,而梦很少是一样的,梦里总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而且这些事情总是脱离现实。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变得理所当然,而时间在跳跃和翻转。所以那时候的知识可能尽是些无用的。也许那时大家看到的那个圆圈里的身体,姑娘们用几根手指就能举起来的身体,看起来十分正常,一点也不违背常识。就像那个死人一样的呼吸:不可能,却有意义。她又一次感到了指尖的重量,那是一种自嘲的重量,是一种重压和轻盈同时存在的感觉。
早晨,她在某一个时刻醒来,突然就睁开了眼睛,看到了一片灰蒙蒙的天光把天花板上的裂纹和褶皱罩进一片泛着珠光的表面之中。一定还很早。
她听到了关门声和柴油机勉强发动的声音。发动机颤抖了好一会儿,然后就熄火了。这样重复了好几次,终于蹦跶起来,她松了口气,马达声也渐渐远去。
每次醒来她都听自己的心跳,看看是不是一切如常,心脏还跳不跳,怎么跳。她还会摸摸自己的身体,看看是否一夜之间就散了架。可是现在她一动不动地仰面躺着,舒服极了,甚至懒得把胳膊抬起来放到胸前。她看着天花板清一色的表面,感到很放松;双手依旧摊开放在粗粝的、上过浆的床单上。她想起来了。
她叫伊达·玛热茨。五十四岁。住在华沙的亚当·普乌戈大街89号21室。身份证号: 50012926704。赞美上帝!
门轻轻地发出吱扭声,她听到一阵细碎的脚步,就像钟表的秒针在走动。她没有睁眼,脸上感到一阵温暖的喘息。她知道,是那只白色的狗。它一定正在看着她,在她的脸颊上发出粗重的呼吸声。她没做反应,于是狗轻轻地走开了。她又躺了一会儿,慢慢意识到,自己在哪儿。她发现自己睡觉时穿着长筒袜和上衣,裙子则扔在了地板上。那是一条灰色的、厚实的羊毛裙,价格不菲,剪裁别致,又收身,又时尚。看着这条裙子,她想起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一种想法涌进她的脑袋,而她抵抗着,想把这种想法遮住,隐藏起来。
她的父母坐在房子前面。父亲正在缠绕羊毛线团,没有看她。母亲很年轻,长相和玛雅酷似,仿佛是那个长大了的、陌生的、总也不在家的玛雅。“你从不来我们这儿,我们都快把你给忘了。”妈妈不高兴地说道,生气地站起身,走进屋里。她跟在母亲后面,看着她的后背,觉得母亲似乎在躲避她。她开始在房子里走来走去,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好像那些房间形成了一个无穷无尽的、纵贯串联的恩菲拉德式建筑[3]。这时,恐惧攫住了她,因为她突然想起来,她把玛雅,她的小女儿留在了屋前。她想回去,走出这个迷宫,可是不知道怎么走。一切都变成了蓝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