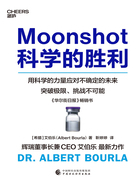
这是一个巨大的赌注
2018年,辉瑞向凯瑟琳和她的研究团队求助,希望他们能推荐一位合作伙伴,推动mRNA的研发,从而研制出一款将产生颠覆性的季节性流感疫苗。在寻找合作伙伴过程中,凯瑟琳与乌尔·萨欣成为挚友。乌尔生于土耳其,后加入德国国籍,是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来到辉瑞位于纽约珀尔里弗的疫苗研发中心,介绍了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的mRNA方案。他事后告诉我,一开始,凯瑟琳为他的团队准备了许多尖锐的问题,但最终还是被说服了。我们立刻意识到,与我们打过交道的其他公司不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对可能有效的RNA种类持不可知的态度。也就是说,他们拒绝将重心放在其中的某一种上。
这家公司起家于神秘莫测的抗肿瘤药物生产,因此会以好奇开放的心态尝试不同方法。虽然科学知识丰富,但他们也认识到了直觉的作用。由于世界观的契合,辉瑞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的团队立即达成一致,并签署了一份为期3年的研究合作协议。在此期间,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的团队将向辉瑞提供专业技术和许可证,供辉瑞开发一种新型流感疫苗。我当时是辉瑞的首席运营官,当下属将合同拿给我审批时,我立即予以批准。按照辉瑞的标准,这份合同的规模相对较小,因此我没有像处理一般大型合同那样要求与对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见面。当时我怎么也没有料到,当新冠病毒感染在两年后来袭时,我们在mRNA流感疫苗方面的研发成果,帮助辉瑞抢占了先机。
2020年1月,辉瑞的合作伙伴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加入了第一批迎战病毒的队伍,根据互联网上的数据对病毒的序列和影响进行研究。2020年1月11日,中国的科研人员公布了病毒的基因序列。这种病毒的传播方式匪夷所思,想要加以控制,更是无从谈起。尽全力研制疫苗的工作迫在眉睫,但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需要一位合作伙伴。乌尔想到了我们,鉴于在此前的合作期间建立的积极沟通和信任,他打通了凯瑟琳的电话。而在凯瑟琳接到电话之前,我已经让她和团队给出建议,指明辉瑞应该使用哪种技术平台研制疫苗。她的建议正是使用mRNA。当米凯尔通过视频电话将消息告诉我时,我大吃一惊。
“米凯尔,说实话,我真没料到会是这个答案,”我对他说,“这个赌注风险很大,难度也很高。”
我的怀疑是以事实和理性思考为依据的。首先,这项技术虽然很有前景,但尚未得到证实。如果我们能够如愿,那么这款疫苗不仅会成为首款新冠疫苗,也会成为全球首款mRNA疫苗。相比之下,通过辉瑞的研究人员更为熟悉的腺病毒和蛋白质技术平台生产疫苗,已存在多个先例。其次,辉瑞还必须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达成协议,而这个过程通常需要数月时间才能完成。我们想要迅速采取行动,而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交涉合同条款并不容易。最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规模较小,辉瑞可能要承担所有研发和生产成本,一旦失败,我们要承担巨大的损失,而一旦成功,辉瑞则必须与对方平分收益。我一一表达了我的担忧,与米凯尔一一进行了讨论。
“你确定我们应该选择这项技术?”我问道。
他十分笃定。凭借辉瑞在研制流感疫苗时积累的经验,米凯尔确信这项技术是正确的选择。
他对我说:“对于当前的情况,这项技术再合适不过了。不仅研发速度快,而且便于为更新和加强疫苗进行快速修改。腺病毒或其他病毒载体技术可能会在研制加强疫苗时遭遇困难,因为免疫系统不仅会对冠状病毒产生抗体,还会对腺病毒产生抗体。”
米凯尔从之前的讨论中了解到,我非常看重研发速度和频繁更新加强疫苗的能力。我担心,就像1918年大流感一样,到了2020年冬天,全球将面临全新且可能更加致命的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暴发。不幸的是,我的话竟一语成谶。在那个时间节点之前,我们必须研制出一款疫苗。我还知道,具有这些特征的病毒迟早会发生变异。拥有一款可在必要时随时加强而不必担心失去药效的疫苗至关重要。我逐渐理解了他的想法,但还是继续讨论下去。
“用蛋白质技术怎么样?”我问。
米凯尔说:“辉瑞的研究人员擅长蛋白质技术,当然可以利用这个平台研制疫苗,但是如果使用mRNA技术,将同时引发体液和细胞的免疫反应。如果使用蛋白质技术,人体会产生强有力的抗体,但不确定能产生T细胞。”
我们又简单探讨了生产过程中潜在的障碍以及mRNA研发计划的概况。最后,我表达了对不得不与另一方合作的担忧。米凯尔认为,凯瑟琳已经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的创始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签署合同应该不成问题。“好吧,米凯尔,”我说,“我们把团队召集起来,看看他们有什么提议吧。”米凯尔松了一口气,很欣慰我没有一开始就把这个想法否决掉,而且愿意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