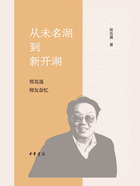
郑天挺与中华书局
郑天挺(1899—1981)先生自1930年后,即担任北京大学及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文科研究所副所长。1952年院系调整,郑先生由北大调至南开大学,任历史系主任;20世纪60年代后,任副校长。
20世纪50年代后期,金灿然先生调至中华书局,任总经理兼总编辑。他原是北大史学系1936级学生,与郑先生有师生之谊,关系甚笃。因此,郑先生遂与中华书局的关系日益密切,经常有业务往还。
郑先生与中华书局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1961年3月至1963年7月,即在北京组织及编选教育部文科教材时期;
二、1963年9月至1966年6月,点校《明史》时期;
三、“文革”以后时期。
一
1961年3月初,郑先生和南开历史系杨生茂先生前往北京参加文科教材编写会议之预备会。参加历史组会议的有翦伯赞、周一良、齐思和、邓广铭、杨向奎、黎澍、陈翰笙、白寿彝、田珏以及南开大学的郑、杨等人。会议以翦伯赞为组长,郑先生及周一良为副组长,田珏为秘书。这次会初步确定了文科教材的内容及计划安排。随后在4月中,又在北京正式召开文科教材编写会议。除原参加预备会者外,金灿然先生及全国各地学者如唐长孺、方国瑜、蒙思明、金应熙、何兹全、傅衣凌、黄云眉、韩儒林、尹达、马长寿、冉昭德等人均参加。灿然先生对当时的文风和学风是不满意的,认为当时许多文章作得不通,“三结合”实际只是学生在做,教师参加的少;教师对学生要求不严格,不敢坚持真理。今后不仅要严格要求学生,同时也应当严格要求教师。他的一席话,博得了与会老教师的共鸣。灿然先生还强调当时的一些学术问题,应当提倡争论。如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魏晋封建说”等,都不能避而不谈。同时他在会上还强调必须深入了解历史事件及典章制度,应当让学生看懂古书,了解中国几千年的变迁。因此,他对会上决定编选《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一至第八册,以及《中国史学名著选读》六册(《左传选》、《史记选》、《汉书选》、《后汉书选》、《三国志选》、《资治通鉴选》)的计划非常支持,并主动承担了这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任务。他还强调了历史系学生应具备史部目录学的知识,史学应先搞史学名著介绍等。灿然先生性格爽朗,平易近人,对一些事又心直口快,敢于议论;干起事来勇于负责,因此一些老教师多乐于和他接近。
就在这次会上,郑先生被确定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与翦伯赞合编)八册及《史学名著选读》六册,同时并负责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八分册(清代部分)。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一至第二分册的主编是北师大何兹全先生,第三分册主编是武汉大学唐长孺先生,第四分册主编是中山大学董家遵先生,第五至第七分册的主编,分别由邓广铭、韩儒林、傅衣凌三先生担任。《史学名著选读》的主编,分别由四川大学徐中舒(《左传》)、西北大学冉昭德和陈直(《汉书》)、山东大学卢振华(《史记》)、华东师大束世澂(《后汉书》)、四川大学缪钺(《三国志》)、山东大学王仲荦(《资治通鉴》)诸先生担任。会议将近结束时,中华书局等四单位还举行座谈会,征求历史组与会先生关于出版方面的意见,灿然先生也参加了。
会议开完后,为了工作方便起见,郑先生在这一两年期间,一直住在北京,负责教材方面的审稿工作,并与有关作者经常商酌问题。
郑先生对待工作从来是认真负责的。尽管当时在“帽子”满天飞,“棍子”随处见的情况下,编辑资料不无顾虑。如选帝王将相材料怕被人说是突出英雄(因而《史记》、《汉书》不选汉高祖及萧何、韩信等传),选涉及少数民族资料怕被人说是诬蔑少数民族,等等。但他既然将任务承担下来,就专心致志搞下去,其他考虑就不屑一顾了。
郑先生在此期间与其他作者互相商榷的信件是非常之多的,可惜在“文革”中许多已散失。现在我将其中一小部分抄录如下,以见其梗概。
1961年8月25日致复旦周予同先生:
顷上海寄来尊选《历史文选》清样,注释精确扼要,而解题尤见概括之审,非淹贯大师不能办此,拜服,拜服。《史通》校注之想,弟怀之四十年。性既疏惰,旧时又奔走衣食不能得善本,蹉跎无成;近已嘱杨翼骧为之。浦二田于刘书诵习尚熟,但识见太陋,且有妄改处,诚如尊论,实不足观。刘子玄书有创有因,有批判有继承,学者多赏其创而忽其所因,遂疑刘氏之前无史学,非笃论也。然刘氏于因袭前贤处,既未一一说明,非饱学如兄者莫能抉示,此则尤盼随时见教者也。
1961年9月13日致函缪钺先生:
九月二日信收到。《三国志选》注释五事,完全赞成,即请进行。
加注后篇幅增多,减选几篇固然可以减轻纸张负担,但如能维持原选篇目,或更能见陈志之全。弟所以不忍割爱于蜀先主、吴主孙权、姜维、吕蒙诸传者,一由于诸人均是三国时最重要之历史人物;一由于可以稍正读史规避帝王将相之偏。(《刘备传》可以反映入蜀前情况;《诸葛传》反映入蜀后;《姜维传》反映蜀后期;孙权可以代表东吴,《吕蒙传》可以与今日提倡读书相配合。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并不排除个别杰出人物在历史上所起作用。个别人物包括帝王将相。不是提倡而是不要规避。)但考虑甚不周全,可能是个人偏见,仍请裁定。
1962年3月15日致王仲荦:
承示《通鉴选》字数共约十二万字。党锢之祸以《后汉书选》有党锢列传,避免重复,不再选。全书选录魏孝文帝变法、隋灭陈、唐破东突厥、贞观论治、安史之乱、黄巢起义、契丹灭晋七篇,弟均赞同,至佩藻鉴。翦老现在苏州,当即送请决定。在复信前,是否即请吾兄先嘱助手按选目进行。
来教示及安史之乱可能压缩为二万字左右。果尔,不知能否将节省之两万字加选汉魏或南北朝一二段,或有叙述纂修目的之“臣光曰”。前此讨论时,或谓编年史最好用全卷抽印办法,与主题无关部分亦不删节,如某年月日“日有食之”之类,以便学生得窥史籍全貌(原定选隋唐二十卷,其理由亦在此)。当时未深入讨论,亦未作决定。吾兄必有高见,尚乞见示。吾兄感染肝炎,闻之甚念。近来已否稍痊?济南有无特殊供应?休养条件是否适宜?并盼便中见示。如需此间代为商洽,亦请不必客气。系中已为配备助手协同进行,极慰。但仍盼多加珍摄,多加休息,切请勿以增加劳累(可交助手先搞),至盼,至盼。
1962年6月23日致冉昭德、陈直先生:
拜读大著《汉书选》新稿,仰见撝谦,弥增钦佩。现拟即行付印,已送请翦老核定。承示封面标题三种形式,拟釆用第二种。以去年决定不用集体名义出书,而书局又不愿封面人名太多也。《董仲舒传》“终阳以成岁为名”,语不易解,诚如来教。然除尊释外,亦难更得他说。为学生易于了解计,或将文句再加简化。如将“但春秋到底还是用‘以生育长养为事’的阳而不是以‘主刑杀’的阴来名岁”,简化为“但春秋到底还是用阳来名岁而不是以阴名岁”,不知高明以为何如?仍候裁示,以便交印。《汉书选》说明不在手边,容取回后寄上。
1962年7月27日致董家遵先生:
隋唐五代史参考资料,闻尊处甄选已毕,略加简注即可完成,至深欣慰。现各校需用孔殷,催促颇急,尚请于八月底以前交下,以便可以克期出版。暑假伊始,助手等如有困难,即请示知,以便由此间婉商学校设法。假期本不应以工作任务麻烦各位老师,惟兄与诸位新学期开始,必有新任务。如能乘暑假之便多请几位助手完成,俟开学再设法补假,不知是一办法否?
往时傅衣凌先生盛道吾兄博学洽闻,为乡邦之最,至深倾慕,幸祈不时赐教。
郑先生在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及《史学名著选读》的同时,文科教材历史组还曾有过编写中国断代史的计划。1962年4月,历史组曾确定撰写中国断代史纲要九种,即先秦史纲要(徐中舒)、秦汉史纲要(翦伯赞)、魏晋南北朝史纲要(唐长孺)、隋唐五代史纲要(汪篯)、宋辽金史纲要(邓广铭)、元史纲要(韩儒林)、明史纲要(傅衣凌)、清史纲要(郑天挺)、民国史纲要(邵循正)等。为此,郑先生当时曾给各册主编分头写信,其中道:
此间近有编辑中国断代史计划,分九册,每册三十至三十五万字,定名为××史纲要。内容、论点及编排,全由主编者自定。九册只求衔接,不求论点一致。合之可以成为一套断代史,分之亦可以独立各成一书。期以两年半完成,一九六四年出齐。其中××史一册,咸推吾兄主编。九册分期如下……如有不妥,尤盼教正。
随后,郑先生又在是年六月廿一日致书徐中舒先生。其中道:
《先秦史纲要》一书,荷承惠允撰述,告之同仁,均深感慰。倘蒙于大著《左传选》定稿后即赐着手,尤所殷望。资料、时间、助手等,如安排须此间代为商洽,仍乞随时函示,以便请部中联系。
这项计划,虽然大多未能完成,但编写教材及中华书局各位先生的热情,是非常可贵的。
通过编选教材的作者之不断努力,以及中华书局的积极配合,在短短的几年中,《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已完成并出版古代部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八,共五册,第七册也在1966年以前付排,但原稿及校样均于十年动乱中在中华书局遗失,故未能出版;近代部分第一、第二共两册;《中国史学名著选读》之《左传选》、《汉书选》、《后汉书选》、《三国志选》、《资治通鉴选》共五册,均在“文革”前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他未及出版的书,有些也已完稿。
今天我们回忆起这段历史时,就会感到:郑先生以及金灿然先生等人,想在当时做一些事,是多么不容易呀!
二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中华书局就确定了出版“二十四史”点校本的规划,由赵守俨先生具体负责。赵先生当时不及四十岁,年轻有为,对年长学者极尊敬,故深得老先生们厚爱。

1965年春“二十四史”点校诸史家合影于颐和园,左起:罗继祖、汪绍楹、郑天挺、刘节、张维华、卢振华、卢振华夫人
南开大学历史系早已答应承担《明史》的点校工作,由郑先生主持。但由于他事情太多,很难分神专心点校。其他各史的点校情况,亦大多类似。因此中华书局乃有将各地专家集中该局、全力以赴、争取尽快完成“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之想。于是,郑先生在初步完成教材审阅工作后,乃于1963年9月底,居住在中华书局西北楼招待所,专心从事《明史》点校工作。与他一起居住并参加其他史点校的人,尚有山东大学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先生;武汉大学唐长孺、陈仲安先生;中山大学刘节先生;吉林大学罗继祖先生,以及山西教育学院王永兴先生。此外,如在北京工作的冯家昇、翁独健、傅乐焕、刘乃和、汪绍楹诸先生,亦每人各校一史,虽然不住书局,每次开会总会聚集一堂。
郑先生在中华书局居住的近三年时间,工作是紧张而愉快的。工作之余的生活是多样的:有时与诸老同至街头食豆浆;有时则于饭后漫步于公主坟畔;有时则随傅振伦先生学习八卦拳;或与诸先生互赠诗文,鉴赏字画及善本珍籍;或与家人子孙团聚,等等。近年,罗继祖先生曾回忆那段往事时写道:
毅老(郑先生字毅生)和我连屋而居,共案而食,日得数见。当时住局诸君以毅老年龄最长,因共推为祭酒。毅老体质甚健,晬面盎背;对人态度寓和蔼于严正之中,言笑不苟;谈起学问来,虚怀若谷。
公余,三五相聚闲话,有时涉及校点中问题,有时上下古今,无所不谈。唐先生好购古画,张先生好搜罗乡邦文献,他们常逛琉璃厂和宝古斋,我有时也同去,有所得,拿回来共同欣赏。毅老虽没有这种嗜好,但如遇到有关清朝掌故的东西,也特别注意。记得有一次谢刚主丈拿来一卷《宣南吟社图》,毅老即借去,想藉以考一考林则徐有没有参加宣南吟社的事。(1)
《明史》标点工作原由南开历史系林树惠、朱鼎荣、傅贵九三先生承担,继由郑先生全面复核修正。郑先生对《明史》点校工作异常细心,充分体现了老先生对整理史籍的认真负责态度。他在中华书局期间,在点校《明史》过程中,曾以札记形式写有《明史零拾》数十篇,打算《明史》点校完毕后,再整理成书。这些札记,所存已不完整。现将个别片段摘录如下,以见一斑。
《明史零拾》一:
王鸿绪两次奏进《明史稿》所言修史经过,均为王氏本人参加修《明史》之经历,后人以为《明史》始修于康熙,大误。《世祖实录》已数见修史事。
王鸿绪两次进《明史稿》,均言熊赐履先之独进史本,是《明史》尚有熊本。与王本有何异同,待考。但本纪必系单独撰成,以王氏于康熙五十三年进书只有列传,奏中言熊本在前也。
《明史零拾》五:
《明史》卷二十《神宗纪》,隆庆六年六月“罢高拱”,宜作“高拱罢”。纪文前后均无此体(页一下)。此条《史稿》不载,或雍、乾史臣所加。
万历十六年四月,“振江北、大名、开封诸府饥”(页九下)。此事《史稿》不载。语颇费解。如为诸府并列,则江北非府名;如非并列,则大名、开封不在江北。或江北诸府及大名、开封也。
《明史》不如《史稿》。万历十年五月免孔子等后裔赋役事,是其一证。《史稿》说明先师、先贤、功臣,比较易于明白。
《明史零拾》二九:
《明史稿》讳建州不讳辽东,《明史》并辽东而讳之。《史稿》纪十四,嘉靖四十二年八月乙亥,“辽东总兵官杨照”云云(二十一页下),《明史》卷十八《世宗纪》只称“总兵官杨照”(十一页下)。《史稿》记四十三年闰月己卯,“寇犯辽东”(二十二页上),《明史》则不载。待多录例以考之。
《明史零拾》三一:
影印《明熹宗实录》至七十九卷而止,即天启七年五月。其下不列卷,有七月至十二月,独缺六月。其毁似出于清人,不在冯铨也。所谓“宁锦大捷”,“奴子大挫于宁,三败于锦”,详情尽在其间,而努尔哈赤所由死也。
《崇祯本纪》记载歧异最多,两卷校记几至三百条,自然由于无实录,诸家记载不一。但由此可证关于明末私人记述,必须详细比证甄辨,以孤证立论甚危险。
《明史零拾》五二:
明代地方亦互相牵制,布政司民财,都司掌兵固矣。然而布政司只管有钱粮之田土,而土司之有实土不纳钱粮者仍归都司。都司既有军、有民、有土,患其权大又设行都司以分其势。布政与都司同治,而行都司则分治于外,亦牵制之意。当详论之。
尽管这几年中,中华书局安排了得以安心业务工作的条件,但政治气候却在不断变化,因此《明史》的点校工作,不能不受到严重干扰。什么“批判继承”的座谈会,批判“海瑞罢官”的座谈会,“清官”的座谈会,“让步政策”的座谈会,等等,纷至沓来。不准备不行,不发言更不行,发了言见了报更担心,形势真是逼人呀!就这样,郑先生在1966年6月8日离开中华书局,奉命回南开大学参加“文化大革命”。
三
“文革”后期,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标点工作又重新开始。由于南开不同意,郑先生失去了最后参加《明史》点校的机会。然而,赵守俨及王毓铨等先生仍然与郑先生不断取得联系,以期将《明史》点校工作顺利完成。郑先生也对此毫不在乎,仍然兢兢业业,认真提出一些重要建议。如在三校时,对《明史》卷二三九,关于“银定歹成”校记,郑先生建议:
原校样“银定歹成”,或加顿号作“银定、歹成”,或不加,不很一致。“银定歹成”在卷二一《神宗本纪》已见,不记如何标点,似可一查。案卷三二七《鞑靼传》,“天启三年春,银定纠众再掠西边,官军击败之。明年春,复谍入故巢……其年,歹青以领赏哗于边,边人格杀之”。歹青与银定分列,似以加顿号为宜。
又如对《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之校记,郑先生谓:
“袁崇焕字元素,东莞人。”案《崇祯实录》卷三、《国榷》卷九一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条都作“藤县人”;《明进士题名录》万历己未科也作“广西梧州府藤县民籍”,是此处东莞应作藤县。但《明史稿传》一三一《袁崇焕传》已作东莞人,清乾隆《一统志》及广东省县志均以袁崇焕列入广东广州府人物之内。三校原稿已将此条改为藤县人,建议只作校记,不改原文。
在明初官名中“参事断事官”间应不应加顿号的问题上,有人也表示拿不准。郑先生也以《明太祖实录》、《洞庭集》等书为例,认为应当断开。郑先生和其他先生一样,对《明史》点校的出版,都是认真负责的,同时也是虚心的。
1980年8月,郑先生发起的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天津召开。应邀到会的国外、国内代表共一百多人。中华书局的李侃及赵守俨先生也应邀参加。与此同时,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探微集》及《清史简述》二书。
《探微集》是郑先生的一部论文集,共收解放前后所写论文四十三篇,是在原《清史探微》的基础上扩大而成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人民出版社负责同志即劝郑先生将《清史探微》扩充出版,态度甚恳挚。并说:“论文集最重要,以此看水平。郑先生如不带头,别人更不敢写。郑先生年纪已大,如不给我们留下点东西,未免可惜。”后来中华书局赵守俨先生也屡次催促此事,并建议可分两部分出版,解放前者名曰《采微集》,解放后者名曰《求正集》。由于当时准备不及,该书未能出版。1979年以后,中华书局经与郑先生多次接洽,始行出版问世。

1979年12月《探微集》中华书局发稿单
《清史简述》原是郑先生1962年在中央党校讲课时的记录稿。当时该校负责人通过翦伯赞、金灿然等人联系,约请高等院校的一些教授,到该校讲授中国通史,郑先生担任清史部分。该校在1964年曾将此记录稿铅印数百本以为教材,并赠送作者一百本。但书印出后,“大批判”之风已至,因之外面流传甚少。中华书局认为该讲稿对有关清史的基本知识,能提纲挈领地加以介绍,因之劝由书局出版。郑先生也欣然同意。
郑先生对中华书局的出版工作是非常关心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书局决定陆续出版《清代史料笔记丛刊》时,即不时向书局有关同志介绍这方面的稀有抄本。书局同志也经常以一些抄本向郑先生征求意见,往来密切。1979年秋,郑先生撰文纪念吴晗先生,谈到了吴辑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一书。中华书局李侃先生见到此文后,立即回一信,告诉郑先生该书即由书局出版。
中华书局与郑先生的关系是密切的,郑先生对中华书局也是有感情的。郑先生去世前,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随后又制订了《古籍整理九年规划(1982—1990)》,中华书局承担了更多的而且是大部头的出版项目,任务较前更加繁重了。这是一个新的起点。1981年12月,家中收到聘请郑先生担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的聘书时,郑先生刚刚离开人间!否则他也一定会乐于对古籍整理工作,竭尽其菲薄之力的。
一九八六年八月九日完稿于天津
(原载《回忆中华书局(下)》,中华书局1987年2月版)
(1) 罗继祖:《忆郑毅老》,载《南开史学》1983年第1期,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