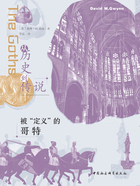
第1章 从传说到历史
公元376年夏天,两支日耳曼人[1]小部族,瑟文吉和格鲁森尼哥特人突然出现在作为罗马帝国边疆的多瑙河岸边。这些人原本生活在罗马帝国势力无法触及的环黑海北部沿岸地区,他们此行的目的不是以入侵者的身份劫掠财物,而是以难民的身份寻求庇护。
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多瑙河岸边搭起帐篷安身,与此同时,他们的头领正式向罗马帝国提出入境定居的请求。据同时代罗马历史学家马塞林[2]在《功业录》一书中的记载,这些哥特人向时任罗马帝国东部皇帝瓦伦斯[3]派出代表团,谦卑地恳求后者允许自己的族人能成为罗马帝国的子民。作为对安宁生活的回报,他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为罗马皇帝服兵役。
哥特人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来自何方?正如本书所要讲述的那样,这已经是一个持续争论了将近2000年的问题。在搜寻哥特人起源的过程中,其实很难将传说和历史明确加以区分。哥特人自己在归附罗马帝国以前,并没有留下任何文献资料,他们对自身文化的传承,采取口口相传的形式。
出自罗马人之手的其他史料,则毫无悬念地对这些威胁到帝国安全、被统称为“日耳曼人”的蛮族,采取了敌视立场。马塞林在这方面的叙述虽说相对客观,不过他能够提供的关于哥特人的信息,却很少有早于公元4世纪下半叶以前的。要想追溯哥特人归附罗马帝国以前的历史,我们能够参考的史料,主要来自一本由哥特人约达尼斯撰写的名为《哥特史》的书。
约达尼斯并非属于蛮族意义上的哥特人。他虽然对自己的哥特血统拥有强烈的自豪感,实际却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撰写过多部以古罗马为主题的著作,只可惜很多目前已经失传。
公元551年前后,约达尼斯在君士坦丁堡[4]编纂完成《哥特史》。虽然约达尼斯叙述的是瑟文吉和格鲁森尼哥特人抵达多瑙河沿岸以后,将近180年间的历史,然而他所处的时代语境,决定了他对哥特历史的讲述必然会受到同时期各种以“哥特”为主题的历史知识制约[5]。尽管如此,他留下的文本仍然为我们审视哥特人如何建构他们自身的早期历史、如何将古罗马人的文字史料与哥特人的口头历史相结合形成一套历史叙事、如何通过这套历史叙事影响了随后所有以“哥特人”及“哥特人的起源”为主题的话语生产,提供了最清晰的参照。
北方极地范围内,有一片辽阔的海,海里有座岛,名叫斯堪的纳维亚。以上帝之名,我所讲述的故事,就要从那座岛开始。你希望了解的那个族群,正如嗡嗡作响的蜂群,在这座岛上被孕育出来,随后才逐渐向欧洲内陆迁徙。
《哥特史》第1章[6]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被约达尼斯形容为孕育了多个族群的蜂巢,或者孕育了多个国家的子宫。这座岛不仅是哥特人的发源地,也是欧洲很多族群的发源地。它位于大洋的北部,正对着维斯瓦河入海口。维斯瓦河流经现在的波兰,最终汇入波罗的海。约达尼斯所说的“scandza”岛,大致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古代哥特人以这座岛为起点,开始了长途迁徙。经过在岛上的数代繁衍,他们在菲利莫首领[7]的统率下,前往欧洲南部,寻找更肥沃的土地定居。这次迁徙过程中,哥特人走到了西锡厄西部[8],大致相当于今天乌克兰境内,定居在本都海[9]附近,古罗马人称这片海为黑海。

图2 《哥特人渡河》,埃瓦利斯特·维塔勒·卢米纳伊斯(Évariste Vital Luminais),19世纪晚期,油画
哥特人在新的家园生息繁衍。他们是勇敢的战士,也是勤劳的农夫,在族长的带领下以村为单位过着集体生活。约达尼斯在《哥特史》中简略谈及了哥特人皈依基督教以前的宗教信仰。他们尊崇祖先中的英雄人物,同时还特别崇拜战神,古罗马人将这位战神称为马瑞斯。出于对战神的崇拜,哥特人将武器悬挂在大树上,以俘虏作为祭品,向战神献祭。
约达尼斯在书中暗示,早期哥特人的宗教信仰与后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流传的各种神话传说,存在某种相似性。直到今天,这样的相似性仍然能够引发人们的丰富联想。
哥特人的宗教仪式虽然存在某些野蛮的成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缺乏对哲学的研究和传授。约达尼斯认为哥特人在逻辑学、天文学和植物学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正如《哥特史》所说:
有鉴于此,哥特人比其他蛮族都要聪明,文明程度最接近希腊人。
《哥特史》第5章
《哥特史》接下来的叙述脉络便是从哥特人定居西锡厄,一直讲到约达尼斯本人生活的公元6世纪中叶,这可以说是个了不起的成就。抛开约达尼斯作为哥特人,可能会替本民族历史文过饰非的问题不谈,他对早期哥特历史的叙述存在两处重大失误。这两处失误对后世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处失误在于,他将哥特人的早期神话传说与生活在同时期同地域的其他民族,例如西锡厄人和达契亚人[10]以及其他被统称为日耳曼人的故事,混淆在了一起。产生这样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哥特人出现以后的几个世纪当中,“哥特”这个概念被无差别地用于泛指各类日耳曼蛮族。由此产生的后果,本书后文还会有详细介绍。
第二处失误在于,约达尼斯错误地将哥特人简单划分为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并认为这样的划分在哥特人归附罗马帝国以前,即生活在黑海北岸的西锡厄时便已经存在:
一部分哥特人信奉东正教,他们的国王名叫“Ostrogotha”,这些哥特人就根据国王的名字,也可能是他出生地的地名,称自己为“东哥特人”。另一部分哥特人则被称为“Visigoths”,也就是西哥特人的意思。
《哥特史》第14章
编纂《哥特史》是在公元551年前后,当时西哥特人统治着今天的西班牙,栖身意大利的东哥特人则正同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帝国,处于交战状态。隶属拜占庭阵营的约达尼斯因此想当然地认为,这种敌我划分清晰明了,且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
他的这种划分方式流传开去,后人便自然而然将瑟文吉哥特人等同于西哥特人,将格鲁森尼哥特人等同于东哥特人。同时还认为公元376年迁徙到多瑙河流域的只有西哥特人,东哥特人则留在了西锡厄。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真实的历史远比约达尼斯的叙述复杂许多。迫使哥特人归附罗马帝国的那次历史事件,同时也打破了他们既有的族群划分,新的排列组合由此逐渐生成。
尽管存在种种局限性,约达尼斯对哥特早期历史的广泛描述,仍然具有极大的说服力。例如,关于哥特人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结论,迄今为止,虽然依旧是个既无法被证实,也无法被证伪的命题;不过我们目前已经了解到的少量早期哥特部落时期的风俗习惯,却可以跟约达尼斯的叙述相互印证。
对于那些曾经生活在多瑙河和黑海以北地区的哥特人,我们已经取得了重要且可靠的考古发现。通过从罗马尼亚到乌克兰南部发掘得到的考古实物,可以证实,公元3世纪中叶到公元4世纪,有一种具有高度连续性的文明形式曾在这个地区繁荣发展。这种文明形式,现在被命名为辛塔德莫尔斯—切尔尼科夫[11]文化时期。
1900年代早期,位于特兰西瓦尼亚[12]中部的辛塔德莫尔斯,以及基辅附近的古代墓穴群陆续得到发掘。第一批被发掘的墓穴中,与辛塔德莫尔斯—切尔尼科夫文化存在关联的超过3000座。这些墓穴出现的时间,可以和公元3世纪早期哥特人控制这个区域的时间相吻合。它们能够为我们了解早期哥特社会提供宝贵的信息。
目前发现的早期哥特人定居点遗迹,大多位于河谷当中或者河谷附近,具有农耕文明的典型特征。建房的材料通常是木材和泥土,而不是石头。有时候,人的住所和蓄养牲畜的场所还会被安排在一起。他们种植的庄稼都属于常见的品种,尤其是小麦、大麦和黍子这三种。定居点遗迹中,经常出土铁制的铧犁、普通镰刀和长柄大镰刀。依据发掘到的动物骨骼可以得出结论,哥特人最喜欢蓄养的牲畜是牛,其次还包括绵羊、山羊和猪。骑马和狩猎并非哥特文化的核心内容。
众多坟墓的发掘展示了大量有关哥特人丧葬习俗的实例,他们安葬死者的方式逐渐由火葬向土葬过渡。辛塔德莫尔斯—切尔尼科夫文化时期墓葬中,数量最多的陪葬品是储物用的陶罐,做饭用的陶锅以及敞口、浅底的大碗,这种碗可能是喝酒用的。
某些被发现的陶瓷碎片上带有日耳曼如尼文字母[13],以双耳细颈瓶为代表的古罗马风格陶器也很常见。早期哥特人随葬的私人物品种类丰富,包括骨质的梳子、金属质地的胸针和扣环,有意思的是,各种形式的武器却非常罕见。陪葬品的质量,标志着每个人生前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普通人拥有的胸针和扣环等金属制品,大多为青铜质地。来自上流社会的死者,则可以使用各种白银质地的装饰品。
通过这些考古发掘获得的证据,我们可以得出宽泛却重要的结论,即生活在辛塔德莫尔斯—切尔尼科夫文化时期的哥特人,无疑是一个过着定居生活的农耕民族。多数人从事农业生产,手工业很可能主要以本地自产自销的形式存在。他们的很多村子同时都配备了制陶作坊、铁匠铺,还有服务于同村人的纺织和篾匠作坊。
早期哥特人墓穴中出土的陪葬品仍然有两个门类,也就是陶器和以青铜器、银器为代表的金属制品,体现出跨文化的特征。它们很可能是通过贸易,特别是通过跟古罗马帝国间的贸易获得的。产自古罗马的双耳细颈瓶和玻璃制品被出口到哥特人的领地,用于换取奴隶。到了公元4世纪,在当时作为古罗马帝国东部边境的多瑙河沿岸,以古罗马货币为媒介的贸易出现了大幅度的增加。
今天的我们以“辛塔德莫尔斯—切尔尼科夫文化”这个概念,来概括当时的哥特文明,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那个时代,从多瑙河以东直到黑海北部地区的广阔范围内,曾经存在过统一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体系。这个区域范围内,不同族群丰富多样的居住、丧葬和手工业文化说明他们是一个分享着某些共同文化价值观念,同时又具有广泛多样性的族群联合体,哥特人无疑在这个联合体中占据着主导力量。
辛塔德莫尔斯—切尔尼科夫文化的繁荣阶段是从公元3世纪中叶到公元4世纪晚期,其中很长一个时间段,都可以在记载古罗马与哥特交往历史的文献中找到相关记载。
很可能是在临近公元2世纪末的时候,哥特人开始向南迁徙到西锡厄,然后跟罗马帝国发生了被称为“公元3世纪危机”(third century crisis)的那场冲突。公元238年,哥特人攻陷了位于多瑙河河口的希斯特里亚[14]。双方随即开始了断断续续长达十年的战争。公元251年,这场战争最终以“阿伯里图斯战役”(the battle of Abrittus)的形式收关。哥特人在首领尼瓦(Cniva)率领下,打败了罗马军队,杀死了罗马皇帝德基乌斯[15]。这位罗马皇帝因为他的反基督教立场闻名于世,他的死因此被认为是上帝的旨意。
随后的20年当中,哥特人凭借很可能是从罗马帝国黑海北部沿岸城市劫掠来的船只,组建了海军部队,进而从水路袭击位于今天土耳其境内的比提尼亚(Bithynia)和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
公元253—268年在位的罗马皇帝伽利恩努斯(Gallienus),公元268—270年在位的伽利恩努斯二世(Gallienus Ⅱ),以及公元270—275年在位的奥勒良[16]前仆后继,陆续取得了对哥特人作战的几次胜利,将他们驱逐到了巴尔干半岛。伽利恩努斯皇帝凭借他的功绩,获得了“哥特征服者”(Gothicus)的名号。时间到了公元3世纪末,罗马帝国的边境终于恢复了稳定。不过与此同时,哥特人也在位于多瑙河以北的土地上牢牢扎住了根。

图3 公元3世纪,科韦利(Kovel)的箭头,出土于乌克兰西北部,箭头上哥特如尼文的含义可能是“目标骑手”
公元4世纪上半叶,形势有了好转,虽然偶尔爆发冲突,哥特人与罗马人之间还是维持了长期的和平状态。君士坦丁大帝[17]即位后,在公元312年成了历史上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罗马皇帝。他当上皇帝以后,随即为争夺帝国控制权,同位于东部的竞争者李锡尼[18]爆发了内战。
哥特人在这场内战中支持了李锡尼,后者被打败以后,他们因此和君士坦丁大帝发生了冲突。一支哥特人的军队在战争中被全歼,双方随后签订和平协议,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约达尼斯在《哥特史》中对这段历史只字未提,反而信口开河地说“君士坦丁大帝在哥特人的帮助下,建造了那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著名城市[19]”。
哥特人与罗马人相安无事的状态,从那以后维持了30年。直到公元360年代,哥特人再次在罗马帝国的内部纷争中,支持了战败的一方。公元364年,瓦伦斯(Valens)即位成为东罗马帝国皇帝,与此同时,他的哥哥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Ⅰ)即位成为西罗马帝国皇帝。
公元364年,瓦伦斯皇帝挫败了企图篡权的普洛科披乌斯[20],随即将矛头指向支持后者的哥特人。从公元367年到公元369年,瓦伦斯皇帝对哥特人发动了一系列战争,虽然没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却严重破坏了哥特人的商业贸易和农业生产,最终迫使他们签订新的和平协议。
历史学家马塞林明确记载,同瓦伦斯皇帝爆发战争的是瑟文吉哥特人,最终代表他们签订和平协议的是阿萨纳里克酋长(chieftain Athanaric):
一块适宜的地方被选中,用来签订和平协议。阿萨纳里克酋长声称,他曾在父亲的要求下,发过重誓,此生再不踏足罗马帝国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去罗马帝国境内参加谈判,罗马皇帝当然也不可能屈尊前往哥特人的控制范围。折中的结果是,双方隔着一条河,展开和平谈判。罗马皇帝由侍从护卫着,站在河的一边,阿萨纳里克酋长带着他的人,站在另一边。
《功业录》
最起码是在公元3世纪上半叶,哥特人与罗马人之间维持了长期的和平状态。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瑟文吉和格鲁森尼哥特人会在公元376年来到多瑙河畔,向罗马帝国寻求庇护。这些哥特人对古罗马文化并不陌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曾在罗马军队中服役。两支哥特部族的首领对强大的罗马帝国,保持着相当的敬意。他们相信,融入罗马社会可以为自己的族人带来很多好处。相应地,罗马人则将哥特人视为令人生畏的战士,希望将这些战士招入麾下为帝国的利益服务。
公元332年和公元369年签订的两次和平协议,确保了罗马人与哥特人之间维持正常的贸易和交往。考古发掘得到的证据可以说明,来自罗马的货币和手工艺品曾在辛塔德莫尔斯—切尔尼科夫文化所属区域内广泛流布。这之后的几个世纪,哥特人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四处迁徙。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断与罗马统治者发生冲突,双方紧张关系持续升级。与此同时,日后出现在高卢、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三个地方的哥特王国也在悄然成型。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公元370年代哥特人逐渐迁入罗马帝国境内以前,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就已经舍弃了祖先的宗教信仰,皈依基督教。公元250年代至公元260年代,哥特人曾横渡黑海组织远征,大量战俘沦为奴隶,这其中就包括来自比提尼亚和卡帕多西亚两地的基督徒。
被尊奉为“哥特使徒”(apostle to the Goths)的乌尔菲拉[21]大主教就是奴隶的后人,公元340年前后,他成了哥特人群体中的第一位大主教。这位大主教同时精通希腊语、拉丁语和哥特语三种语言,他以希腊字母为基础,结合拉丁文字母以及如尼文字母的特点,发明了最原始的哥特文字母,后来将《圣经》翻译为哥特文。
根据公元5世纪一位名叫菲罗斯托尔吉乌斯[22]的作者在《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一书中的记载,乌尔菲拉大主教将《圣经》除《列王纪》以外的全部内容,都翻译成了哥特文:
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列王纪》包含了太多关于战争的历史,哥特人是个好战的民族。他们需要抑制自己的嗜血冲动,而不是进一步刺激它。
哥特文《圣经》的只言片语在《新约》和《旧约》中都有所保存,其中却不包含《列王纪》的内容。
凭借自己在传播福音过程中的不懈努力,公元4世纪中叶,乌尔菲拉大主教获得普遍支持。君士坦丁大帝去世后,他先后从即位的君士坦丁二世[23],以及接替君士坦丁二世的瓦伦斯皇帝那里,获得资助。这期间,随着罗马人和哥特人间摩擦的频繁发生,某些更传统的哥特人开始将外来的基督教视为一种危险因素,乌尔菲拉大主教和他的追随者因此遭到驱逐。
即便如此,公元370年代,归附罗马帝国的瑟文吉和格鲁森尼哥特人,信仰的还是乌尔菲拉大主教传播的基督教。基督教的共同信仰就像一把“双刃剑”,帮助他们拉近了与罗马人间的距离,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问题。乌尔菲拉大主教是一位著名的“反三位一体主义者”[24],他认为圣子虽然跟圣父存在很多相似性,却不能完全等同于后者。

图4 乌尔菲拉大主教发明的哥特文字母(表)
君士坦丁二世和瓦伦斯皇帝先后即位后,这样的观点获得了东正教的支持。然而在公元4世纪末,同样的观点在罗马教会那边[25]却遭到了谴责,被视为“阿利乌异端”(Arian heresy)的重现,“阿利乌异端”这个说法源自传说中的异端,埃及牧师阿利乌[26]。哥特人因此被多数罗马人视为异教徒,与持相同信仰的其他日耳曼蛮族,例如汪达尔人是一丘之貉。这样的宗教信仰差异,将对随后由日耳曼蛮族建立的诸多王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
公元4世纪罗马人与哥特人虽然时常发生龃龉,大方向上还是维持了相对的稳定。辛塔德莫尔斯—切尔尼科夫文化遗迹表明,这个时期,黑海北部地区的哥特人社会体现出了丰富的多元性。既然如此,又是什么原因迫使瑟文吉和格鲁森尼哥特人在公元376年,踏上危险的旅程,前往多瑙河沿岸呢?
总体而言,哥特人属于农耕民族。公元376年,迁徙到多瑙河沿岸的那批难民,他们当中平民与军人的比例为4∶1或5∶1。这些人的迁徙,并非出于自愿,迫使他们背井离乡的是一群新的、可怕的敌人——匈人[27]。
就像更晚些时候的蒙古人一样,匈人是一支强大的游牧民族。他们向西横扫整个俄罗斯,侵入欧洲腹地,任何阻挡在他们马前的其他民族要么被消灭,要么被驱逐。匈人本身就是个谜,他们的起源和文化存在很大未知性。匈人没有自己的文字,历史上关于他们的记载也只是有限几个人的名字。
本书参考的关于匈人的史料,主要出自罗马人和哥特人之手,他们并不完全了解草原上的游牧生活。实际情况和以著名历史学家马塞林为代表的看法相反,游牧民族每年依据不同季节驱赶着自己的畜群,在草原上四处游走。马背上的生活赋予了匈人高度的机动性和忍耐力。与此同时,凭借特殊的制造工艺,他们的弓箭射程远,侵彻力强。
学者们原先推测,匈人和匈奴人(Hsiung NU)间存在渊源。匈奴人是一支强大的蒙古人种,游牧部落联盟,曾经和汉朝时期的中国在公元元年前后,发生过长期的战争。类似这样的想法,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历史上的匈人和中国史料中记载的匈奴,并不能完全吻合。不过,仍然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匈人是从古代传统地理意义上“东方”这个范围以外的地方迁徙而来的。
毫无疑问,匈人是古罗马帝国有史以来遭遇的最危险的草原民族。不同于类似哥特人这样传统的日耳曼蛮族,对罗马人而言,匈人更加陌生,言行也显得更加没有人性。约达尼斯在《哥特史》中记载,匈人是那些遭到早期哥特人驱逐的巫师与西锡厄旷野中的精灵相互结合的产物。即便是立场相对公允的马塞林,也没有掩饰他对匈人的偏见:
匈人身材矮小,四肢发达,脖子短促,外貌丑得异乎寻常,可以说就是一群直立行走的动物。他们的模样,就像用桥头常见的那种矮树桩随手雕刻出来的一样粗陋。
《功业录》
匈人对哥特人的冲击可以说是灾难性的。由于这段历史发生在远离罗马帝国边境的地方,我们对它的了解因此非常零散,只能借助马塞林的记载了解大致的情况。
这段历史开始在公元350年前后,匈人打败了居住在黑海东北部顿河沿岸的阿兰[28]人。与阿兰人比邻而居的瑟文吉哥特人因此受到威胁。时任瑟文吉酋长的厄门阿瑞克(Chief Ermenaric)率领族人进行了长时间的抵抗,最终却徒劳无功。据说,这位酋长最后的结局,要么是向敌人投降了,要么是独自自杀了,要么就是以自己为祭品在神面前谢罪。
他的继任者酋长维西米尔(chief Vithimir)在战斗中阵亡。瑟文吉哥特人只能就此背井离乡,向德涅斯特河[29]流域撤退。在那里,他们与阿萨纳里克酋长率领的格鲁森尼哥特人会合。正是后者在公元369年,代表两支哥特部族与瓦伦斯皇帝举行了谈判。

图5 《匈人》,阿尔封斯·德·纽维尔(Alphonse de Neuville),19世纪插图
阿塔纳里克酋长最初的打算是对匈人发动反击,却遭到族人坚决反对。最后,这些人索性舍弃了酋长自顾自地先跑到了多瑙河流域。曾经控制黑海北部地区,如今却只剩下残兵败将的瑟文吉哥特人随后也追了过去。舍弃家园的瑟文吉和格鲁森尼哥特人,由此进入了西方历史的视野范围。某些留在家乡没走的哥特人沦落到了匈人的铁蹄之下。直到公元450年代,匈人的统治土崩瓦解,这些哥特人才东山再起,建立了东哥特王国。
毋庸置疑,正是匈人的入侵,迫使瑟文吉和格鲁森尼哥特人向西迁徙,进而来到罗马帝国境内寻求庇护。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匈人当年实际并没有向多瑙河沿岸乘胜追击这两支哥特部族。据马塞林《功业录》记载,直到公元4世纪晚期,对罗马人而言,匈人仍旧属于遥远的传说。
历史上,匈人统治的核心始终维持在黑海的北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公元376年,瑟文吉和格鲁森尼哥特人来到罗马帝国边境时,实际也并未受到任何攻击。了解了这段往事,我们便可以窥见历史背后的某些隐情。当哥特人派出代表团,请求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寻求庇护时,瓦伦斯皇帝正远在叙利亚境内的安提阿,他手下的军队则主要被投放在东部地区,用于对付波斯帝国。
眼看超过10万人的男女老少主动送上门来,瓦伦斯皇帝犹豫了很长时间。就像今天的欧洲国家一样,古罗马帝国拥有漫长的吸收移民的历史。哥特人作为潜在兵员,向来非常受欢迎。然而这么多人突然涌入,毕竟是个威胁。特别是在罗马帝国东部军队的主力被投放在波斯帝国方向的前提下。顺便说一句,由于一系列悲剧性的失误和误判,这支军队在公元378年8月的亚德里亚堡之战中,遭遇了惨败。
秉持着传统的瓦解和分化策略,罗马人最初的反应是想将瑟文吉和格鲁森尼哥特人区别对待。也就是说,只允许瑟文吉哥特人使用筏子和独木舟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境内。遗憾的是,仅仅供养和控制这些瑟文吉哥特人,就当时的情况来说,也远远超出了罗马人的能力范围。
据马塞林记载,瑟文吉哥特人自从背井离乡以后,就再没获得过可以耕种的土地,某些罗马地方官员试图通过在哥特人当中人为制造饥荒,达到自己的某些目的。作为针对这种不公平待遇的回应,公元377年年初,瑟文吉哥特人在弗里提格伦酋长(chief Fritigern)的率领下,发动起义。留在多瑙河东岸的格鲁森尼哥特人趁势响应,渡河支援同族。
随后为期一年的时间里,双方连续爆发了若干场无关大局的战斗,罗马人和哥特人互不相让,互有损失。直到公元378年,罗马帝国方面做出回应,瓦伦斯皇帝来到君士坦丁堡,调集了当时所有可以调集的兵力准备出兵镇压。与此同时,瓦伦斯皇帝的侄子,后来接替瓦伦斯皇帝的兄弟瓦伦提尼安成为罗马帝国西部皇帝的格拉提安(Gratian),也率大军向东进发,赶来增援。
据说是因为嫉妒自己这位人气更高的侄子,再加上格拉提安率领的援兵因为某种原因中途出现了耽搁,得到错误情报、认为哥特起义军只有1万多人,自己手下的部队可以两个打一个的瓦伦斯皇帝,没有等援军到来,便带着自己手下的人抢先上阵了。
公元378年8月9日,瓦伦斯皇帝在亚德里亚堡附近遭遇了哥特人的大军。马塞林描述了当时的严峻情况:
蛮族的眼中喷吐着怒火,追击那些抱头鼠窜的敌人,后者的血,因恐惧而变得冰凉。有些人倒在了战场上,却根本不知道袭击来自何方,有些人死于战友的踩踏,有些人则死于战友误伤。
继续反抗已经没有意义,放下武器却也不能获得对手怜悯。地上躺满了垂死的人,这些人因难以忍受伤痛折磨而兀自呻吟。战马也不能幸免于难,到处都是它们的尸体。
黑夜降临,天上没有月亮,这场悲剧总算画上了句号,罗马人付出了惨重代价。有消息说,皇帝本人也中了一箭,当场就死了。皇帝阵亡的时候,没人看到过他,也没人在他身边,他的尸体也从未被找到,有可能是和那些普通士兵的尸体混到一起了。
《功业录》
双方在这场战役中投入兵力的具体规模,如今只能全凭想象,不过罗马人的损失应该在1万—2万人,其中包括瓦伦斯皇帝。马塞林将这场战役与公元前216年发生的坎尼[30]会战,相提并论。那场战役中,汉尼拔率领的迦太基军队,重创了罗马共和国[31]的大军。
亚德里亚堡战役的规模可能没有后者那么大,影响却更加重大且深远。虽然这场战役只是那位在战场上阵亡的罗马帝国东部皇帝,率领的罗马帝国东部军队的一次局部性惨败,它所产生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了整个罗马帝国的分崩离析,以及西罗马帝国的覆灭。
对瑟文吉和格鲁森尼哥特人来说,这场战役的胜利,起码让他们在罗马帝国的土地上暂且获得了立足之地。然而,他们的未来仍然充满未知性。无法真正安居乐业的移民们,仍然处于一种混乱状态,仍然在寻找着安全感和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这种未知性,将在未来的若干年中产生戏剧性的影响。
[1] Germanic,这个概念在古罗马时代包括东哥特、西哥特、法兰克、勃艮第、汪达尔、盎格鲁、撒克逊、诺曼等多个族群。
[2] Ammianus Marcellinus,古罗马历史学家,《功业录》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讲哥特人的历史,以及古罗马人和哥特人间的战争。
[3] Valens,弗拉维斯·埃弗利乌斯·瓦伦斯,罗马帝国后期虽然表面维持统一,内部已经存在东西分裂的趋势,出现过二帝共治甚至四帝共治的情况。瓦伦斯和时任罗马帝国皇帝的弗拉维斯·瓦伦提尼安即为共治皇帝,前者主要控制罗马帝国东部地区。
[4] Constantinople,拜占庭帝国首都,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攻克后,更名为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陷落,标志着东罗马帝国的终结。
[5] 作者这里阐述的是一个历史叙事学的命题,即历史是人为构建出来的文本,历史讲述者本身的知识结构会制约他对文本的构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6] 原书作者引用的《哥特史》原文出自英文版,中文版《哥特史》则依据德文版翻译而来,这两本书的章节划分并不完全一样。
[7] king Filimer,据《哥特史》记载,他是第5任早期哥特首领。
[8] western Scythia,古代欧洲以黑海北岸为中心的地区。
[9] the sea of Pontus,这个说法源自古希腊语,即宜人的海。
[10] Dacians,生活在今罗马尼亚的古代民族,后被古罗马人征服同化。
[11] Sîntana de Mures-Cernjachov,辛塔德莫尔斯位于今罗马尼亚境内,切尔尼科夫位于今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
[12] Transylvania,这个地方原本是个独立国家,后在1920年并入罗马尼亚。
[13] Germanic runes,北欧古代文字。
[14] Histria,位于今罗马尼亚。
[15] Decius,盖乌斯·麦西乌斯·昆图斯·德基乌斯。
[16] Aurelian,他在位期间最终解决了“公元3世纪危机”。
[17] Constanine,指君士坦丁一世。
[18] Lincinius,当时罗马帝国出现了东西南北四帝共治的情况,李锡尼是东部皇帝。
[19] 即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
[20] Procopius,公元364年,他在君士坦丁堡发动武装政变。
[21] Ulfila,即bishop Ulfilas,被认为出生在位于今土耳其东南部的卡帕多西亚。
[22] Philostorgius,生活在公元368—439年,基督教历史学家,他留下的信息非常有限,西方学者通常认为他可能只是位业余的历史研究者,成年后定居君士坦丁堡。
[23] Constantius Ⅱ,公元337—361年在位。
[24] Homoian,主流基督教认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三者是合一的,地位相同。
[25] the Roman Church,指以梵蒂冈为代表的正统天主教。
[26] Arius,公元250—336年任埃及亚历山大主教,主张圣子的地位应该次于圣父,因此被主流基督教视为异端。
[27] the Huns,这个概念在学术界存在争议,有人认为huns 指的就是中国历史上同西汉发生过长期战争的匈奴,他们战败以后,转而向西拓展势力,也有人认为欧洲人说的huns 跟中国历史上的匈奴并不能完全等同,本书作者采纳的是后一种观点。
[28] Alan,古代占据黑海东北部和西伯利亚西南部的寒温带草原游牧民族,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为奄蔡国。
[29] the river Dniester,发源于东喀尔巴阡山脉罗兹鲁契流经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两国,注入黑海。
[30] Cannae,古罗马城市,在今意大利东南部,巴列塔附近奥凡托河入亚得里亚海口处。
[31] the Raman Republic,公元前509—前27年古罗马实行共和制,没有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