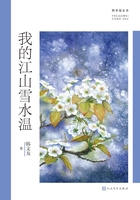
序:故土之上的家国情怀
知道“雪水温”已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这三个字一组合,很有些令人称奇。雪本来是冷物质,即使是雪水,也多近寒凉,而偏偏后边出了一个“温”字,顿时有了一种向暖而生的情愫,这简直就是诗。
那是二十多年前,在大学的写作课堂上,我从韩文友的一篇作文里看到了这三个字,雪水温是他的故乡村落的名字,地处中俄边境的嘉荫。
因为写作的共同追求,渐渐地我们成为经常交流的朋友,再后来韩文友的言谈和作品中,“雪水温”总是高频率地出现,我和许多朋友们早已是耳熟能详。这三个字与生命、文学有关,是一种人生世界鲜活充沛的诗意境界,是他散文中一个让人流连的古朴而明媚的风景。
近些年来,韩文友的文学成就渐成气候,尤其散文写作更是风生水起,他在许多报纸杂志发表散文,赢得了一大批读者的青睐,雪水温成了韩文友散文的地标性建筑。
雪水温,是韩文友生命的发源地。他出生时父母的年龄较大,在兄长和姐姐的后边他是老弟弟。虽在并不富裕的年代,由于众多亲人的呵护,韩文友在故乡雪水温度过了美好的童年。当然,这铭心刻骨的雪水温也是韩文友文学的根脉所在,是他灵魂和心性长久驻足的地方。那些温暖的记忆,质朴的乡风民俗,如委婉而清纯的泉水,从心灵流向笔端,构成了他散文情怀悠远、思想深邃的基本内核。情境优美,人物鲜活,大处着眼,小处落墨,精短的篇幅丰富透彻,从内心到外物,一丝一缕,都牵系着时代和社会的阴晴冷暖。他是用心去写散文,几乎每一笔都在动情之处。
韩文友的散文集即将出版,这是他的第一本书,可以说是他近年创作的集锦,也可以说是他文学起步以来的总结。散文集书名为《我的江山雪水温》,把故乡称谓的小天地冠之以江山社稷的大时空,其情怀的辽远、襟抱的开阔让人眼前一亮。故乡的大地,就是韩文友的江山,是他人生永远的立足之地。即使日后离开,也便有了一份不离不弃的牵挂,也要把它装在心中,那个太阳初升的地方会永远指引着后来的日子。
读韩文友的散文,几乎找不到激情澎湃的豪言壮语,没有那些大词、大话的虚妄和空洞,但他的小文章却写出了大境界。我以为,韩文友写童年、写故乡、写自然的风景、写岁月划过的痕迹,他笔下留存的都是怀念和感恩的文字,读来有一种贴心贴肺的温馨和宁静,是写到了人心里的那一种。诸多的小人物,诸多的小事件被韩文友有情有调、有滋有味地叙述出来,我们看到了雪水温的“江山”之上的家长里短和风土人情。在《像针尖》一篇中,他这样写道:
我特别怀念站在马路边大口大口嚼馒头的那些旧时光,倒不是我依然憧憬那个傻头傻脑的恋爱时代,我实在是受用那样的一种吃法,你吃得到人间的烟火,你闻得到庄稼的气息;你眼前看到的不是车水马龙,不是人头攒动,而是麦浪滚滚、金色斑斓。你的心里贪婪而富足,仿佛有无数个馒头堆在这里,云蒸霞蔚,虚无缥缈却又无比踏实,你大可以这样鬼鬼祟祟吃下去,吃下去,然后轻松自在地走到人群中去,走进你对都市的热恋中去。
当一个有些懵懂的孩子一下子从他的故乡撞进了都市,一切突如其来的变化都将冲击着生命固有的根性,作家见微知著,抓住了“嚼馒头”这种特殊时光的细节,进而呈现了一种从内心不断上升的故土情怀,他打开的不仅仅是一己之私的境遇,而是连接着时代及历史的更广阔的天地。对于故乡的感念,其中当然包含着极为复杂的体验和感受,一粥一饭所指向的是人生命运的每一个平常日子,或者说悲剧性的、苦难性的因素必然充满在经历的某些瞬间,从而留下那些或一闪而过、或刻骨铭心的记忆。韩文友的散文就是在这许多看似不经意的描述中透视出一种生命的大气象,他以一己生命之“小”去感受人生世界之“大”,见情怀见襟抱,四两拨千斤,超度了凡俗,把“馒头”和“麦浪”放在大背景之上,升华了土地、故乡,是在精神的高地上看到了未来和希望。
一个优秀的作家就是这样,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所说的“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就是要敞开一己的情怀,去接纳无限之大的世界,那么所有“小”的事物入心入眼才能“思接千载”,才能“视通万里”。韩文友的散文善于选取小人物小事件小风景小感触,但他是超越了琐碎和凡俗,把诸多看似平常的细节纳入思想烛照的灵光之中,升华为生命反思而充满悟性的“珠玉之声”和“风云之色”。其实文学的本质很大程度上是“以小见大”,着笔之处必以“小”来显现人生世界的具象之境,但仅是具象之“小”而无心性、情怀之“大”,文学就将丧失其内在的精神本色,就难以在超脱中实现一种生命深度自由的表达。韩文友的散文没有停留在记事和状物的层面上,是深思和感悟的造化之功,是借助于具象之物的心性重构。在《如果青山独自漂泊》一文中,作家有这样一些文字来表现回故乡的内在感受:
十三岁我被父亲送出去读书,在异乡漫长的夜里,我无数次想象回家路上的感觉。
许多年过去了,我仍在路上。窗外是慢慢倒去的树影,低短的灌丛,高大的杨树,枝枝叶叶连成一片浩浩荡荡的枯黄,把一条山路堵得密不透风。车窗被树丛间闪出的光线晃得斑驳刺眼。近乡情怯,曾经年少的心,如今淡如杯水。
望着身边年幼无知的儿子,我想说,我要被这里抛弃了,我快要无家可归了。泪水在我的眼窝里,但我仍不能彻头彻脑地悲哀起来。
作家笔下的这条回乡之路,是一种景物依稀、人事叠加的历史性感怀,时光流逝,此情此景所负载的是内在的、灵魂的千钧之重,而不是那种在对于世相形貌的浮泛描写中所敷衍的外在陈说。许多年的时光无情地流逝,那“慢慢倒去的树影”,以及“枝枝叶叶连成一片浩浩荡荡的枯黄”,决然构成了归属于心性的灵魂图像,这一切看似寻常的物事就被赋予了一种浑然而悠远的凝重。少小离家老大回,一条牵系人生命运的回乡之路也便浸透了岁月风雨和没有穷尽的沧桑之叹。就是这样一篇千字小文章写患病的父亲,写为父亲准备的上好的棺木,几代人在无言中体验着有关生死的切肤之痛,虽文字不多,却能在尺幅之中掀动人情和人性的大波澜。
韩文友的散文是有自己鲜明特色的,在有限的篇幅里,把自我的感悟充分地表现出来,理性显豁,但却不是那种说教式的宣讲大道理,具象,境界感十足,人情人性的汁液游刃有余地浸润开来,让人不自觉地进入一种生命的、哲学的深度中去。书中有一篇题为《水洼的那一端》是他当年读书时所写的一篇佳作,很有些史铁生叩问人生与生命终极的艺术风度。文章写的是一个小胡同下雨积下许多雨水而形成了一个水洼,一群骑单车上学的孩子踌躇着无法过去,有一个小男孩想要试一试,骑车冲了进去。结果是陷在泥水中,探路者付出了弄湿鞋子弄脏衣服的代价。但他以自己的行为提示了众多的踌躇者,此路不通,另选他路吧。我还是把此文的结尾抄在这里:
那个单车走水洼的男孩子上了岸,他低头瞅了瞅满是泥浆的裤腿,跳上车,向前去了。
我猛然发现那个渐行渐远的男孩子酷似记忆里的一个人:毛茸茸的头发,脏兮兮的裤腿……
那个人不是我么?
那个人可能是我么?
可是,我长大了。长大了的我开始时刻提醒自己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长大了的我开始在任何一个场合论证自己是多么的与众不同……
望着远去的那辆单车,我不知怎么了,仿佛虚脱一般,我不知自己要赶的路在哪儿了,半明半昧中,我听见了自己默念着:
水洼那一端的男孩子,他去哪儿了?去哪儿了?
这一段我曾在二十多年前就读过的文字深深地打动了我,这些看似其貌不扬的叙述深藏着思辨的锋芒,作家把“单车走水洼的男孩子”与“我”巧妙地重叠在一起,并顺势完成了生命与灵魂超脱的叩问,散文不经意地走进了哲学的深度。在文学创作中,其实“深度”是作家一种重要的“经营”,关系着质量成色,关系着胸襟气度,甚至关系着是非成败。只有善于经营深度,一个作家才能走得更高,走得更远。韩文友即使捡拾一些琐碎事物,也总能提升度化,把一枝一叶、一丝一缕打造得深思高举、意趣盎然。
在情感抒写方面,韩文友也是很有自己的套路,他的文章几乎每一篇读来都是情动于中,一如春风扑面。虽然不同于诗歌,但散文的情感抒写对于强化感染效果仍是不可小视的。著名诗人、散文家余光中说:“情之为物,充溢天地之间,文学的世界正是有情的世界。也正因如此,用散文来抒情,似乎人人都会,但是真正的抒情高手,或奔放,或含蓄,却不常见。一般的抒情文病在空洞和露骨,沦为滥情,许多情书、祭文、日记等等也在此列。直接抒情,不但失之露骨,而且予人无端说愁的空洞之感。真正的抒情高手往往寓情于叙事、写景、状物之中,才显得自然。”韩文友的散文可说是情感充沛,读他的文字总是被一种深情所打动,他的情感抒写不是裸露的宣示,而是那种似不经意的在写人记事中所蕴含的情感。在《一小会儿》一文的结尾,韩文友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我没有和父亲真正地拥抱过,直到他老了,老得没有了气力,直到他去世,我们生死相隔山高水远,直到他去世五年以后,在一天夜里突然回到我的梦里,紧紧地抱住了我——我从来没有主动拥抱过父亲,哪怕是一次,哪怕是一小会儿。”回环往复的怀念和忧思,真可谓情深义重,这情感的表达是在叙事中完成的,是那么自然而妥帖,具有极大的感染力。
韩文友的散文语言丰富鲜活、自由率性,就像春天的柳树枝条摇荡于风中,活泛韧性,有足够的韵致,让人眼前一亮,然后尽可回味。比如写吃包子的场面:“冒着热气的韭菜鸡蛋包子端上来了,上尖的一大盘,拿一个想咬,烫手,放下,再拿一个,还是烫,旁边是咯咯咯的一串笑声。热气腾腾的包子,让孤苦异乡的人感慨万千!”这样的叙述朴素自然,没有花哨的装饰,是写实但又不乏灵动。看似简单平常的语言,若无良好的文学天赋和多年修炼的内功,是无法游刃有余地营造出这样高质量的艺术情境的。
写人在韩文友的散文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像《花知道》《江边散步的上海夫妇》《我的老乡孙小宝》《同学少年》《王四儿》《豆腐张》等一大批散文,都是写人的,这些生动鲜活的人物构成了“雪水温”的群象,包括那些描写父亲、母亲、姐姐等亲人亲情的作品,这可以说是韩文友散文中的精品。善于写人,也是一大特色,他的文章,笔致简洁,有时三言两语即可描画出生动的人物,让人铭记于心。那篇《江边散步的上海夫妇》文笔极简,写得洁净雅致,一段特殊的人生画面或风景,很让人流连和回味。尤其结尾的一些文字就特别精彩:
上海夫妇也越来越老了。
上海夫妇的小女儿早些年就回上海了。那孩子从小看就不是农村人,不回上海干什么。村里人以为,退休后,夫妇俩是要回上海的,大城市人,在山沟里待一辈子,老了,应该回城享享福啦。
上海夫妇没有走。他们搬到村东头的一处小房子里,教一脸天真的大女儿认字。一朝春雨后,上山坡采些木耳啦、蘑菇啦、猴头啦、蕨菜啦,晒干了缝进包裹里,给小女儿寄过去。日子过得很缓慢,很田园,也很安静。
傍晚,上海夫妇依旧手挽着手,在江边散步。江风起兮,女人便把身子躲进男人的胳膊弯里,慢慢地走。
夕阳下,半江青瘦,半江红霞。他们的一生,就这样慢慢地走过来了。
这些文字在韩文友的笔下,是那么自如舒展,在一种近似黄昏的静穆中勾勒出人生与世界的和谐。文中的人物虽然如简笔画般单纯,但却以素朴宁静之美呈现了一种乡土的民风质地和生命形态。来自上海,来自大城市的人,与诸多山里特产牵手生存,大江,夕阳,以及满天红霞是命运的大背景,由此而牵系的情怀境界,也自会是天高地远。文字就是韩文友从散文的角度对于故土的深情思恋,于是他的笔下才会聚成一群生动的、可爱的小人物,就像那对上海夫妇,他们是雪水温地平线上最为亮丽的风景。
我说韩文友的散文离小说很近,他的许多写人的散文,有着小说完全可以接受的人物故事,委婉细腻,情节性不是太强,正合了当今小说“淡化”的趋向。这些写人的散文可读性很强,主要是人物的性格很鲜明,其内在的人情人性因素极充沛,入心,可以产生共鸣。如《我的老乡孙小宝》,简直把个人物写绝了,命运的遭际,老乡的关系,还有机关里的工作环境,不仅是人物活灵活现,时代的生存的大背景也是揭示得入木三分。一篇短短的小文章有如此含量,而且生动有加,真是难能可贵。像《花知道》一篇,文中所及的几个人物,老头、老太、母亲、大嫂,还有“我”,几乎都有个性,读来小说的味道很足。
除了人物故事外,韩文友的话语方式也很小说化,是讲故事的方式,面对的是一帮听众,语调温润舒缓,很入耳,能一下子抓住读者的心。这种小说化的叙述,使散文别有了一番情调,别有了一片天地。在此我抄下《豆腐张》开篇的一些内容:
豆腐张似乎与我家还有点儿亲戚。
豆腐张的吆喝声飘进屋,母亲端着豆子出来,过了秤,去了皮(盛豆的盆,不用称了,每次用的都是这个小盆),再找过点儿零碎工钱,拣了豆腐,总要说,进屋坐一会儿吧,他二姐夫。
不了,婶子,还有几家,送过去,还得回去推磨呢。
豆腐张心里是揣着把小算盘的,哪天哪天,谁家谁家是要吃豆腐的,中午吃,还是晚上吃,他都有数,送过去就完了。
这种语气和情调,就很有小说的特点,说话便进入了角色。人物的心理,举止行为,现场感比较强烈,已不是散文惯用的平铺直叙。另外行文中还饱含着口语化和民俗化特色,语言的维度更多了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散文的艺术表现疆域。或许还有负面的效应,有越界之嫌,小说和散文分不太清了。当然,对于写作者来说,不能想得太多,多谋无断,还是写出来再说吧。或者说,韩文友在小说上有着别人难以企及的优势呢。
《我的江山雪水温》即将成书,文友身为作家命我写序,只能勉其难而为之。我们相识,不知不觉几十年过去,老了,说话习惯了啰里啰嗦。故土和童年,记忆与怀想,路引沧桑,无尽的感慨便玉成了文学。韩文友真是一个幸福的人,他把少年时代舞文弄墨的爱好坚持到今日,看来是要一辈子不离不弃了。所谓江山者,安身立命之地也。“雪水温”之于韩文友,这江山更是安“心”立命之所了。故乡地处雪域山林,但有土地生长之“温”,有亲情血脉之“温”,韩文友的家国情怀的文章对己自是情深义重,对人则是意味深长。
仅以杂乱无章的文字祝贺文友,这第一本书开了路,便能步入日后的辉煌。我坚信,韩文友的超人才气和坚持努力,必将在文学的朝圣之路上修成正果。我们期待着!
邢海珍
2018年3月8日于绥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