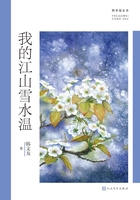
包子会记住许多事
一个包子放在面前,有资格对它的馅、它的皮、它出锅的火候说三道四的人,起码要超过三十五岁才行。
吃包子是要有心情的。刚刚参加工作的两三年,我是单位附近胡同里一家包子铺的食客。那时候,肚里没油水,又是单身,行为古怪,无处打牙祭,饭量大得可耻。那也得吃饱、吃得快乐,怎么办,便寻到了那个叫“老汤包子铺”的好吃处。
包子和单身男人实在是贴心贴胃了。牛肉萝卜,猪肉芹菜,厚皮儿,嫩馅儿,馨香不腻,沁人心脾,一样来四个,才两块钱,桌角的酱油醋,门口铁锅里的鸡蛋甩袖汤,全免费;要是赶上心情甚好,比如主管领导随便夸了那么一嘴,比如读了一篇上好的小说,比如和心仪的女同事单独在电梯里升降了一分钟,那就外加一碗小米粥、一碟咸芥菜丝、一杯本地小烧,四块钱了——有点儿奢侈了。
光棍汉的生活怎么可以这么铺张呢。
那个包子铺是一对中年夫妇经营着,男的小个,总是斜着眼神瞅着你进来,然后用油腻腻的手接过零钱,扔进门后的布袋子里;女的很干练,永远系着一个蓝花围裙,在后厨的面案上揉面、揪剂子、包馅。他们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儿,速滑运动员一样,给小屋子里的三四张桌子上包子、盛粥、递餐巾纸,白白净净,像是小铺里最水嫩的一个包子。
傍晚时分,顺着胡同昏暗的灯光,走进小铺,速滑运动员望一眼案台上大笸箩,瞅瞅我,浅浅一笑,牛肉猪肉的都凉了,今天就来几个素馅的吧,刚出锅——
冒着热气的韭菜鸡蛋包子端上来了,上尖的一大盘,拿一个想咬,烫手,放下,再拿一个,还是烫,旁边是咯咯咯的一串笑声。热气腾腾的包子,让孤苦异乡的人感慨万千!
我愿意吃的,除了母亲做的手擀面,就是大姐的包子,肥肉丁白菜馅的那种。大姐是长姐,我是排行最小的弟弟,每到假期,大姐总要把我接到他们在县城里的家,小住几日。
换洗掉我一身泥巴土的衣服和鞋,大姐转过身问我,馋什么了,说,姐给做去。
我不好意思说,我觉得我都十岁了,十岁的人了还娇里娇气地说自己馋什么吃,多不像话。
大姐看我低头错脚,不吱声,仔细猜了一下说,包包子行么,白菜肉的,嗯?
我直愣愣地瞅着大姐,脑袋已经被自己折腾得有些晕头转向了(是听见包子饿的,还是兴奋呢)。我单知道大姐快成诸葛亮了,太厉害了,一猜就猜到我的心里去了,真是神啦。
大姐家住在一个大锅炉房二楼的一间小阁楼里。姐夫是知青,返城后被分配在一家国营印刷厂里,白天黑天就一个事儿,烧锅炉,大姐在车间当捡字员。大姐是我们家第一个在城里工厂上班的人,许多年以后,无论我当记者,还是在机关工作,回家后父亲总要问我,你们厂里还那么忙么?
姐夫在小阁楼的过道里为大姐搭了个简易厨房,双头的煤气灶,啪一拧,可以炒菜,可以蒸包子,不像家里的大灶台,成年到辈子掀不出个包子来,天天馒头大 粥,抱柴续豆秸,拖拖落落,烟熏火燎。
粥,抱柴续豆秸,拖拖落落,烟熏火燎。
大姐把长头发高高地束起头,系上粉色碎花的围裙,一边哼着“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一边和我说,你写完两页作业,咱就开饭了。
我趴在小桌子上咬着铅笔根儿。我没心思写作业,我的心思在包子上,我在想,这个假期要是能多放几个月该有多好,我可以天天吃包子,我调着样儿吃,反正大姐神机妙算,会猜到我心里想吃什么馅的。
大姐在过道里喊,看一眼挂钟,大针指到“6”了么?我瞅都没瞅,过了,过了,都快到“7”啦!
——启锅了,去喊你姐夫,吃饭了。
一直以来,无论大小,再热的包子,我都愿意用手捏着或者捧着吃,我觉得这是对包子的一份敬意。
一个人对吃的都没有敬意,他还会敬畏什么呢。
我在小馆子里看过很多吃早餐的人,漫不经心地用筷子夹起一个包子,咬了一口,又放下,再去夹油条。他不配吃包子,就像我不配吃基围虾一样。
包子出锅了,冉冉升腾的白色雾霭,雾霭里有一张为你辛劳的温暖的脸,你看不清她鼻尖上的水珠,也看不清她鬓角的白发,但你能感觉到,有一双温情的目光穿过氤氲弥漫,久久注视着你,看着你吃。
在县里的一所中学读书时,我十四岁,正是干吃不长个子的时候。我的学校灰突突的,上课的教室、住宿的寝室都毫无生色,只有那个雪白墙面的食堂是亮堂堂的,令人向往。
食堂的丁大婶,有一双菩萨一样宁静的眼睛。听说她的丈夫曾是学校的音乐老师,是全县唯一一个会拉小提琴的老师,兢兢业业了二十年,但并不受重视(一个小县城的学校为什么要看重一个音乐老师呢)。一年冬天,女生寝室突然着火,围观有许多老师,没有人靠前,他冲进去了,结果和电视纪实片演的一样,最后几个学生得救了,他晕倒在里面,没出来。
学校反复研究,决定把丁大婶安置在食堂做饭。丁大婶是一个细心的人,她发现我总是拿着从家里带来的硬馒头烤饼来食堂,打一份寡淡的萝卜丝汤,找个僻静的座位,把馒头或饼泡在汤里,吃下去。
有一次,食堂里的学生很少,丁大婶来到我身后,悄悄和我说,孩子,你要是还有馒头,都拿过来,大婶每顿饭顺便给你热两个,小小年纪,总这样吃,胃就完了。
那是食堂晚饭快要结束的时间,几个同学猫一样转着圈在抢一个足球。晚霞挥洒在我对面的窗户上,像一面金色的镜子,我在镜子里面看到了一个满怀忧伤而又激动不已的孩子。
一个中午,我照例拿着饭盒去食堂。在打饭窗口里,丁大婶笑呵呵地对我说,今天不吃硬馒头了,今天吃包子,韭菜馅的,算大婶请,说着在我的饭盒子里夹满了热乎乎的大包子。我差不多连续吃了一个月的馒头就汤,看到汤里面了吧唧的馒头,我心想,我这辈子活得也太窝囊了。
端着丁大婶递过来的包子,我没有多想,坐下就吃起来。当时我很年轻,阅历太浅了,都没来得及想一想那些包子是怎么回事,会不会是丁大婶中午的份饭呢,如果不是,万一被那个暴脾气的食堂主管知道了,丁大婶如何解释呢,她会不会被扣工钱,或者失去这个来之不易的差事呢。
包子在手,整个世界就在我手里。我捧着饭盒子吃起来。天可怜见,一个包子还没吃完,我怎么也咽不下去了——虾皮,韭菜鸡蛋馅里放了虾皮!
春天的雨后,母亲在小园里割下一把韭菜,唤我去鸡窝里摸两个蛋来,我知道,又能吃到包子了。母亲绝不会在馅里放虾皮。邻居来家里尝一个后总是要说,抓一把虾皮扔里就鲜灵多了;父亲从地里骂骂咧咧回来,也要大吼,要死了,不放一把虾皮。母亲就软软地替我遮掩,没了,虾皮子没有了,下次要放点儿的。
下一次,母亲断然还是不会放的。
只是因为,我不愿意吃,或者严肃一些说,我天生吃不了虾皮。我的确无法忍受包子馅里的虾皮。这东西和韭菜鸡蛋混在一起,变熟以后,散发着一种非常荒诞的味道,我说不清这个味道是腥,是膻,还是别的什么令我难以抵抗的奸诈,这个味道和虾皮一起,紧紧地粘贴在我的上腭上,在我的嘴里、肚子里,以及我的心里,几天几夜不肯散去,让我伤心。
当年我真的很年轻,我不知道如何处理这样的意外情况,即使在吃的方面我有超乎寻常的智慧,也不知道如何应对了。我只知道我不能把手里吃了一半的包子放下。这不是普通的包子,这是天底下最热乎的包子。丁大婶在窗口笑呵呵地望着我,像望着自己的孩子放学回来吃她最拿手的饭菜。
那个深夜,整个校园静得像婴儿的梦。操场后面的一棵大槐树下,我把手指伸进嘴里,我的喉咙发出受伤野兽一样痛苦的呻吟,冰冷的泪水和黏稠的口水掺杂一起,无限美好的青春时代在一塌糊涂的吃相上,草草落幕。那个深夜,我很难过,这些难过和饥饿、和青春、和理想,没有丝毫关系——我只为那一饭盒包子,独自难过。
一个人迟早会对自己所钟爱的吃食开始一份深深的怀念。三十五岁,六十五岁,也可能是八十岁,他无意中走进一条街,一个胡同,看见一个低矮的店铺,会不由自主地停下来,顾兮盼兮,若有所思。无论年轮几何,无论尚能饭否,我希望自己念念不忘的,还是那些曾经温暖过我肠胃,爱抚过我灵魂的高贵的包子。
许多年过去,我没有离开这个城市。携家带口几次搬来搬去,鬼使神差,始终都没有远离那个“老汤包子铺”。偶尔出差回来,或工作到很晚,我总要拐进那条胡同,店铺的灯还亮着,屋子里很安静,我推门走进去,墙角的电视里播着缠绵的宫廷戏。
当年的速滑运动员坐在桌边做十字绣,《清明上河图》,还是《百福图》,看不太清楚。桌子旁边,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包子,眼睛瞥着宫廷,手里划着歪歪扭扭的字。见有人来,不耐烦地说,包子全没了,明天再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