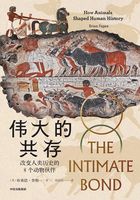
第一章 伙伴关系
24 600年前的冰期晚期,法国西南部佩赫默尔洞(Pech Merle Cave)。脂肪灯在黑暗中闪烁。灯光照亮了洞穴,黑影在凹凸的洞壁上起起伏伏,没入明亮的地面下。猎人蜷缩在潮湿的岩石上,抬头凝视对面两匹黑色斑点马。两匹马的面部各朝一方。岩石的自然形状使右边那匹头部凸显,柔和而波动无常的灯光给人一种似动非动的感觉。一个萨满轻声吟唱,从墙壁深处召唤马的力量。他手持赭色尖棍,在两匹马身上印上红色斑点,将其想象成捕猎时留下的伤口。吟唱声逐渐增强。至少有3个人,可能有男有女,走上前去,手撑着马旁边的岩石,将黑灰吹到石壁上。动物的超自然力量顺着他们的手流动,使狩猎成为正当行为。过了将近25 000年,上面的手印仍未退去。[1]
这是一种普遍的做法,在冰期的其他地方也有发生。在比利牛斯山脉的加尔加斯洞(Gargas Cave),一代代来访者——男人、女人和儿童,甚至婴儿——在洞壁上留下了他们的手印,有些印在塞满骨头碎片的缝隙旁,仅一个洞室中就有200多个。红色氧化铁或黑色锰粉使来访者的手印更加明显,好像他们的手已经融入岩石,进入超自然的世界。

佩赫默尔马
佩赫默尔位于一个有着幽深峡谷和冲积平原的地带,在最后一个冰期的鼎盛期,成群的野马在这里吃草。几代猎人在种马及其配偶的附近生活,在空旷地带,双方靠近行走也不用互相担惊受怕。他们能通过长相认识许多动物,甚至给一些动物起名。每一个季节,年轻男子都静静地潜伏在阴影里,观察动物进食或用蹄子刨开冬天的积雪寻找枯叶败草。他们见证冬夏季节动物模样的变化,观察当地马群的盛衰起伏,目睹交配过程和种马之间的激烈争斗。通过对动物的观察,猎人掌握了许多有毒植物和天然药物方面的知识。他们对这些马的了解不亚于对自己群体成员的熟悉程度,并因为马匹的精神力量始终对它们充满敬意。似乎他们已经爱上了自己的猎物。他们悄悄靠近,围拢捕杀,小心肢解杀死的猎物,尊敬的态度就像对待自己的狩猎伙伴。
这种描述肯定只是一种推测,但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判断,它肯定并非空穴来风、毫无根据。地球上没有一个狩猎社会不尊重它们的猎物。围绕各种真实或传说中的动物,澳大利亚原住民有着复杂而令人迷惑的口头传统,它们是“梦幻” 神话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种“梦幻”就是他们对大地和人类存在的无限遐想。加拿大北部森林里的克里族猎人认为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精灵(spirit),正如世间万物有灵,无论是动物、植物、岩石,甚至帐篷及其门道。[2]除了这些个体精灵(有些精灵比其他的更为重要),某些类型的自然存在,特别是一些动物,也有据说是其自身主宰的精灵属性,比如北美驯鹿或驼鹿。人类也同样如此。有些个体具有特殊的力量,比如长者,他们获得了关于动物和环境的毕生经验。有时他们拥有占卜权、知识以及促使狩猎成功的精神力量。毫无疑问,在法国和西班牙的洞穴中,冰期壁画背后的象征意义反映出人和他们猎杀的动物之间有着强大的联系。而这些联系并不构成支配关系。[值得注意的是,“animal”(动物)一词起源于拉丁语的anima,意思是“灵魂”。]
神话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种“梦幻”就是他们对大地和人类存在的无限遐想。加拿大北部森林里的克里族猎人认为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精灵(spirit),正如世间万物有灵,无论是动物、植物、岩石,甚至帐篷及其门道。[2]除了这些个体精灵(有些精灵比其他的更为重要),某些类型的自然存在,特别是一些动物,也有据说是其自身主宰的精灵属性,比如北美驯鹿或驼鹿。人类也同样如此。有些个体具有特殊的力量,比如长者,他们获得了关于动物和环境的毕生经验。有时他们拥有占卜权、知识以及促使狩猎成功的精神力量。毫无疑问,在法国和西班牙的洞穴中,冰期壁画背后的象征意义反映出人和他们猎杀的动物之间有着强大的联系。而这些联系并不构成支配关系。[值得注意的是,“animal”(动物)一词起源于拉丁语的anima,意思是“灵魂”。]
平衡、参与和尊重
冰期晚期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并不是围绕大规模杀戮展开的,而是以个人狩猎为基调。捕捉落单的鹿、诱捕北极松鸡、网捕野兔或围猎野马——所有这些都是这种生活的构件和片段,与引人注目又常常令人畏惧的动物世界近在咫尺。猎人们与动物杂居,每天目睹它们的生活,对彼此间的关系了如指掌。他们与自己的猎物一起生活,彼此亲密无间,这对我们来说难以理解。它们不只是可以被连发步枪或弓弩屠杀的生灵,还是有着自我习性和鲜明特征的生命个体,它们往往结成小群,连续几个月在附近徘徊。但是,这与我们今天对野生动物的态度有着怎样的反差呢?4 000多年前的《创世记》表达了西方社会的世界观:“神……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3]
《创世记》让我们深信,我们人类控制着地球以及在地球上生活的所有动物。自然界是一种不同的存在。人类把自己置于环境、动物和植物之外,并控制着它们的命运。这是现代自然保护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也就是提倡“原始荒野,人类不得入内”。人类学家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的说法令人印象深刻:“这就像把一个‘请勿触摸’的提示牌挂在博物馆展品前:只可远观,请勿靠近。”[4]我们培养了一种与荒野分离的深刻意识,一种“请勿干涉”综合征。然而通过对洞穴壁画和澳大利亚现有猎人的研究,我们发现这种“不干涉”完全不符合我们了解到的传统狩猎生活方式。传统社会在对待动物时,保持着活跃、亲密和尊敬的态度。
在过去一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里,通过对世界上许多地区现有猎人和采集者的研究,我们认识到自然环境并不是任由我们索取食物的被动存在。它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充满各种各样的力量。人们如果想要生存,就必须和这些力量建立联系,无论它们是动物、植物还是矿物——就像他们必须和同类中的其他人建立关系那样。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以体恤之心对待山川大地及其中的动物和植物。这就涉及截然不同的做法。成功的狩猎仰仗猎人与动物力量之间所建立的个人关系,这需要在以往的狩猎活动中精心构建。捕猎所获得的肉食是在遵循恰当捕猎程序方面长期投入的回报。通过对资源的管理,许多古代和现代狩猎社会采取了有意识的保护措施。
对传统狩猎者来说,同样的力量,既能让大自然充满生机,也能决定人类的生存和毁灭。正如另一位人类学家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在提及阿拉斯加的科育空(Koyukon)猎人时写道:“人类最恰当的角色就是为主宰一切的大自然服务。”[5]人类的福祉取决于和解与尊重。所以,科育空人屈服于环境的力量:他们从不与环境对抗。我们可能会说,有两个独立的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但是,对科育空人和其他狩猎者来说,实际上只有一个世界,而人类只占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与大羚羊共舞
北极和亚北极、热带非洲和澳大利亚的人类学研究记录了猎人与各种自然环境的力量之间紧密保持的平衡,以及猎人与猎物之间的平衡。在世界各地,猎人都全身心投入到一项意义深远的与动物亲密接触的活动中。以杀死猎物而告终的成功猎捕被认为是猎人和猎物之间友好关系的见证,在此过程中,猎物被杀完全出于自愿。杀死猎物不是一种暴力征服行为,而是将动物带入一个熟悉的社会存在领域的成功尝试,是共存和相互交换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肯定,作为人类生存战略的一部分,这种紧密的联系在几万年以前就已经建立。
非洲南部桑族(San)狩猎采集者生活的大地上充满了各种大大小小的动物——大群的羚羊、迁徙的牛羚、斑马以及许多小动物。然后还有捕食者,如狮子、豹、鬣狗,以及令人生畏的水牛、大象和犀牛。每一只动物,无论大小,都是桑族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无限广大的超自然秩序中,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位置。在这个包括猎人在内的充满活力、生机勃勃和超自然的世界里,每一个生命都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和个性。桑族人是动物生活万花筒中的成员,他们主动融入其中,与他们猎杀并食用的动物享受不分彼此的亲密关系。无论大小,他们对所有动物都体贴照顾,即使有些动物背负着杀手或骗子的恶名。一个人小心谨慎地行走在过去捕食者频繁出没的地带,在这里,他要保全性命取决于仔细的观察与代代口耳相传并精心积累的经验和知识,也取决于他与周围世界超自然力量之间的微妙沟通。
对桑族人来说,大羚羊(eland)是最重要的猎物之一,它们是形体最大、速度最快的羚羊类动物。桑族艺术家在岩洞的墙壁上刻画了数以百计的大羚羊,周围还有人在跳跃。这些绘画主要出现在南非东部的德拉肯斯堡山脉。[6]直到最近,博茨瓦纳卡拉哈里沙漠的桑族人仍然保持着在刚杀死的大羚羊周围跳舞的传统。当药师(萨满)将他们的能力激活时,他们全身颤抖,然后大汗淋漓,鼻孔出血。一只垂死的大羚羊张着大口,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化成液体的脂肪像鲜血般从大张的口中喷涌而出。也许,桑族人是在将人类的张狂比作垂死大羚羊的阵痛。在桑族牛舞中,模拟表演和声音效果是如此逼真,仿佛野兽真的出现在参与者面前一样。萨满起舞时,会产生幻觉,“看见”大羚羊站在火光的尽头。
不久,舞者与大羚羊合二为一,完成变形:他们也就成了大羚羊。这样,动物和人便实现了互换。桑族艺术家将大羚羊的鲜血与赭石混合,使他们的绘画在完成很久之后仍然是力量的源泉。在一些岩洞里,岩壁上留下了染过色的人类手印。把手指印在岩石或图画上,人类就获得了涌入自身体内的大羚羊的力量。这就好像大羚羊就在岩石后面,至少通过某种精神上的紧密联系与猎人分享它的力量。比这更早几千年的冰期的猎人可能也同样如此。猎人与猎物以及人与动物之间的亲密关系跨越了几千年。
不仅是桑族人,所有以猎物为生的猎人都发现自己陷入与动物的密切交往中。因此,猎人以什么方式与人相处,就要用什么方式对待他的猎物。他小心谨慎,因为他从来无法确切预见它们的行为。出于这一原因,对动物的详细了解,包括习惯和饮食、外貌和行为,都至关重要。猎人花费大量时间观察动物,不仅要了解它们的习惯,而且要像了解朋友及朋友的心情和特点那样去了解它们。猎人运用自己和他人的经验,以及大量对动物及其个性有着详尽描述的神话、传说和故事,长期掌控着自己与猎物的关系。
动物和人类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二者不仅以身体或意识,而且以整个生命彼此互动。人类与动物地位平等,本无高低之分,直到人们开始驯化各种动物,支配和从属关系才出现。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界限可以轻松跨越,两者可以相互渗透。以猎人为背景,记述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史,就相当于写一部人类关注动物的历史,体现了我们照顾动物和与动物相互依存的理念;这和我们将动物与社会、自然与人类做出明显区分的做法截然不同。我们今天需要探究的是我们和动物之间关系的质量。就这一问题,过去的猎人(实际上还有今天尚存的猎人)有着清楚的答案。
遥远时代的故事
猎人与动物之间的交流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时代。无数源自遥远过去的故事由猎人和采集者代代相传,经久不衰。在北方,很多这样的故事都是由人们在漫漫寒夜的温暖被窝里讲述的。科育空人讲述现有秩序形成之前就开始的“遥远时代”的故事。在那个时代,动物就是人类,具有人的外形,生活在人类社会,说着人类的语言。在遥远时代的某个时间点,有些人死后变成了动物和植物,生活在今天的土地上。理查德·纳尔逊称之为“梦幻变身”,这个过程在当地动物的身上留下了一些人类特征与人格特点。与世界上其他无数社会一样,在科育空社会里,这些通常极为冗长的故事相当于《创世记》里的创世故事。它们解释太阳、月亮和星座的起源,说明重要地标,常常以渡鸦为主角。
在许多美洲原住民社会里,渡鸦在创世神话中有着重要地位。对科育空人来说,渡鸦是个矛盾体:“万能的小丑、仁慈的捣蛋鬼、滑稽的丑角以及神。”[7]渡鸦控制着环境,使河水单向流动,给摆渡者造成麻烦。渡鸦创造了动物,为人类设计了死亡,并给他们设置了重重困难。正如一位科育空人对理查德·纳尔逊所说的那样:“就像和神对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和渡鸦说话。是渡鸦创造了世界。”[8]动物和人很接近,尽管它们有所不同:它们没有灵魂,而灵魂和动物的精灵是不同的。但是它们和人类确实很接近,它们感情丰富,能和同伴沟通交流,还能明白人的言行。动物和人类之间的互动非常密切,这意味着它们的精灵很容易被人的无礼行为冒犯。
科育空人认为,要以恰当的行为对待自然,因为强大的精灵随时会惩罚无礼或侮辱行为,也包括浪费行为。猎杀动物不构成冒犯行为,但是活着的或死去的动物必须被作为人类生命之源温柔以待。如果猎人行为不敬,他将与好运失之交臂。科育空人忌讳对动物指指点点,他们面对动物时,说话谨慎,不打诳语。他们在杀死动物时,不可以给它们造成痛苦,也不能将受伤的动物丢下不管。关于如何对待被杀死的动物,有着严格的规定,包括如何正确屠宰动物,如何恰当处理肉食。肉食消费有许多禁忌,不能食用的部分要受到尊重,并被合理掩埋或焚烧。
科育空人认为,环境是自然和超自然的结合,是人们生活的第二社会。猎人在森林中狩猎或穿行的时候,心里明白精灵正围绕着他们。每一只动物远非人们肉眼所见那么简单。遥远时代的故事告诉我们,动物也有人格特性。正如纳尔逊所言:“它是生物群体的一员。”[9]在科育空人的世界里,涉及动物的每一样东西至少部分存在于超自然时空。在科育空人及地球另一边的桑族人中,每一个族群的萨满都用自己的力量控制大自然的精灵,以此来疗伤治病;作为精灵的助手,他们还与北美驯鹿和其他猎物的保护神沟通,从而吸引动物,并使物产丰茂。
超自然力量的闪现
在非洲和澳大利亚等更加温暖的环境中,远古时期和有史可查的狩猎社会严重依赖各种植物食品。相比而言,狩猎只不过是些零星活动,即使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猎物繁多的地区也不例外。没有零度以下的天然冷藏环境,鲜肉的储存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与此不同的是,高纬度地区的猎人几乎以猎物的肉以及鱼类维持生存。[10]冬季的食物储存至关重要;猎人必须捕杀数量足够多的动物,不仅是为了获取食物,也有其他目的,因为植物食品及用于穿衣、建房的植被全年严重短缺。
在冰期晚期以及之后的几千年里,卡里布鹿 和驯鹿这样的迁徙物种一直是高纬度地区人们钟爱的猎物。直至今天仍然如此,因为基本狩猎行为少有改变,尽管武器已大为改观。这两种动物都大规模成群迁徙,对于它们的行进线路和关键渡河地点,人们比较容易预测。有人可能会认为,猎人只要跟随行进的鹿群,就能随心所欲地捕杀。这一传统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驯鹿的移动速度比人快得多,也不像人那样,受儿童和个人财产拖累。卡里布鹿或驯鹿在过去和现在一直遭到大量捕杀,在战略要地被猎人伏击和诱捕,特别是在夏末秋初这些动物处于最佳状态的时候。仅仅获取肉食还远远不够,因为猎人需要等量的脂肪。这使得处于最佳状态的高脂肪动物成为猎人喜爱的捕杀对象,特别是秋季的雄鹿,在发情前,它们的脂肪含量可达体重的20%。今天,许多北方猎人在杀死动物后只拿走脂肪,而将尸体抛弃,任由它们腐烂,除了舌头和小腿部位的骨髓,因为它们是难得的美味珍馐。一年的多数时候,雌鹿和幼鹿是人们的首选,而未出生的幼鹿更是大受欢迎——令当今动物保护人士极为震惊。远古时期的人类很可能采用同样的做法。
和驯鹿这样的迁徙物种一直是高纬度地区人们钟爱的猎物。直至今天仍然如此,因为基本狩猎行为少有改变,尽管武器已大为改观。这两种动物都大规模成群迁徙,对于它们的行进线路和关键渡河地点,人们比较容易预测。有人可能会认为,猎人只要跟随行进的鹿群,就能随心所欲地捕杀。这一传统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驯鹿的移动速度比人快得多,也不像人那样,受儿童和个人财产拖累。卡里布鹿或驯鹿在过去和现在一直遭到大量捕杀,在战略要地被猎人伏击和诱捕,特别是在夏末秋初这些动物处于最佳状态的时候。仅仅获取肉食还远远不够,因为猎人需要等量的脂肪。这使得处于最佳状态的高脂肪动物成为猎人喜爱的捕杀对象,特别是秋季的雄鹿,在发情前,它们的脂肪含量可达体重的20%。今天,许多北方猎人在杀死动物后只拿走脂肪,而将尸体抛弃,任由它们腐烂,除了舌头和小腿部位的骨髓,因为它们是难得的美味珍馐。一年的多数时候,雌鹿和幼鹿是人们的首选,而未出生的幼鹿更是大受欢迎——令当今动物保护人士极为震惊。远古时期的人类很可能采用同样的做法。
另外,还有用途广泛的鹿皮。例如,幼鹿皮可以用来做内衣,雄鹿皮可以用来做皮靴。除此以外,鹿皮还可以用来做皮鞭、帐篷、皮包和皮划艇等。早在1771年,博物学家塞缪尔·赫恩估计,仅为了家用,哈得孙湾附近的每个契帕瓦人(Chipewyan)每年要消耗20多张卡里布鹿皮。[11]同样,大量的肉食被遗弃,在夏末高温下腐烂,造成巨大浪费。这些被遗弃的死尸成为渡鸦和狼等食腐动物的美餐,它们每年大部分时间都跟在鹿群后面。浪费尽管巨大,却不足以造成驯鹿或卡里布鹿的灭绝。然而,浪费在所难免,因为人们只要仔细观察并把握好机会,就能捕杀大量猎物,且只要食用其中一部分就能满足生存的需要。成功与否取决于能否正确衡量气温、雪的深度和雪的硬度等多种因素,唯有如此,人们才能提前预测迁徙路线如何改变。否则,只能挨饿。
在小型狩猎团体中,头领在体能、耐力和狩猎技巧方面都要高于平均水平,并能对大家的意见进行分析、判断并将其转化为行动。作为头领,他将通过狩猎技巧获得的肉食及其他物品集中起来,然后再把这些“财富”分配给团队里的其他成员。家畜这样的个人财富并不存在,没有人会极力将更多的动物据为己有。短暂的领导权由一位猎人传给下一位猎人,在这样的社会里,猎物的繁殖由超自然力量控制。[12]超自然力量的所有权极其重要,常常由专职萨满掌控,在这种社会里,只有兽群才能确保人类的生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驯养家畜的社会中,负责维护牧群长盛不衰的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普通社会成员。
对许多猎人来说,超自然力量突然闪现,猎物就唾手可得。作为精灵的主宰,超自然力量决定哪些动物可供人类食用并再生。这就是为什么猎人对杀死的动物充满敬意——为了避免冒犯精灵。对北方人而言,驯鹿和卡里布鹿是永生不灭和不可战胜的。实际上,对古代和当今的猎人,如桑族人和北方猎人来说,捕杀猎物是一种再生行为。由于人们在消费和使用肉食和毛皮的时候都充满了敬意,死去动物的精灵就能回归精灵的主宰。
跟随指蜜鸟
野生动物和人类紧密互动的例子不胜枚举,而这些肯定与动物驯化毫不相干。二者组成了互惠互利的松散利益联盟,这经常是无意识的行为,并延续了几代人,就像肯尼亚北部博朗族(Boran)牧牛人和指蜜鸟之间的关系那样(见插叙“指蜜鸟与人类”)。指蜜鸟发现蜂巢,博朗人将它们打开。这就是博朗人和指蜜鸟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因此人们认为,杀死指蜜鸟无异于谋杀行为。
指蜜鸟与人类
黑喉指蜜鸟(Indicator indicator)喜欢蜂蜡及蜂巢的其他组成部分。[13]它是能够消化蜡的少数几种鸟类之一,但它也有一个弱点。指蜜鸟虽然能够找到蜂巢,却无法将其打开。因为蜂巢位于狭小的裂缝、空心树干和白蚁堆里,入口处有攻击性极强的蜜蜂把守,蜂刺能够穿透羽毛,足以使指蜜鸟丧命。旱季快要结束时,昆虫变得稀少,鸟类只能以蜡为食——这个时候博朗人同样缺粮、缺奶,只能靠蜂蜜为生。他们还认为蜜蜂是高超的药剂师,认为它们酿制的蜂蜜可以治疗多种人类疾病,包括疟疾和肺炎。另外,蜂蜜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特别是与鲜牛血或牛奶混合后,效果最佳。但是,人类也有弱点。他们虽然能够打开蜂巢,取出蜂蜜,却没有能力找到蜂巢。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来,指蜜鸟和人类为获取蜂蜜并肩作战。
寻找蜂巢的时候,人们会吹响握紧的拳头、贝壳或掏空的坚果。响亮的哨音在几千米以外都能听到。有时,猎人会点一堆烟火,或敲击木头,或大声喊叫,以此来吸引指蜜鸟。指蜜鸟循着声音找寻它们的人类伙伴。它们飞近猎人,落在显眼的灌木或树枝上,并发出“嘚嘚”的叫声。当人靠近时,指蜜鸟加快鸣叫的节奏,并向蜂巢飞去。指蜜鸟飞一会儿停一会儿,基本以直线飞行,直至抵达蜂巢,然后保持安静,让猎人完成最后的搜索。每个取蜂蜜的人都会为指蜜鸟留下一些蜂巢。没人知道这种独特的亲密关系是如何形成的,但是寻蜜季节正好是鸟和人都缺乏常规主食的时候,因此,二者就以这种独特的共生方式相互依赖,寻找食物。这种伙伴关系得益于机动性发挥的作用-牧牛人的不断迁移、蜜蜂迁徙的习性以及指蜜鸟广阔的活动范围。有鸟做向导,猎人节省了大量时间,他们成功的概率大大提高了。

黑喉指蜜鸟
在传说和民间故事中,动物在创造性活动和永不停歇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些传说,就像狩猎经验,通过故事、歌谣、仪式、舞蹈以及艰难经历,以口头方式代代相传,在人类和他们的猎物亲密相处的时代,成为关于动物的知识瑰宝。随着动物对人类社会的改造,这一切终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