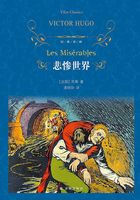
五 风雨欲来
随着时间的流逝,各种敌意渐渐烟消云散。起初,是对马德兰先生的诬蔑和诽谤:这是一种规律,大凡上升的人,都会遇到。然后,只剩下恶言恶语了。再然后,只剩下戏弄挖苦了,最后,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全城上下,对他由衷的崇敬,竟至于快到一八二一年时,滨海蒙特勒伊人称呼“市长先生”的口吻,和一八一五年迪涅人称呼“主教大人”的口吻简直如出一辙。方圆十里内,人们都来求教马德兰先生。他调解纠纷,阻止起诉,让敌对双方和解。谁都把他看作理所当然的仲裁。他的心灵仿佛是一部自然法典。对他的崇敬仿佛会传染似的,在六七年中,挨家挨户,渐渐蔓延开来,最后遍及全乡。
在整个城市和整个区,只有一个人千方百计避免传染,不管马德兰老伯做什么,他都持抗拒态度,仿佛有一种不受腐蚀、不可动摇的本能在唤醒他,使他局促不安。的确,在某些人身上,似乎真有一种动物的本能,和任何本能一样纯洁正直,它制造反感和好感,注定能区别两种不同的性质,从不犹豫,从不慌乱,决不沉默,坚持不渝,它在黑暗中心明眼亮,正确无误,蛮横无理,对于心智的一切劝告,对于理智的一切溶剂,它都拒不接受,不管命运如何安排,它都要悄悄警告狗别忘了猫的存在,警告狐狸别忘了狮子的存在。
马德兰先生平静而慈祥地从街上经过,受到众人的祝福,但常有一个身材高大、穿一件铁灰色礼服、拄一根粗拐杖、戴一顶垂边帽的人,与他交叉而过,又猛然会转过身来,目光跟着他,直到看不见;那人交叉着双臂,缓缓摇晃着脑袋,嘴唇撅到鼻子上,这一含义深刻的怪样,仿佛在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我肯定在哪里见过他。——无论如何,我是不会上他当的。”
这个人的神情严肃得吓人,让人一见就会紧张不安。
他叫雅韦尔,是警察。
他在滨海蒙特勒伊做警探的工作,这差使很艰难,却非常有用。他没有看到马德兰的起步。雅韦尔得到这个职位,全仗夏布耶先生的保荐,夏布耶先生是国务大臣安格莱伯爵的秘书,当时,安格莱伯爵是巴黎警察局长。雅韦尔来滨海蒙特勒伊时,那大厂主已经发达,马德兰老伯已变成马德兰先生。
有些警官有着与众不同的面孔,他们神态复杂,威武之中带点猥琐。雅韦尔的面孔也与众不同,但不猥琐。
我们确信,假如人的心灵是看得见的,那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每一个人和某一种动物有相通之处;而且,还可以发现一个连思想家也还若明若暗的事实,那就是从牡蛎到飞鹰,从猪到老虎,一切动物的特性都会在人身上反映出来,每个人都会有某种动物的特性。有时候,一个人甚至兼备几种动物的特点。
动物不过是我们自身美德和恶习的具体形象,它们在我们眼前游荡,是我们心灵看得见的幽灵。上帝让我们看见它们,就是要让我们深思。不同的是,因为动物是幽灵,上帝创造它们时,就没有把它们塑造成可以教育的;再说,那又有什么用呢?相反,我们的心灵是实实在在的,有它们自己的目的,于是,上帝就给了它们智慧,也就是说,赋予它们可教育性。良好的社会教育,总可以从一个心灵中发掘它的有用部分,不管是什么样的心灵。
当然,这只是从狭义的角度,即从表面的尘世生活来说的,并不预先断言那些非人的生灵在前世和在来世有什么特点这样一个深刻的问题。有形的我,绝不允许思想家否认潜在的我。这一点我们持保留看法。现在继续往下讲。
假如大家暂时同意我们的看法,承认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动物的特性,那么,现在就不难交代治安警官雅韦尔是怎样一个人了。
阿斯图里亚斯[189]的农民深信,每一胎狼崽里,总有一只狗,生下来就会被母狼咬死,否则,它长大后就会把其他狼崽吃掉。
假如给那只母狼生的狗崽按上一张人脸,就成了雅韦尔。
雅韦尔是在监狱里出生的,他母亲靠用纸牌算命谋生,父亲是苦役犯。长大后,他感到自己被排除在社会之外,毫无希望回到社会中。他注意到,社会不可原谅地将两种阶层的人排除在外,一种是攻击它的人,另一种是捍卫它的人。他只能在这两个阶层中作选择。同时,他感到自己本质上刻板、勤恳、正直,对于自己所属的流浪阶层,有一种难以形容的仇恨。他于是当了警察。
他成功了。四十岁时,他当上了便衣警官。
他年轻的时候,在南方当过苦役犯看守。
在展开谈之前,我们先就刚才给雅韦尔按上的“人脸”说一说。
在雅韦尔这张人脸上,有一个塌塌的鼻子,鼻孔幽深,两片浓密的络腮胡从两个脸颊伸向鼻孔。初见这两片森林似的颊髯和两个岩洞似的鼻孔,会感到不自在。雅韦尔难得一笑,但笑的时候,样子十分可怕,两片薄嘴唇张开,不仅露出牙齿,还露出牙龈,鼻子周围还会生出野兽吻端特有的那种惊讶而粗野的皱纹。雅韦尔严肃的时候,是一条看门狗,笑的时候,是一只老虎。此外,他的颅骨小,颌骨大,头发遮住了额头,直落眉毛。他总是双眉紧蹙,形成的皱纹犹如一颗愤怒的星星,在两只眼睛之间闪烁;他目光深沉,嘴唇紧闭,令人生畏;他神态凶狠,咄咄逼人。
此人只有两种情感:崇尚权力,仇视反叛。这两种情感本来很朴实,相对来说是不错的,但他总是用之过分,也就几乎成为不好的了。在他看来,偷盗、谋杀等一切罪行都是反叛的形式。他对所有担任公职的人,大到内阁大臣,小到乡村巡警,都盲目而绝对地相信。对失过一次足的人,他一概蔑视、憎恶和反感。他看事物总是很绝对,不承认有例外。一方面他说:“当官的不可能出错。法官永远是对的。”另一方面,他说:“那些罪犯都是不可救药,做不出什么好事来。”他完全赞成思想极端者的看法,认为人类法律有权将人罚入地狱,或者,如果愿意的话,有权确认罚入地狱的人,他们在社会底层设置一条冥河。雅韦尔坚忍淡泊,严肃刻苦,神情忧郁,喜欢沉思;他就像那些宗教狂,既谦卑又高傲。他目光像钻子,冷酷而犀利。他的一生可用两个词概括:警戒和监视。他把直线引进世上曲曲折折的事物中;他清楚自己的作用,崇拜自己的职责,他干密探,就像有人做神甫一样。谁落入他的手中,谁就倒霉!他父亲越狱,他照样会把他抓回来,他母亲违背放逐令,他照样会告发。他会为这种大义灭亲的举动沾沾自喜。此外,他过着一种节制、孤独、忘我、洁身自好的生活,从来也没有娱乐。他履行职责铁面无私,他理解警察,有如斯巴达人理解斯巴达一样。他是一个无情的密探,正直的警察,冷酷的侦探,一个具有布鲁图斯[190]特点的维多克[191]。
雅韦尔从头到脚都显出他是一个鬼鬼祟祟、暗中窥视的密探。约瑟夫·德·迈斯特尔[192]的神秘学派肯定会说雅韦尔是一种象征;那时候,这些神秘论者们正在用高深的宇宙演化论,点缀所谓的极端报纸。他的额头隐没在帽子下,眼睛隐蔽在眉毛下,下巴埋进领带里,手缩进袖管里,拐杖藏在礼服下面,因此,看不见他的额头、眼睛、下巴、手和拐杖。但是,时机一到,他那瘦削的额头、阴沉的目光、骇人的下巴、粗大的手和可怕的木棍,就会霍地从黑暗中露出来,仿佛伏兵从埋伏的地方冲出来一般。
他很少有空闲,但闲下来时,就读读书,尽管他憎恨书。因此,他不完全是文盲。这可从他略带夸张的谈吐中看出来。
我们说了,他没有任何恶习。他得意的时候,就闻一闻鼻烟。这是他还有人味儿的地方。
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司法部统计年表上标明为“流浪汉”这个阶层的人都害怕他。他们一听到雅韦尔的名字就胆战心惊,一看见雅韦尔的面孔就惊慌失措。
这个可怕的人就是这副形象。
雅韦尔有如一只眼睛,总是盯着马德兰先生。那是充满了怀疑和臆测的眼睛。马德兰先生最后觉察了,却好像无动于衷。他甚至连问都不问雅韦尔,既不找他,也不避他。对于这令人不自在的,甚至令人难以忍受的目光,他似乎不理不睬,满不在乎。他对待雅韦尔,同对待所有人一样,轻松自然,和蔼可亲。
从雅韦尔露出的一言半语中,可以猜出他已在别处暗中调查过马德兰老伯可能留下的所有蛛丝马迹;强烈的好奇心是他这类人所特有的,既出于本能,也出于意愿。他好像知道些情况,有时也闪烁其词地流露出一些,说是有人曾去某地,调查了某个失散的家庭,了解到了某些情况。有一次,他甚至自言自语地说:“我相信已抓住了!”继而他连续三天不言不语,沉思默想。看来他以为抓住的那根线又断了。
况且——这也是对有些词义的过于绝对而进行的必要的纠正——人不可能做到一无差错,人的本能恰恰会陷入混乱,迷失方向。否则,本能就会胜过智慧,兽类就会比人聪明了。
显而易见,雅韦尔看到马德兰先生那样自然,那样平静,感到有点困惑。
然而有一天,他那古怪的举止似乎使马德兰先生受到了震撼。事情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