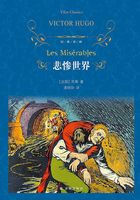
八 一匹马死了
“埃东餐馆比邦巴达吃得好。”瑟芬嚷道。
“我喜欢邦巴达,不喜欢埃东。”布拉舍韦说。“邦巴达更豪华,更有亚洲情调。瞧楼下的餐厅,墙上有镜子。”
“我宁愿盘子里多装点[166]。”法武丽特说。
布拉舍韦坚持说:
“瞧瞧这些刀。邦巴达这里的柄是银的,埃东那里的是骨头的。银当然比骨头贵重。”
“对装了银下巴的人来说,就不一样了。”托洛米埃提醒说。
此刻,他正在凝望残废军人院的圆屋顶,从邦巴达的窗口望得见。
一阵静默。
“托洛米埃,”法默伊大声说,“刚才,我和利斯托利埃争论了一场。”
“争论好啊,”托洛米埃回答,“争吵就更好了。”
“我们争论哲学。”
“好啊。”
“你喜欢笛卡儿,还是斯宾诺莎[167]?”
“代佐日埃[168]。”托洛米埃说。
作了这判决后,他喝了口酒,接着又说:
“我同意活在世上。这世上并非一切都完了,毕竟还可以胡言乱语。所以我感谢永生的神。我们说谎,但我们欢笑。我们肯定,但我们也怀疑。从三段论里,会冒出意外。这很精彩。这世界上到底还有些人知道如何打开和关上玩偶盒,从里面拿出些悖论来让大家开心。这玩意儿,女士们,你们现在平静地喝着的,是马德拉葡萄酒,要知道,是库拉尔·达斯·弗莱拉斯产的,那里高达海拔六百三十四米!喝的时候可得当心!六百三十四米!邦达巴先生,出色的饭店老板,给你们这六百三十米,却只收你们四法郎五十生丁!”
法默伊再次打断他的话:
“托洛米埃,你的意见可以作证。你最喜欢哪个作者?”
“贝尔……”
“贝尔坎?[169]”
“不。贝尔舒[170]。”
托洛米埃接着说:
“向邦达巴致敬!他要是能给我弄来一个埃及舞女,就可以同埃莱方塔的米诺菲斯相提并论!若能给我带来一个希腊名妓,就可以与凯罗内的蒂热利翁并肩比美!因为,啊,先生们,希腊和埃及都有过邦巴拉们。是阿普列乌斯[171]告诉我们的。可惜总是老一套,毫无新意。在造物主的创造中,拿不出什么新东西了。所罗门说:世上没有新东西[172]。维吉尔说:爱情对所有人都一样[173]。卡拉宾娜和卡拉宾一起上了圣克鲁的帆船,正如当年阿斯帕西娅和佩里克利斯[174]一道登上了去萨摩斯岛的战舰。最后说一句。女士们,你们知道阿斯帕西娅是什么人吗?她虽然生活在女人没有灵魂的时代,但她却有一颗灵魂,是一个玫瑰红和紫红的灵魂,比火焰更明亮,比晨曦更清新。阿斯帕西娅集中了女人的两个极端,她既是妓女,又是女神。苏格拉底[175]加上曼侬·莱斯戈[176]。阿斯帕西娅是在普罗米修斯需要一个婊子的时候创造出来的。”
托洛米埃一旦打开话匣子,就很难停下来,幸亏此时一匹马在沿河马路上倒了下来。马车和这位演说家戛然停住。这是一匹博斯母马,又老又瘦,早该送到屠夫那里了。它拖着一辆沉重的大车。到了邦巴达酒店门口,累得精疲力竭,不愿意再往前走了。这一事故引来一大群人围观。车夫气得张口就骂,他刚拼足力气骂了声“杂种”,同时狠抽了一鞭,那匹瘦马就倒了下去,再也起不来了。听到行人的喧闹声,聆听托洛米埃讲话的快乐的人们全都转过头去,托洛米埃趁机朗诵一段忧伤的诗,来结束他的演说:
“这马真可怜。”芳蒂娜叹息道。
大丽花嚷道:
“瞧芳蒂娜!她竟可怜起马来了。有这样的傻瓜吗?”
这时候,法武丽特交叉着双臂,头向后仰着,坚决地望着托洛米埃,说:
“喂!你答应给我们的惊喜呢?”
“我正要说呢,时候到了。”托洛米埃回答。“先生们,给这几位女士惊喜的时间到了。女士们,稍等片刻。”
“以吻开始。”布拉舍韦说。
“吻额头。”托洛米埃补充说。
他们在各自情妇的额头上庄重地吻了一下,然后将指头放在嘴上,一个接一个地朝门口走去。
他们出去时,法武丽特拍手相送。
“这已经有点意思了。”她说。
“不要去得太久哇,”芳蒂娜喃喃地说,“我们等着你们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