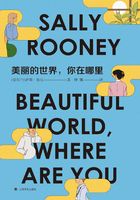
第7章
同一周的周四,艾琳参加了她供职的杂志社举办的诗歌朗读会。场地在北城中心一个艺术中心。活动开始前,艾琳坐在一张小桌前售卖最新一期杂志,人们在她面前来来往往,举着红酒杯,避开眼神交流。偶尔有人问她厕所在哪儿,她每次都用同样的语气和手势作答。朗读会快开始前,一位年长男士凑过来,说她有“诗人的眼睛”。艾琳自谦地笑笑,假装没听见,说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朗读会开始后,她锁上现金盒,从后面的桌上拿了一杯酒,走进大厅。里面坐了二十到二十五个人,前两排全空着。杂志编辑站在讲台后介绍第一位读者。一个叫葆拉的女人坐在靠走廊的座位上,她和艾琳同岁,是场馆工作人员,她往里挪了个空位给艾琳。卖了多少本?她低声问。两本,艾琳说。看到一个小老头过来,我还以为能再卖一本,结果他只想赞美我的眼睛。葆拉吃吃地笑了。她说,多么美好的工作日傍晚。艾琳说,至少我知道自己眼睛还挺美。
活动请了五位诗人,大致围绕“危机”这一主题。其中两人读的作品处理的是个人危机,比如丧亲和疾病,另外一人的主题是政治极端主义。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男人抑扬顿挫地诵读了一首非常抽象的诗,听上去和危机没什么关系。最后一位朗读者是一个穿黑色长裙的女人,她花了十分钟讲自己找出版商有多困难,最后剩下的时间只够读一首诗,一首押韵的十四行诗。艾琳在手机上记下笔记:六月的月亮,主要落在勺上。她把笔记拿给葆拉看,葆拉含糊地笑笑,继续专心聆听。艾琳把笔记删掉。结束后,她又拿了杯酒,坐回桌后。那位年长男士再次接近她,说:应该让你上去读。艾琳和善地点点头。我确定,他说,你有才华。嗯,艾琳说。他没买杂志就走了。
活动结束后,艾琳和其他几位组织者以及场地工作人员去附近一家酒吧喝酒。艾琳和葆拉又坐在一起,葆拉点的金汤力装在一只大如鱼缸的酒杯里,里面放了一片硕大的葡萄柚切片。艾琳点了加冰的威士忌。他们谈起“最糟糕的分手”。葆拉正在描述自己为期两年的一段恋爱,拖了太久没分手,她和前女友不停地喝醉,相互发短信,最后总是“要么大吵一架要么上床”。艾琳喝了一口酒。她说,听起来很糟。但你们起码还在上床,不是吗?你们的感情起码没有完全死掉。如果艾丹喝醉了给我发短信,好吧,我们或许会吵一架。但我至少会觉得他还记得我是谁。葆拉说他肯定记得的,毕竟他们在一起住了那么多年。艾琳强装欢笑地说:这才是让我受不了的地方。我二十到三十岁一半的时光都和他在一起,他最后却对我厌倦了。真的,事实就是如此。我让他无聊。我觉得某种层面上这说明了我的问题。不是吗?肯定是这样的。葆拉皱着眉说:不,不是这样。艾琳不自然地、尴尬地笑了一声,捏了捏葆拉的手臂。不好意思啊,她说,下杯酒算我的。
到了十一点,艾琳独自一人侧卧在床上,身体蜷曲,眼睛下面的妆有点花了。她眯眼盯着手机屏幕,点开一个社交软件。界面打开,显示加载图标。艾琳在屏幕上移动拇指,等待页面加载,但又突然关掉了软件。她来到通讯录,选择名为“西蒙”的联系人,点击通话按钮。三声后,对方接起电话,说:喂?
嗨,是我,她说,你现在一个人吗?
电话那头,西蒙坐在酒店房间的床上。右侧有一扇窗,拉上厚厚的米色窗帘,床对面是一台大电视,固定在墙上。他背靠着床头,双腿伸直,在脚踝处交叠,笔记本电脑开着,放在大腿上。对,他说,就我一个。你知道我在伦敦对吧?你还好吗?
哦,我忘了。你现在不方便说话吗?我可以挂的。
没有,方便的。你去今晚那个诗歌活动了吗?
艾琳跟他聊了活动的事。她给他讲了“六月的月亮”的笑话,他很配合地笑了。还有一首写的特朗普,她说。西蒙说光是想想就让他真心渴望投入死亡的怀抱。她问他在伦敦参加的会怎么样,他详细描述了一场座谈会,题目叫“欧盟之外:大不列颠的国际未来”。有四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中年眼镜男,他说,真的,他们看起来像是照着对方的样子用Photoshop复制出来的。太诡异了。艾琳问他现在在做什么,他说正在给工作上的事收尾。她转身躺平,抬头看向天花板上一块模糊的针状霉斑。
上班上到这么晚,对身体不好,她说,你现在在哪儿?酒店房间吗?
对,坐在床上,他答道。
她双膝勾起,脚踩床垫,腿在被单下拱起一顶帐篷。你知道你需要什么吗,西蒙?她说,你需要来自娇妻的呵护。是不是?娇妻会午夜时分来到你身边,手放在你肩上,说,好了,今天就这样吧,太晚了。咱们睡觉去吧。
西蒙把手机移到另一边耳侧,说:你勾勒出一幅非常可信的画面。
你女朋友没法跟你一起去吗?
她不是我女朋友,只是我最近的约会对象,他说。
我不懂二者有什么区别。女朋友和你最近的约会对象有什么不同?
我们是开放关系。
艾琳用没拿手机的手揉了揉眼睛,深色妆容抹到了手和眼窝下。所以你现在也在和别人上床,是吗?她问。
不,我没有。但我认为她在。
艾琳的手垂下来。她在吗?她说,老天。那个男人是多有魅力啊?
他忍俊不禁似的答道: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问?
我是说,如果他没你有魅力,那干吗去找他?如果他和你一样有魅力——好吧,我想见见这个女人,跟她握个手。
要是他比我更有魅力呢?
算了吧。不可能的。
他向后靠在床头上。你是说因为我太帅了?他说。
是的。
我知道,我要听你说。
她笑了起来,说:因为你太帅了。
谢谢你,艾琳。你人太好了。你自己长得也不赖。
她把头放在枕头上。我今天收到艾丽丝的邮件了,她说。
很好啊。她怎么样了?
她说艾丹和我分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没那么幸福。
西蒙顿了顿,似乎在等她说下去,然后他问:这是她的原话?
对,只字未改。
你怎么想的?
艾琳叹口气,答道:算了。
听起来不太顾及你的感受。
她闭着双眼,说:你老是维护她。
我刚刚才说她这么说没有顾及你的感受。
但你觉得她说得对。
他皱着眉,把玩着床头柜上印着酒店品牌的钢笔。没错,他说,我觉得他配不上你,但这是另一码事。她真的说这事没什么大不了吗?
是那个意思。你知道她下周要去罗马宣传新书吗?
他再次把笔放下来。是吗?他问,我以为她要暂时休息一下。
是的,可她又觉得无聊了。
原来如此。有意思。我一直想去见她,但她老说时间不方便。你担心她吗?
艾琳冷酷地笑了一声。不,我不担心,她说,我很光火。由你去担心吧。
你可以既担心也光火,他说。
你究竟站哪边?
他笑着低声安抚道:我站你这边,公主。
她也笑了,带着恼怒和不情愿,然后把额上的头发向后拂去。你上床了吗?她问。
没,我坐着呢。难道你希望我躺在床上跟你打电话?
是的,那样最好。
啊,好吧。这我能办到。
他起身把笔记本电脑放在墙头镜前一张小写字桌上。那张床占据了他身后绝大多数地板的面积,铺着白色床单,床单紧绷绷地塞在床垫底下。他把笔记本电脑的插头插进墙上的插座。
艾琳说,你知道吗,如果你太太现在和你在一起,她会帮你把领带解下来。你系领带了吗?
没。
你穿着什么?
他看了一眼镜中的自己,移开视线,转回床上。没配领带的西装,他说,当然了,没穿鞋。我一进门就脱了,文明人都这样。
那接下来要脱的是西装?她说。
他把西装脱下来,过程中双手交替拿着手机,说:的确是这顺序。
然后你太太从你手上接过西装,把它挂起来,艾琳说。
她人真好。
然后她会帮你解开衬衣扣子。不是例行公事的那种,是带着爱意温柔地解开。衬衣是不是也要挂起来?
西蒙用单手解开衬衣扣子,说不用挂起来,他会直接把它扔进行李箱里,回家了再洗。
接下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艾琳说,你系皮带了吗?
系了,他说。
艾琳依旧闭着眼,说:然后她把皮带取下来,把它放在该放的位置上。你现在把皮带取下来放哪儿?
晾衣架上。
你好整洁啊,艾琳说,太太喜欢你这点。
是吗,因为她自己很整洁?还是因为她不整洁,异性相吸?
唔,她自己不算邋遢,但没你那么爱干净。她很向往这种品质。你脱完了吗?
马上,他说,我一直举着手机呢。你介意我把手机放下来一小会儿,然后再拿起来吗?
艾琳羞涩而敏感地笑答道:当然可以,我又没把你当人质。
不是,我只是不想让你觉得无聊,然后把电话挂了。
放心,我不会的。
他把手机放在最近的床角上,脱完了衣服。艾琳闭着眼睛躺在床上,右手松松地握着手机,靠在脸旁。西蒙现在只穿了一条深灰色平角内裤,他拿起手机,靠着枕头在床上躺下。我回来了,他说。
你一般几点下班?艾琳问,我很好奇。
大概八点。最近大概接近八点半,因为大家都很忙。
你太太下班时间会早很多。
是吗?西蒙问,我很嫉妒。
等你到家时,她已经做好晚餐在等你了。
他笑了。你觉得我很传统吗?他问。
艾琳睁开双眼,仿佛她的遐想被打断了。
我认为你是人,她说,上班上到八点半谁会不希望有晚餐等着他呢?如果你宁愿回到空无一人的房间,自己做晚餐,那我向你道歉。
不,我不喜欢回到空无一人的家里,他说,如果非要幻想的话,我不介意被人服侍。只是我不会期待我的伴侣这么做。
哦,我冒犯到你的女性主义原则了。我就此打住。
别啊。我很想知道我和太太晚餐后要做什么。
艾琳再次闭上双眼。她说:好的,无需赘言,她是个好妻子,所以她会让你再工作一会儿,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话。但是不要太晚。之后她就想上床了。我猜你现在就在床上。
的确如此。
艾琳自顾自地放肆微笑着,继续说道:你今天上班怎么样?
还行。
你现在累了。
还不至于累到不跟你说话,他说,但确实累了。
太太对这些小细节非常敏感,所以她连问都不用问。如果你这天很辛苦,你累了,我觉得你会在十一点左右上床,然后太太会为你服务,一切都非常亲密、非常和美。
西蒙右手举着手机,左手透过平角内裤的轻薄棉料自慰。他说,我不是不领情,只是为什么是她在为我服务呢?
艾琳笑了。你说你累了嘛,她说。
啊,还不至于累到没法和我太太做爱。
我无意质疑你的男子气概,我只是以为你会喜欢。好吧,没关系,我可以弄错。但太太是不会弄错的。
她弄错了也没关系,我还是会爱她。
我真的以为你喜欢口交。
西蒙咧嘴笑道:没有,我的确喜欢的。只是如果我只能和虚构的太太共度一晚,我希望能涉猎更多的领域。你要是不愿意的话,不必说细节。
恰恰相反,我为了细节而活,艾琳说,我们说到哪儿了?和往常一样,你轻轻松松就脱掉了太太的衣服。
他将手伸进内裤。你太好了,他说。
你可以想象她很美,但我就不描述她的外貌了。我知道男人各有各的小趣味和癖好。
感谢你的许可。我可以栩栩如生地想象她。
是吗?艾琳说,我开始好奇她长什么样了。她是金发吗?别跟我说。我猜她是金发,大概一米五七的样子。
他笑了起来。不是,他说。
好吧。别告诉我。不管怎么说,她已经很湿了,因为她一整天都等着你的爱抚。
他闭上双眼,对着手机说:我现在可以摸她了吗?
可以。
然后呢?
艾琳用空出来的手握住自己的乳房,拇指尖绕着乳头画圈。她说,从她的眼睛你能看出她很兴奋,同时也很紧张。她很爱你,但有时她很焦虑自己并不真的了解你。因为你有时很疏离。或者说不是疏离,而是内敛。我只是在勾勒大致背景,这样你会更了解你和太太之间的性张力。她很紧张,因为她很崇拜你,她想让你开心,而有时她担心你不开心,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管怎么说,你上床后,她在你身下像叶片般颤抖。而你什么也没说,你只是开始操她。或者你刚才怎么说的来着?你开始和她做爱。怎么样?
嗯,他说,她喜欢这样吗?
哦,当然了。我觉得和你结婚前她很天真,所以当你们上床时她非常依赖你,因为这种经历太强烈了。她大概随时都想高潮。而你跟她说她是个好女孩,你为她骄傲,你爱她,她相信你的话。记住你有多爱她,这让一切都不同了。我很了解你,但这一面的你我并不了解。我不知道你和你爱的女人在一起是什么样的。我说远了,抱歉。我之所以会这样说,潜在原因是因为这是我喜欢想象的事。你还记得我们在巴黎时就是这么做的吗?算了。我只记得你当时很喜欢。这让我感到很自信。不行,我又跑题了。我在描述你和你太太做爱。我猜她肯定比我年轻漂亮得多。而且或许是有点蠢但很性感的那种。如果让我放纵一次,我会说当你和你太太上床时,你开始想象我。不是每次都想,就这一次。不用刻意。一个念头,一段记忆,穿过你的脑海,如此而已。不是我现在的样子,是我二十岁左右的模样。你当时对我真的很好,你知道吗?你在和你完美的太太做爱,她是世上最美的女人,你爱她胜过一切,但就当你在她体内,她颤抖着战栗着呼喊着你的名字时,有那么一两秒,你想起了我,想起我们年轻时做过的事,比如在巴黎时我让你在我嘴里射了,于是你想起当时的感觉有多美,这样拥有我是多么美妙,你跟我说这很特别。或许它的确很特别,你知道吗。如果这么多年过去,你和你太太在床上,你还会想起它,或许它就是特别的。有的事情就是这样。
他开始高潮,呼吸变得粗重。他闭上双眼。艾琳不再说话,一动不动地躺着,脸看上去很烫。他说了声:嗯。有一小会儿,两人都很安静。然后她低声问:我们能再聊一分钟吗?西蒙睁开双眼,从床头柜的纸盒里抽出一张纸巾,开始擦手和身体。
你想聊多久就多久,他说,刚才的感觉很好,谢谢你。
艾琳笑了,笑得几乎有点傻气,仿佛她放下心来。她的脸颊和额头发亮。哇,不用谢,她说,我忘了你是那种会说“谢谢你”的男人了。你给人的这种感觉特别好。你差不多百分之九十是浪子,但是时不时表现得像处男一样。不得不说,我很佩服你这点。以后我们生活中碰到会不会很尴尬?
西蒙把用过的纸巾放在床头柜上,从纸盒里又抽了一张纸,说:不,我们会表现得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不是吗?我记得你说过我反正只有一种面部表情。
艾琳皱着眉答道:我真的说过吗?太冷酷了。你起码有两种表情。一种是笑,一种是担心。
他手抚胸口,微笑着。你不是冷酷,他说,你在开玩笑。
反正你太太绝不会这么跟你说话。
为什么,因为她崇拜我吗?
没错,艾琳说,你就像她父亲。
他开玩笑地发出一声哀嚎。这敢情好,他说。艾琳咧嘴笑着。我敢打赌你觉得这很不错,她说,我知道你好这口。西蒙把手放在平坦的肚子上,说:你什么都知道。艾琳噘起嘴。不,我不了解你,她说。他闭着双眼,一脸倦容。我觉得刚才那段幻想里最真实的部分是我开始回想你在巴黎时的情景,他说。她听后似乎深吸了口气。少顷,她静静地说:你这么说只是为了取悦我。他自顾自地微笑,说,投桃报李,不是吗?但我说的是真话。我们最近能见面吗?艾琳说好的。他说,我会假装若无其事的。别担心。通话结束后,她给手机插上电,关掉床头灯。城市橙色的光污染浸染了卧室窗的薄窗帘。她睁着眼睛自慰了一分半钟,悄无声息地高潮了,然后转身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