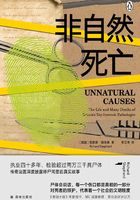
第3章
现在人们所说的亨格福德大屠杀,就发生在我刚刚从事法医病理学家这个职业后不久,也是我接手的首个大案。当时我年纪轻轻,一心上进,花了好长时间才最终成为一名具备资质的病理学家。经年累月的专业训练,绝非仅仅是常规的解剖及病理分析。我必须承认,一直盯着显微镜下的切片,试图发现细胞级别的微小区分,无聊透顶,差点让我半途而废。很多时候,我都需要偷偷溜进导师鲁弗斯·克朗普顿医生的办公室寻找灵感。导师慨然应允我查阅他所收集的文件档案,以及其所参与案件的相关照片影集。有时,枯坐于孤灯之下的我陷入沉思,直至深夜。在学成出师前,我时刻都在提醒自己,切莫忘记初心。
最终,我获得了执业资格,并被直接安排到盖伊医院法医学部门,在当时英国最知名的病理学家伊恩·韦斯特医生手下工作。
在当时,即20世纪80年代末,病理学家被认为应和资深警官一样,是喝大酒、说脏话的硬汉子。那些完成了让别人望而却步的艰巨任务的家伙,觉得自己有资格在别人面前耀武扬威。伊恩就有这种范儿。他颇具领袖气质,不仅是一名杰出的病理学家,更是证人席上桀骜不驯的“公牛”,从来不会向律师低头服软。他懂得如何品酒、吸引异性,他口吐莲花,擅长用奇闻逸事将酒吧里的所有人都吸引过来。至于我本人,虽说有时也较为害羞,但在意识到自己只能笨拙地扮演伊恩的小弟之前,曾一度对自己的社交能力信心满满。当他在伦敦各处酒肆大放异彩之时,我只能默默和其他崇拜者站在旁边,很少敢插嘴。或者,我只是没有,起码在盛况结束后一个小时之内,想到更好的说辞而已。
伊恩作为部门负责人,很显然需要挑起重担。亨格福德大屠杀是英国国难,更使得生活在那里的居民,特别是直接受其影响的家庭,面临一场人生悲剧。正常情况下,伊恩都会第一时间奔赴现场,但因为事情发生在8月中旬,他当时正在休假。因此,警方打来电话时,我接下了这项任务。
开车下班途中,我的传呼机响了起来。现在我们很难想象离开了手机如何生活,但在1987年,只有传呼机的“滴滴”声能提醒我需要尽快回个电话。我打开收音机,以防这个不期而至的传呼与某个大事件相关。果然不出所料。
一名枪手正在伯克郡的某个偏僻小镇出没。此前,我本人从未到访过,甚至几乎从未听说过这个地方。枪手最开始在萨弗纳克森林大开杀戒,并一路逃至亨格福德镇中心,现在藏身于一处学校建筑内负隅顽抗,警方已经将他包围,并试图劝说他放下武器自首。报道这一新闻的记者认为,枪手可能已经杀死了十名受害者,但目前这里处于宵禁状态,人们尚无法获知准确的伤亡数字。
我回到了家,当时,我们家在萨里郡算得上不错的住宅。我的婚姻生活幸福,两个孩子正在花园和保姆嬉戏玩耍:这一切和我即将调查的凶案现场形成了极大反差。我猜到妻子,珍,因为忙于学业可能并没有在家。
我穿过正门,径直走向电话,同时与保姆告别。通过电话,我了解到了最新的事态进展,并与警方和验尸官商讨是否当晚便动身赶往亨格福德。他们的态度十分坚决,要求我必须去。我也承诺,妻子回来后便立刻出发。
打开收音机,我一边收听亨格福德事件的最新报道,一边为孩子们准备晚餐,之后给孩子洗澡,读故事,哄他们睡觉。
“做个好梦。”我说道。一直以来,我都是这么说。
彼时,我不仅是关注子女的慈父,更是一心想要在目前自己职业生涯碰到的最大案件中一展身手的法医专家。珍回来时,这位法医专家早已整装待发。吻别爱妻后,我径直出发。
刑事侦缉处指示我在第14交叉路口驶离M4公路,并在路边等候警车前来接应。过了不久,一辆警车便停靠在我的车旁,两张严肃的面庞出现在我的眼前。
警官并没有寒暄客套。
“谢泼德医生?”
我点了点头。
“跟我们走。”
当然,我一路上都在收听广播,早就知道随着枪手丧命,屠杀已经宣告终结。27岁的男子迈克尔·瑞安,基于无人知晓的原因,携带两把半自动步枪以及一把伯莱塔手枪,徘徊于亨格福德。瑞安已经确认死亡,或者是因为吞枪自尽,或者被狙击手一枪了结了性命。媒体记者一律被挡在外面,伤者已被送往医院,居民被要求待在家中,街上剩下的不是警察,便是死者。
我开着车,经过一处路障,以极慢的车速跟在警车后面,驶入阴森可怖的空旷街道。夏日暖阳的最后一抹余晖,让这座鬼城沐浴在温和的夕阳下。活着的人都把自己关在家里,但感觉不到他们在窗边活动的任何迹象。除了我们这两辆车以外,其他车辆一动不动。听不到一声犬吠,花间少了猫咪的徜徉,连鸟儿也变得静默起来。
蜿蜒迂回,穿过小镇郊外,我们途经一辆斜斜地停在路边的红色雷诺。一位女士陈尸于车轮前。再向前走,向南转,瑞安家的残垣断壁还在路的左侧闷燃。这条路已经被堵死。一位警官的遗体在他的警车里一动不动,车上满是弹痕。一辆蓝色的丰田与警车迎头撞在一起,里面则是另外一具尸体。
一位男性长者躺在自家花园门口的血泊里。路边还有一位上了年岁的女性的遗体,她的脸朝下。我从广播里了解到,这位死者应该就是瑞安的母亲。她就躺在燃烧着的家门口。再往前,躺着一位男士,手里还攥着一条狗链子。8月,天黑后司空见惯的街景,与道路上发生的极度随意的杀人惨剧并置,坦白讲,这一切颇具超现实色彩。此前,英国还从未发生过类似事件。
在警察局门口,我们停了下来。先是我的车门发出关上的声音,随即警车的车门也被关上,此后,亨格福德便继续笼罩,不,是窒息在沉寂之中。几年之后,我将再次亲身经历这样伴随着恐怖气氛的死寂。一般来说,凶杀案件的现场总是人潮涌动——制服警员、便衣警探、勘验现场的技术人员,人们忙着记录、拍照、打电话、设置警戒线。但是,那天的事件似乎让亨格福德陷入冰封状态,犹如尸僵。
警察局肯定不仅仅是只有警察的屋子,总之,这里都进行过装修,地上涂了层灰泥,墙内架设了通信线路。一定有人对我表示了欢迎,我应该还和某些人握了握手。但对我来说,回头再看,这些礼节致意都应是在一声不吭的情况下完成的。
天色很快便彻底黑了下来。我搭乘一辆警车,前往案发学校,迈克尔·瑞安最后负隅顽抗并自戕的地方。
我们慢慢驶过死一般寂静的街巷,车灯照到了一辆撞毁的汽车,里面的司机很显然已经没有任何生命迹象。再一次,我走到近前查看。手电光依次滑过死者的双脚、躯干与头部。死因无可辩驳,面部留有一处枪伤。
我们后来又在几辆车旁稍作停留。死者的枪伤各有不同。有些人身中一弹,有些人则数次遭到枪击。
救援车静静地停在旁边,等待警方查验并运走遗体后,将撞毁的车辆拖走。我转向开车的警官,我的声音有如碎玻璃摩擦之声,打破了寂静。
“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到现场查看这些遗体了。他们的死因都毋庸置疑,我会在验尸时再处理。”
“即便如此,我们也需要你去看看瑞安的尸首。”他表示。
我点了点头。
在约翰·奥冈特学校,有大批警员集结。
我在楼下听取了警方的简报。
“瑞安告诉我们,他身上有炸弹。我们担心一旦移动尸体,可能会引发爆炸,因此还没有对遗体进行搜查。但是,我们希望你能现在去看一眼,确认这家伙已经死了,以防我们过去的时候他一下子引爆。没问题吧?”
“好。”
“我建议千万别翻动他,先生。”
“好。”
“是否需要件防弹背心?”
我谢绝了警方的好意。这东西是用来挡子弹的,根本没办法应付如此近距离的爆炸。并且,无论如何,我都不想去翻动瑞安的尸体。
我们拾级而上。空气里弥漫着些许学校的味道,警官打开教室的门,里面摆放着好多课桌,虽然其中一些被弄得乱七八糟,但大部分都还排列整齐。四周墙上挂满了照片和科学公式。一切再正常不过了。唯一的例外,便是教室前面黑板附近那具呈现坐姿的尸体。
枪手穿着一件绿色的夹克。如果没有头部的枪伤,他看起来就像刚刚结束了一天打猎。他的右手耷拉在衣服的下摆处,赫然攥着一把伯莱塔手枪。
就在我走向瑞安的同时,我意识到所有警察都在安静地撤离。我听到身后的门被轻轻关上。远处传来对讲机的声音,“正在进入现场”。
我,孤身一人,和英国有史以来杀人最多的刽子手共处一室。可能还有一枚炸弹。因为受到法医病理学界巨擘基思·辛普森教授相关著述的吸引,我才以此为志业,但他未曾提及任何与此类似的场面。
我能精准地意识到周遭的一切。门后寂静无声。窗外弧光灯投射在天花板上的光影。我的手电筒发出的光束。教室里弥漫着粉笔和汗水的味道,怪异地夹杂着鲜血的腥气。我穿过教室,目光注视着墙角的尸体。我走到近前,屈膝弯腰,仔细察看。那把当天大开杀戒的手枪,正直直地对着我自己。
迈克尔·瑞安往自己的右太阳穴开了一枪。子弹穿透颅骨,从另外一侧太阳穴飞出。当我准备离开教室的时候,发现了这枚弹头的最终归宿——它嵌入了教室对面墙上的告示板里。
我向警官简短描述了一切。没有隐藏的引信。死因是右侧太阳穴的枪伤,典型的自杀迹象。
之后,我因为可以离开这块悲伤涌动的死亡之地而如释重负,在车道上不断加速。但亨格福德的死寂似乎已经浸入车内,有如一名无比沉重且不受欢迎的乘客,坐在我的身旁。瞬间,在这一天内我所目睹的一切,凶残、恐惧的一切,彻底将我击垮。我将车驶上路肩,呆坐在黑暗的车内,任由其他车辆的灯光从身边一次又一次划过,既看不到,也听不到。
直到一辆警车停在后面,有人敲击车窗,我才回过神来。
“打扰您了,先生,没事吧?”
我将自己的身份以及看到的一切,告诉这位警官。对方点了点头,上下打量,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相信我的说辞。
“我只需要一分钟,”我告诉他,“然后马上开走。”
警官当然知道在工作状态和家庭生活之间的调整之难。他再次点了点头,回到自己的车上。他无疑会查证我讲述的故事。几分钟后,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将亨格福德甩在身后,前方便是回家的路。我向警官示意、挥手告别,然后开车汇入滚滚车流。警车在后面护送了一段距离,然后掉头离去。我一个人向家的方向开去。
回到家中,孩子们早已进入梦乡,珍还在楼下,电视机开着。
“我知道你去哪儿了,”她说道,“情况很糟糕?”
是的。但我只是耸了耸肩。因为不希望让妻子看到自己的表情,我选择背对着她,同时,必须马上关上电视机,以免听到记者们眉飞色舞、急不可耐地报道亨格福德事件。死者永远都不会眉飞色舞、急不可耐了。这些逝去的男男女女,在为生活、为他们认为重要紧迫的生计奔波的过程中,被屠杀了,他们的生活戛然而止。对这些死者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是重要的,再也没有什么是迫不及待的。
当天晚些时候,我一直都在打电话,以便安排好第二天如何对人数众多的死难者进行验尸。我希望能够帮助警方重建每个死者的死亡过程,加上证人的帮助,还原瑞安的作案轨迹。重建至关重要,不仅对于每一位亲历者,乃至对于更广大的社会来说,都是如此。生而为人,我们渴望了解,了解具体的死因,了解死亡本身。
次日一早,我在威斯敏斯特停尸间进行了若干常规验尸工作:醉酒者、吸毒者、心脏病突发者。就在同事向我打听亨格福德事件的细节时,警方正在将死者的遗体运送至位于雷丁的皇家伯克郡医院的停尸间。下午2点,我抵达这里。拜会这里的工作人员之后,大家沿袭法医行业行之有年的传统,聚在一起喝杯茶,彼此寒暄。泡茶在过去或现在都称得上停尸间里的必要仪式,是病理学家在验尸前的一项权利,也是一种义务。
这时,门开了,帕姆·德比冲了进来。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灵动起来。帕姆是我们娇小但极为重要的秘书。
“好吧!”她说道。
一如既往作为指挥者的她,此刻正在展现令人生畏的超高效率。两位不太情愿的停尸间助理费力地抬着一台电脑,跟在她的身后。
“我应该把电脑插在哪儿?”
这并不是个问句,而是一句命令。1987年,办公电脑才刚刚起步,像极了体积硕大的巨婴。事实上,我们的办公电脑就像从恐龙蛋里破壳而出的小恐龙那么大,帕姆必须用货车把它从盖伊医院拉来。
她看到我穿着绿色的围裙,蹬着白色的雨靴,正准备对尸体进行外检,并对其内部人体组织做X光检查。验尸马上就要开始了。
“不不不,在电脑没有预热之前你不能开始,这需要至少十分钟,否则你会比我快太多。去给我泡杯茶。”她指示道。如果伊恩·韦斯特认为自己是部门老大,那他一定在自欺欺人。
当电脑和茶壶都开始嗡嗡作响后,帕姆才坐到键盘旁边。
“这一切根本没有什么意义,人人都看得出来,他们是被子弹打死的。”她说话多少有些刻薄。对于往往因为一时冲动、并无预谋的真实杀人案件,帕姆再熟悉不过。这也是她和其他同事为了放松,经常会选择阅读情节设计精巧细密的侦探小说的缘故。小说中的谋杀往往会给读者留下清晰的线索,最终一块块碎片得以拼接完整。但这种虚构往往和真实情况相去甚远,真正的罪案调查经常需要面对的,乃是彼此矛盾冲突的事实及解读。
她说得没错,今天的验尸不会发现什么秘密。但每个案件都会涉及某人的同胞、父母、子女、爱人。每位受害者,对于某个家庭或者亲友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也为我提出了亟待破解的特殊难题。解剖室内的六张桌子一字排开,尸体间隔摆放,中间空出的桌子用来放我们取出的用于包装、记录的数以百计的物证。
首先是迈克尔·瑞安的尸体。或许大部分受害者家属并不希望让受害者的遗体与这个刽子手的尸首停放在同一停尸间,更别说一起解剖了。事实上,所有人都希望尽快将他铲除。媒体报道依旧大肆渲染凶手被特种空勤团“一枪毙命”,尽管警方已经在我当天晚上勘验现场后,向媒体确认凶手死于自杀。现在,我们依旧需要通过验尸来确认这一死因。
验尸,或者尸体解剖,一般在两种情况下进行。通常情况下,发生在医院的自然死亡,尽管死因已知,也可以进行验尸,旨在确认病人的医疗诊断或者尽可能评估治疗的效果。但这种验尸必须征求死者直系亲属的同意,后者有权予以拒绝。幸运的是,许多遗属都会表示同意。他们的这一决定给医疗人员提供了学习、提高自身技能的绝佳机会,从而造福其他病人。在我看来,同意验尸的决定实乃宅心仁厚之善行。
第二种尸体解剖,出现在死因不明或者非自然死亡的情况下。此类验尸由验尸官负责。一切可疑、异常、涉及犯罪或无法解释的死亡,不仅需要尸体解剖,还需要进行全面的法医学检验。后者是对尸体内外进行的极度全面的深入调查。之后,所有的细节都会被病理学家记录在验尸报告当中。
验尸报告必须确认死者的身份,这个过程相当冗长复杂,甚至有些时候最终也无法完成。验尸报告也要解释警方和验尸官要求进行验尸的原因。报告中会列出验尸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以及后续实验室检验的结果。
验尸报告的主体部分是病理学家对所发现的情况的精确描述,我们经常会给出对这些情况的解读,并最终给出死亡原因。如果无法确定死因,我们也会实话实说,当然,总是会讨论相关可能性。
尽管我们多年来的训练是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分析成千上万种染病器官的表征,但仔细检验死者体表,常常是验尸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详尽的尸体外部检验过程中,病理学家需要测量、记录每一道伤痕、每一块瘀青、每一个弹孔以及每一处刺伤的位置、尺寸和形状。与对尸体内部的医学分析相比,尸体外部检验似乎很简单,但通常后者才是重建杀人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尸体外部检验视为一种例行公事,因此草草带过。但如此一来,在尸体被火化之后,我们很可能会对草草写就的外检记录感到追悔莫及。
迈克尔·瑞安实施了大规模屠杀。他一共杀死了16名受害者,伤者的人数大致与此相当。迄今为止,我的职业生涯关注的都是意外、犯罪或者单纯就是厄运造成的受害者,很少见到行凶者,更别提造成如此多人伤亡的刽子手的尸体了。我能够,或者说,我应该像对待其他受害者那样,带着敬意处理瑞安的尸体吗?
我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在验尸房里,主观感受没有容身之地。我甚至怀疑,多年专业训练让我学到的最重要技巧,便是对其他人感觉有理由甚至有必要嗤之以鼻的死者,不产生任何道德意义上的抵触情绪。因此,无论我如何评价眼前这位年轻人及其所作所为,现在都必须心无旁骛。我清楚,在检验他的尸体时,需要付出与检验其他受害者相同甚至更多的心力与关注。只有经过彻底、权威的医学调查,我才能为验尸官提供所需信息,使他有信心作出正确的死因裁断。[2]我知道自己提交的这份证据对于最终裁断来说至关重要,借此可以平息未来出现任何质疑或者不可避免的阴谋论。
很难想象,现在赤身裸体躺在手术台上的这名纤弱的年轻人,刚刚实施了一场大规模屠杀。屋子里的所有人——警官、停尸间工作人员,包括帕姆,都一头雾水地盯着这个家伙。他看起来和任何犯罪受害者,任何他杀死的受害者一样脆弱不堪。
接下来,我按部就班地开展工作:对凶手体表进行充分细致的检查,特别是头部的贯通伤部分。然后,打开腹腔进行内检,提取器官标本进行毒理学检验。最后,对脑部进行弹道轨迹探查。
工作开始后,四周陷入一片静寂。没有人大声说话,没有人窃窃私语,没有叮当作响,没有杯盘碰撞。有的,只是静寂。甚至连室内温度似乎都出现了明显下降。验尸一结束,瑞安的尸体便被推走。没有人愿意靠近他。这个和母亲共同平静生活的怪异男子,痴迷枪械,脑子里尽是些只有上帝才清楚的想法。
接下来,开始解剖瑞安的受害者的遗体,可以预见,我将面临漫长、艰苦且压力重重的一天。随着一具具尸体解剖完毕,冷藏柜的门开了又关。除了这个,以及我对帕姆的口头说明,屋子里鸦雀无声。担任我助手的是实习病理学医生珍妮特·麦克法兰。帕姆负责将我的说明敲入电脑,一班负责拍照的摄影师及几位警官跟着我来到一张又一张解剖台前,其中较为资深的警官负责记录,年轻警官则负责接过我展示的器官。
停尸间的工作人员紧随其后,负责清洗、缝合尸体,以备遗属瞻仰。
死因一见即明,均系枪伤所致。没有受害者因为看到瑞安大开杀戒而心脏病突发死亡。但我的职责便是查看是否存在导致或加速死亡的先天疾病。我再一次仔细记录每处伤痕,对其加以分析说明,对于枪伤造成的弹道轨迹一一探查测量。我在每具尸体前驻足,指导摄影师拍照,测量伤口,记录异常情况,向帕姆口述我的程式化结论。渐渐地,瑞安当天实施的疯狂犯罪开始浮出水面。
总体而言,一枪毙命的受害者都是被远距离射杀。对于距离较近的受害者,瑞安通常会连开数枪。
瑞安的母亲在学校里做厨娘,她从朋友那里惊悉此事,赶回家中试图规劝瑞安。瑞安的母亲让友人开车将自己送到镇子南侧,然后徒步走回家,其间她经过了若干死伤者,但还是无畏地走向自己的儿子。
她大喊:“住手,迈克尔!”
他转过身来,用手里的半自动步枪朝自己母亲的腿开了一枪。正是这一枪,导致瑞安的母亲脸朝下栽倒在地。我判断,瑞安开这一枪的目的只是为了伤害。他随即走上前去,居高临下,连开两枪,从背后射杀了自己的母亲。
最后两枪呈现出枪支近距离(大约六英寸)击发后典型的烟晕残留及烧灼痕迹。或许,这仅仅是因为凶手在杀害自己母亲的时候,无法直视她的脸。在瑞安的母亲赶到现场之前,这位凶手的犯罪活动基本上集中于家附近,在我看来,正是因为弑母,凶手才将杀戮的范围扩大至全镇。我认为,这件事一下子释放了瑞安,他使用枪械对付手无寸铁者所带来的超常权力感被激发到了极致。
接下来的几天,我继续从事这项奇怪的工作,从一具尸体缓慢地移向另一具尸体。对于这些受害者来说,死神不期而至,本来波澜不惊的生活瞬间被暴力倾覆。停尸间里的每个人都对此感同身受,但我们不能任由恐惧或悲伤的情绪肆意蔓延。在病理学家的字典里,没有“惊吓”二字。我们必须抽离情绪,探求真相。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病理学家有时候必须中止某些部分的人性。30年后,当我再次飞临亨格福德上空时,长期被压抑的人性再次强力来袭。
事实上,此去经年,直到现在我才不得不承认,这场大屠杀对我造成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当时,我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承认自己受到了惊吓,或者感受到了悲伤。我的同人,那些硬汉或渴望成为硬汉的人,曾是我的人生楷模,他们肯定不会表现或表达这种感受,甚至不允许自己去想这些东西。不,为了从事这项工作,我必须牢记孩提时代激励我选择走上这条路的法医病理学界前辈基思·辛普森所倡导的职业操守。他曾经提及任何惊吓或恐惧吗?显然没有。
伊恩休假结束后,并未向我问及亨格福德事件,并未给我提出任何建议,甚至干脆对此只字不提。很显然,尽管在伊恩休假期间顶替他的工作,本是我的分内之事,但可以肯定,他对我在这一空档接手如此大案,心中颇有嫌怨。我是否本应该想办法找到他,要求他中断休假回来履职?或许应该,而且,他一定会赶回来。我们俩都十分清楚,这样的大案本该由他负责:伊恩曾经处理过爱尔兰共和军[3]实施的诸多爆炸及枪击案件,事实上,他的专长便是弹道分析。
伊恩表达愤怒的方式是表现冷漠[4],但后来同事透露的小道消息是,伊恩认为,瑞安最愚蠢的地方之一,便是选择在伊恩本人休假时大开杀戒。好像是觉得意犹未尽,我们私底下添油加醋道,伊恩认为,就是因为瑞安蠢到自杀的地步,自己才没有办法作为韦斯特医生在出庭做证时大出风头。
此后很长时间,亨格福德事件俨然成为横亘于我和伊恩中间的鸿沟,但恰恰是因为接手此案,彻底改变了我在盖伊医院乃至全英法医病理学界的地位。我不再是伊恩身后的腼腆小弟或者顺从跟班。现在,我成了一名具有话语权的知名法医病理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