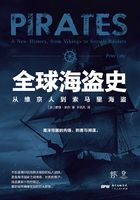
第8章 袭掠海岸
海盗袭击不只发生在海上,还有一些更高水准的海盗活动,以规模或大或小的真正的海盗舰队的形式,对陆地上的目标展开大规模水陆两栖作战行动。在阿拔斯王朝和法蒂玛王朝的统治时代(750—1258),撒拉森海盗经常会对地中海沿岸的基督教国家进行有组织的袭掠,其侵扰范围从希腊诸岛一路到法国和西班牙。例如,在838年,一支撒拉森海盗舰队袭击了马赛,在劫掠一番后将城市付之一炬。他们还会洗劫教堂和修道院,掳走教士、修女和普通信徒,这些俘虏有的被赎回,有的则被卖到奴隶市场。【73】在四年后的842年10月,撒拉森海盗在另一次袭击中,沿着罗讷河上溯30公里到达阿尔勒(Arles),沿途烧杀抢掠,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抵抗。【74】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袭掠阿尔勒,也不是最后一次:他们不断地回来,直到973年,他们与阿尔勒伯爵威廉一世(William I)的军队交战并被击败。但是撒拉森人并不满足于仅仅袭掠法国海岸:846年8月27日,一支强大的海盗舰队攻击了罗马。他们无法攻破罗马城坚固的城墙,于是洗劫了城郊那些毫无防备的奢华庄园,就连圣彼得大教堂也没能幸免。【75】但是,撒拉森海盗们没能够活到享受这批新财宝的那天。据说在返程的路上,他们的船在一场“可怕的暴风雨”中沉没了,因为他们“用污秽的嘴亵渎了上帝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及他的使徒”,《圣贝尔坦编年史》(Annals of Saint Bertin)如此虔诚地记录道。【76】甚至有传言说,有一部分从大教堂里偷出来的财宝后来被冲上了第勒尼安海的海岸,一同冲上岸的还有海盗的尸体,他们死死抓住财宝不放手,这些财宝后来被带回罗马。但这更像是虔诚的一厢情愿,而不是对事实的叙述。
仅仅数十年之后,撒拉森人和基督徒再次发生冲突。869年9月,一支撒拉森舰队劫掠了卡马格(Camargue),袭击并生擒了一位货真价实的大主教——阿尔勒的罗兰(Rolland of Arles)。讽刺的是,这位大主教被俘虏时,正在视察沿海地区的反海盗防御工作。按照这种尊贵人质的通用待遇,基督徒支付了赎金。不幸的是,年事已高的罗兰在被释放之前就亡故了。撒拉森人信守承诺,给他的尸体穿上华服,安置在椅子上交还了回去。
不止地中海沿岸的基督教国家遭受过毁灭性的大规模袭掠。在北方,维京人也进行了长期的大规模沿海侵袭。这些袭击一开始规模不大,主要是探索性的远征:维京人冒险穿越北海到达不列颠、爱尔兰和法兰克海岸,袭掠目标是沿海地区,也包括内河航运系统。通常,这样的袭掠只有大约10—12艘船参与,船员最多有500人【77】,基本上都是“打砸抢”(smash-and-grab)式的攻击。【78】第一次有记录的袭掠是针对多塞特(Dorset)海岸的波特兰岛(Portland),发生在787年:
这一年,[威塞克斯[46]的]贝奥赫特里克国王(King Beorhtric)迎娶了奥法(Offa)[47]的女儿埃德博(Eadburg)。在他统治的年代,第一次有北方人的三艘船出现,他们来自[挪威的]霍达兰(Hordaland)。于是,当地的采邑总管(地方最高行政长官)骑马去见他们,打算带他们去国王的居城,因为他也不知道这些到底是什么人。结果他们杀了他。这些是第一批袭击英格兰的丹麦船只。【79】
把他们当作诚实的商人,对毫无戒心的采邑总管比杜赫尔德(Beaduheard)来说是一个可以理解的错误,因为在那个时代,“很难分得清商人和强盗”——他们经常是同一拨人,是进行贸易还是劫掠视当地情况而定。【80】但这样的错误是致命的。最初对这些“来访者”动机的迷惑变成了几年后极大的震惊——793年,维京人洗劫了著名的林迪斯法恩(Lindisfarne)修道院。
这次袭击来得就像是晴天里的一道霹雳:岛上的僧侣们在这一天开始时,并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由于没人想过会有什么来自海上的危险,因此没有值班人员,也就没有人来警告将会发生什么事。可能有人看到快速驶近的长船时觉得好奇,并有一丝担忧——但是到了那时,除了逃命之外做什么都晚了。英国编年史家兼修道士达勒姆的西米恩(Simeon of Durham)如此记录道:
林迪斯法恩的教堂遭遇了毁灭、杀戮和强夺,几乎被彻底摧毁。(他们)用脏污的脚踩踏圣物,他们掘倒圣坛,抢走了教堂里所有的珍宝。有的弟兄被他们屠杀,有的被他们拴上锁链掳走,更多的人被他们剥光、凌辱、扔出门外,有些人淹死在了大海里。【81】
对林迪斯法恩的这次恐怖袭击是历史的分水岭,从此以后整个世界[48]看起来完全不同了:“维京时代”(Viking Age)拉开了序幕。
毫不意外的是,人们认为维京人是出于宗教仇恨才把目标对准教堂,他们在“吞食基督之血”——冰岛作家马格努斯·马格努松(Magnus Magnusson)如此生动地解释道。【82】对维京人来说,教堂和修道院只不过是他们肯定能找到,可以搬走战利品,让他们满载而归、不虚此行的地方而已。【83】像林迪斯法恩这样的宗教中心不仅仅是敬神的地方,它们还是作坊,包括金匠和银匠在内的各种具备高超技艺的工匠都住在这里,他们制造精美的艺术品,装饰圣坛、圣物箱和弥撒经书;在一副由农场、小村庄和零星小城镇构成的中世纪景观中,修道院是存放任何一件具备经济和文化意义的物品最合理的地点。【84】最后,非常讽刺的一点是,修道院会特意修建在岛屿上或者海岸边,以避开陆地上的军事冲突,结果却恰好成了海上掠夺者们唾手可得的目标。综上所述,并不是信条(也就是“信仰”)而是贪念(也就是“掠获物”)让毫无防备的僧侣和牧师成了有利可图的劫掠对象。
在法国和德意志地区,持续不断的王位之争和随之而来的内战,让维京人可以深入大陆内部,发动更加大胆的袭掠,而无须担心遭遇协同防御。隐修学者努瓦尔穆捷的埃尔门塔里乌斯(Ermentarius of Noirmoutier)在860年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以描述这场灾难的庞大规模:“船只越来越多,维京人无休止地涌入,从未停止。各地的基督徒都遭受着烧杀抢掠。维京人征服了沿途所有地方,没有什么能阻挡他们。”【85】公元885年,一支强大的维京军队——约有3万人、700艘船——在一个名叫西格弗里德(Sigfred)的丹麦首领率领下,包围了巴黎。这是维京人第三次进行这样的冒险行动,不过这次不像之前那样成功。在巴黎伯爵厄德(Odo)的英明领导下,人数居劣势却众志成城的守军——包括200名士兵和一些被征募的市民——克服了重重困难,击退了骇人的维京战士。
活跃在东海的海盗们同样施行维京式的“打砸抢”式袭掠,但年代更晚一些。关于日本掠夺者在15世纪对中国海岸的袭击,《明史》这样记载:“倭性黠,时载方物、戎器,出没海滨,得间则张其戎器而肆侵掠,不得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86】这再一次应验了:商人和掠夺者确实很难分辨,在很多情况下这两者都是同一拨人。和维京人的例子一样,这些早期有点机会主义性质的袭击迅速升级,发展成由几十艘甚至数百艘船组成的舰队进行的大规模沿海袭掠。海盗也会进入内河航运网络劫掠城市,那些城市远离海岸,因此并没有任何防范海盗的措施。如果不采取有力的反制措施来遏止这些袭掠,它们很快会演变成陆战。以僧人徐海为例,他更像一个维京军事领袖,而不仅仅是个海盗船长:1556年春,他派出两个倭寇海盗团伙,混成一支数千人的队伍,沿着长江两岸的港口和村镇一路残忍地奸淫掳掠、滥杀无辜。他们遇到的抵抗微不足道,都是一些战斗力不强的地方乡勇。对于受难者来说非常不幸的是,此时训练有素的政府正规军队正在跟北方地区的军队全力作战。【87】劫掠过后,海盗们却因为战利品的分配问题起了内讧。【88】这就是他们失败的根源。在此次成功劫掠后的第二年,这些海盗就被归来平乱的中央正规军彻底歼灭,指挥军队的是胡宗宪和阮鹗等将领。这几位将军在与海盗团队交战之前使用巧妙的策略减少了他们的有生力量:
胡宗宪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智取胜于强攻。他把一百坛毒酒装在一艘小船上做诱饵,派两名可靠的兵士假扮成后勤人员,一看到敌人的先锋部队就弃船而逃。强盗们得了酒,便停下来畅饮一番。有些人就这么死了。【89】
尽管如此,相对防守方而言,说到具体的行动和策略,维京人和倭寇总是能占据上风,因为他们可以主动选择攻击地点。他们可以在滨海地区进行侦查,发动两栖作战来保护滩头阵地,然后向内陆深入,依靠侧翼包抄战术和灵活的机动性完胜防守兵力。如果地形允许,入侵者会充分利用内河航运系统。维京人经常沿着莱茵河、塞纳河、卢瓦尔河以及瓜达尔基维尔河(Guadalquivir)一路袭扰科隆、特里尔(Trier)、巴黎、沙特尔(Chartres)和科尔多瓦(Córdoba)这样人口众多的中心城市。与之类似的是,倭寇的舰队也会冒险深入中国腹地,借助主干河运系统和渠道网络攻击内陆城市。见证者修杰(音)回忆说,一开始“海盗只是绑架百姓,逼迫其家属到他们的巢穴去交付赎金。后来他们占领我们的土地,赖着不走,杀死我们的官员,攻击我们的城市,造成了几乎无法挽回的局面”【90】。维京人和倭寇的暴行显然跟通常情况下的海盗行为相去甚远。他们的行动甚至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海盗不再是海盗,而是其他一类人——比如说,帝国的缔造者。不过,如果将海盗行为定义为未经法律授权,在海上发起的抢劫、绑架或暴力行为,那么很显然,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维京人和倭寇就已经远远地走在了海盗活动发展的最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