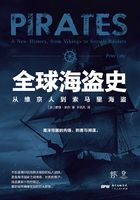
第3章 神的旨意
如果当海盗不会留下什么社会污点,那么这条路会容易走得多。在某些海洋文明里——比如从中世纪早期的8世纪起就肆虐不列颠群岛、爱尔兰和欧洲大陆沿海地区的维京人;再比如位于地球另一端的差不多同时期的罗越人(Orang Laut,直译为“海洋之民”),他们经常袭掠马六甲海峡沿岸地区。这些掠夺者被视为高贵的勇士,值得被崇敬和尊重。【31】在这些文明中,参与海盗劫掠是公认的为自己赢得名望、获取财富的手段之一。
对于那些生活在尚武的社会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封建领主的人来说,有三个要素是最重要的:赢得勇猛战士的声誉、通过捕获奴隶来积聚人力、积累财富。这在维京社会尤其重要:
在维京人的世界里,财富并不是深埋地下或者藏在箱子底的被动累积的黄金白银,而是社会地位、盟友和人脉。维京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社会通行的是开放的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之下,每个社会成员、每个家庭单位理论上都是平等的,都必须不停地对抗其他人以维护自己的或自家的地位。【32】
在这样的社会中,为了维持或者提高一个人的地位,随时可用的可支配财产是必须的,这样才能送出符合他身份的丰厚礼物。毫无疑问,黄金和白银是更受偏爱的财产。【33】送出的礼物至少要跟收到的礼物价值相当,这种持续的压力导致了“毫无约束”的掠夺嗜好。当然了,在少见的、短暂的和平时期,合法掠夺是不存在的,而海盗——不太合法但也没被过多谴责的海上掠夺形式——提供了一种可以被社会普遍接受的选择。因此,“攫取浮财和奴隶的暴利肯定诱惑了很多人投身强盗行列”【34】。这种习俗在10—12世纪维京人普遍信仰基督教之后仍然保留了下来。
中世纪晚期,地中海两岸普遍处于非常虔诚的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宗教极大地推动了“我们对抗他们”的思想,诠释了为什么“他们”可以——不,是必须——被攻击、被消灭。无论是8—13世纪的撒拉森[17]海盗,还是巴巴里私掠海盗[18],抑或那些“护教者”,也就是圣约翰医院骑士团[19],这些地中海的私掠者们用这种非常简单的二分法来给自己的行为辩护,实际上他们的潜在动机更多带有经济和政治性质。远在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勒芒会议[20]上用“神的旨意”(Deus vult)作为口号宣布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这一用语就是一个对海上劫掠行为强有力的合法解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发现有许多基督教骑士会参与这样的冒险。而在“另一边”,也就是伊斯兰世界,由于缺少正规海军,他们更多依靠海盗袭掠来削弱基督徒的海军力量。他们的看法和天主教世界完全一样:穆斯林海盗和私掠者视他们自己为“ghazi”,也就是为了伊斯兰而战的勇士。不消说,这种掺杂着宗教动机的、为了政治和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海上斗争在印度洋以及远东地区随处可见——只要穆斯林和基督徒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发生冲突。
正如“神的旨意”所表达的那样,真正的宗教狂热在这些冒险活动中是一股强大的驱动力。比如说医院骑士团,他们“轻视生命,随时准备捐躯以侍奉基督”,伟大的英格兰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如此贴切地叙述道。【35】比萨和热那亚经常袭击北非海岸的穆斯林港口,“用其收益来光耀上帝,因为他们把其中一部分钱捐给了圣玛利亚大教堂,那时候比萨人刚刚开始着手建造它”【36】。这些行为充分表明了一个事实,即宗教被用来合法化海盗行为:“这些侵袭让他们感觉自己是在跟穆斯林进行一场神圣的斗争。上帝会用胜利、战利品和难以具象化的精神满足来嘉奖他们的努力。”【37】然而,仅仅从宗教的角度来形容上述冲突未免太过于简单化了:如有必要,强大的经济和政治驱动力可以轻易跨越这种被大肆鼓吹的宗教鸿沟。据说,活跃于15世纪早期的唐·佩罗·尼尼奥(Don Pero Niño)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卡斯蒂利亚[21]私掠海盗,他在卡斯蒂利亚的国王恩里克三世(Enrique III de Castilla)的命令下执行私掠任务,也曾经受到当地政府的邀请,对直布罗陀和马拉加的港口(当时都是科尔多瓦哈里发国家的领土)进行过友好的访问。在他的传记中作者指出:“他们带给他牛、羊、家禽、大堆烤面包和盛满了古斯米[22]和腌肉的平底大盘子;不过,这不表示船长会碰摩尔人[23]给他的任何东西。”【38】尽管如此,由于当时卡斯蒂利亚与科尔多瓦哈里发国家并未交战,所以穆斯林没有受到他的伤害——不像他们那些生活在北非海岸的兄弟们,正在跟卡斯蒂利亚交战。即便是狂热的圣约翰医院骑士团,也没有把每一个穆斯林都当作敌人——根据“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这一准则,例外情形肯定是有的。
在穆斯林一方,类似的机制同样在运转着。尽管私掠被视作陆上“圣战”(jihad)的海上延续,那些参与其中的人理论上也算是为伊斯兰而战的勇士,很多希腊人、卡拉布里亚[24]人、阿尔巴尼亚人、热那亚人甚至犹太人也叛逃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倒不一定是由于皈依伊斯兰教之后激发出来的宗教狂热(大部分叛徒并没有真正皈依),而是出于经济方面的动机:贪婪和快钱的诱惑。【39】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活跃于14世纪的令人闻风丧胆的“海盗埃米尔”乌穆尔帕夏(Umur Pasha)。乌穆尔帕夏作为一名伊斯兰战士是无懈可击的,他因更喜欢“送法兰克俘虏的灵魂下地狱”而不是留着他们换赎金的作风而闻名。教皇克雷芒六世因为他的危险行径,亲自向其宣战。但这并不妨碍乌穆尔帕夏为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安德洛尼卡三世及其继任者约翰六世效命,执行私掠任务。尽管《乌穆尔帕夏史诗》(Destan d' Umur Pasha)的作者在这篇2000行的长诗中颂扬了帕夏的一生,但他还是忙不迭地补充道:“[对]皇帝和他的儿子像奴隶般顺从。”显然在掩饰帕夏对于“真正的大业”公然的背叛——想必主要还是出于经济原因。【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