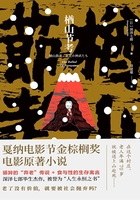
楢山节考
山连着山,一眼望不到尽头。在这信州(1)的群山之中有个村子,叫作“对面的村子”。阿玲的家就在该村的尽头。她家门前有一个大榉树砍伐后留下的树桩子,切口十分平整,跟一块板儿似的,孩子们以及过路人都喜欢在那上面坐一坐、歇歇脚,备受珍爱。于是,村里人干脆就把阿玲家叫成了“树墩儿家”。阿玲嫁到这里来,已经是五十年前的事儿了。这儿的村民把阿玲的娘家也叫作“对面的村子”。其实,这两个村子都没有正式的名称,所以就都把对方叫作“对面的村子”。然而,说是“对面的村子”,其实中间还隔着一座山呢。阿玲今年六十九岁,老伴儿二十年前就死掉了。她有个独生子名叫辰平。辰平的老婆也在去年捡栗子的时候,跌入山谷死掉了。留下的四个孙儿、孙女全靠阿玲照料。可比起照料孙儿来,阿玲觉得给已成了鳏夫的辰平找个续弦更伤脑筋。因为,本村也好,“对面的村子”也好,都没有合适的寡妇。
这天,阿玲终于听到两种她盼望已久的声音。其一是去后山的行人所唱的祭歌:
楢山祭哟来三次了
栗子树哟也开花了
正想着“该有人唱了吧”的当儿,阿玲就听到了这首村里人跳盂兰盆舞(2)时唱的歌。“今年怎么还没人唱呢?”——其实阿玲早就惦记着了。这歌也没什么特别的意思,无非说过上三年人就添了三岁。可与此同时,由于村子里有老人活到七十岁就要“上楢山”的习俗,所以这歌也在提醒老人:年纪不饶人啊。
阿玲把耳朵侧向歌声传来的方向,偷偷地瞟了一眼身旁辰平的脸,见他抿着嘴,正听着那歌声出神呢。同时她也看到他眼珠子瞪得大大的,泪光闪烁,心想,他到底还是为这事儿上心的——因为到时候辰平是要陪着阿玲“上楢山”的。
“这小子,是有良心的!”
阿玲不由得感到心头一热。
阿玲期盼着的另一个声音,是由飞脚(3)从她娘家捎来的一个口信。说是“对面的村子”出了一个寡妇。那人与辰平同年,四十五岁,三天前刚刚办完亡夫的丧事。只要年龄合适,这事儿就等于确定了。因此,飞脚来的时候仅仅是来通知出了个寡妇的,而回去的时候就连过门的日子都定好了。当时,辰平进山去了,不在家。不过这事儿与其说是阿玲的擅自决定,倒不如说,听到飞脚捎来的这个口信时,就已经万事大吉了。等辰平回家后,告诉他一声就行了。
在这儿,婚事极为简单,谁家都一样。男女双方要是自己好上的,他们说定了就行了。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婚礼,只是当事人住到对方家里去而已。即便有媒人从中作伐,只要年岁相当,事情也就成了。当事人到对方家里去玩玩,住下不走了,不知不觉间就成他家的人了。到了盂兰盆节、过年的时候,也没什么地方可去游玩的,只是不干活儿罢了。只有在过楢山祭的时候才会做点好吃的,平日里则得过且过,万事从简。
阿玲眺望着飞脚回去的方向,心中暗忖道:这飞脚说是娘家派来送信的,却怕是那寡妇的亲戚吧。男人才死了三天,就马上跑来说定改嫁的事情,估计他们也很担心寡妇的归宿吧。同时她又想到,从自己一方来说,也是希望那寡妇快点进门的。因为到明年自己就满七十岁了,该“上楢山”了。就在这个当儿,有人来说年岁相当的亲事,可谓正中下怀。所以她一想到再过几天,那寡妇就会在他父亲或别的什么人的陪同下上门来,就松了一口气,像是卸下了肩头的一副重担。其实,别说是娶个儿媳妇了,只是想象一下家里来个女人,她就已经觉得是解决了一个老大难问题。孙儿辈中前三个都是小子,打头的是袈裟吉,十六岁了,最小的是个女娃,才三岁。儿子辰平由于老也找不到续弦,近来已死了这条心了,浑浑噩噩的,阿玲也好,村里人也罢,都觉得他无论做什么都无精打采的。不过这下可好了,他总算又能振作起来了。想到这里,阿玲觉得连自己都充满了朝气。
傍晚时分,辰平从山里回来刚刚在树墩儿上坐定身躯,阿玲就在屋里朝着他的后背大叫道:
“喂,你媳妇要从‘对面的村子’过来了!前天才守的寡,说是一过‘七七’就来啊。”
讲起儿子的亲事已定,阿玲就跟替自己表功似的,得意扬扬。
辰平回过头来说道:
“是吗?从‘对面的村子’过来吗?多大岁数呀?”
阿玲飞快地来到辰平的身边,说道:
“说是叫作‘阿玉’,四十五,跟你同岁哦。”
辰平笑道:
“无所谓,事到如今,我早就没色心了。啊哈哈。”
辰平似乎有些害臊,跟阿玲搭着腔,倒也有些兴奋。根据老人特有的敏感,阿玲觉得辰平除了又得个老婆,仿佛还纠结着别的什么心事,可她眼下正在兴头上,顾不上这个。
楢山上是住着神灵的。进过楢山的人全都见过神灵,所以对于这一点是没人怀疑的。事实上也正因为有神灵存在,所以比起别的节日来,大家对于祭祀才特别卖力。甚至到了一说起祭祀,就专指楢山祭的程度。楢山祭跟盂兰盆节是连在一起的,跳盂兰盆舞时唱的歌跟楢山祭时唱的歌也是一样的。
盂兰盆节在阴历的七月十三至十六,楢山祭则在其前一夜,七月十二,是个夜祭。到了那天夜里,人们要吃初秋的山货,野栗子、野葡萄、米槠和榧子树的果实、蘑菇什么的。除此之外,还要吃更为宝贵的白米饭,喝米酒。白米在这儿被称作“白萩花”(4),在穷村子里,即便种上了,产量也很低。由于这儿是山区,平地很少,所以平时是以收成好的小米、稗子、玉米为主食的,白米饭只有在过楢山祭或生重病时才吃得上。
跳盂兰盆舞时唱的歌中也有这样的歌词:
我家老爸不像话
病了三天就吃白米饭
这是个劝人节俭、反对奢侈的歌。说是自己的父亲才生了一点小病就要吃白米饭,嘲讽他是个败家子、大浑蛋。这首歌就跟格言似的,可以在各种场合运用。譬如在嘲讽儿子好吃懒做时,父母或兄弟就会这么唱:
我家小哥不像话
病了三天就吃白米饭
相当于警告儿子说:你游手好闲,不知劳苦,居然还好意思吃白米饭?另外,儿女在不听父母的吩咐,跟父母提意见的时候,也能唱这首歌。
楢山祭的歌,其实只有“栗子开花”那么一首,但村里人用此唱腔,编出了各种各样好玩儿的歌来。
阿玲家位于村子的边上,自然就成了人们进山时的必经之路。眼下离楢山祭只有一个月了,而这种歌经人一唱开了头,就接连不断地有人唱,也纷纷传入了阿玲的耳朵。
盐铺的阿酉运气好啊
上山那天哟下了雪
歌里所唱的“上山”二字,在这个村子里是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的。尽管发音和声调一模一样,但谁听了都能分辨出到底是哪种意思。一种是为了砍柴、烧炭等目的而上山干活的意思;另一种是“上楢山”的意思。传说“上楢山”那天如果下雪的话,这人的运气就很好。其实,现在的盐铺里并没有一个叫作“阿酉”的人,但在多少代之前,是有这么个人的。那人上山的时候正赶上下雪,所以他就成了运气好之人的代表,被编入了歌词且流传至今。就这个村子而言,下雪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儿。到了冬天,村子里也时常下雪,山顶上也一片雪白,不过这个叫“阿酉”的人,是到了楢山的时候老天爷才开始下雪的。要是在雪中行走,那就是不走运了。所以,阿酉遇到的那种情况是最为理想的。不仅如此,这首歌其实还包含着另一层含义,那就是提供了一个暗示:要“上楢山”的话,不要夏天进,尽可能地要在冬天进。因此,“上楢山”的人要选择将要下雪的当儿上山。如果已经下了雪并积得很厚了,也就进不了山了。神灵所居住的楢山离得很远,要爬过七个山谷,绕过三个池塘才能到达。所以,行走在没有积雪的山道上,到了那儿仍不下雪的话,就没什么幸运可言了。所以说这首歌其实还指定了一个极为严苛的上山时间:要在下雪前上山!
阿玲早就做好了“上楢山”的心理准备。动身前请客人喝的米酒是必须早早预备下的,上山后自己要坐的草席也在三年前就编好了。给成了鳏夫的辰平找续弦,也是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之一。现在,请客用的米酒、草席、儿子的续弦全都料理停当了,但还有一件事,也必须事先办好才行。
瞅准了一个谁都不在的当儿,阿玲捏起一块打火石,张开嘴,用打火石“咔咔咔”地敲打起自己的门牙来。她要敲掉自己那口结实的牙齿。“咔咔咔”——敲击声直冲脑门,口中疼痛难耐。她心想,只要忍着疼不停地敲,总会将牙齿敲下来的。由于她非常希望自己掉牙齿,甚至连现在敲打牙齿时的疼痛都觉得十分爽快。
阿玲在上了年纪之后,牙齿依旧好好的。她在年轻的时候就为自己有一口好牙而自豪。那会儿,她甚至能“嘎嘣嘎嘣”地将晒干了的玉米粒嚼碎了吃下肚去。上年纪后,牙也一颗都没掉。这让阿玲感到害臊。儿子辰平已经掉了好几颗了,她却依旧满口牙整整齐齐的,让人觉得她一点也不肯少吃,什么都能吃。在这么个食物匮乏的村子里,这可是件令人害臊的事啊。
村里有人跟她说:
“就你这口牙,没什么不能嚼的了,松塔也好,放屁豆也罢,全能一扫而光的吧。”
这可不是什么玩笑话,而是赤裸裸的嘲讽。所谓“放屁豆”,其实就是蚕豆,硬得跟石子似的,吃了就会放屁。所以吃了它而放屁的时候,就会说“吃放屁豆了嘛”。由于它又硬又难吃,通常又叫作“硬豆”。阿玲从未在人前放过屁,却被人说吃放屁豆什么的,确实是一种嘲讽。这一点她自己也很清楚。因为已经有好几个人这么说她了。她觉得自己老了,并且已经到了要“上楢山”的年纪,可牙齿还这么结实,也难怪人家要说三道四了。
就连孙子袈裟吉也来嘲笑她,说:
“婆婆的鬼牙有三十三根。”
居然连孙儿辈都这么肆无忌惮地嘲笑她了。可是,阿玲用手指摸着数了一遍,上下加起来是二十八颗。
“胡说八道!明明只有二十八颗!”她反驳道。
“哈哈,你只会数到二十八吧?其实还有呢。”袈裟吉故意气她道。
其实袈裟吉就是想说“三十三根”罢了。
去年跳盂兰盆舞唱歌时,他唱道:
“我家婆婆的隐私处,长着鬼牙三十三根……”
结果把大家笑得满地打滚。其实这首歌是袈裟吉从村里一首最下流的歌改过来的。原本唱的是“我娘的隐私处/长着三十三根毛”,是一首侮辱自己母亲的歌。袈裟吉将“毛”替换成了“鬼牙”,结果大受欢迎,所以他觉得不说成“三十三根”就不够味儿了。并且,他还到处去跟人说阿玲有“三十三根”牙齿。
阿玲嫁到这个村子来的时候,曾被称为村中第一美女,老伴儿死了之后,她也没像别的寡妇那样惹出什么风言风语,甚至从未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三道四过。没想到的是,居然因为牙齿的事情而丢人现眼了。因此她觉得在“上楢山”之前,怎么着也要让自己掉几颗牙齿。她希望自己坐在辰平的背架上“上楢山”时,是一个掉了牙齿的、体面的老太婆。就因为这,她才背着人,偷偷地用打火石敲掉自己的牙齿。
阿玲家的隔壁,是一户被叫作“钱屋”的人家。其实钱在这个村子里是无用武之地的,所以无论谁家都没有钱,但钱屋家有人去了趟越后(5),回来时带着一枚天保钱(6),从此,人们就称他家为“钱屋”了。钱屋家有个老父亲,叫作阿又,今年也七十岁了。由于他住在阿玲的隔壁,又是同岁,所以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阿玲的话伴儿。阿玲是几年前就开始为“上楢山”上心了,可钱屋家是全村最小气的人家,像是连上山前的请客都想赖掉似的,一点也没做“上楢山”的准备。原本听说阿又会在今年春天之前上山,可到了夏天也不见动静,于是人们又在背后议论说,看来他会在今年冬天不辞而别,悄悄地上山。不过阿玲早就看出他是要遭报应的家伙,觉得他根本就不想上山,也一直觉得他是个“混账东西”。
阿玲自己是打算在满七十岁那年的正月里就“上楢山”的。
钱屋再过去一家,是一户被叫作“烧松”的人家。他家后面有一棵枯死了的松树。那粗大的树干,模样就跟岩石似的。那是因为很久以前,松树被雷劈了。他家这个“烧松”的名号也由此而来。
烧松再过去一家,是一户被叫作“雨屋”的人家。在村子的巽(7)位处,有一座巽山。据说这家里的人一上巽山必定下雨。说是因为从前这家里有人在巽山上看到了一条两头蛇,并将其杀死了,所以他家人一上巽山就肯定会下雨。他家这个“雨屋”的名号,就是这么来的。
雨屋再过去一家,就是因山歌传唱而出了名的“榧树”家。这个村子,总共有二十二户人家,而村中最大的树,就是他们家的那棵榧树。
榧树家的阿银是个臭婆娘
有了儿子孙子,还有老鼠崽
阿玲嫁到这儿的时候,那个叫作“阿银”的老太婆还活着。她可是个坏女人,所以其恶名留在了山歌里。所谓的“老鼠崽”,是指孙子的儿子,也即曾孙。在这个食物奇缺的村子里,她家跟老鼠似的生一大堆孩子,甚至接连三代都早熟、多产,连曾孙都抱上了,这是要被人嘲笑的。阿银正是因为生下了儿子,抚育了孙子,还抱上了曾孙,所以才被人羞辱,让人觉得她是个净生些好色子孙的坏女人。至于“臭婆娘”的说法,是指不检点的女人,或者干脆就是淫妇的意思。
一到七月,就谁都有些心神不定了。虽说祭祀只有一天,可因为一年里也只有这么一次,所以只要一进入七月,整个氛围就跟过节没什么两样了。
如此这般,很快就到了祭祀的前一天。
辰平忙这忙那的,一刻也不停。由于大家都兴奋异常,袈裟吉又不知到哪儿野去了,一点也帮不上忙,所以就他一个人忙了个团团转。
辰平走过雨屋跟前时,听到那家的男人正在里面唱那首“鬼牙歌”。
树墩儿家阿玲的隐私处
长着鬼牙三十三根
辰平心中骂道:“好你个浑蛋!”
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这首歌虽说是袈裟吉在去年开始唱开的,可去年阿玲和辰平都没听到。今年倒好,居然指名道姓地唱起“树墩儿家阿玲”来了。
辰平猛地闯入雨屋家中,见他家男人在土间(8)里,就也一屁股坐到了土间的泥地上。
“喂!你上俺家去一趟。数数俺家奶奶到底有几颗牙!”
辰平平日里沉默寡言的,现在噘着嘴往那儿一坐,显得十分凶狠。见此情形,雨屋家的男人立刻就慌了手脚。
“啊呀呀,我可没那个意思啊。是你家袈裟吉先这么唱的,我不过是学样儿罢了。你这么凶巴巴的,我可受不了啊。”
到这时,辰平才知道这歌是袈裟吉率先唱开的。说来也是,袈裟吉那小子确实老嘀咕着“婆婆有三十三根牙”什么的,这下子总算明白了。这也难怪,因为袈裟吉从不在阿玲或辰平跟前唱这首歌。
辰平一声不吭地冲出了雨屋。
“袈裟吉这小子上哪儿去了?”——他在路边捡了根粗木棍就四处找开了。
这时,袈裟吉正在池前家的旁边跟四五个小孩儿一起唱歌呢。
一年一度山祭日
拧紧缠头吃白米饭
那儿的杉树很密,跟篱笆墙似的挡着,看不到袈裟吉的身影,但歌声中夹杂着他的声音,辰平一听一个准儿。
辰平抡起大棒大声喊道:
“袈裟!你奶奶的牙齿是鬼牙吗?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奶奶那么喜欢你,把你养这么大,你倒好啊。你这个浑蛋!”
他蹿起身子,一棒打了下去。可袈裟吉“哧溜”一闪身躲开了,辰平一棒打在了石头上。由于他用力过猛,双手震得发麻。
袈裟吉朝对面逃去,随后若无其事地望着他。
辰平朝着袈裟吉怒吼道:
“浑蛋!不给你饭吃了!”
村里人常说“不给你饭吃了!”或“不许吃饭!”之类的话,虽说也有作为惩罚而真的不让人吃饭的时候,但通常只是气头上的骂人话而已。
那天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大家在饭桌边坐好后,袈裟吉从外面进来,也跟大家一样在饭桌前坐了下来。他瞟了一眼辰平的脸,发现刚才那种怒发冲冠的凶相早已没了踪影,反倒显得有些垂头丧气。
其实,辰平是不想当着阿玲的面提及那个“鬼牙歌”。别人怎么着都行,就是不想让阿玲知道有这么一首歌。他甚至心中暗想,要是袈裟吉不把刚才的事情说出来就好了。
可袈裟吉心里想的是:不就是个“鬼牙歌”吗?犯得着为这点小事大动肝火吗?好吧,既然这样,以后遇上什么事儿,我就翻来覆去地唱这歌!
就是这个主意!——他反倒来劲了。其实,袈裟吉心里也窝着火呢。他对于父亲续弦,心里一百个不乐意。
随后,大家就往自己碗里盛了饭,开始吃了起来。
说是“饭”,其实就是汤水中有些玉米面疙瘩和蔬菜罢了。因此,与其说是“吃”,不如说“喝”更确切些。
阿玲在想着别的事情。
“从‘对面的村子’过来的媳妇,虽说略早了一点,说不定祭祀那天就会到。”——她有这样的预感。本以为今天就会来,可今天没来。那么,或许明天就该来了。她觉得还是提前让大家知道这一点为好。
“说不定你们的妈妈明天就会从‘对面的村子’过来哦。”
她像宣布一件大喜事似的跟孙儿们说道。
辰平也显得很高兴,搭腔道:
“虽说才过了一个月,可她早点来,你就能轻松点儿,不用受累做饭了。”
可谁知他的话音刚落,袈裟吉就举手喊道:
“慢着!”
他摆出一副不让辰平往下讲的姿态,把脸转向阿玲怒吼道:
“用不着什么‘妈妈’从‘对面的村子’里过来!”
接着他将脸转向辰平,挑衅似的说道:
“我会娶个媳妇来的。不要什么后妈!”
随即,他又转向阿玲说道:
“做饭这点小事你要是觉得麻烦,以后就让我媳妇来干好了,你给我闭嘴吧!”
阿玲大吃一惊。她将手里拿着的两根筷子扔到了袈裟吉的脸上,大声喊道:
“浑蛋!不许你吃饭!”
这时,十三岁的那个孙子像是给阿玲助威似的说道:
“袈裟哥想娶池前家的阿松做老婆呢。”
他当众这么说出来,是想出出袈裟吉的丑。原来这个次男早就知道袈裟吉跟池前的阿松好上了。
“啪!”袈裟吉猛地抽了弟弟一巴掌,瞪大眼睛怒吼道:
“浑蛋!你给我闭嘴!”
辰平大吃一惊,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从未想过袈裟吉娶媳妇的事情。这个村子里流行晚婚,没人会在二十岁之前娶媳妇。而且他也被袈裟吉敢于反对他续弦的胆量给镇住了。
就连山歌中也有鼓励晚婚的歌:
过了三十也不算晚
添加一人就翻倍了
所谓“翻倍了”是指口粮翻倍,也暗示村里的食物极度匮乏。因此无论是阿玲还是辰平,都做梦也没想到袈裟吉要娶媳妇了。
流经村子的那条潺潺小溪,在半道上形成了一个池塘,于是人们就把位于池塘前的一户人家称作“池前家”了。那家有个叫作阿松的女孩,阿玲对她也是很了解的。尽管阿玲刚才对袈裟吉暴跳如雷,可火气消退了以后一想,就觉得那无疑是不明事理的恶老太婆的丑态。因为她这会儿已注意到那个阿松已经是个成熟的女人,袈裟吉也是个大人了。刚才突然受到袈裟吉的顶撞,不由得又惊又气,可这会儿她甚至觉得,这两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而自己却毫无察觉,实在是有些过意不去。
这时,袈裟吉已经离开饭桌,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到了第二天,就是祭祀当日了。孩子放开肚皮吃饱了“白萩花”后就跑去祭祀场了。所谓“祭祀场”,就是位于村子正中央的一块平地。虽说这是个夜祭,可孩子们却从一大早起就聚集在这儿了。他们在祭祀场上跳起了盂兰盆舞。说是跳舞,其实也就是两手拿着长柄勺,围成一个大圆圈,边敲边走罢了。辰平和孩子们不知道上哪家玩去了,所以家中只留下阿玲一人。
中午时分,家门前的树墩儿上坐着一个女人,脸冲着外面,身旁还放着一个信玄袋(9),像是在等什么人。
其实阿玲打刚才就寻思开了:这女人莫非就是从“对面的村子”过来的儿媳妇?可她转念又想:要真是的话,就应该进屋来吧。所以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今天过节,兴许是从“对面的村子”来这儿的哪家串门的,走累了,在这儿歇歇脚亦未可知。可是,那个信玄袋鼓鼓囊囊的,怎么看也不像是一般的访客啊。最后,阿玲终于按捺不住好奇心,出门问道:
“我说,不知道您是哪位,莫非是来这儿过节的?”
谁知那女人用不拘礼的口吻反问道:
“这儿就是辰平的家吗?”
阿玲心想:还真是儿媳妇来了。
“您是从‘对面的村子’过来的阿玉吗?”
“是啊,我就是阿玉。我们家也忙着过节呢。大家都让我上这儿来过节,所以我今天就来了。”
阿玲揪住了阿玉的袖子,说道:
“那就快进屋吧。”
阿玲腾云驾雾似的满屋子乱转,将过节时吃的好饭菜全摆在了阿玉的跟前。
“来,来,快吃吧。我这就去把辰平找回来。”
“嗯,他们说不要在家里吃,还是到这儿吃为好,所以我早饭前就动身了。”
“来,来,快吃吧。别客气。”
阿玲心想:你这话可就多余了。原本还以为你昨天就过来的呢。你就说吃了早饭来的又有什么关系呢?你说吃了来的,我也照样会马上给你上饭菜的嘛。
阿玉边吃边聊了起来。
“大家都说婆婆你是个好人,都叫我‘快去,快去吧’。”
阿玉吃得津津有味,阿玲则乐滋滋地望着她。
“上次来的人是我哥。他说婆婆是个好人,所以我也想早点过来。”
阿玲不由得朝阿玉挪了挪身子。她心想:这个媳妇性子直,说的都是心里话,不是拍马屁。
“你再早点来就好了。我还以为你昨天就会过来呢。”
说着,她又朝前探出了身子,但随即就意识到,靠得太近,会被对方看到自己的一口好牙,于是又赶紧用手掩住了嘴,收紧了下巴。
“所以说,你干吗老在那树墩儿上坐着呢?早点进屋来就好了嘛。”
阿玉微微一笑,说道:
“我是一个人来的嘛,有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哥哥原说要送我来,可他喝过节用的米酒,喝得酩酊大醉。‘婆婆是个好人,你快去吧。’——从昨晚开始,他翻来覆去地就说这么一句话。”
被人夸成这样,阿玲心里乐开了花,连身子都有些飘飘然了。她不由得暗忖:这位媳妇可比死了的那个好。
“哦,是这样啊。早知道这样,我就去接你了。”
阿玉说:
“那敢情好啊。你要是来接我,我就会把你背回来的。”
阿玲心想,看这个女人,还真是会把我从“对面的村子”翻山越岭地背回来吧。以至于她为自己没去接阿玉,甚至都没动过这个念头而后悔不已了。当然了,就那么一座山,凭着自己的身子骨,不用她背也能翻过来。可阿玉要背着自己翻山过来的这份好心,令阿玲欣喜万分,简直都想给她磕头下跪了。
有件事,阿玲想早点告诉阿玉,那就是,自己一过年就要“上楢山”了。她那个飞脚哥哥来的时候,阿玲跟他讲的第一件事,也是这个。
阿玲无心地望了阿玉一眼,见她正将手绕到背后摩挲着。像是吃东西噎着了。阿玲转到了阿玉的背后,本想说一句“你慢慢吃好了”,可又有点拿不准,不知道这么说会不会被人觉得自己小气,一时间反倒不知说什么好了。随即她又想到,还是不说了吧,等会儿自己去找辰平的时候,她一个人会慢慢吃的。
于是阿玲就站在阿玉的背后,替她摩挲着脊背,随后说道:
“我呀,一过了新年,就要上山去的。”
这话出口后,阿玲的手就停了下来。阿玉也一时无语,过了一会儿才说道:
“我哥也跟我说过这事儿。不过他说这事儿也不用着急的。”
“那怎么行呢?早点去,才能早点得到山神的赐福嘛。”
还有一件事情阿玲也想马上就跟阿玉说。她将饭桌正中间的一个盘子移到了阿玉的跟前,那是满满一盘的炖马哈鱼。阿玲觉得必须将这马哈鱼的事也马上告诉阿玉。
“这些个马哈鱼,都是我给捉来的哦。”
马哈鱼号称“河鱼之王”,晒干后可是山中极为珍贵的美味。阿玉露出了不敢相信的神色,问道:
“婆婆,你能捉住马哈鱼?”
“是啊。辰平也好,袈裟吉也好,他们都很差劲。要说这一手,村子里没一个及得上我的。”
阿玲想在上山前,将自己唯一拿手的本事,也即捉马哈鱼的秘诀,传授给阿玉。
她两眼放光地说道:
“我呀,知道马哈鱼藏在哪儿,这可是跟谁都不能说的哦。回头我会教你的。夜里摸过去,只要将手伸进洞里,一抓一个准儿。呵呵,这可是跟谁都不能说的哦。”
说着,阿玲就将装着炖马哈鱼的盘子塞给阿玉,说:
“这些个,你全吃了吧。吃吧。鱼干还有好多呢。”
随后她就站起身来,说了声“我去叫辰平回来,你接着吃”就从后门口出去了。
阿玲走进了一间放杂物的堆房。今天她被阿玉一口一个“好人”地夸着,心里乐呵得不行,于是决定要使出今生今世最大的勇气和力气来。她闭上眼睛,将门牙“咔——”的一声磕在石磨棱上。她觉得嘴巴一阵发麻,仿佛已经不是自己的了。还觉得口内热乎乎、甜丝丝的,牙齿在里面滚来滚去。她用手捂住了嘴里往外直冒的鲜血,踉踉跄跄地跑到小溪边,漱了漱口。两颗断牙从嘴里掉了出来。
“啊,怎么才两颗呀?”
阿玲大失所望。不过由于是上面并排着的两颗门牙没有了,觉得嘴里空荡荡的,让她觉得也还行。
这时,袈裟吉喝着“白萩花”酿造的米酒,已经酩酊大醉了,正在祭祀场上唱他的“鬼牙歌”呢。而磕掉了牙齿的阿玲,嘴里的什么地方像是也受了伤,甜丝丝的鲜血不住地往外冒。
止住。快止住。她心里这么想着,不停地用手舀着水漱口,可这血却老也止不住。
尽管这样,她心里还是挺高兴的,觉得缺了两颗门牙已经很不错了。想来是之前用打火石敲过的缘故,今天才能一下子就磕掉。看来用打火石敲打的功夫也没白费。
阿玲像是要将脸蛋浸到小溪里似的,不停地吸水漱口随即又吐掉,渐渐地,血止住了。只是口腔内还有些火辣辣的,但就这么点疼痛她已经不当一回事儿了。为了让阿玉看看自己牙口不好的模样,她又回到了家里。阿玉这会儿还在吃着。
阿玲在阿玉的跟前坐了下来,说道:
“慢慢吃,多吃点。我马上就去叫辰平回来。”
随即她又说道:
“我已经到了要上山的年岁,牙齿不行了。”
阿玲用上面的牙齿咬住下嘴唇,噘起了嘴,像是只给人家看她上面的一排牙齿。
这下可好了,总算是全都安排妥当了。阿玲乐呵得简直想手舞足蹈。她又离开了家,十分神气地朝祭祀场走去。心想,找辰平的时候遇到了村里人,也要让他们看看自己的牙齿。
祭祀场上,袈裟吉正领着大伙儿唱“鬼牙歌”,不料阿玲张着嘴突然冒了出来。并且刚才一度止住的血,又开始往外冒了。至于他们唱的什么歌,阿玲一句也没听到。找辰平成了她到处展示她那口缺牙的最佳借口。她的全副心思都用在这上面了,根本听不进去什么山歌。
聚集在祭祀场的大人小孩,一看到阿玲的嘴巴,全都“哇——”地大叫一声,四散奔逃开了。原来阿玲见到大伙后,非但闭上了嘴,用上面的牙齿咬住下嘴唇,让大伙看她上面的一排牙齿,还故意抬起鲜血淋漓的下巴给人看,那模样也实在是太瘆人了。见大伙一看到自己就逃跑,她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呢。
“啊哈哈哈……”
为了讨好人家,她还强颜欢笑着。
结果就是,阿玲磕掉了门牙,效果却适得其反,楢山祭过了之后,她也仍是村里的话题人物。
“树墩儿家的鬼婆婆”,背地里人们都这么称呼她,并且叫着叫着,有些小孩就真以为她是“鬼婆婆”了。
“被她咬上了就绝不松口的。”
“会被她一口咬死的哦。”
甚至出现了这些传言。
还有人用她来吓唬哭闹的孩子:“再哭,就带你到阿玲家去!”
傍晚时分,有些孩子只要在路上一遇到阿玲,就“哇——”地大哭起来,撒腿就跑。
事到如今,阿玲已经知道了那首歌,也很清楚自己被人叫作了“鬼婆婆”。
楢山祭一过,树叶就开始在寒风中飘零。天气冷的日子,已经跟冬天没什么两样了。辰平还是老样子,新媳妇上门后,仍是无精打采、浑浑噩噩的。
阿玉来了还不到一个月,“树墩儿家”里就又多了一个女人。
那天,“池前家”的阿松先是在树墩儿上坐着,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就坐到阿玲他们的饭桌边来,一起吃了起来。阿松吃起饭来十分快活,看她那表情,仿佛吃这件事令她兴奋无比,使她享受到了人间极乐。与此同时,她也吃得很多。她坐在袈裟吉的身边,就那么一声不吭地吃着。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阿松也跟袈裟吉并排坐着。她还不时地用筷子戳戳袈裟吉的脸,跟他调笑着。对于阿松的出现,阿玲和辰平夫妇也并不觉得讨厌。阿玲甚至还为自己从未意识到袈裟吉已经长大成人而感到羞愧。到了晚上,阿松就钻入了袈裟吉的被窝。吃午饭的时候,阿玲就看出阿松的肚子有些不同寻常,觉得像是有了五个多月的身孕了。“看样子新年里就该生了吧。早一点的话,或许就等不到过年了”——只有阿玲一人为这事儿担心。因为阿松要是早早地生下了孩子,她就看到“老鼠崽”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后,阿松就坐到了树墩儿上去了。她只在吃午饭的时候才进屋来,吃完后,就又坐到树墩儿上去了。快到傍晚的时候,阿玉对她喊道:
“阿松,你来灶下烧火吧。”
阿松烧火烧得很差劲,一会儿的工夫就弄得满屋子都是烟。最小的那个孙女都被呛得哭起来了。烟实在是太浓了,阿玉和阿玲都从屋里逃到了树墩儿那儿,最后连正烧着火的阿松自个儿也揉着眼睛跑出来了。
阿玉笑道:“干那事儿倒是挺在行的,烧火可还没入门啊。”
阿玲强忍着浓烟,跑到灶下用水浇灭了火。然后重新点火,很快,火就熊熊燃烧了起来。阿玲将被水浇灭了的那根阿松怎么也烧不旺的柴火扔到了外面,说道:
“你怎么把这玩意儿塞进去了?这是榉木啊,阿松,不能用它来烧火的。老话说,榉木烧饭瞎三年啊。”
随即她又小声嘀咕道:
“像我这样上年纪的人,瞎了也就瞎了。你们要是瞎了,可就糟了。”
阿玉说:
“既然阿松不会烧火,就来带孩子吧。”
说着,就让阿松背上了最小的那个女孩。小女孩由于被烟熏着了,还在哭个不停。阿松将小女孩背在背上后,使劲儿摇晃起肩膀来,嘴里还唱道:
“六根,六根,六根哟……”
听她唱出这歌来,阿玲和阿玉都惊呆了。因为这歌在平时是不唱的,只有在陪人“上楢山”的时候,或者是带孩子的时候才唱的。而在带孩子的时候唱“六根,六根,六根”的话,这歌又被称作“聋子晃”或“恶鬼晃”。
六根,六根,六根哟
带孩子看似轻松又不轻松
肩上沉重背上哭
啊,六根,六根,六根哟
阿松就这么唱了起来。这歌在唱到“六根”的时候,唱歌的人就会晃一下肩膀,想通过剧烈的晃动来止住孩子的哭声,同时也想通过大声吆喝来盖过哭声。晃动肩膀的幅度也很大,简直就是将孩子“咚”地一下子从右肩摔到左肩似的,想以此让孩子张不开口。所以与其说是在晃动肩膀,倒不如说是在虐待孩子。
陪人“上楢山”时,如果陪的人修为不够,或要遭报应的,就要唱这歌;对于不肯上山的人,陪同的人也会唱这个“聋子晃”歌。阿松不懂,只会一个劲儿地唱“六根,六根,六根”,其实这歌的最后,还要吆喝两遍“六根清净”,为的是洁净身心,消除罪孽。跳盂兰盆舞唱的歌跟这个“聋子晃”原本腔调不同,但也可以用同一个腔调来唱。不管哪个,都是楢山地区的山歌。
阿松一边摇晃着肩膀一边唱这歌,可她背上的小女孩却像是被火炙着了似的,哭得更厉害了。于是阿松摇晃得更厉害了,还唱起了下一首歌:
六根,六根,六根哟
你就号吧,讨债鬼,我有好东西要给你
反正我耳朵冻僵了,什么也听不到
啊,六根,六根,六根哟
这首“聋子晃”中所谓“号吧”云云是说你这个小鬼想哭就尽管哭好了,我会给你好东西的。“有好东西要给你”,其实就是去拧背上的小孩。同时还说你再怎么哭我也不怕,反正我的耳朵已经冻僵了,什么都听不到的。
阿玲活到这大把年纪,还从未背着孩子唱过“聋子晃”呢。阿松昨天刚来,今天就唱起这歌来,可见是个冷酷无情的女人。所以阿玲和阿玉听到后惊得目瞪口呆。
小女孩在阿松的背上又哭又叫,闹得比刚才更厉害了。阿玉实在看不过去了,跑过去将小女孩抱了过来,但那像是被火炙着了似的哭喊声并没有立刻止住。“莫非……”阿玉心中不免生疑。她将小女孩抱到阿玲跟前,撩起衣服看了下她的屁股,但见像是被拧出来的青紫块竟多达四处。阿玲与阿玉面面相觑,目瞪口呆。
自从阿松来了之后,袈裟吉倒是消停了,也不再说阿玲的坏话了,而是换了一套说辞。
“奶奶你什么时候上山呀?”
吃饭的时候他经常这么问。
“过了年马上就去。”
同样的事情被问了好多遍后,阿玲也只有苦笑了。
于是袈裟吉就会语速很快地说道:
“早点去的好啊。早点去——”
每次阿玉也都会用同样的口吻说:
“晚点去的好啊。晚点去——”
说完就捧腹大笑。
由于阿玉是紧接着袈裟吉的话,并且说得跟他一样快,显得滑稽可笑,连阿玲都跟着笑起来了。
家里多了两个女人,阿玲就有点闲得发慌了。她原本是个要强、闲不住的人,所以这么着就觉得有些空虚,甚至有些无聊了。阿松有时候也能帮上点忙。阿玲则有时候觉得不知所措了。不过,阿玲毕竟是怀有“上楢山”这么个目标的。她心心念念、反复盘算的,只有这一天。她心中暗忖道:你们虽然叫我“鬼婆婆”,可到了上山的那天你们就瞧好吧,我才不像钱屋的阿又那副熊样呢。我备好了那么多的好吃的,能把“上楢山”办得跟过节一样。白米饭、香菇、马哈鱼干什么的早就另外准备下了,能让家里人放开肚皮吃个饱。给村里人也准备了用“白萩花”酿制的米酒。虽说淡了些,可有将近一斗呢。当然了,这些,现在是谁都不知道的。等我进了山,第二天,家里人肯定会像饿虎扑食似的猛扑上去,狼吞虎咽,吃得津津有味的。“奶奶竟积攒了这么多?!”——到那时他们肯定会大吃一惊的。那时,我已经上了山,毕恭毕敬地坐在新草席上了。
如此这般,阿玲心里念叨着的,就只有“上楢山”这一件事。
狂风刮了一整天,又刮了一整夜,到了天快亮的时候,突然传来了奇怪的喊声:
“向楢山神灵请罪了!”
村里人这么嚷嚷着,四处一片混乱。听到喊声后,阿玲也从被窝里爬了出来,跌跌撞撞地冲到了大门口。虽说她已经上了年纪,可手里依旧攥了根棍子。阿玉也从一旁蹿了出来,背上捆绑似的背着最小的那个女孩,手里也抄起了一根粗木棍。
“在哪儿?”阿玲大叫道。
阿玉没有回答,脸色刷白,像是根本顾不上说话似的,立刻就跑了出去。这时,家里的其他人也已全都跑出去了。
小偷不是别人,就是雨屋家的男人。他偷偷地摸进隔壁的烧松家,正要偷走一草袋豆子的时候,被人家堵在里面一顿胖揍。
在这个村子里,偷粮食是最重的罪,要受到最严厉的制裁——“向楢山神灵请罪”。与此同时,小偷家里的粮食也会被抄出来分给大家。但必须是赶到现场、准备打架的人才有资格分粮食。因为,如果小偷反抗,那就要大打出手了,所以必须尽快赶到现场。并且,既然是急着赶去打小偷的,那就得赤着脚去,要是穿着鞋子去,则自己也会遭到群殴,所以赶去的人也都是拼了命的。这说明,在每个人的心里,粮食被人夺走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是早已刻骨铭心了的。
雨屋家的男人,这会儿已像一摊烂泥,浑身上下都动弹不了了。他在烧松家被逮住后挨了暴打,然后被抬到了祭祀场。他的家人也不得不坐在他的身旁。他们哇哇大哭着,却无能为力。接着,就是“抄家”了。一些身强力壮的男人在他家里翻了个底朝天,将所有能吃的东西全都扔了出来。看到那些被扔出来的东西后,大家全都惊得目瞪口呆。光是红薯就接连不断地被人从走廊地板下抛出来许多,居然堆成了一坪(10)左右的小山。他们家怎么可能种出这么多的红薯呢?要知道种红薯是必须先埋下红薯种的。由于红薯种也能吃,所以过完冬天后,无论哪家也都只剩下一点点了。再说,谁家种了多少红薯,村里人全都一清二楚,雨屋家所种下的红薯,顶多也只能有这“小山”十分之一的收成。不用说,这堆得跟小山似的红薯,肯定是从全村人家的地里偷偷刨出来的。
雨屋家这是连着两代人向楢山神灵请罪了。上一代是因为过冬时偷挖了山药吃。可当时就有人说,说不定他们是将粮食藏在山里的什么地方才度过冬天的。
“雨屋的血统就是小偷的血统,不把他们全家都干掉,我们晚上都睡不着觉了。”
人们小声商量着。雨屋家共有十二个人。
这天,一整天都没人干活儿。因为全村的人都情绪失控,怎么也收不住心。
阿玲家也这样,一个个的都直愣愣地发着呆。辰平伸开两脚,抱着脑袋坐着。
“这个冬天,我们家能平安度过吗?”
他在想这事儿。
雨屋家发生的事情,可不是跟自家毫不相干啊。辰平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并且十分严峻。应该说,是雨屋家的事件,一下子将该问题推到了他的面前。食物不足,这是明摆着的,可也不能去偷去抢呀。雨屋家有十二个人,辰平家也有八个人哪,且正在食欲旺盛头上的人也多,所以要说这日子难过,跟雨屋家也不相上下啊。
阿玲在辰平的身旁坐了下来。她也在担心过冬的事情。虽说每年都会为过冬而伤脑筋,但今年不比往常。因为,今年人口增多了,并且孩子们都长大了,所以比以往的哪个冬天都更难熬过去。还有就是阿松这家伙太过分了。阿玲甚至觉得:
“她不是来给袈裟吉做老婆的,看她那副吃相,像是被家里人赶出来的。”
阿玲觉得一准儿就是这样的。
阿松虽然是个女人,饭量却奇大。不仅如此,她还一点也不把东西够不够吃放在心上。煮豆子的时候,她总会说:
“都说在煮豆子的时候,越吃豆子越多。”
说着,就不停地吃了起来。
阿玲和阿玉都觉得她很不靠谱,心里没着没落的。其实那话说的是煮豆子时要多放水的意思。
有一次,辰平挖苦她说:
“阿松,要是越吃越多的话,那不吃不就没有了吗?”
阿松根本就没听懂,还一脸天真地反问道:
“是吗?真的吗?”
辰平实在忍不住了,高喊道:
“袈裟吉!你给我扇阿松的嘴巴!”
阿松这才停止吃豆。
辰平和阿玲都在想着过冬的事,阿玉其实也想着同样的事情:
“我们家吃起饭来有点胡来啊,非得分好了各吃各的才行。”
这时,袈裟吉扬扬得意地说道:
“今天我立了大功了哦。”
确实,他今天早上是出了大力的。外面闹起来的时候,他是第一个从家里冲出去的,抄家的时候他也是得力干将之一,所以他带回家的红薯也比较多。
阿松也坐在那儿。由于她肚子很大,又向前弯着腰,那模样跟青蛙差不多。不过她今天的脸色有些紧张。
阿玉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去堆房抱了一副石磨来,开始磨豆子。不一会儿,随着“咕噜咕噜”的磨盘声,黄色的粉末就开始从石磨的四周往下掉。看到这情形后,袈裟吉就唱了起来:
要吃豆子就先冻一下
老爸眼瞎看不见
所谓“先冻一下”,是说先把豆子在冷水里浸泡一下。因为豆子炒熟了吃,或者生吃的时候会发出“嘎嘣嘎嘣”的声响,会被瞎眼老爸发觉。而在水里泡软后再吃,就能一个人悄悄地吃了。歌中所谓的“眼瞎”也并非真的指瞎子父母,而是泛指眼睛不好的老年人。由于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容易饿,这歌就是在教年轻人如何瞒着长辈偷偷地多吃一点东西。
“他可真干得出来啊!”
这时,钱屋家的儿子嚷嚷着走了进来。
他所谓的“真干得出来”,其实是想说“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居然也干得出来”。事到如今,他还在为雨屋家男人所干的坏事而感到震惊不已。
“瞧!那些红薯尽是些小个的。”
他要说的是:很明显,那些红薯就是从地里刨出来的。
“我还纳闷儿呢,怎么种下的红薯只能收那么一点,原来都被他刨去了。所以,不是什么分了他的红薯,而是物归原主罢了。再说,被他刨去的还不止这些吧。”
辰平也是这么认为的。无论哪家,分到的远没有被刨掉的多。
钱屋家的儿子又说道:
“这个仇,非报不可。到了晚上,雨屋家的家伙肯定要来偷的!得早做打算才行啊。不然的话,怎么能高枕无忧呢?一定趁早将他们斩草除根啊。”
辰平说:
“斩草除根?他们一共有十二个人呢。”
袈裟吉听了,开玩笑道:
“傻瓜!挖个大坑,将他们全都活埋了……”
阿玉停下了手中的磨,也开玩笑似的说道:
“别介,这么一大堆人,还能往哪儿埋?”
钱屋家的儿子说: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哦。现在家家户户都停下了手中的活儿,正琢磨这事儿呢。”
他焦躁不安地扔下这么一句话后,就往外走了。这时,外面传来了乌鸦“嘎——嘎——”的叫声。
“你看,你净说这种话,连乌鸦都叫开了不是?”
听到阿玲这么一说,钱屋家的儿子就回过头来,说道:
“今天晚上,说不定会有人下葬的。”
一边说,他一边出去了。
后面的山里有块村里人的坟地。虽说村里食物不足,可遇到有年轻人死去,下葬后也还是要供一餐饭的。可这饭结果都是被乌鸦吃光的。因此,人们都说乌鸦最喜欢葬礼。还说乌鸦有种神秘的预感,能提前知道葬礼,并开心地叫。而乌鸦叫,也就被人看作葬礼的前兆了。
钱屋家的儿子回去后,大家都默不作声。一想到村子里杀气腾腾的,而从今天晚上起,雨屋家的人就会一个个消失,大家都不由得有些毛骨悚然。就连阿玉牵磨发出的“咕噜咕噜”声,听着都有些异样了。
这时,躺着的辰平突然开口道:
“妈妈,你明年要上山了吧。”
阿玲听了,觉得松了一口气。她是见辰平终于同意她上山而感到放心了。
阿玲赶紧接过话头来说道:
“‘对面的村子’里,我奶奶是上山去的,后来,我婆婆也上山去了,我当然也要上山去的。”
阿玉停下了手中的石磨,说道:
“没事儿的,生下了‘老鼠崽’,我会丢到山沟里去的。奶奶你不会像榧树家的那样,被人编进歌里去的,放心好了。”
袈裟吉听了就不服气地说道:
“什么呀?我去丢好了,管什么呀?”
所谓“管什么呀?”就是“有什么关系呢?”的意思。
接着他又朝着阿松说道:
“说好了我去丢的,是吧?”
阿松答道:
“嗯,这事儿,就有劳你了。”
大家一齐把眼光射向了阿松的大肚子。
阿玉手中的石磨又“咕噜噜”地响了起来,就跟远处传来的隐隐雷声似的。大家又不吭声了,见此情形,袈裟吉又大声地唱起歌来。他撩起衣服的下摆,盘腿而坐,将袖子一直卷到肩膀上,大声唱道:
老爸你快出来看,枯树又长新芽了
不能不去啊背上背架
近来袈裟吉的山歌大有长进,腔调像模像样的。阿玲也觉得袈裟吉唱得很在行。可今天他唱的这歌不太正经,虽说也是从前就一直这么唱下来的,可他唱着唱着就跑调了,叫人听着不是味儿。
“袈裟吉,哪有这样的歌呢?是‘山上着火了,枯树发新芽’。”阿玲指点他道。
“咦?钱屋家老叔就是这么唱的呀!”
“傻瓜!从前,有一次山上着火了,大伙儿都跑上山去,所以才有了这首歌。是吧,辰平?”
说着她看了一眼辰平,见他正仰面朝天地躺着,额头上搭着一块抹布,一直盖到了眼睛那儿。
阿玲不动声色地瞟了辰平一眼,突然觉得他真可怜。张罗着过冬就够艰难的了,陪着“上楢山”也绝对是一件苦差事。“明年要上山了吧”——虽说直到刚才,他才说出这句话来,其实他是一直将这件事放在心上的。想到这儿,就越发地觉得他可怜了。
阿玲挪到辰平的身边,掀掉了他头上的抹布。她看到辰平的眼睛亮晶晶的,便后退了几步,又赶紧离开了。她心想:他眼里亮闪闪的,莫非流眼泪了?唉,怎么能这么没出息呢?
她斜眼凝望着辰平的眼睛,心中暗忖: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帮他渡过难关!
石磨声停了,阿玉跑出去到屋前的小溪边去洗了把脸。刚才她也停下了手里的活儿,去洗过一把脸。
“她也哭了吗?这可怎么好?怎么都这么没出息呢?尤其是辰平,得更强硬些才好啊。都这么软绵绵的怎么行呢?”
袈裟吉又唱了起来:
山上着火了,枯树发新芽
不能不去啊背上背架
这次他是正儿八经地唱的。“枯树发新芽”那句应该是用“御咏歌”(11)的调子唱,可他唱得跟“浪花节”(12)似的,十分感人。
当他唱到结尾处的“背上背架”时,阿玲不由得喝彩道:
“哎哟喂!唱得好!”
第三天的半夜里,外面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听上去人数很多,都是从阿玲家门前经过往后山去的。翌日,全村人都知道雨屋家的一家人都已不在这个村子里了。
“别提起雨屋家的事儿了哟。”
村中这么约定后,从此就再也没人说三道四了。
一进入十二月,就是严冬了。由于说的是阴历,所以在月半时分就入寒(13)了。听到孩子们嚷开“雪婆婆飞起来喽”后,阿玲便斩钉截铁地说:
“我上山的时候,肯定会下雪的。”
所谓的“雪婆婆”,是一种白色的小飞虫。据说在下雪前,这种小白虫会在空中飞舞。
阿松的肚子越来越大,毫无疑问,已经到了即将临盆的程度了。她的举动和气喘吁吁的样子,也十分引人注目。
就在过年的前四天,阿玲一大早就在等辰平起床,随后又将他带到外面,在他耳旁说道:
“今天晚上我要请上过山的人过来,快去跟大伙儿说一声。”
阿玲已经决定明天“上楢山”了。所以想在今晚把进过楢山的人都叫来,请他们喝酒。
“还早啊,过了年再请吧。”
辰平一直以为母亲要过了年才上山,所以现在听说明天就要上山,不免有些惊慌失措。
“傻瓜。虽说是早了点,可还是早点好呀。趁着‘老鼠崽’还没生下来。”
辰平有些不太起劲,故而没吭声。阿玲又说道:
“快去跟大伙儿说呀!磨磨蹭蹭的,一会儿大伙儿就都上山去了。”
她的口气中包含着一种辰平不得不服从的强大的力量。辰平出去后,她又追着他的背影喊道:
“你听好了,一定要去请来哦。要不,明天我就一个人上山了!”
当天夜里,被请来的人在阿玲的家里济济一堂。在“上楢山”的前一天晚上,要请人来喝酒,这是规矩,而受邀请的,则仅限于上过楢山又回来的人。这些人在喝酒的同时,也会指导一些上山时的注意事项,而他们这么做既是为了说明情况,也有着宣誓的意味。指导的时候,也有着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那就是每人只指导一条。受邀前来的共有八人,七男一女。其中的一名女性,是去年陪人“上楢山”的。由女性做陪同,是很少见的。一般而言,家里没人陪同的,会请外人陪同,陪同上山的人基本上都是男性。被请来喝酒的八人中,最先陪同人上山的那个自然就是老前辈了,他是最有发言权的,也是八人中的头儿,喝酒也要他先喝。就是说,在此场合下,一切都按照上山的先后顺序来定。
今晚的老前辈,是一个被叫作“急性子阿照”的人。阿照五十来岁,其实他的性子并不急,相当稳重,因为他家上几代人中有性子很急的人,所以就这么叫他了。因此,这个“急性子”与其说是他的绰号,倒不如说是他家的“招牌”更确切些。
阿玲和辰平虽说是在家里招待客人,却是自己坐在正面,让客人们并排坐在对面的下首座位上。阿玲和辰平在大伙儿的跟前放了一个大酒坛子。这就是阿玲为了今夜而早早预备下的,用“白萩花”酿成的米酒,分量将近一斗。
阿照率先对着阿玲和辰平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随即,其他客人也都朝他们鞠躬行礼。
阿照对辰平说道:
“‘上楢山’是要人陪的,辛苦你了。”
按照规矩,阿玲和辰平在这种场合下是不能开口的。
阿照说完后,就捧起酒坛子递到自己的嘴边,“咕咚咕咚”地喝了起来。随后,他就将酒坛子递给下一位。那人只喝酒,不说话。就这么着,酒坛子转了一圈后,又回到了阿照的跟前。
阿照这次对着阿玲,用背书似的口吻说道:
“‘上楢山’时必须守规矩。其一,上山后不准说话。”
说完后,他又对着坛子口,“咕咚咕咚”地喝起来,然后递给下一位。
这些规矩,其实无论是阿玲还是辰平,都在平时的交谈中听说过,所以早就了然于胸了。但在这种场合必须重新听一遍,因为这也是习俗的一部分,并且还含有在客人面前起誓的意味,所以他们都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
酒坛子又转过来后,阿照就将其放到了下一位的面前。那人也跟阿照似的,用背书似的口吻说道:
“‘上楢山’时必须守规矩。其一,离家时不能让任何人看到。”
说完后,他就对着坛子口,“咕咚咕咚”地喝了起来。酒坛子转过去后,这次被放在了第三位客人面前。那人也用跟阿照相同的口吻说道:
“‘上楢山’时必须守规矩。其一,从山上回来时,不能回头看。”
说完后,他就对着坛子口,“咕咚咕咚”地喝了起来。酒坛子转过一圈后,这次被放在了第四位客人的面前。其实“规矩”在轮到第三位客人的时候就已经讲完了,这第四位客人说的是“上楢山”的路线。
“上山的路是这样的:绕过村子后山的山脚,从下一座山的柊树下走过,绕过这座山的山脚,爬上第三座山后就能看到池塘了。绕过三个池塘后,爬上第四座山的山顶后,就能看到对面的楢山了。这时,你要从山谷左侧和下一座山的右侧之间往前走。绕过山谷大约有二里半(14)的路程。途中有一条有着七个拐弯的道路,那儿就是‘七谷’。过了‘七谷’,前面就是上楢山的道路了。说是有路,其实也似有若无,你只管在枹栎树林间往上走就是了,楢山的神灵在那上面等着呢。”
他说完后,就把酒坛子往下传。至此,该教导的规矩也就结束了。按规定,这时就谁都不能说话了。也就是说,整个过程中,除上面四人说些教导的话之外,其他人都不准说话。接下来,就是大家一声不吭地轮流着把酒喝完了。不过要是谁喝够了,也可以默默地离去。结果,最后一个走的是阿照。大家都回去后,阿照也站起身来,可他又朝辰平招了招手,把他带到了屋外。
阿照对辰平低声说道:
“你要是不乐意,也可以不上楢山的,到了‘七谷’那儿,就可以回来了。”
虽说周围一片漆黑,连个鬼都没有,可阿照说这话的时候还是四下里望了一下,显得鬼鬼祟祟的。
“他怎么说出这种话来了?”
辰平觉得十分奇怪,心想,阿玲她那么一心想“上楢山”,我怎么可能照他的这话去做呢?所以辰平只当这话是耳旁风,根本就没当回事儿。
阿照马上又补了一句:
“我说这话不能让第三个人听到,也就说说罢了,听不听随你。”
说完,他就回去了。
大家都回去后,阿玲和辰平就都钻入被窝了。可由于明晚就要“上楢山”了,阿玲根本就没有一点睡意。
大约在半夜里的丑时三刻(15)左右吧,阿玲听到外面有人在哭。
是一个男人在号啕大哭的声音。这哭声越来越近,来到了阿玲家的门前。不仅如此,还传来了像是为了盖过哭声而唱的“聋子晃”的歌声:
六根,六根,六根哪
陪伴的人看似轻松不轻松啊
肩上沉来背上重
啊,六根清净,六根清净
阿玲在被窝里抬起头来侧耳静听,听出了这是钱屋家阿又的哭声。
“真不像话!”她不由得在心中骂了一句。
过了一会儿,她听到有脚步声过来了,门板上还响起了被人用手指抓出来的声音。
“怎么回事儿?”
阿玲一骨碌爬起身来,来到了檐廊上,打开了那扇吱吱作响的门。只见外面月光十分明亮,阿又缩作一团蹲在那儿,遮住了脸,浑身瑟瑟发抖。
这时,又“啪嗒啪嗒”地跑来了一个男人。是阿又的儿子,手里攥着一根粗草绳。他站在那儿,两眼瞪着自己的父亲。
“辰平,辰平!”阿玲高声喊道。
辰平像是也还没睡着,立刻就跑了出来。辰平与钱屋家的儿子打了照面,看到了他手里攥着的绳子,问道:
“怎么了?”
“他咬断了绳子逃回来了。”
说完,他又恶狠狠地瞪着自己的父亲。
“真不像话!”
辰平心中暗忖道。他是为钱屋儿子的荒唐行为感到震惊。
“真不像话!”
阿玲则是为阿又的这副熊样而感到震惊。
从前,有这么一首山歌:
被“聋子晃”呀摇晃着
绳子晃断了呀缘分也断了
歌里唱的是,摇晃得太厉害了,连绳子都晃断了,可既然说他是将绳子咬断的,就比歌里唱的更过分了。于是,阿玲就跟呵斥似的对阿又说道:
“阿又,被‘聋子晃’那样的,确实无趣,可你还活着呢,就跟山神和儿子都断了缘分,又算怎么回事儿呢?”
阿玲是在用她自己觉得正确的想法开导阿又。
辰平说道:“今夜就不去了吧。”
说完,他就背起阿又,把他一直送回了钱屋家。
第二天夜里,阿玲严厉催逼着有些磨磨叽叽的辰平,踏上了“上楢山”之路。天刚黑的时候,她就淘好了明天大家要吃的“白萩花”,香菇和马哈鱼干的事儿也吩咐了阿玉。看到家里的人都睡觉了,四下里静悄悄的,就悄悄地打开了屋后廊檐处的门。外面,辰平正背着背架等着呢。那天夜里没有风,却特别冷,天空阴沉沉的,没有月光,辰平简直跟盲人似的走在漆黑一片的路上。阿玲和辰平走后,阿玉从被窝钻出来,开门来到了屋外。她手扶着树墩儿,在黑暗中凝视着前方,目送他们远去。
辰平绕过后山的山脚,来到了柊树下。这树长得枝繁叶茂,巨大的树冠像一顶大斗笠,下面一片黑咕隆咚,从树下走过,就跟走进屋子里似的。到这儿为止,辰平以前也来过的,再往前,就是传说中的不“上楢山”就不得随便走的道路了。通常是不从柊树下穿过,都是或左或右地绕着走的,可现在必须笔直地往前走。绕过了第二座山的山脚,再绕过第三座山的山脚,池塘就出现了。这时,天空微微地有些发白了,而绕完池塘之后,已是天光大亮了。石阶共有三级,再往上就是很陡的坡道。这第四座山,是必须往上爬的。山很高,越靠近山顶,山路就越险恶。
爬到了山顶上之后,辰平不由自主地瞪大了眼睛:对面的楢山一清二楚,就像是正等着他们似的。脚下的这座山与楢山之间,隔着一道很深很深的山谷,简直叫人联想起十八层地狱来。要去楢山,就得从山顶稍稍往下走一点,然后沿着一条像是沿着山脊似的小路往前走,右边是悬崖,左边是陡坡。山谷被四座山包围着,深得跟地狱一般,所以辰平不得不一步步踩踏实了慢慢地往前走。他被告知,绕过这个山谷,要足足走二里半的路程,可这也仅仅让他明白,楢山是越来越近了,而他也只有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而已。他觉得,自从看到楢山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成了住在那儿的神灵的仆人,自己必须遵从神灵的命令,一步步地往前走。
随后,他来到了七谷。抬头望去,楢山就跟坐在了他跟前似的。他被告知,过了七谷,前面的路就似有若无了,所以他就一个劲儿只管往上爬。这里的树,全都是枹栎树。辰平心想,终于来到楢山了,于是便拿定主意,再也不开口了。其实,阿玲自从离开家门,就什么话都不说了。辰平一边走一边跟她搭话,她也从不回答。辰平不停地往上爬,可不论爬得有多高,周围也还都是些枹栎树。最后,终于爬上了一个像是山顶的地方。在经过一块很大的岩石的时候,他发现岩石后面好像有人。辰平吃了一惊,不由得倒退了几步。仔细一看,发现原来那是个死人,身体蜷缩着靠在岩石上,双手紧握,如同合十一般。辰平站定了身躯,一动也不动。这时,阿玲突然从背后伸出手,朝前挥了挥,似乎在吩咐他“快往前走”。
辰平继续往前走着。走到前面的一块岩石处,发现其背后有一具白骨。两条腿的腿骨还是整齐地并排在一起的,脑袋滚落在一边。肋骨跟刚才那个死人一样,也是靠在岩石上的。两条胳膊的骨头散落在两边,与身体离得很远。整具骨骼七零八落,就跟有人恶作剧,故意这么摆放似的。阿玲又朝前挥了挥手,催促辰平快走。事实上只要是有岩石的地方,必定有尸骸。再往前走,连树根处也有尸骸了。还有一具刚死不久的尸体,看着跟活人似的。走到那跟前的时候,辰平吓了一跳,又停下了脚步。因为,眼前的这个死人居然动了一下。他仔细端详了一番那死人的面孔,发现他确实已经死了。“可他刚才确实动了一下呀。”——辰平心中大骇,两腿也僵硬了。不料这时,这个死人又动了一下。是他的胸口处动了一下。辰平定睛一看,原来那儿有一只乌鸦。由于那死人穿着黑乎乎的衣服,乌鸦蹲在那儿一下子看不出来。辰平用力跺了跺脚,可那只乌鸦根本不逃。他从死尸旁经过,继续往前走。这时,那只乌鸦突然飞了起来。它静静地舒展开翅膀,悠然自得地盘旋而上,不慌不忙的模样实在可憎。辰平不经意地回头望了一眼那个死人,却发现他胸口还有一只乌鸦。“原来刚才那儿蹲着两只乌鸦啊”——他才这么一想,又发现那乌鸦的下面,还有一只乌鸦的头在动呢。原来那死人摊开手脚,肚子里面已经被乌鸦掏空后做了窝了!“或许他肚子里面还有乌鸦呢”——一想到这儿,他不由得感到又恶心又恐怖。
这儿虽然已经是山顶了,可路还在往上延伸着,并且越往上走,乌鸦就越多。辰平一走动,乌鸦们也走动了起来,仿佛这一整片地方都动起来了。乌鸦踏在枯叶上发出“沙沙”声,就跟人的脚步声似的。
“这山上的乌鸦真多啊。”
乌鸦的数量如此之多,令辰平感到震惊。乌鸦给人的感觉一点也不像鸟,它们的眼睛就跟黑猫似的,行动起来慢条斯理的,看着就叫人恶心。从这儿往前,东倒西歪的尸骸也越来越多了。稍稍再往前走一点,就来到一个光秃秃、到处都是岩石的地方。那里遍地都是白骨,仿佛积雪似的白茫茫的一大片。辰平低头看着脚下,尽量避开白骨一步步往前走,但也难免两眼发花,差点被绊倒。他心想:“这些白骨中,肯定也有生前我认识的人吧。”突然,他发现白骨中还有一只木碗。他不由得站定了身躯。
“真了不起啊!”
他由衷地感到佩服。居然有人到这儿来还带着木碗。他心想:之前来的人中,竟有想得这么周到的。同时,他也为自己没带一只碗来而懊恼不已。
有一只乌鸦蹲在岩石上,滴溜溜地转动着眼珠子。辰平捡起一颗石子,“啪”的一声扔了过去,那乌鸦就“哗——”地飞了起来,随即,周围的乌鸦也全都飞了起来。
“它们还知道逃走,看来是不会啄活人的。”
明白了这一点后,辰平也就稍稍放心了。
路还在往上延伸着。又往前走了一段后,发现有一块岩石的背阴处没有尸骸。来到那岩石旁后,阿玲就拍起了辰平的肩膀,还不停地蹬着脚。她是在催辰平把她从背架上放下来。辰平将背架放了下来。阿玲从背架上下来后,就将挂在腰间的草席铺在了岩石的背阴处。然后解下系在自己腰间的一个小包袱,并要将其系在辰平的背架上。辰平瞪大了双眼,露出生气似的表情,将那个小包袱放到了草席上。阿玲从小包袱里拿出一个饭团放在草席上,随后又要将小包袱系在辰平的背架上。辰平把背架夺过来,再次将小包袱放到了草席上。
阿玲笔直地站在草席上,两手紧握着放在胸前,两肘左右分开,紧闭着嘴,一动不动地看着下方。她的腰里没扎腰带,取而代之的是一根绳子。辰平端详着一动也不动的母亲的脸。发现这张脸上已经显出死相了。
阿玲伸出手来,抓住了辰平的手。随后将辰平的身体转向刚刚来那个方向。辰平浑身发热,就跟浸泡在热水中似的,大汗淋漓,头上直冒热气。
阿玲紧紧地握了握辰平的手,然后“砰”的一下,在他背上推了一把。
辰平迈开了步子。他遵守誓言,头也不回地走了。
走出十来步后,辰平将没了阿玲乘坐的背架举起来,直指天空,大颗大颗的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他像喝醉了酒似的,踉踉跄跄地往山下走去。走了一小段路后,他就被尸骸绊倒了。他的手撑在身旁一个死人的脸旁。那是一张肉已剥落、露出了灰色骨头的脸。他正要站起身来的时候,又看到尸骸细细的脖子上还缠着一根绳子。看到这个,辰平不禁垂下了脑袋,自言自语道:“我是没这个勇气的。”随即,他又往山下走去。走到了楢山的半山腰的时候,辰平的眼前出现了一些白色的东西。他站定身躯,凝神观瞧,发现枹栎树之间飞舞着一些白色的粉末。
下雪了!
辰平不禁“啊!”地大叫了一声。
他出神地凝望着白雪。雪花纷飞,随风乱舞,并且越下越大。阿玲平日里曾斩钉截铁地说过:“我上山的时候,肯定会下雪的。”现在,果然下雪了。
辰平猛地转过身来,开始朝山上跑去。必须遵守“上楢山”的规矩、宣誓什么的,此刻已被他抛在脑后了。他要将“下雪了”这件事告诉阿玲。不,不仅仅是告诉,他更想与阿玲一起高喊:“下雪了!”“真的下雪了!”哪怕只喊一声也好。辰平如同猿猴一般,沿着被视为禁地的山道往上爬。
等他来到阿玲所在的岩石旁的时候,雪已经将地面都染白了。他偷偷地朝藏在岩石背后的阿玲望去。他已经破了“上楢山”的誓言,不仅回头看了,如今还回到了这儿,并且还要再破“不准开口”的誓言。这简直跟犯罪没什么两样。可是,正如阿玲所说的“肯定会下雪的”那样,老天爷真的下雪了。“下雪了”这句话,他是无论如何也要说的。
辰平朝岩石后面探出脸去,见阿玲正坐在他的眼前。她用草席盖住了头和肩膀,可她的前发、胸脯和膝盖上已经开始积雪了。她像一只白狐似的两眼望着前方的某一点,嘴里念着佛。辰平大声说道:
“妈!下雪了!”
阿玲平静地伸出手来,朝辰平的方向挥了挥。仿佛在说:“回去!你快回去!”
“妈!你很冷吧!”
阿玲连连摇头。
这时,辰平发觉,周围连一只乌鸦也没有了。他心想,兴许是因为下雪,乌鸦都飞到村子里,或是都躲在巢里了吧。下雪真好啊!比起被寒冷的山风狂吹来,还是蒙在雪中不怎么冷吧。妈妈她会这么睡过去的吧。
“妈!下雪了,你运气真好啊!”
随后他又加了一句歌词:“上山那天……”
阿玲点着头,又朝辰平发出声音的方向挥了挥手,催促他:“快回去!你快回去!”
“妈!还真的下雪了啊!”
说完这句,他就跟兔子一般地快步跑下山去了。他心想,坏了楢山的规矩这事儿,也不会有人知道的。
当他来到本该空无一人的七谷的时候,却看到钱屋家的儿子正站在雪中,将背架从肩上卸下来。背架上坐着阿又,像个犯人似的被粗草绳捆绑着。
“啊!”
辰平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
因为他看到,钱屋家的儿子正要将阿又从七谷那儿推下去。要将自己的老子推下被四座大山包围着的、深得如同地狱一般的山谷。——辰平的眼下正在上演的,正是这么一幕。
“这是要将他滚落下去呀。”
当辰平意识到这一点后,忽然想起了阿照昨天所说的话:“你要是不乐意,也可以不上楢山的,到了‘七谷’那儿,就可以回来。”
“原来他是在教我干这事儿啊!”
到这时,他才刚刚领会。
阿又昨夜逃脱了,可今天遭到了五花大绑。他根本不像个活人,而是像一口袋红薯似的滚落在一旁。他儿子用手推着,想把他滚下山去,可他却从横一道竖一道的绳子中间,伸出稍稍能够动弹的手指,死命地揪住了儿子的衣襟。他儿子将他的手指掰开,他又用另一只手的手指抓住了儿子的肩膀。此时,他的脚已经快要掉下去了。阿又跟他儿子就这么拼死争斗着。可从辰平这儿看去,他们就跟在不出声地耍闹似的。就在这时,只见那做儿子的抬起脚来,“砰”的一脚踢在他老子的肚子上。他老子便头朝山谷方向仰面朝天地倒了下去,又滚了两下,身子横着就咕噜噜地沿着陡峭的斜坡滚落下去了。
就在辰平要朝谷底下探望的时候,猛地从谷底下龙卷风似的升起了一股黑烟。仔细一看,原来是无数的乌鸦腾飞了起来。
“啊!是乌鸦!”
辰平感到十分恶心,不由自主地缩紧了身子。这些乌鸦“嘎——嘎——”地聒噪着,在辰平的头顶上高高地盘旋着。辰平心想,看来山谷下有乌鸦的老巢,下雪后乌鸦都躲进巢里了,而阿又掉下去时正好砸中了那儿。
不一会儿,满天乱飞着的乌鸦开始纷纷落回山谷了。
“要成乌鸦的美餐了吧。”
一想到这么多可恶的乌鸦就不禁发抖,可他转念一想,阿又掉到谷底的时候,恐怕已经死掉了。
辰平又朝钱屋家的儿子看去,见他想必也是见了乌鸦觉得十分恶心,此刻已经背起空背架,脚不着地似的跑了起来。
辰平望着那弓着的背,像一头狼似的狂奔着,心中暗忖道:
“既然要这么干,自然不用请人喝酒了。”
雪,越下越大。这会儿已成了鹅毛大雪了。辰平回到村子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回家后,小女儿肯定会因为阿玲不在了而寂寞难耐的。”
他心想,要是她问“奶奶什么时候回来?”我该怎么回答呢?
来到家门口后,辰平首先站在外面张望了一下屋里的情形。
见屋里二儿子正唱着歌跟小女儿玩。
老婆婆呀扔到后山去
后山呀爬出螃蟹来
辰平心想,自己不在家的时候,孩子们已经谈论过阿玲的事儿了。他们已经什么都知道了,所以才翻来覆去地唱“螃蟹歌”。
爬来后也不让进门呀
螃蟹可不是夜哭鸟呀
这歌唱的是从前村里将老年人扔到后山去的事情。有一回,一个老婆婆被扔到后山去后,又爬回来了。家人一边嚷嚷着“爬来了,爬来了,像螃蟹一样爬回来了”,一边紧闭门户,不让她进屋。家里的小孩子还真以为是螃蟹爬来了呢。老婆婆在屋外哭了整整一夜。听到哭声后,孩子就说:“螃蟹在哭呢。”家里人觉得跟孩子讲不清,就骗他说:“哭的不是螃蟹。螃蟹是不会在夜里哭的。那是鸟在哭。”所谓的“螃蟹歌”,唱的就是这么个事儿。
辰平站在门口,听着“螃蟹歌”,心想:孩子们之所以老唱这歌,是已经知道阿玲不会再回来了吧。想到这儿,他觉得心里轻松了一些。
辰平将背架从肩上卸下来,掸了掸雪,正要开门的当儿,看到阿松正从堆房里走出来。她那个大肚子上扎着的腰带,就是直到昨天为止还扎在阿玲腰间的条纹细带。堆房里面,袈裟吉正盘腿坐着。他身上披着昨夜阿玲叠得整整齐齐的棉袄,身边放着个酒坛子,里面是昨夜来客们喝剩的酒。他像是已经喝醉了,正乐滋滋地眯缝着眼睛,歪着脑袋嘟囔着:
“运气真好啊。下雪了。奶奶的运气真好啊,还真的下了雪了。”
一副悠然自得、由衷感佩的样子。
辰平站在门口,用目光寻找着阿玉的身影,可哪儿也没找到。
辰平忽然长叹了一声,心想,岩石后面的阿玲这会儿要是还活着,肯定披着满身的大雪,念叨着“棉袄歌”吧:
不管怎么冷呀
也不让穿着棉袄上山哟
楢山节
老爸你快出来看呀
枯树又长新芽了
不能不去呀
背上背架
夏天最讨厌呀
路上不好走
蜈蚣加长虫哟
还有赤链蛇
榧树家的阿银呀
是个臭婆娘
包着头巾呀
抱着老鼠崽
“聋子晃”之歌
六根,六根哪
六根,六根哪
陪伴的人看似轻松
不轻松啊
肩上沉来
背上重
啊,六根清净
六根清净
(1) 译注:日本旧地名,信浓国的简称。相当于现在的长野县全境。
(2) 译注:在祭祀祖先的盂兰盆节上跳的舞蹈。
(3) 译注:日本旧时传递信件、小件货物的快递人员。因跑得比较快,故称。我国古代称“急足”。
(4) 译注:白色的胡枝子花,因为也是白色的,所以被类比成大米。
(5) 译注:日本的旧国名之一,相当于现在除佐渡岛以外的新潟县全境。
(6) 译注:天保通宝的俗称。由江户幕府铸造于天保六年(1835),故称。椭圆形,中间开有方孔,币值百文,于明治二十四年(1891)停止流通。
(7) 译注:东南方。
(8) 译注:屋内没铺地板的地方。
(9) 译注:一种底部放一块平板,袋口穿绳收紧的手提袋。据说日本战国时代的著名武将武田信玄曾用这种袋子装过盒饭,故名。
(10) 译注:面积单位。1坪约合3.3平方米。
(11) 译注:僧人唱咏的赞歌。
(12) 译注:日本一种在三弦伴奏下说唱故事的曲艺形式。
(13) 译注:指小寒、大寒之节气。
(14) 译注:这里的“里”是日里。1日里为3.927公里。二里半就是将近10公里。
(15) 译注:凌晨2时3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