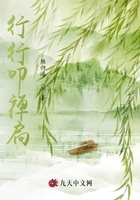
第8章 江上吟(6)
一个手里拿着纸鸢的小屁孩撞入他的怀中。他头上扎着两个双髫,系着两根红丝带,一身喜气洋洋的,肉嘟嘟且十分讨喜。
这小孩见纸鸢卡到了梨树上,惊落了一树的花苞,虽然很气愤,但看到面前的人,还是有模有样地道歉:“我错了,皇叔……”
男子的大手抚上他的发髻,梨花浅浅,白衣琴者,温柔的眉眼在阳光底下衬得更加和煦。
“那皇叔带你玩?”汝阴侯试探性问了一句。
“好啊好啊。”七八岁的娃拍手称快,眼睛眯成一条缝。
这没抓稳桌子,差点摔一跤,大概也是一片花海无人闯入,这位大名鼎鼎的汝阴侯竟把他抱在臂弯,拿个竹排给他绑上,满山上上下下拖来拖去。
叔侄俩玩得不亦乐乎。
只是后来汝阴侯请命去了雪荭关,后来又卷入风波葬身火海,一世清白,却落得个尸骨无存。
萧妃娘娘也整日以泪洗面。
世人不明白为什么好端端的就变成了这幅模样,红尘轶本里议论纷纷,甚至有说书人直接在皇城脚下说是汝阴候封号不好,克了长命的八字,应改做汝阳侯,还有个更过分的说法是洪乐不满汝阴侯两袖清风,不问世事的作态,宦官们在后面挑衅,洪乐帝大怒,于是借助一把火把汝阴侯暗杀了。
离当年的事已过去整整十二年,当年活泼调皮的小姑娘嫁做人妇,织桑裁衣的新妇发缕间也藏着些许白发。
知道这件事的人,早已进了棺材。
洪乐帝暴毙后,洪熙太子顺势继位,也就是现在的卫封。他一手抓民生,一手抓奸佞,终于用严苛谨饬的方法治住了这股汹涌的洪水,可到头来,也无人相知相会,留在回忆的,只是前朝揭开伤疤后,露出的嫩粉的肉。
这也是他心中永恒的痛。
而藏匿于深山老林的秘密,十二年后也终于被发掘出来了。
许乘鸾望着面前那张脸,记忆却却多年前错位重合。
“谢谢大哥!”许乘鸾察觉出来此举不妥,立即松开了手。
此时,角落的两人面面相觑,买糖人的大哥赶快拿起睡在柴草丛里的芦草靶子,愧疚感无处安放,手上的汗抹了还是在出,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低着头十分抱歉地说道:“妹子,那个……大哥不是故意的哈,如今看你平安无恙,大哥也就放心了,如果没有什么事大哥就走了……”
许乘鸾计从心生,扯着她的衣服,装模作样地掉了几滴眼泪:“大哥,我实在没地去了,你收留收留我吧!”
买糖人的大哥十分为难,正在此时,这些摆脱不了的刺客又追了上来,并冲着他们喊:“杀掉他们,咱们的奖赏很丰厚啊!”
两人:“……”
“我们快走吧。”买糖人的大哥皱了皱眉,并未跟这些刺客有正面冲突,而是退而求其次地躲了起来。
这一次,许乘鸾主动拉住了他的手。
这位买糖人的大哥即便手举靶子,仍旧未影响他健步如飞的速度。
倒是这些人提了刀,令许乘鸾害怕起来,尤其是天黑下来,两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竹林阡陌前行,除了两人彼此挂念的心,再者是蔓延开来的杀意。
由于许乘鸾身上的物件太多,她直好一边拆一边跑,身上的凤冠霞帔,余下的零件,如若不是下一顿吃什么,估计连这些银子都顺手扔掉。
于是画面就变成了这样,枯叶飘零的竹林里,后面是一群黑衣人,前面则是踩着松软土质,逃生的一对男女。
破庙外荒草丛生,还有几座孤坟,而蜘蛛网和残缺的佛像自然不必多说,晚风席席时,芒草轻拂,山丘异动,这般诡异现象,竟引来山魈也凑热闹。
寺庙里的门窗关不上的,连窗叶都老旧不堪,许乘鸾只好从边上捡些石头堆砌在一起,透是真的透心凉,买糖人的大哥有副好心肠,为了今晚能睡个安稳觉,在门外还步下了不少简易的陷阱,许乘鸾料想到今晚降温,在跪拜完佛祖后,寻了些稻草放到壁炉里烧掉。
看着火焰冉冉升起,许乘鸾安定了些许,买糖人的大哥却散不去眉心的忧愁,大概是怕那些黑衣人来犯吧,他一直保持警惕的姿态,始终崩紧了琴弦。
“看来今晚我们要在这里落脚了。”
许乘鸾没答话。
刚刚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这会刚缓上来,奈何脚踝处硌了一个大大的水泡,还有被尖刺划破的划痕。
“脚崴了?”
买糖人的大哥随口一问,许乘鸾的目光却不自觉地跟着他走,她仔细端倪起买糖人的大哥来,棱角分明的线条,布满老茧的大手,明明长得也不算俊郎,她居然也会觉得有点帅气,是怎么回事?
如若她回到十五年前,还是南阳太守许景宸捧在手心里的小女,如若没有嫁做人妇,她估计也会找一个寻常人家,过上相夫教子的生活吧!
“问你呢?”
他有点命令的语气,许乘鸾回过神来,脱了布鞋,只留米黄色的长袜。
她揉了揉痛处,龇牙咧嘴地说道:“鞋不合脚,走到一半起泡了。”
“脱下来。”买糖人的大哥冷冷的,许乘鸾不敢乱动,毕竟这个时候了,闹内讧不太合适,按照着他的指令照做了。
买糖人的大哥一把把她的脚拉进自己的怀里,大手摊开看了看伤势,疼惜:“你怎么这么多血痕?”
许乘鸾面色不改:“路上不小心伤到的,过两三天就好了。”
买糖人的大哥一口气全堵在嗓子里,她怎么这么不爱惜自己?要是以后遇上坏人了怎么办?
大哥不动声色,从衣兜里掏出一瓶药膏,端过许乘鸾的脚踝,一点点抚过她的肌肤,浅浅的刺痛从伤口传来,大哥的力度有点重,想必也是为了更好的入药,麻木的伤口重新活络起来,接着竟有丝丝的冰凉,浓厚的白色乳膏散发出浓厚的中药味,怎么掩鼻也遮不住,许乘鸾索性放开了,闭上眼睛仔细感受着这股若有若有的力气游走,恰到好处时,这样的磨蹭感却消失了,取而代之地是买糖人大哥无情地回应:“暂时不要穿鞋袜了,回去之后拿温水好好泡一泡,别再着凉了,也不要吃刺激食物。”
许乘鸾轻轻“嗯”了一声。
闷闷的,很不是味道。这比起平常的她来说,那可太不一样了。
好像经历了季槐暴走之后,她似乎成长了。
还没等许乘鸾开口,买糖人的大哥倒是问起来:“你还有事吗?”
许乘鸾心事重重地说:“你先睡吧,我怕冷,得烤暖了再睡。”
买糖人的大哥立即躺下,手枕在臂弯里,把佛垫让给了许乘鸾,翻过身去抱作一团,却夜不能眠。
过了一会儿,这位大哥朦朦胧胧中,依稀听见许乘鸾熄了火,就着稻草躺下,和他平行躺下。
“季槐?”
买糖人的大哥身躯一颤,虽知这是一场梦,也宁愿赴汤蹈火。
随之许乘鸾凑近,紧紧抱住了他。
“你虽未摘下面具,但我仍知你是季槐。”
买糖人的大哥忽然惊醒,但见许乘鸾的动作,似与他一样不曾熟睡。
黑暗里,只有彼此轻微的呼吸声。
外面风雨凄凄,落叶摩挲过大地,发出沙沙的响声。
似是自言自语,许乘鸾默然长叹道:“从你第一次抱住我我就知道了,你身上有股熟悉的松香,此后我一直跟着你,只是你这般,到让我想起某个故人来。”
那声音很小,可落在他的耳中,却带着女子的魅惑,轻易便将他的小心思俘获。
“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你,比如说这枚铜钱的来历,李笈为何疯疯癫癫的,追杀我们的人是谁,林丛身上背负了什么秘密,以及你为什么暗下救我,但我都忍住了,因为我在等你亲自告诉我。”
许乘鸾眼里闪烁着泪光,她一向知道,季槐从来是个三缄其口的人,即便她往冷石头拼命地凑,他也不会热忱半分。
她慢慢叙述着平生的故事,那声音像极了风雨,就这样浸润着他的心田:“开元十二年,从你来华清宫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一些事情,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何甘心为奴,也不清楚是谁褫夺了你的封号,但我也不外乎这些名利,只希望等真相真正浮出水面的那一刻,你还愿陪在我的身边,此生期许,不过如此。”
许乘鸾哽咽地说完这些话,却发现自己泪如泉涌,两颊流下了滚烫的泪水,身边的人没有反应,她也就收了几分。
等身边人沉沉睡去后,买糖人的大哥终于撕下了面具,露出了一张极为反常的脸,他再也按捺不住了,侧过身来在许乘鸾的额头上落下一吻。
凤娘,这就是我给你的回应。
季槐的开端,或许不止从开元初年说起,早在洪康帝还在世时,他就在南阳郡王府,见到了躲在太守身后,一嗅青梅的许乘鸾,他们一群孩子还约好一起去田园里追黄蝶,捉蜜蜂,身为孩子王的季槐当时年少无知,暗许乘鸾一定会是他将来的妻子,没承想一道御旨下来,却打破了他最美好的幻想,她作为宫女被选中,从此也嫁给了大了十五岁的洪乐帝。
而他也因为学业繁忙,被迫成为了下一代储君的选任,洪乐帝身子不好,常有个头疼脑热,还十分钟爱炼丹,一有事都是内侍几个在旁轮番服侍,有时不能亲临朝政,都是底下几个肱骨之臣代劳操办的,自有了这种无形的压力后,他便一直想摆脱困惑,直至想出了金蝉脱壳的法子,直至洪乐帝仙逝病榻,他才如愿地进入宫里,成为了华清宫唯一的侍从。
不过洪乐帝驾崩一年后,洪熙太子继位,底下抓得十分牢靠,不仅借助全国举丧的由头削弱了诸侯亲王的拥兵权,并且对待赋税服役方面也更加保守了,后来听说南阳那块投城了,被赠给了荞国,作为东泽海、符国与荞国商贾名流的麋集地,还赋上“新野”这般大名。所幸城主的根基还在,自许景宸后,这几代的太守都是许家人,只是他的乘鸾,再也回不了娘家了。
他想着来到开屏后,当成新的开始,没想到洪乐帝走了,洪熙帝又把他当成一块肥肉。
半夜电闪雷鸣,门外的风铃发出杂乱的响声,许乘鸾朦朦胧胧地从草席上爬起来,冷得哆嗦的同时,看了看披在身上的衣服。
黑衣人披着蓑衣,鬼鬼祟祟地攒动在破庙的四周,所幸他们没有飞檐走壁的本事,也没携带任何攀爬工具,就这么匆匆地潜伏在四周。
季槐常年同冷兵器打交道,一点风吹草动他都会警觉,许乘鸾听到外面窸窸窣窣,浑身起了鸡皮疙瘩,但想起季槐还要赤手空拳对敌,她便莫名受了鼓舞,想做男人背后的女人,勇气是必不可少的,许乘鸾刚想说你打算就这么出去嘛,季槐忽然从串糖人的靶子里取出一把威风凛凛的大刀。
许乘鸾:“说好的赤手空拳呢?”
她终于知道为什么季槐要随身带着芒草靶子了。
虽隔着厚厚的一尊佛像,许乘鸾还是可以看得到,季槐身穿粗麻,挥舞着大刀不费力,守在门口不让任何人靠近。
这些黑衣人很狡猾,知晓大门进不去,就从破烂的窗户进,许乘鸾看到刀在脖子间飞速落下,刺客血溅当场的画面,吓得双唇瑟瑟发抖,季槐却一身果敢,虽未有任何装束,凭借高超的武术驱动大刀,却不让刺客靠近许乘鸾一米。
甚至还拉着许乘鸾一起抗敌。
许乘鸾见一时刀光肃杀,她正打算开个玩笑缓和缓和气氛:“你这个刀可真……”
半晌,黑衣人的剑身发出嗜血的光芒,朝季槐横劈,竖立起来,季槐毫不畏惧,一个翻转将许乘鸾揽入怀中,单手对抗三五个刺客,耗尽力气后,又换了一只手,将黑衣人砍落在地。
许乘鸾看到几个倒下的身影,萌生了胆怯,但缩在他怀里反而更加不自在,只好拿起两个糖葫芦,假模假样地摆弄着。
等这群黑衣人攻上来时,却一手将黑衣人的脑袋使劲敲了几下,大概是山楂被麦芽糖完全包裹住了,竟然这么砸都不碎,倒是这群黑衣人哎呀几声,转眼就朝许乘鸾砍过来——
这是,刀与剑交融,厮杀声此起彼伏,雨夜里的几个身影已悉数倒下,只有几个嘴里咕嘟着什么奇怪的语言,随即被铺天盖地的风雨掩埋。
这一夜所谓多舛,搅得人难以安宁,许乘鸾还想着给这几位盖个墓碑,季槐却说他们不是平国人,大抵是从边疆招募来的吧,这群无家可归的浪子,最终还是变成了刀下亡魂。
许乘鸾正想求助季槐时,季槐却心平气和地和她解释道:“这只是第一波而已,他们的主子发现无功而返,肯定会再派人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为了节省时间,我还是抄近路送你回去吧?”
许乘鸾咯噔一下,心想:她好不容易逃出去的,怎么又给送回去。
季槐与许乘鸾相处十年之久,猜透了她那点小心思,却没点透,抿了抿唇继续说道:“跟着我跑,反倒是危机四伏,不如找个人照顾你。”
这句懂了,可是鞋小磨脚,就不能修一下吗?
“这是为了你好。”
季槐目光赤忱,看来说他没说假话了,许乘鸾转了一下脑筋,料想皇宫里应该是有人接应她吧,或许要杀他们的人就在皇宫之外。
这样的安排不算好,倒也不算太差。
既来之则安之吧。
许乘鸾挥了挥手,走在最前面:“荒山夜岭的,就走路回去啊?”
季槐看到她一下子轻松起来,倒没有之前的局促,他也有些不敢置信:“你想开了?”
许乘鸾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要不然能怎么办呢?此地不宜久留,与其过关斩将,不如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你不怕路上设伏?”季槐反问道。
“如若跟你一起,倒也无妨。”
许乘鸾的声音有种令人安定的魔力,说不上来什么感觉,但有季槐在,她便可以放心大胆地走夜路。
“你还没接我的话呢?”
许乘鸾淡淡地笑了笑,季槐慢了一拍,愣了几秒从怀里掏出一个口哨,重重地“呼”地一声,马蹄声由远及近,依稀见晨光中一匹烈马的身影浮现,它刚一停下,便嚼了嚼旁边的芒草,随即马腿双跪,棕红的马尾轻轻摇摆着。
很明显,它也是伺机已久。
许乘鸾见那马乖乖的跪拜,始终不敢上前,这马实在太高了,宽大的骨架,泛起油光的漂亮的棕红色,胃里真能塞条船似的,季槐抓起鞍鞯,骑在马背上英姿飒爽,又把手伸出来,叫她先上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