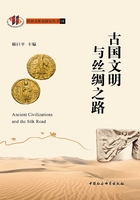
第二节 托勒密、塞琉古王国与丝绸之路
托勒密王国和塞琉古王国,是诸希腊化王国中最为强大、存在时间最长的两个大国。由于其统治重心在东地中海地区,尤其是塞琉古王国在公元前二世纪后期彻底失去了对两河以东地区的控制,它们与丝绸之路的直接联系要晚于远东的希腊人王国,但它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利用各自的区位优势,也以不同的方式和手段推动着东西方之间的交通和贸易。
托勒密王国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托勒密王国对红海、印度洋航路的探索上。公元前2世纪末,托勒密王国同印度建立了海上贸易往来,虽然这些交往的频率还很低,双方没有建立起常规的贸易交换,而且商品交换的种类我们也不得而知,但这些开拓性的尝试为后来罗马帝国与印度建立密切的贸易来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积极推动了公元1世纪由印度至埃及海上丝绸之路西段的贯通。
塞琉古王国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塞琉古王国在东西方陆路贸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塞琉古王国的疆域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覆盖了东西方商路的中亚至东地中海一段。公元前3世纪中期,虽然帕提亚帝国崛起,并在前2世纪中期占领了伊朗高原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但帕提亚人却担当了东西方贸易的中介角色,所以从印度、中亚到地中海东岸的商路并未中断。公元前2世纪末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之前,塞琉古王国的国内贸易及其与东方的贸易均取得了发展,这有赖于塞琉古王国的道路系统及其统一的币制。公元前2世纪后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从长安到中亚的路线正式连通,这也就意味着从中国到中亚、印度,再到地中海东岸的丝绸之路全线贯通,偏安一隅的叙利亚—塞琉古王国成为丝绸之路的西段终点及主要贸易市场,为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契机。
总之,丝绸之路正式开通前,托勒密王国已在积极探索通向印度的海上商路,塞琉古王国也在东西方陆路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之后,这两个王国的管辖地成为丝绸之路西段的终点。丝绸之路开通前后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构成了塞琉古王国、托勒密王国历史的一部分。
一 托勒密王国与海上丝绸之路
(一)托勒密王国时期内陆-红海方向的交通发展
托勒密王国(公元前305—前30年)又称托勒密埃及,由亚历山大部将托勒密一世(Ptolemy I,公元前305—前282年在位)开创。托勒密王国建立了许多中心城市,由内陆城市通向红海的商路得到发展。[87]除了尼罗河流域之外,托勒密王朝还占领了埃及的红海沿岸,这就使它与阿拉伯地区、波斯湾、印度进行海上贸易成为可能。托勒密二世(菲拉德尔弗斯)(Ptolemy II Philadelphus,公元前282—前246年在位)时代,首先在红海西岸科帕托(Kopato)东南的乌姆克塔夫(Umktarf)开发贝来尼凯港(Berenice),在那里建立了造船厂,[88]并且修建了从贝来尼凯到尼罗河港科普托斯(Coptos)的道路。[89]此外,托勒密王国大力开展至瓜达富伊角(Cape Guardafui)的贸易。公元前275年,托勒密二世重新开通了红海和尼罗河间的运河,[90]称为托勒密运河。通过海路进口的货物可以在红海沿岸卸载,然后转运至尼罗河港,最终到达亚历山大里亚。公元前247年,托勒密王国在贝来尼凯北建立密奥斯·荷耳摩斯港(Myos Hormos)。[91]通过对贝来尼凯和密奥斯·荷耳摩斯的建设,以及运河的疏通、沙漠商路的建设,由上埃及经红海、东部埃及沙漠商路或运河,继而连接尼罗河至下埃及的交通网络形成,为托勒密王国进一步发展与阿拉伯地区、印度的贸易奠定了基础。托勒密二世当政时,正是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Asoka,约公元前273—前232年在位)统治时期。他积极推动印度与西方的交往,曾派佛教使团访问埃及。托勒密二世也向孔雀王朝派出使者狄奥尼修斯(Dionysius)。[92]
托勒密八世(欧尔杰提斯·费斯孔,Ptolemy VIII Euergetes Physcon,公元前146—前116年在位)时期,为了同埃塞俄比亚和阿拉伯地区进行贸易,大力发展红海航运。这一时期,托勒密王国的船队常年从密奥斯·荷耳摩斯和贝来尼凯出发,首先到达阿拉伯半岛西南地区,通过此地区的贸易港口奥凯里斯(Ocelis),进而和印度西海岸的港口建立间接的商贸联系。
几乎整个托勒密王国时期,红海、印度洋的交通多控制在帕提亚人和阿拉伯半岛的纳巴泰人、希木叶尔人(Homerites,Himyarites)手中。[93]对于托勒密王国而言,对外贸易的环境并不乐观。首先,它与塞琉古王国存在领土争端,双方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先后进行过六次叙利亚战争。它通过塞琉古王国控制之地区与东方进行陆路交往有相当大的困难;第二,阿拉伯半岛北部地区的当地族群是独立的,而且相对野蛮,沙漠道路又充满艰辛,所以,托勒密王国试图通过阿拉伯北部地区与东方建立交往也很难实现;最后,红海和曼德海峡(Bab El-Mandeb)虽然长期处于阿拉伯人的控制之下,但由于托勒密王国占据了临靠红海的有利位置,又逐步发展港口、建造船只,所以,通过海路保持与东方的联系,是托勒密王国发展与东方贸易的无奈选择。
(二)托勒密王国的海洋贸易和海路探索
托勒密王国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海路的探索。托勒密王国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其海上势力,不论是在地中海地区还是红海。托勒密王国时期,亚历山大里亚成为托勒密王国的都城,也是其贸易中心,在此聚集了大量的外国商人、仓库管理人和商船船主。[94]亚历山大里亚位于尼罗河河口,有利于王国在地中海区域的发展。
地中海地区贸易对托勒密王国至关重要。托勒密一世时,控制了腓尼基(Phoenicia)海岸的港口,与塞浦路斯(Cyprus)签订协约,扩大了在地中海东部的势力。[95]它与罗德岛(Rhodes)关系密切。罗德岛和托勒密王国存在紧密的商业往来。它位于埃及到腓尼基、叙利亚(Syria)、小亚及希腊的海路上,是这一地区的贸易中心之一,对托勒密王国意义重大。托勒密王国和罗德岛间(地中海东部贸易圈)的贸易组织形式有所创新,一种新的商业组织—商业合作社取代了以前小规模的商人组织。[96]约公元前150年的一份纸草文献记载,亚历山大里亚的五位希腊人合伙,计划从红海到“香料之国”进行贸易。按照惯例,他们通过银行向一位希腊人借贷资金,另有五人担保。[97]正是商业信用进步,贸易合作加强,才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商人们开始运输大批量的货物,分享市场和商品信息,这一点对于交通落后的古代社会尤为重要。爱琴海地区在近东、地中海贸易圈中占据主导地位,可为托勒密王国提供造船用的木材、金属、沥青等急需物资,还能提供船只和水手,[98]也为从阿拉伯、印度等地进口的商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这一时期,托勒密王国在红海地区的贸易和探索活动有了显著进步。托勒密王国对红海的探索,首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和供应。埃及的马匹、大象、金属、木材资源匮乏,[99]决定了托勒密王国不得不通过进口得到这些重要的战略资源。托勒密王国海上势力的扩张,促进了人们地理知识的进步、刺激了人们对世界的好奇心,这反过来推动了托勒密王国在红海地区的探索活动。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托勒密二世开发红海西岸,重建红海港口,建造船只。[100]托勒密王国在琉克斯·里门(Leucos Limen)设有造船厂。[101]为了与埃塞俄比亚进行贸易,埃及的希腊商人首次尝试去阿拉伯半岛西南地区的商业航行。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非洲角的索科特拉(Socotra)的作用凸显,成为托勒密王国到印度、阿拉伯贸易的主要中转地。
托勒密王国早期,埃及和印度的直航尚未开通。根据《厄立特里亚航海记》的记载,早期,印度和埃及的船只都仅航行至阿拉伯半岛的一个叫作尤岱蒙(Eudaimon)的港口,双方在此进行交换和贸易,不会再往前走。[102]这表明:大部分埃及船只最远到达亚丁湾的西南阿拉伯海岸,在此获得东方商人带来的货物。此外,来自印度的货物也可从阿拉伯半岛南部沿着西海岸的陆上商路,运至纳巴泰人(Nabataeans)的城市佩特拉(Petra),然后到达加沙(Gaza),之后经西奈半岛,到达埃及。尤其是托勒密二世控制了巴勒斯坦(Palestine)和腓尼基地区之后,这条经阿拉伯半岛西北部的商路更加畅通。巴勒斯坦和腓尼基的商业及港口城市对托勒密王国与阿拉伯的贸易发挥了重要的中转作用。对腓尼基港口的控制,对托勒密王国意义尤其重大,腓尼基人在历史上就以“海上商业民族”著名,他们所在的地区良港众多、造船业发达,托勒密埃及控制了腓尼基就等同于控制了公元前3世纪的大部分的欧亚贸易。[103]此外,托勒密王国对到达巴勒斯坦和腓尼基地区的阿拉伯或印度的商品征收进口税,而且这些商品运至埃及本土时,托勒密王国还会对其征税,[104]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托勒密王国的财富。
由于托勒密王国占据着红海西岸,红海贸易的规模扩大至阿拉伯半岛南部沿海和印度洋,托勒密王国和阿拉伯地区的部落产生利益冲突在所难免。当托勒密王国派出战船进攻阿拉伯的独桅船或者毁坏纳巴泰人的居住地时,阿拉伯人就会开始报复,袭击托勒密王国的船只。公元前2世纪末,希木叶尔人控制了赛伯邑王国,占据了也门和亚丁湾的港口,包括奥凯里斯港,使用武力阻止印度船只进入红海,亦阻止埃及船出红海,托勒密王国的商人很难逾越希木叶尔人的阻碍。
尽管如此,埃及的商人仍然通过海外贸易获得了一部分商品,它们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王室。[105]托勒密王国将一部分进口商品供给神庙,其余部分提供给私人经销商。托勒密王国实行垄断贸易经营的政策,所以,个体经销商需要得到官方的特许,才能从事某些商品的贸易和经销。比如,进口香料的销售,需要得到官方的特许经营许可。[106]托勒密王室重视纺织品、香水制造、金属制品等行业,把这些行业的许可权授予专业的制造工人,没有许可,其他人不得进入相关行业的生产领域。[107]托勒密王国的希腊官员阶层掌握了大量财富,通过行政特权,获得税收权和垄断的合同契约,[108]还贷款给私商以盈利。
总的来说,托勒密王国实行的是严格控制贸易的垄断政策,有很多限制远航贸易的措施,所以,对于远航印度的托勒密王国的商人来说,自由贸易是奢望,利润也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可以看到,由埃及到印度的航线也在逐渐发展,但总体规模仍然很小,在托勒密王国的最后几十年,远航印度的船只很少,斯特拉波记载道:“在早期,只有20艘船只航行至亚丁湾外”。[109]再加上罗马在地中海世界的扩张,这一地区的局势不稳定,使得托勒密王国到印度的贸易,在公元前1世纪中期衰落。[110]
托勒密王国之所以没有与印度建立起稳固的贸易往来,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托勒密王国统治者继承了法老时期的国家经济垄断制度,实行相对封闭的对外贸易政策。托勒密王国通过设置关税关卡,保护王室对国内经济的统制和垄断。比如,托勒密官方对从叙利亚进口的橄榄油,征收高额的进口税和商品税,证明托勒密王国对油资源实行垄断经营。同时,托勒密王国对国内生产的商品的税收似乎和进口的商品区别较大,税收要低很多,[111]这实际上就是为国内居民购买外国商品设置价格障碍。托勒密王国对国内商人的监管较为严苛,垄断商品进出口,不利于商人群体的壮大和贸易相对自由地开展。第二,托勒密王国和塞琉古王国长期争夺黎凡特(Levant)地区,时常发生战争。托勒密王国中后期受到罗马的威胁,忙于战事,使其无暇也无力发展对外海洋贸易;第三,埃及商人面临阿拉伯人、印度人甚至塞琉古人、帕提亚人在海洋贸易上的激烈竞争,托勒密王国在经验、实力、物产、地理位置等方面均不占绝对优势,所以,它也始终没有成为红海、印度洋贸易的主导者,但是,它并没有放弃对印度洋海路的探索。
(三)托勒密王国与印度间航运的连通对海上丝绸之路西段开通的意义
由于帕提亚人、阿拉伯人对红海、印度洋商路的严密控制,公元前2世纪末的希腊人欧多克斯(Eudoxus)直航印度虽然是个偶然事件,但意义重大。据斯特拉波记载,“托勒密八世时期,欧多克斯为了宣传其家乡基齐库斯(Cyzicus)举办的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庆典,作为使者来到埃及。此时,一个印度人被带到王室,他学习了希腊语,告知托勒密八世,他由于迷路而到了埃及,他的同伴由于饥饿而死。托勒密八世命令他作为向导,带领埃及人前往印度,其中包括欧多克斯。欧多克斯从印度返回时,带来了香水和宝石。”[112]欧多克斯远航印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托勒密王国的海洋政策。托勒密王室意识到,由埃及航行至印度进行贸易,可以规避沿途各国陆上贸易的高税收和绕开时有海盗侵扰的阿拉伯海海岸。而且,托勒密王国船只并非全部航行至印度,希腊商人在中途的港口,也可与印度商人直接交换。这是托勒密王国时期有明确记载的首次远航至印度,时间不晚于公元前116年。[113]但是,由于没有留下对欧多克斯航行印度具体路线的记载,所以,不能确定他是否利用了季风。《厄立特里亚航海记》记载的季风发现者是希帕鲁斯(Hippalos),他有可能是欧多克斯航行印度时的船员。[114]如果以上假设成立的话,那么,希帕鲁斯生活的时期是公元前2世纪末,学界的一种主要观点即认为希帕鲁斯的时期是公元前120年至前90年之间。[115]欧多克斯航行印度后,托勒密王国掌握了直航印度的第一手资料,促进了托勒密王国与印度间的海上贸易,为罗马帝国时期埃及与印度的大规模直航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2世纪末至前1世纪初,托勒密王国开始设置高级官员专门管理红海、印度洋的相关事务。证据之一是在科普托斯发现的铭文记载了相关的官员,其名字缺失,年份为“8年”。关于此年份所指学界有争议,有公元前110/前109年、公元前74/前73年和公元前45/前44年之说。[116]证据之二,在埃及不同地区发现的五份铭文,均记载了一位名为卡里马库斯(Callimachus)的官员负责管理红海事务,五份铭文记载的时间分别为公元前79年、前75年、前62年(有两处铭文出自同一年)、前51年,[117]虽然,部分铭文的年代尚有争议,但是可以确定,至少从公元前79年开始,托勒密王国就已经设立专人管理在红海、印度洋航行的埃及船只,征收关税等。
总之,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对资源的需求等原因,托勒密王国在红海沿岸建设港口,探索商路,并实现了与印度第一次直航,为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西段的正式开通提供了基本且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公元前30年,罗马占领了埃及,托勒密王国灭亡。罗马帝国继承了托勒密王国的海洋遗产,继续对红海、印度洋商路进行积极探索,发展与阿拉伯地区、印度的海上贸易。
二 塞琉古王国与丝绸之路
塞琉古王国囊括了从叙利亚至中亚的广大地区,是版图最大的希腊化国家,也是后来丝绸之路主要经过的地区。
塞琉古王国时期,对外贸易获得长足发展,这首先得益于它实行的一些国家政策。塞琉古王国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波斯人的行省制度,委任总督管理。[118]国王不仅决定国家进出口何种货物,而且对各总督进口货物的数量也严加管理。[119]塞琉古王国的税收体系中包括专门的贸易税,由各行省的总督针对国内外贸易征收,包括了港口税、关税等税项。[120]塞琉古王国早期,特别重视国内的交通建设,各个城市间都有道路系统相连。而且,塞琉古王国国内使用同一种货币,采用阿提卡标准,也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贸易的发展。
塞琉古王国的建立保持了陆路贸易的贯通,后来帕提亚帝国独立后,塞琉古王国和帕提亚对峙于幼发拉底河一线,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地区仍然在塞琉古王国的控制之下,成为丝路西段的终点之一。
(一)塞琉古王国境内的城市与商贸网络
城市是贸易进行的载体,为商品交换提供了场所,商业城市间的道路则成了贸易通道。希腊化时期,塞琉古王国建城的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为各王国之最。这些城市既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也是商业中心,加上波斯帝国遗留的城市,构成了四通八达、星罗棋布的商业网络。[121]
塞琉古王国在两河流域的城市中,以巴比伦尼亚地区(Babylonia)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最为重要。斯特拉波特别提到塞琉西亚取代了巴比伦(Babylon)的地位,他记载道:“巴比伦现在成为一片废墟。后人没有完成修复它的任务,尤其是塞琉古一世在靠近巴比伦的位置建立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城之后。因为塞琉古一世和他的后继者把统治重心转移到这座城市,从此塞琉西亚比巴比伦的规模还要大,巴比伦被废弃。”[122]塞琉西亚是两河流域地区主要的商货集散地,由此过幼发拉底河可以西运至大马士革(Damascus)、安条克(Antioch),也可以向西南经沙漠商道过阿拉伯北部、巴勒斯坦到达埃及,由此可以东运至中亚、印度甚至中国,北通里海、黑海和高加索地区,连接草原丝绸之路,向南可通过波斯湾由海路抵达阿拉伯、埃及、红海地区,与海上贸易通道连接。所以,塞琉西亚是亚洲陆路贸易的枢纽,汇集了四面八方而来的商货,支配了整个希腊化时期的亚洲贸易。[123]帕提亚兴起后和塞琉古王国争夺两河流域,塞琉西亚无疑是必争之地。
在塞琉古王国兴建的诸多城市中,倾举国之力兴建的都城安条克城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斯特拉波记载道:“安条克是叙利亚的都城,也是历代国家统治者建立都城之地。安条克城稍逊于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城和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城。”[124]安条克是丝绸之路全线贯通后地中海东岸的陆路终点之一,东来的商品由此装船运至欧洲大陆,或再经陆路北运小亚、南运巴勒斯坦、阿拉伯与埃及地区。由地中海西运而来的商品也可在此登陆,通过东西贸易主干道运往东方。
(二)塞琉古王国时期丝绸之路西段贸易路线的走向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塞琉古王国陆路贸易路线覆盖的范围不同。在帕提亚独立(公元前3世纪中期)之前,从塞琉古王国控制下的中亚地区到叙利亚的陆路主干线都属于塞琉古王国管辖。帕米尔高原以西的陆路主干线大致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从葱岭至木鹿,可以经大宛、撒马尔罕、布哈拉(Bukhara)至木鹿,也可经巴克特拉(Bactra)至木鹿;第二段从木鹿至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可走伊朗北道,即沿着伊朗高原北缘向西前行,经百门城(Hecatompylos),穿过里海门,抵达埃克巴塔纳(Ecbatana),然后进入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最终抵达塞琉西亚,这是陆路贸易的主干道。另外,这一段还有其他路线可以通行。如,伊朗南道是沿着伊朗高原南缘西行的商路,和中亚南部、印度西北部相连。更靠北的路线由埃克巴塔纳向西北行,可抵达小亚、黑海沿岸地区;[125]第三段从塞琉西亚到安条克,一般情况下,从塞琉西亚沿着古波斯“御道”前行,在宙格玛(Zeugma)渡过幼发拉底河,西行抵达安条克,[126]此路线是最常用路线。从塞琉西亚也可以向西南行,到波斯湾后,走海路绕过阿拉伯半岛抵达红海东岸的阿拉伯地区,然后向北至地中海东岸、叙利亚地区。塞琉古王国时期,由塞琉西亚向西,穿过叙利亚沙漠至大马士革的路线还很少采用,直到公元前1世纪末罗马帝国兴起后,这条路线才开始兴盛起来,巴尔米拉(Palmyra)城的繁荣就是标志之一。公元前2世纪中期以后,帕提亚与塞琉古王国争夺两河流域地区,塞琉古王国实际控制的陆路贸易路线只是幼发拉底河至安条克段,而且由于和帕提亚的战争不断发生,这一段路线事实上难以保持畅通无阻。
(三)塞琉古—帕提亚关系与丝绸之路西段的形成
塞琉古王国和帕提亚的关系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陆路贸易的兴衰。公元前248/前247年,阿尔萨息一世(Arsaces I,公元前247—前211年在位)独立建国。此后到米特里达特二世时期,帕提亚同塞琉古王国战争不断,争夺的焦点是伊朗和两河流域地区。塞琉古三世(Seleucus III,公元前225—前223年在位)时期,曾东征帕提亚,占领了帕提亚的西都百门城,帕提亚顽强抵抗,最终,塞琉古三世和阿尔萨息一世达成和解。[127]
自米特里达特一世起,帕提亚开始了大规模地扩张。他占领了米底(Media),攻入美索不达米亚。至此,塞琉古王国的边境缩小至幼发拉底河以西。米特里达特二世即位后,迁都至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128]不久,他又向两河流域北部地区进发,征服了亚美尼亚地区(Armenia)。至此,塞琉古王国仅占有幼发拉底河—亚美尼亚一线以西以叙利亚为中心的地区。
帕提亚控制了自里海门西去米底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黄金通道,也就控制了从中亚、印度到地中海东岸的商道主干线。这一时期恰逢张骞出使西域、到达中亚地区。《史记·大宛列传》记载:“骞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及诸旁国。”[129]此外,《史记·大宛列传》还记载:“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至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众多。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130]可见,张骞向帕提亚派遣了副使,受到了帕提亚王的热烈欢迎,并且,帕提亚同样派遣了使节去往中国。由此,帕提亚同中国建立了直接交往,起自中国的丝绸之路得以经西亚向西延伸。两国的外交活动可以看作中国丝绸向外正式出口的标志。因为这些来自中国的使者“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131]带来的丝绸或作为礼物,或作为交换,一定为数不少。这些丝绸或经帕提亚人的中介从陆路进入塞琉古王国或后来的罗马帝国是完全有可能的。
张骞出使西域标志着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此时,正值帕提亚王米特里达特二世统治时期。帕提亚控制两河流域地区,对于丝路西段保持连续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帕提亚的地理位置和它所奉行的东西并进战略,帕提亚逐渐成为丝绸之路上的最大受益方。但帕提亚只是在丝绸之路中亚至两河流域一段拥有实际控制权。塞琉古王国对丝绸之路实现东西全线贯通同样至关重要,它不仅控制着通往地中海的丝路西段,而且也是丝路贸易的积极参与者。塞琉古王国长期占据着两河流域以西地区,推动了东西陆路贸易延伸至叙利亚、地中海东岸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