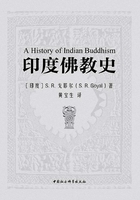
佛陀与吠陀和奥义书
公元前六世纪的吠陀宗教有两个主要的分支:仪式主义和非仪式主义。在早期佛经中,多次提到佛陀与代表前一分支的婆罗门学者辩论。话题主要是种姓、祭祀[1]和吠陀的权威性。佛教在这三方面的反对立场始终是明确的。佛陀也着重批驳一切外在的崇拜。在一些佛经中,他嘲讽吠陀神崇拜。《长尼迦耶》的《三明经》(Tevijja sutta)中,他嘲讽婆罗门召请因陀罗、自在天、生主、梵天和阎摩等。他嘲讽通过抚慰诸神获得果报的观念。
关于奥义书,佛经中保持沉默。然而,从很古的时候起,就流行奥义书学说和佛陀学说存在深刻关联的观点。乔荼波陀 [2]就认为奥义书的主要观念与佛陀一致。其他许多古代思想家持有同样的观点[3]。马克斯·缪勒、布鲁姆菲尔德、T.W.里斯·戴维斯、C.A.F.里斯·戴维斯和奥登伯格坚持认为佛陀深受奥义书教导的影响。基思认为佛陀是不可知论者,但甚至也将佛陀的涅槃概念与奥义书的绝对作比较[4]。伯鲁阿(B.M.Barua)已经作出充分的努力,试图追踪佛陀观念的奥义书来源[5]。但是,佛陀是否对吠陀和奥义书有深入的知识无法确定。没有佛陀与具有奥义书智慧的任何代表人物进行过任何讨论的记载。然而,佛陀肯定多少有些熟悉奥义书思想的基本论题。佛陀和奥义书嘲讽吠陀的态度以及他们认为道德热忱、沉思和禅定比仪式主义更崇高,两者有相似性。然而,佛教不赞同祭祀的态度更加明确和更具批判性。确实,我们发现一些奥义书温和地贬斥祭祀崇拜,一些奥义书企图将祭祀仪式寓意化和精神化。但是,它们接受吠陀仪式主义作为一条通向较低的祖先领域之路
[2]就认为奥义书的主要观念与佛陀一致。其他许多古代思想家持有同样的观点[3]。马克斯·缪勒、布鲁姆菲尔德、T.W.里斯·戴维斯、C.A.F.里斯·戴维斯和奥登伯格坚持认为佛陀深受奥义书教导的影响。基思认为佛陀是不可知论者,但甚至也将佛陀的涅槃概念与奥义书的绝对作比较[4]。伯鲁阿(B.M.Barua)已经作出充分的努力,试图追踪佛陀观念的奥义书来源[5]。但是,佛陀是否对吠陀和奥义书有深入的知识无法确定。没有佛陀与具有奥义书智慧的任何代表人物进行过任何讨论的记载。然而,佛陀肯定多少有些熟悉奥义书思想的基本论题。佛陀和奥义书嘲讽吠陀的态度以及他们认为道德热忱、沉思和禅定比仪式主义更崇高,两者有相似性。然而,佛教不赞同祭祀的态度更加明确和更具批判性。确实,我们发现一些奥义书温和地贬斥祭祀崇拜,一些奥义书企图将祭祀仪式寓意化和精神化。但是,它们接受吠陀仪式主义作为一条通向较低的祖先领域之路  的效力。这样,吠陀的“仪式篇”
的效力。这样,吠陀的“仪式篇” [6]至少在奥义书的设计中具有附属地位。但在佛陀的教义中不是这样。
[6]至少在奥义书的设计中具有附属地位。但在佛陀的教义中不是这样。
佛陀是否受奥义书的梵的学说的影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7]。按照拉达克利希南(Radhakrishnan),奥义书的梵被佛陀称为“法”(dharma),“向我们表示经验层面上的基本伦理价值”[8]。但是,按照佛陀,法是道德规范,从来不是一种至高的原始真实。按照厄克特(W.S.Urguhart),佛陀没有明确表明态度,而“暗含承认一种终极真实”[9]。按照G.C.般代,确实没有看到佛陀在任何地方批评奥义书的“自我说” 或“梵说”
或“梵说” ,甚至在后期,佛教也很少批评吠檀多。“商羯罗的绝对论追溯到奥义书,同时,佛教的绝对论追溯到尼迦耶。”G.C.般代暗示,如果我们设想“尼迦耶本身受奥义书影响,这就能看清后期吠檀多和佛教的接近。……它表明早期佛教基本上受奥义书影响,由此佛教早期倾向唯心论和绝对论。可以注意到,这些倾向不可能源自沙门思想界”[10]。
,甚至在后期,佛教也很少批评吠檀多。“商羯罗的绝对论追溯到奥义书,同时,佛教的绝对论追溯到尼迦耶。”G.C.般代暗示,如果我们设想“尼迦耶本身受奥义书影响,这就能看清后期吠檀多和佛教的接近。……它表明早期佛教基本上受奥义书影响,由此佛教早期倾向唯心论和绝对论。可以注意到,这些倾向不可能源自沙门思想界”[10]。
早期吠陀对待生活及其问题持有乐观主义态度。但奥义书表现出悲观主义。世界现象被认为充满烦恼。在《伽陀奥义书》中,我们发现提到普遍的“世界的痛苦” 。然而,奥义书赞同一种沉思伟大真理的生活,但并不强调摒弃世俗的家主生活。而在佛教中,全然强调摒弃一切家庭生活的束缚。按照雅各比,寺院运动起始于奥义书时代,在佛陀和大雄领导下获得长足发展。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耆那教和佛教的寺院组织的原型是婆罗门苦行者。“他们从婆罗门苦行者那里借用苦行生活的许多重要的实践和体制。”[11]这种看法并不新鲜。马克斯·缪勒[12]、比勒和科恩持有同样的观点[13]。我们已经详细批评这种理论。
。然而,奥义书赞同一种沉思伟大真理的生活,但并不强调摒弃世俗的家主生活。而在佛教中,全然强调摒弃一切家庭生活的束缚。按照雅各比,寺院运动起始于奥义书时代,在佛陀和大雄领导下获得长足发展。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耆那教和佛教的寺院组织的原型是婆罗门苦行者。“他们从婆罗门苦行者那里借用苦行生活的许多重要的实践和体制。”[11]这种看法并不新鲜。马克斯·缪勒[12]、比勒和科恩持有同样的观点[13]。我们已经详细批评这种理论。
按照奥义书,人的终极精神命运是“存在、意识和欢喜” 。甚至像梅怛丽依[14]这样的太太也渴望永生,不满足于世俗的富裕生活。对此,佛教提出涅槃概念作为人生的至善。这种概念是否受奥义书的梵的概念影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佛陀本人并不热衷对奥义书教导的基础进行深奥的心理学和形而上学的考察。他采取实际的态度,将这类问题称为“不可说明”
。甚至像梅怛丽依[14]这样的太太也渴望永生,不满足于世俗的富裕生活。对此,佛教提出涅槃概念作为人生的至善。这种概念是否受奥义书的梵的概念影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佛陀本人并不热衷对奥义书教导的基础进行深奥的心理学和形而上学的考察。他采取实际的态度,将这类问题称为“不可说明” “无记”),是毫无用处的戏论。
“无记”),是毫无用处的戏论。